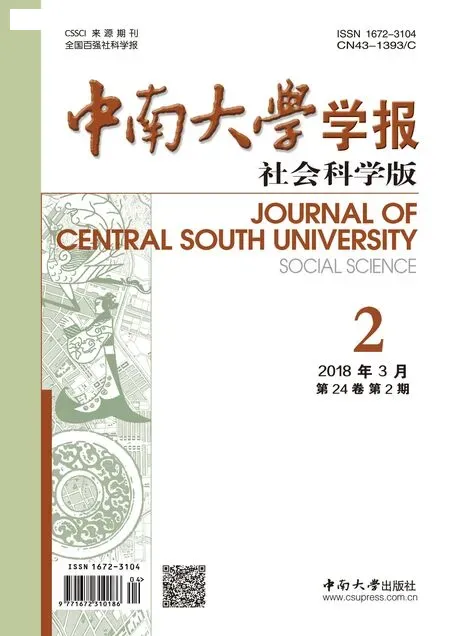“后真相”时代:作为制造者的媒介
(山东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从形式上催生了以数据资料的撷取、处理和整理为核心的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更从内容上引发了“后真相”时代的到来。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这两大政治事件将“后真相”带入大众和研究者的视野。牛津词典将“后真相”(Post-truth)列入2016年年度热词,这既是对时下政治现象的概念化总结,也是对当代媒介发展状况的描摹;亦可作为警钟,对大众媒介的真实性提出警示,并且表明媒介作用不仅限于传播,其作为制造者亦可操纵人的行为。于是媒介作为双刃剑,不仅对认识领域也对媒介和社会文化领域提出了新的挑战。
2016年,一个名叫巴娜·阿拉贝德(Bana Alabed)的 7岁叙利亚女孩在个人社交媒介“推特”(Twitter)上发布了大量的照片和视频来讲述战争中普通人的生活和心理。轰炸后的残垣废墟和幼小孩子的鲜明对比让人们无比关注这个女孩和她的生活境遇,而“我需要和平”“世界你好,我们还活着。今早我们活着醒来了”这样的文字也打动着人心,但随之质疑也开始出现。这个在采访中无法用基本的英语交流的7岁女孩何以能够在推文中使用复杂的词汇和语法?在战争轰炸中,她何以能有稳定的网络信号支撑来发送数据量较大的图文?随后记者探访发现这些推文所发出的地方并不在叙利亚,小姑娘和这个故事只不过是被用来刺激大众情感的工具。且不论这整个事件背后有着怎样的政治纠葛和目的,巴娜的故事鲜明地宣告着:基于社交媒介的发展和活跃,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后真相”的时代。
巴娜的故事绝不是个例。事实上,存在于社交媒介上的很多新闻并不完全真实,甚至有些是被精心地炮制出来的。在美国一个名为“韦莱斯”的小镇,那里炮制假新闻的流程如同工厂的流水线,工作人员足不出户就制造并传播出成千上万的新闻。如果说大数据时代是信息技术发展的必然,那么“后真相”时代如何认识和面对媒介信息,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一、“后真相”时代的到来
“后真相”即 Post –truth,在《牛津英语词典》2016年的年度词汇中被定义为“circumstances in which objective facts are less influential in shaping public opinion than appeals to emotion and personal belief ”,即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较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舆论的情况。对于传统媒介来说,真实、事实是最为基本的要求,而在“后真相”的时代,真相已经不是传播的重点,情感、情绪、信仰或者观点才是重要的。
(一) “后真相”的概念与特征
“后真相”的概念并非于2016年横空出世,其最早是作为政治概念来描述政治文化的。“后真相”最早出现在1992年斯蒂夫·特西奇(Steve Tesich)撰写的剧本《民族》中。他在剧本中写道:随着水门事件的真相浮出,更多关于曾经被掩盖的伊朗叛军的丑闻和波斯湾战争的报道渐渐流出。这些都表明:“我们作为自由的人民,应该自由决定我们希望生活在后真相时代中。”[1]2004年,拉尔夫·凯伊斯出版了名为《后真相时代》一书,认为这个时代存在着谎言和事实以及一种介于二者之间的话语。2010年,大卫·罗伯茨提出了“后真相政治”的概念,意指一种几乎完全脱离政策或法律的政治文化(大众观念和媒介叙事)。但这些理论并未产生大范围的影响,直至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牛津词典将其收录并作为年度热词,“后真相”才开始进入大众生活和理论研究视野。
“后真相”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是一个时间概念,似乎可被解读为“真相”时代之后的阶段,如同“后奥运时代”“后世博时代”指的是奥运会、世博会结束之后所面临的场馆配套设施如何加以利用和价值再创造的时代。但是这便引出了一个问题,即是否有一个时代可以称得上是“真相时代”或者“前真相时代”?显然这是不存在的,因为真相从来都是与谎言并存,即便是印刷文本时代也很难保证文本信息即是真相。与时间相关的还有另一种解释,即所谓“后真相”是指真相来临的时间滞后,即新闻传播过程中需要经历从谎言到真相的过程。比如英国脱欧前大量关于英国向欧盟缴纳税款数字的报导,在脱欧后被证明是由脱欧组织故意引导民众所编造的。民众先看到了数字的谎言,后来才渐渐知道了真相。纵观近期类似的社会事件都是以谎言开始,但是真相终究会到来,只是需要过程。“真相滞后”确实能够描述“后真相”的一个特征,但却并非其真实含义。
从其英文词源来看,“post”作为前缀的命名方式表明其不仅是局限于时间域上的概念,如“后现代主义”“后资本主义社会”“后人类时代”等,还指向某一阶段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出现新的特点和特征来消解原有的体系和规则,但却并未形成一个新的足以获得命名的阶段,即是一个过渡阶段。“它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在于揭示出诸事件的本质,而在于构筑抑或激发出一个主体群,他们面对类似事件,有了共同的分析视域,那些目前诸多无法理解的‘事件’,即一个脱离了既有的因果序列,因此不可捉摸的现象激发我们产生新的解释系统。”[2]因此,“post”指向的是消解,是对业已存在的规则、现象、精神的消解和重构,正如“后现代主义”文化对“现代主义”文化特征的消解一样,用大众文化的愉悦来消弭精英文化的高雅和崇高,用非理性、碎片化、无中心来消解理性主义。“后真相”用“情感”来消解“客观事实”,其目的已经不是简单的传播真实,而是如何运用传播的内容来激发人们的某种情感进而控制大众行为以实现自身的目的。因此,“后真相”时代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第一,“情感”取代“事实”成为核心。在传统媒介中,事实是信息的绝对核心,经由媒介所传播的内容应是客观而理性的,应据实陈述、立场中立,因此信息发布者在撰写文本时都应尽可能地挖掘事实、揭露真相。然而在“后真相”时代,真实已不是目的,“真相”的重要性被解构,如何操纵舆论走向、进而控制大众行为成为信息发布者的首要目的。因此,所撰写的文本的落脚点在于“情感”。大众已经不满足于被动的被传达,而期待“在场”和参与,长期远离媒介中心的大众经由自媒体拥有了在场的权利。另外,现代社会对于经济利益的重视和追逐使个人臣服于经济目的,绝大部分的自媒体热点事件都因与焦虑、无能为力感、敌视和愤怒相关而得到了巨大的关注。快节奏的生活、欲望和情感的压抑使得人们有大量的感情需要宣泄,当时机到来时,借助无需承担责任的自媒体平台,人们的情绪才能得以充分释放。
第二,内容真伪难辨。传统媒介以“求真”作为主要原则,然而“后真相”更重视舆论导向。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体的火热拓宽了信息来源渠道,也加大了辨别信息真假的难度。诉诸于“情感”的“后真相”将焦点集中于感情而不是事实真相。比如《罗一笑,你站住》一文,书写者用感人的父女情弱化了医疗费的实际数额和家庭支付能力这样的事实信息。政治层面的“后真相”更是如此。如果由政府或者别有用心者借助权威媒体发声,那么其内容即便是伪造的也很难被识破。英国脱欧公投前所发布的庞大的纳税数额刺痛了英国民众的神经,进而推动了脱欧进程,尽管这些数字后来被证明是伪造的。但是作为普通民众,在“后真相”时代时刻面临着真伪难辨的窘境。
第三,“后真相”是作为否定意义的存在。如同所有的以“post-”命名的概念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否定性一样,“后真相”不论在媒介文本中还是在学术研究视域中都是否定性的存在。究其原因在于“后真相”颠覆了以往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媒介规则,扰乱了传媒秩序,并以猝不及防的姿态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不仅危及媒体的信任度,也会引发群体性问题。如果有不法分子深谙大众心理和“后真相”的情感核心,以情感为纽带操纵大众的言行,那么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后真相”时代将认知偏误、媒介监管、大众的媒介素养以及大众的情感宣泄需求等问题都暴露了出来。我们不仅需要从理论上对其进行认识分析和纠正,更应以在实践层面上指引大众在社会生活中以正确理性的方式应对“后真相”时代。
(二) “后真相”时代存在的危机和挑战
1.网络信任异化
“后真相”时代大量反转新闻的出现,使得大众对于网络的信任出现异化。首先,这种异化表现在大众对于信任对象的错位。基于自媒体的“后真相”时代的信任主体本应是媒体,然而自媒体已经消解了传统媒体的权威性,使其变得不可信任。而媒介所制造的“情感”却成为了信任的对象,但是这种信任又在新闻的反转中呈现出不可信任、不该信任的现象。如在“罗一笑事件”中,大众出于对《罗一笑,你站住》这篇文章的信任大量进行转载、捐款,然而却在随后的反转新闻中发现事实并非如文章所描述的那样。整个事件呈现了如下的过程:由相信媒体内容变为不相信,由不相信医疗保障、社会福利变为相信,这无疑是一种信任的异化。其次,信任焦虑。反转新闻几次出现之后大众意识到“后真相”的存在,随之而来的便是信任焦虑,无法确认是否该信任、该信任什么。这种信任焦虑不仅影响到个人的自我身份认同,更对社会群体价值判断造成负面影响,久而久之形成信任危机。
2.谣言传播迅速,影响范围极大
自媒体作为“后真相”的主要载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谣言的传播速度和范围。与传统媒介不同,自媒体是一种节点共享的即时信息网络,它不依赖新闻部门的新闻记者,不局限于专业的新闻工作者及权威机构,不受时间、空间局限,身处其中的每一个节点都可以成为信息源和传播者。另外,自媒体最为突出的特征便是圈子化现象,每个节点都存在于若干个圈子中,在圈子中信息可以即时共享,并通过圈子的交集实现扩大传播,而这样的圈子化所带来的便是“回声室”效应的加剧。谣言通过自媒体被迅速传递到使用便携式媒介的大众,然后大众通过转发和点赞等行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情感,从而被更多人看到和谈论,进而将舆论的力量进行量化,影响事件的走向。
3.非理性思考占据主流
自启蒙运动起,理性主义的思潮就对社会的各个方面影响深远,于是严谨的逻辑推理所得到的知识和事实成为真相的唯一依据。不论是媒介还是文学作品,都以传播知识、传递信息为己任。彼时的新闻媒介最大的功用即是传播事实。后现代社会的到来,社会文化形态由精英文化转向大众文化,由审美文化转向消费文化,文化模式则由文本文化向视觉文化转化,其核心都是非理性逐渐占据了社会的思想高地。于是知识和囊括着知识的信息不再重要,对于感官的重视使得大众远离了理性的思考,身体的地位得到显著抬升,与之伴随的便是情感的重要性。在后现代社会中媒介的发展使得大量的信息充斥大众的生活,于是信息的获取因为稀松平常而变得不再重要,转而注重情感上的“在场”需要。“这一个,这一刻”无论是快感、满足还是同情、愤怒都因为无法重复的在场,成为被渴求的独特事件[3](212)。在这些事件中,非理性取代理性成为大众的主要思考方式。
4.大众媒介素养亟待提升
“后真相”时代的到来集中凸显了媒体从业人员和大众的媒介素养问题。“后真相”的难辨真伪、事实滞后以及舆论导向大于事实真相都反映了媒介从业人员的基本素质问题,即不能坚守媒体从业者的严谨求真的职业态度。同样,媒介监管和审核不到位的弊端也随之暴露出来,于是谣言滋生、影响视听。就大众而言,过于相信媒介传播的内容,缺乏基本的判断力,是“后真相”得以存在的现实条件。另外,“后真相”刺激了大众的情感痛点,自媒体又为情感宣泄提供了途径,导致网络暴力事件频发。因此提升大众媒介的素养已迫在眉睫。“后真相”时代“重点不再是取得这个世界的有关信息,而作为信息的世界之时,就顺利地诞生了”[4](66)。“后真相”之所以发生,其根源还是媒介。
二、“后真相”产生根源:作为制造者的媒介
(一) 述行性媒介
进入“后真相”时代的研究,首先要关注的是其独特的媒介环境。与电视、广播、互联网等大众媒介不同,自媒体成为时下影响最为广泛的新型媒介。所谓的自媒体是在社交媒体的基础上产生的。作为“后真相”产生工具的媒介其实践和理论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后真相”时代,媒介作为工具传递讯息,不仅是信息的一部分,也是麦克卢汉所说的“人的延伸”,具有了一定的主观能动性和主体性,进而成为了希利斯·米勒所论的“制造者”。正是媒介的这种“制造者”的身份,推动了“后真相”时代的到来。
媒介是基于信息交流的需求而产生的,是交流的渠道,具有载体性质。“媒介这个词,它的重点是中介行为,这同它是一个操作设备分不开的。”[5](10)因此,在传统的媒介理论中,媒介是一个工具,具有物质性和工具性。然而,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理论改变了这一认知。媒介即讯息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6](18)。麦克卢汉的理论拉近了技术与情感的关系,媒介由形式走向了内容。以电视、电话、电子产品和互联网为代表的媒介改变了人们的感知模式,延伸了人们的感知范围。人们可以与千里之外的人见面、通话,甚至这种延伸还塑造了一种新的感知。这种感知依存于媒介而存在,并受到媒介的影响和控制。正如麦克卢汉所说:“因为对人的组合与行为的尺度和形态,媒介正是发挥着塑造和控制的作用。”[6](19)
希利斯·米勒则在麦克卢汉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更进一步的理论,即媒介就是制造者。他认为:“你想要通过一种或者两种媒介传递的信息的内容并不重要。媒介自身就有效用,它是述行性的,在每一个情况下用不同的方式来说出一些东西,使一些事情发生,它是制造者。”[7](2)所谓的制造,是述行性(perfomative)的。语言学家奥斯汀提出语言具有述行的功能,即用言语来做事。米勒将这一观点进行阐发,他认为不仅语言、文学和阅读具有述行的力量,图画甚至媒介自身都拥有这样的功能。作为媒介它的述行功能便是让事情发生,“无论它(指通过媒介传播的主体)说的是什么内容,或通过一个指定媒体在指定时间传达,其内容和效果都会受到所用媒介的影响。通过对信息的大力支持,一个指定的媒介不是被动的传递信息,而是通过它自己的方式,积极地改变了所说和所做的内容”[7](22)。
于是媒介不仅是一种工具或者客观的存在,而是被赋予了使事情发生的力量。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宗教、精神和心理都分别成为各个历史阶段掌控、引发和推动人的行为的力量,而在当下,拥有这种力量的则是媒介,即我们所运用的诸如互联网之类的新媒体和微博、微信之类的自媒体。德里达曾将新的电子通信媒介和技术作为决定意识形态的物质材料,然而不同的媒介传播是否能够从根本上产生新的文化这一点尚待探讨,但是显然在新的媒介时代,媒介通过参与和在场加速了“后真相”时代的到来。
以“罗一笑事件”为例,《罗一笑,你站住》这篇文章通过自媒体发布,经过阅读者的转发和评论,在短时间内扩散至全国并获得大量的捐款。自媒体可以直接行事,通过读者转发、评论和打赏,将阅读转化为实践行为。如果这个故事以书本的形式刊出,人们在阅读时会被打动,或许会有一段时间的感叹,但随后便会抛下它进入自己的世界。如果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通过电视、互联网等传播,那么首先受众的范围会受到影响,只会被一定地域、一定时间段看到该节目或者新闻的人所了解。而如果经由媒体报道,那么文章的相关内容包括医药费的数目、保险报销比例和家庭实际情况等相关问题都会被核实,那么事实上该事件根本就不会被播出。而通过自媒体这种依托便携式设备的媒介进行传播,便省略了很多环节,加速了整个事件的进程,扩大了其影响。不仅如此,后来的反转新闻、辟谣和道歉等一系列事件也都是媒体述行的结果。
如果说以往的媒介只是对于人的感官的延伸,改变了人的听觉、视觉和触觉的尺度,那么“后真相”时代的媒介则将言语行为理论中“以言行事”的结果公众化、群体化。无论是文字还是传统的电视媒介都具有述行性特点,读者的行为会受到阅读或者电视播放内容的影响,但是这样的述行是偶然性、个人性的。阅读或者观赏同一个内容,有的人会因此改变自己的行为,有的人却不会。另外,这样的述行影响也是间接的,因为无法绝对确证行为的改变与此有关。而自媒体的述行功能却不同,自媒体所拥有的转发、点赞、评论等功能都是确证的述行功能。自媒体的每一个使用者,不管是专业的媒体人还是普通大众都具有发布、转发、点赞、评论或者打赏的权利。不论是转发还是点赞,都表达了自身对于该内容的态度和关注,从而推动了其传播和扩散。于是,才有了微博求助、朋友圈事件的大热等现象,个人通过转发、评论等看似简单的行为成为了媒介的推动者,也成为“后真相”的“帮凶”。
(二) 述行性情感
情感不仅是“后真相”的核心,媒介的述行功能同样具有产生情感的力量。情感的产生是很难界定的,“激情的问题不仅仅是经常难以确定的被动与主动的区分,而且是内/外对立的问题。或者从述事与述行话语之区别来看,所存在的问题是,是否激情的外在表现——无论是通过词语或其他符号——只是述事性地描述了已然存于内心的情感,还是那些外在表现述行性地创造了内在激情”[8](194)。德里达在论述述行性的情感时以“我爱你”这句话为例,详细区分了“我爱你”这句话所包含的情感状态和情感发生过程。恋人在说“我爱你”这句话时,到底是说话者先感受到了爱情的感觉然后才说的“我爱你”,还是因为说出“我爱你”这句包含情感的话语之后,感受到了恋爱的状态,产生了爱情?德里达更倾向于后者,即语言产生了激情,他倾向于语言表述所带来的述行力量。除了德里达所说的激情以外,维特根斯坦的痛苦以及奥斯汀的愤怒都是带有述行性力量的情感。“后真相”便利用了话语的述行性,通过语言来表达信息发布者的愤怒、痛苦等情绪,进而述行性地激发读者产生同样的情感。
述行性的情感前提之一是意图,“唤起有意识的意图(conscious intention)的需要,使这种意图成为恰当的述行话语之前提”[8](210)。“后真相”时代的每一个事件都有着明显的意图。如果说以往的媒介意图只是传播讯息,那么作为制造者的媒介在“后真相”时代中的意图却远非传播讯息那么简单。发布假消息的意图是受经济利益或者政治利益驱动,反转新闻以及辟谣的意图则是正本清源、以正视听。无论是制造假新闻还是试图还原真相,其意图都在于引导舆论走向,以实现更深层次的目的。
自媒体了解大众并善于制造情感。它们深谙“群体不能被理性所影响,他们只能理解那些临时拼凑起来的想法”的道理。因为“想要群众拥有信念,首先必须完全理解那些令它们为之兴奋的情感,并且假装自己也具有这样的情感,然后尽自己的最大努力,通过低俗的组合模式,用一些出众的暗示理念来改变它们的观点,一点点地探索产生这种说法的情感”[9](78)。“罗一笑事件”之所以能够得到大众的关注和信任,其原因正在于作者能够很好地把握父母心系子女、为子女不惜付出一切的心态,以及群众对于医疗保险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长期不满和不信任,使读者在阅读文章时能够感同身受,进而将这种情感付之行动。
述行性情感的另一前提则是社会文化和现代社交媒体的碎片化及浅阅读特征。信息和数据被碎片化地接收,于是严谨的逻辑关系不再重要。这与大数据时代的特征相同,在大数据时代因果关系不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相关关系[10](51)。首先,这种碎片化体现在信息本身的碎片化。自媒体的字数限制以及发布源的模糊和无限制、发布的及时性都使得信息传播呈现碎片化。使用者可以快速上传一段视频、一张图片而无需对其进行调查和审核。其次,碎片化还体现在用户使用过程中。自媒体以移动设备为载体,使用者的使用时间和场所不固定,通常只是闲暇时匆匆一瞥之后就转入其他事务中。因此,在面对本身就碎片化的信息时,人们根本无暇进行逻辑上的推理和论证,而只是凭感觉来进行判断,进而选择忽视、转发或是点赞。因此,在整体碎片化的环境中,在无数的信息中,什么才能够抓住人们的眼球?是严谨的事实报道,还是贴近大众的情感?答案当然是情感。人们无暇去顾及逻辑和深度,在几十秒甚至更短的阅读过程中能够留下直观印象的唯有情感。同情、感动、愤怒、共鸣……都成为媒介制造的重点,围绕着这样的感情,人们才会不论地理位置和身份地位而牢固地站在一起,并依此作出行动,推动事件的发展,这就是“后真相”得以发生的根源。别有用心者或者无意者发布带有情感导向的信息,该情感打动了网民,网民通过亲身参与事件成为在场者,同时这样的在场也化为了行动,参与到事件进程中。
此外,“后真相”时代,媒介所制造的不仅仅是情感,还促成了新的群体的产生。这样的群体“冲动、易变和暴躁,易于接受暗示和轻信”[9](19),于是一旦操纵者诉诸情感和信念,则很容易成为大众群体中的意见领袖,进而影响和操控群体的认识和判断。同时,群众“不善于论证,却急于求成”[9](3),选择性地忽视因果关系,出于自己情感的本能而采取行动或者求得结果。首先,相较于现实生活中个人的无力和渺小,网络空间的匿名性给予了每个人发声的机会和能力,因此,个人的自信得以增加。在这样的环境下,大众易于接受暗示,也易于轻信。其次,由于群体的匿名性,网络环境中的个人不必承担责任,脱离了现实生活中的规则和责任感的束缚,更易于发泄自己的情感,而这样的情感通常是暴躁的。“群体感情的暴躁,尤其是在异质性群体里面,又会因为全部责任感的缺失而得到加强。”[9]在这种复杂的情感中,个人极易找到精神群体,并受到其中有倾向性的意见影响,进而增强了群体的力量。通过观念和情感所建立起的群体远比现实生活中的群体更为牢固,也更容易建立规则。
于是作为制造者的媒介通过情感建立了新的规则和尺度,这一尺度与现实生活中的行事方法截然不同。这种规则真正实现了约翰·巴洛在《网络空间独立宣言》一文中所说的,“我们正在建造的全球社会空间,将自然独立于你们试图强加给我们的专制的约束。你们没有道德上的权力来统治我们,你们也没有任何强制措施令我们有真正的理由感到恐惧。你们所宣称的许多问题并不存在。哪里确有冲突,哪里有不法行为,我们会发现它们,并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来解决。我们正在达成我们自己的社会契约”[11]。
这激情洋溢的宣言在为“后真相”时代鸣锣开道的同时,也同样是一种警示。显然,自媒体和群众易被别有用心者利用。同时,“这种对所有意见的引导的缺失,以及普遍信仰的破坏力,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对所有的秩序都保持着极端分歧的信念,并且让群众对于一切没有触及他们直接利益的事情,采取越来越漠不关心的态度”[9](107)。面对这样的危机,我们不禁要思考,“后真相”时代,作为制造者的媒介应该如何面对?
三、“后真相”时代的媒介策略
首先,增强大众的理性阅读能力。“后真相”时代面对真伪难辨的信息,当务之急便是增强大众对于媒介传播信息的理性阅读能力。第一,大众应消除固有的媒介即真相的认知。尽管大众媒介中的广告效应已经让部分人提高了警觉性,但是自媒体平台这种看似与传统权威媒介相同的信息渠道却使人更加难以分辨内容的真伪和目的,再加上“后真相”的情感策略和圈子化的熟人效应,人们更易于相信自己所看到的和感觉到的。第二,面对碎片化的信息,大众应该理性分析、慎重对待。虽然阅读时间短暂、信息碎片化严重,但是更应该从逻辑的角度理性对待所接收到的信息。围观的心态不可避免,但付诸行动还需慎重。第三,掌握一定的阅读技巧。米勒提倡将修辞性阅读作为时下的阅读策略,通过对隐喻等修辞手法的解读明确文字背后的深意。
其次,提升大众媒介素养。就自媒体从业人员来说,应进行基本的业务素养的培训,增强自媒体从业人员的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坚守媒介从业人员的道德操守,从客观的立场出发还原事实真相。就大众而言,应理性看待媒介信息,在参与自媒体事件时反复思考,增强社会道德责任意识,控制自己在社交媒体和群体中的言行。
再次,完善监督管理机制,杜绝“假新闻”。需要进一步完善作为载体的自媒体的准入和监督制度。“后真相”时代的情感比传统媒体所传播的新闻更容易制造,既不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专业工作人员,也无需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调查求证。另外,自媒体的发布者的身份没有限制,内容也不需要经过层层审核。除非被举报,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场所进行发布,因此,真相自然被这个快速、简易和鱼龙混杂的流程抛却在外。随便一个看似有观点的内容便可成为意见领袖,引导大众的观念走向。因此,“后真相”时代更应该建立严格的监督管理制度和审查制度,定期清理不合格的媒介发布者和平台,并加重惩罚手段,从源头上杜绝“假新闻”和试图运用“后真相”事件谋利的行为。
最后,建立信任体系,培养公众信任意识。信任体系的建立需要发挥权威专业媒体的传统和智能。具有专业媒体素养的新闻工作者和机构也应当进入自媒体平台,及时发布权威新闻和评论,借助其长久以来所树立的公信力来引导公众舆论的走向。“罗一笑事件”发酵之后,很快便有传统权威媒体介入,实地调查核实情况,将事实真相公之于众,扭转了事件的走向。自媒体作为制造者实现了不分地域的信息即时共享,这是媒介发展的重大进步。“后真相”并不等同于无真相或者假真相,因此“后真相”不全是假新闻,“后真相”里有部分真相,只不过不是全部的真相。因此,需要有人来进行辨伪存真。
媒介作为制造者,制造出了以情感为核心的“后真相”。“后真相”时代不仅仅是政治领域需要面对的新的政治生态,也为文艺传播和媒介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挑战。如何应对“后真相”时代,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而言,都是任重而道远的。
[1]Alison Flood.“Post-truth” named word of the year by Oxford Di ctionaries[EB/OL].http://theguardian.com/books/2016/nov/15/post-truth-named-word-of-the-year-by-oxford-dictionaries,2016-11−15.
[2]夏莹.“后真相”: 一种新的真理形态[J].探索与争鸣,2017(6): 66−70.
[3]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M].陆扬, 张岩冰,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4]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M].商正, 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5]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引论[M].刘文玲, 译.陈卫星, 审译.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4.
[6]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 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 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7]Hillis Miller J.The medium is the Maker: Browning, Freud,Derrida, and the New Telepathic Ecotechnologirs[M].Great Britain: Sussex Academic Press, 2009.
[8]J.希利斯·米勒.希利斯·米勒文集[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9]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 大众心理研究[M].王浩宇, 译.北京:群言出版社, 2015.
[10]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 肯尼斯·库克耶.大数据时代[M].盛杨燕, 周涛, 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2.
[11]约翰·P.巴洛.网络空间独立宣言[J].李旭, 李小武, 译.清华法治论衡, 2004(4):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