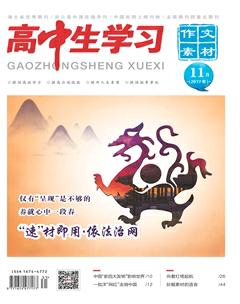给梁启超后人的一封信
陈泓佚
梁启超先生的后辈们:
你们好!
我是近日才得知这一消息的,梁启超先生位于北京的故居早已被私搭乱建,不复原貌,实话来说,甫得消息,我便心下难安,但碍于自己不过一学生罢了,反复斟酌之下,只能辗转为您写这封信。
请原谅我的唐突,我不得不发出诘问:你们为何要对这种情况听之任之、视若无睹?作为梁先生的后辈,你们完全有理由去保护好他为你们留下的最后的记忆与遗产。
我还能记得当初阿房一炬、宫阙万间都做土的模样,我仿佛亲历一般刻骨铭心;我还能听见颐和园被毁时野兽们的欢叫与世间数万奇巧工匠心碎之音……于我而言,这不仅是一个建筑物的消失,更是一个时代印记渐渐远去的标志——梁先生故居的现状也正是如此。
又一处名人故居的消失——老人又少了一处缅怀之处,学生又少了一处传承之处,记忆又少了一处承载之处——现代人正以一种残忍而无知的方法,将历史从记忆的骨髓里剔除。
梁啟超先生是我极为尊敬的革命老人,他不顾自己寒窗苦读十余载的一介学子的身份,冒着千夫所指之风险,联合康有为及其他觉醒的学子发动公车上书,再以瘦弱之躯担起民族之责的同时,也将自身前途含泪切断。同时他又有着忠君之心,即使得知光绪帝不得志仍愿意以臣子身份辅之,以图重新匡扶清室,当然从他的这种政治错误上也可看出他人品上的忠诚;他对儿子长期念叨之语便是望孩子谨记爱国之心……上述种种,让我想来总觉心潮澎湃,更添敬佩。
可如今,先生在世间所留印记越来越少,我真怕先生乘鹤西去不久,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也随之而去,使我等后辈失去了引路的明灯,进而日益麻木,难成民族栋梁。
我也知此事固非你们责任,可我真不知道,倘若你们这些后辈都麻木不仁,我还能奢望谁能出面为先生讨回一个公道?又有谁能出面为那个在民族混沌中惊醒而做那开天辟地的盘古,至死仍在忧心国家忧心后人却被后人遗忘,历史遗忘,连在尘世的一点印记也被损毁的梁先生讨回一个公道呢?
我卑微地哀痛着——对于此景,我害怕昨日历史都作尘土飞去,英雄在地底悲泣,而我们却已忘却一切,在乱搭乱建的大杂院中欢歌笑语。
而尤使我担心的是——纵使我长大之后,以一己之力四处奔走呼吁,那时还有用吗?又有谁与我一道呼走呢?
此致
敬礼
文心
2017年11月2日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