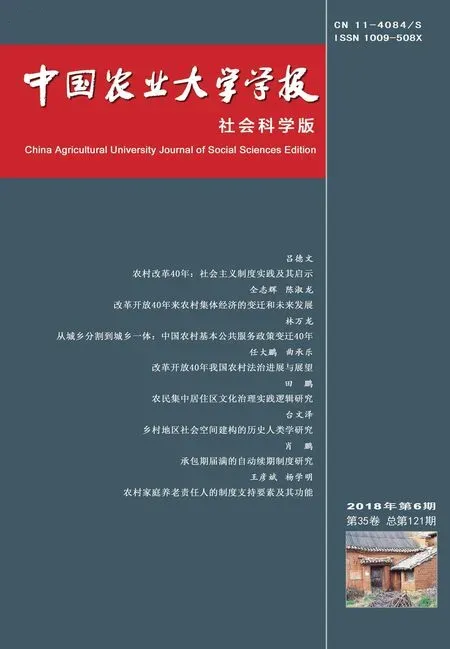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治理实践逻辑研究
——以豫北N社区为例
田 鹏
一、问题的提出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指出,强化社区文化引领能力是不断提高城乡社区治理水平的重要举措之一。具体举措包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心口相传的社区精神并增强社区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和荣誉感,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居民公约、村规民约,内化为居民群众的道德情感,外化为社会服务的自觉行动;重视发挥道德教化作用,建立健全社区道德评议机制;组织社区开展文明家庭创建,倡导移风易俗;发展社区志愿服务,形成以邻为善、以邻为伴、守望相助的良好社区氛围;加强城乡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能力[1]。因此,建立健全文化引领机制,强化社区文化引领能力是当前补齐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短板之一[2]。爬梳学术界既有研究发现,目前,关于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引领和治理的相关研究大致呈现两种论调:第一种论调基于“移民文化适应”理论视角,系统探讨农民集中居住后的经济生活、社会交往、社区参与、社区归属感等一系列与主体人的生产生活及转型适应有关的问题,并强调通过构建社会网络和身份认同实现农民集中居住区移民的文化适应感与文化重构[3]。笔者将其称之为“文化适应论”。第二种论调则基于“沃思—雷德菲尔德模型”(Wirth—Redfield model),将农民集中居住区视作一种乡土—都市连续统的特殊地域社会类型,从公共空间转型和社区意识崛起等维度系统考察农民集中居住区“都市性嵌入”与“乡土性嬗变”的实践逻辑,并强调作为一种规划性变迁的农民集中居住区[4],其变迁过程不仅仅是人口聚居模式和社会样态的“后乡土性”(Post-earthbound Sociality)之生成[5],更是告别乡土社会实现一种新型的城乡文明关系的过程[6]。笔者将其称之为“文化转型论”。
就理论预设角度而言,基于“移民文化适应”理论视角的“文化适应论”将城乡文化视作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模式,且从村落散居到社区聚居的社会空间集约化转型过程中,存在城乡文化的二元竞对和移民文化协调[7]两种基本状态。不同于“文化适应论”,基于“沃思—雷德菲尔德模型”的“文化转型论”则将农民集中居住区视作一种“乡土连续统”(Earth-bound Continuum)的特殊地域社会类型[8],并视其变迁为城乡二元文化的有机协调。当然,笔者认为正是由于上述两种论调的理论预设均忽视了治理理论视角,无论“文化适应论”抑或“文化转型论”,均未能很好地回应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治理的运作机理和实践逻辑,这不仅无助于客观全面地理解文化适应及其转型的微观机制,也不同程度地导致了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引领和文化治理乱象丛生[9]。
因此,鉴于上述局限性,基于“文化治理”(Culture Governance)理论分析框架,以豫北N社区为例,从乡土文化延续和公共文化嵌入两个维度系统阐述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治理的实践逻辑。
二、“文化治理”:一个整体性理论分析框架
社会学者关于文化的阐释大多来自于文化人类学,从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成为美国社会学主流范式时,文化一直被用来回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这一社会学元问题。当代大部分文化人类学者所持有的文化观都出自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的经典定义,“文化(Culture)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和习惯”[10]。而文化作为社会整合机制则集中体现在文化与社会的关系上,即“通过文化的分层的自我组织,在这里自我的不同层面在一个自我审视和自我改革的无穷无尽的过程中相互对抗,改革规划能被转换成文化自我管理的技术”[11]。
因此,所谓“文化治理”是由社会结构之内的各种相关主体借助网络化的治理体系,参与到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与国家文化领导权的建构,形成一种国家政权主导的国家建构与社会整合的宏大叙事[12]。而社区文化治理是政府将社区文化作为治理对象与工具,借助社区治理网络体系,依靠文化公共领域、文化空间场域以及文化展示等组织形态和活动样式,培育与塑造新型社区文化,发挥文化的治理性功能并推进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建构,奠定国家政权合法性的社会基础,最终实现国家治理之集体行动[13]。一言以蔽之,社区文化治理可以成为社区整合和秩序重建的行动策略。而作为一种整体性理论框架的“文化治理理论”具体包括下述分析维度。
首先,治理主体的多元性。一方面,文化治理强调政府自身、市场文化组织、社会文化组织以及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同时,各利益相关治理主体基于不同治理逻辑围绕特定治理规范形成文化治理网络体系;另一方面,该体系具有自我调节和协同互构的基本特征,从而形成一种多元文化治理结构[13]96。因此,社区文化治理具有主体多元性特征。
其次,治理机制的双重性。一方面,文化治理不再仅仅依赖于政府行政机制和文化管理,而是积极运用社会自我治理机制营造良好的文化自治理氛围,优化文化资源配置并提升文化自我服务能力,即文化治理的社会自我治理机制;另一方面,文化治理的机制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即国家权力主导下的行政治理机制,如社区政治文化空间营造、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等等[13]97。换言之,文化治理过程是自治型社会治理机制和他治型行政机制的综合作用和辩证互构。因此,社区文化治理机制具有自治和他治的双重属性。
最后,治理技术的隐蔽性。一方面,文化治理更多地聚焦于社会日常生活世界的辩证与建构,强化文化作为隐形权力的工具性、展示性和运作性;同时,侧重于培养并依靠社区文化人的运动式治理和社区公共人的复兴,从而建构社区文化公共领域和公共生活;另一方面,社区文化治理并不采用公权力的表征技术,而是通过社会互动、关系营造和生活建构等多样化隐性运作技术实现柔性治理[13]98。因此,实践中社区文化治理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特征。
就理论解释效度而言,作为一个整体性理论分析框架的“文化治理”理论,一方面,社区文化治理积极协同多元治理主体并充分耦合自治—他治双重治理机制,从而建构一种特殊的多中心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同时,社区文化治理积极发挥文化作为微观柔性权力的治理技术及其治理功效,并实现潜移默化的规训与认同,塑造文化人和公共人从而构建社会生活共同体;另一方面,社区是具有社会学意涵之社会生活世界的实践空间,也是社会意义建构的文化空间,换言之,社区文化治理不仅在学理上具有一定的启示性和借鉴价值,且在经验层面也是构建社区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形态。一言以蔽之,“文化治理”理论可以成为社区共同体重建的重要行动策略和社区文化实践的学理分析框架。
因此,笔者借鉴“文化治理”理论分析框架系统性审视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生成的一种特殊地域社会类型——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治理的实践逻辑。不仅因为缺少治理视角的既有研究理论预设——“文化适应论”和“文化转型论”无法有效阐释实践中的文化引领机制及其微观治理逻辑,而且作为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唯有政治治理、经济治理和文化治理的有机协调和功能耦合,方能增强基层治理能力、提升治理绩效。因此,为弥补当前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研究的局限性,笔者尝试性采用“文化治理”理论视角,系统考察并阐释当前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治理的实践逻辑。
三、“找回文化”:N社区文化治理实践
所谓农民集中居住区是指基于城乡连续统一体,由若干行政村村民自愿组合并享受城乡公共均等化服务的一种新型人口聚落模式和地域社会类型。实践中的农民集中居住区具有迁徙动机自愿性、公共服务均等化、生计模式多元化、社区治理现代化等基本特征。笔者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失调的实践样态集中表现为:第一,就社会生产方式而言,传统农耕生产方式与现代物业管理模式的冲突,如N社区居民为延续传统庭院经济、减少生活成本进行“占地种菜”“毁绿种菜”;第二,就生活习惯和社会习俗而言,传统农村风俗与现代社区居住习惯和非农化生活方式的不协调,如N社区居民集中居住后导致传统婚丧嫁娶等民间习俗难以维持和延续,红白喜事没有操办场地;第三,就日常社会交往和人际互动而言,农民集中居住后使得传统村落终结和共同体消失,基于乡土空间运作逻辑和熟人社会互动法则失去必要的社会基础,导致农民集中居住区社会运行呈现个体化、原子化、无主体化和半熟人化等实践特征,从而使得“农民上楼”后缺乏本体性安全感;第四,就社会认同和社区意识而言,农民集中居住后仍然持有较强的村落共同体认同,缺乏必要的社区认同和公共意识,导致社区秩序整合面临主体缺失、认同危机等现实困境。
胡静林:2011年中央财政安排在西部地区的水利投入大概是660亿元,占整个中央财政水利总投入的36%。除了水利口安排的以外,还包括南水北调、国土资源中用于农田水利的。在农田水利方面,大概也是占33%左右。下一步,中央财政要继续加大力度:
作为社区社会生活共同体重建的重要行动策略,社区文化治理具有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治理机制的多重性和治理技术的隐蔽性三大基本特征。笔者借鉴“文化治理”理论分析框架并以豫北N社区为例,从乡土文化延续、公共文化嵌入两个维度系统考察农民集中居住区社区文化治理的实践逻辑。N社区采用撤村并居模式,即土地部分征用后实行部分拆迁,将分散的拆迁户并入中心村,以中心村为基础建成新社区,把城市社区管理办法向农村延伸、辐射到周边的村落。目前,N社区共有16幢,1幢分为3个单元,每单元33户,1幢99户,共计1 566户。
(一)乡土文化延续:自治型自我治理机制
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在《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一书中提出“半文化观”,即“一个农民社区的文化绝非是独立自主的,它只是它所附着于其上的那个文明的一个方面,或一个层次。既然农民社会只不过是附属于一个大的社会的‘一半',因此,农民的文化就只能是一个‘半个文化'”;且应从“大传统”(Great Tradition)视角考察“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的演化历程[14]。笔者在N社区实地调查中发现,作为一种自治型文化自我治理机制,“半文化”的乡土文化延续在N社区主要体现在乡土宗教的自我维系,其实践形态则表现为“迁建三神庙”与“家中过会”。
第一,“迁建三神庙”。笔者在N社区的田野调查发现,农民集中居住后生活世界的意义建构具有明显的差异化特征,在作为一种差序场的新社区里,职业成为劳动力群体,尤其是年轻劳动力日常生活之社会意义的重要来源。而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则显得比较保守,更倾向于通过民间信仰方式应对社会生活空间转换后一系列不确定和焦虑;因此,考虑到老年人进社区后缺乏必要的精神依托和民间信仰,N社区决定迁建坐落在原村旧址上的土地、牛王、山神庙(当地人俗称“三神庙”),并修建了“三神庙史记”碑帖以警示后人。但当笔者追问土地、牛王、山神在当地农民日常生活中究竟分别扮演着什么角色并起到何种作用,且为何三者可以供奉在一个庙堂里时,大部分受访者都无法解释清楚,只是说“都是这么一代代传下来的,背后肯定有传说和故事,但具体是什么我们也知道”;同时,当笔者问及在土地资源如此宝贵的新社区里为何还要另辟一块地皮用于供奉“三神庙”时,负责起草“N社区三神庙史记”碑帖的一位老年人告诉笔者,“迁建‘三神庙'是大家的一致意见,进社区过上了更好的生活,但是也不能忘了历史不能断了祖宗传下来的香火,更要让孩子们继承这段历史,当年从外省迁入此地,现在这里就是我们氏族的血脉”①文中引述访谈材料均来自笔者对豫北N社区的田野调查笔记,下文不再一一标注。。显然,从“三神庙”迁建的实践者角度而言,试图通过社会记忆的选择性建构实现心灵的集体化并使得宗族文化和村落历史得以传承和延续。日本民俗学者柳田国男在《民间传承论与乡土生活研究方法》中指出,作为“Folklore”的重要组成部分,祭拜神灵已成为村落民俗生活的重大事件,各种祭礼和祭仪也内化为农耕文化的核心[15]。而中国大陆人类学者景军对兰州附近的大川、小川两村孔庙的修复的“深描”并从社会记忆的角度指出,庙宇迁建及其仪式在中国村庄发挥着记忆再生产、权力秩序整合、村落公共空间再生产等一系列作用[16],换言之,作为一种选择性记忆的实践行为,庙宇迁建本身也是一次集体记忆的再生产;因此,作为一次民间自发的文化自治实践,N社区“迁建三神庙”本身必然起到重构村落记忆、再生产集体意识的治理功效。
第二,“家中过会”。如果说以村落为单元进行的民间信仰活动是一种“非常态”,那么,以家庭为单元开展的乡土祭拜仪式则是村民日常生活的“常态”。民俗学者岳永逸在《行好:乡土的逻辑与庙会》一书中明确指出,犹如变形中的变色龙,乡土庙会会因外界的变化而变形或变色——可能变小、变色但绝不会消失,可能变大变浓,但却绝不可能改天换地——成为与时俱进的一种文化社会生态景观;因此,“家中过会”就成为跨村落或村落庙会行好逻辑的地域性延伸,换言之,家庙让渡的辩证法成为以灵验、敬拜、和许愿还愿为核心的乡土庙会传衍机制、策略与技艺,且以香火为载体的家居空间既是人生活起居、生老病死的所在,也是乡民认同的神的住所[17]。笔者在N社区实地调查中发现,农民集中居住后的“家中过会”现象依然普遍存在,大部分受访者均以家庭单位进行民间祭拜活动,且大多只在自己家中开展简单的日常仪式,而非大规模、有组织的制度型宗教实践,即那些拥有自身的神学、仪式和组织系统,且拥有自身的基本观念和结构体系,并独立于其他世俗建制的宗教。而当笔者问及为何搬进社区后还在现代化的居住空间里烧香供神时,大部分受访者都认为仅仅只是为了消灾避祸,祈求家人健康、平安,正如一位受访居民所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哪能不烧香拜佛,我们这里的人多少都有会信奉一些神灵,主要还是为了消灾避难,F村有个很有名的例子,我们这里的人都知道,他家里的老父亲得了一个疑难杂症,医院都没办法了,后来听人说供奉一种什么娘娘,专门管人生老病死的,最后就好了,你说奇怪不奇怪,我也是听过了这件事才开始在家里供了一些神”。显然,“举头三尺有神明、常怀敬畏一生平”,从功能主义角度而言,中国人的神灵观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应对日常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同时,这种儒释道三教合流、民间信仰多元混杂的信仰格局是一种典型的追求和谐实用的宗教观,且这种实用主义宗教观的认受度直接取决于其灵验度。
因此,就治理功能和实践成效而言,作为自治型自我治理机制的乡土宗教延续能够有效缓解“农民上楼”后产生的一系列文化失调和适应真空,如“迁建三神庙”不仅延续了农耕文化传统里的民间习俗,而且重构村落记忆、再生产集体意识,有利于社区秩序整合;又如“家中过会”不仅缓解了“农民上楼”导致的个体化焦虑、本体性安全感缺失等社会心理困境,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集中居住后对传统村落共同体民俗生活的现实诉求。一言以蔽之,实践中的自治型治理具有缓解适应困境、平衡文化失调的治理功效。
(二)公共文化嵌入:他治型行政治理机制
如果说“迁建三神庙”和“家中过会”是一种基于乡土逻辑的文化自治理和文化自服务行为,那么,乡村公共文化嵌入则是基于基层政权建设逻辑的文化他治行为,且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治理机制是一种典型的政府行为和国家工程。一方面,现代性的侵蚀使得乡土社会在智慧方面、宗教信仰方面和道德水准方面处在一个残缺不全的状态之中,充分整合本土文化资源和地方性知识强化村庄公共文化供给自主性和独立性,从而使其表现出低消费性—高福利性特征;另一方面,农民集中居住区的文化并非独立自主,而是在与大传统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中实现传承。因此,随着市场化和个体化的双重冲击,农村公共文化日渐式微,如何有效完善城乡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职能,尤其是建立健全农村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制机制,充分发挥作为隐性权利的文化治理技术和规训认同策略,从而实现公权力合法性再生产并提升国家基础性权能,显然是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治理的重要议题。笔者在N社区实地调查中发现,作为一种他治型行政治理机制的公共文化嵌入,实践中主要体现在“电影进社区”和“文化石工程”。
第一,“电影进社区”。作为乡村公共文化的实践载体,乡村露天电影曾是新时期农村民俗文化中一道亮丽风景,成为婚嫁、寿辰、丧葬等红白喜事礼俗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换言之,作为一种民俗活动的露天电影已成为乡村公共文化和公共空间建构的重要策略和基本形式[18]。作为“电影进社区”工程的基层实践者,电影放映员LPT告诉笔者,“2006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市文化局就实施了电影进社区工程,一直到现在,都要求各县文化站坚持落实这项惠民工程。我从2008年开始接受这项工作,负责C镇和Z乡两个乡镇,每月23场影片放映任务,主要以行政村为放映地点,每晚19:50开始,两部影片共3个小时,一直到影片放映结束才能下班,不能提前下班,因为有GPS定位考核,一般村民在20:30到21:30时间段内比较集中,22:00以后都陆续回家睡觉了,但是我还得坚持放映结束。电影题材一般都是上级规定好的,基本是关于农村题材类的,比如豫剧文化,这类贴近农村现实生活的影片,引导农民形成健康的价值观。我感觉国家还是不想丢掉这个文化工程,意识形态教育很重要,文化下乡全部由国家财政支出,专款专用,文化精神丰富了才能更好地实现社区建设”。从传播学角度而言,露天电影是电影放映在特定时空中的特殊表现形态,尤其是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日常化载体,是一种兼具多种功能并承载特定使命的电影传播。因此,作为一项国家工程,电影进社区不仅以一种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在满足农村居民精神文化需求、完善公共文化供给机制、培育新时期社会公民等维度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是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一种国家治理术,N社区俨然是格尔兹意义上的尼加拉——一种国家—村落互动的“村落政体”(Village Regime)下的“剧场国家”(Theatre State),而作为政治表述的流动影像放映则成为国家权力和政治机体再生产的仪式化行为[19]。具体而言,一方面,在公共空间相对受限、公共活动相对缺乏的农村基层社区,露天电影的复兴唤起了部分村民尤其是中老年群体的集体社会记忆,能填补农民进社区后精神世界的部分空缺;另一方面,公共文化供给对宗教信仰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构和文化服务能力增强能部分实现乡土文化的功能替代,并降低村内信教比重[20]。因此,“电影进社区”能部分规避作为文化自治机制的乡土文化延续中宗教信仰的社会风险,尤其是缺乏主流价值观引导情况下部分农民进社区后出现的价值观真空。
第二,“文化石工程”。如果说“电影进社区”是农村高音喇叭式的国家动员模式和权力隐喻术之延续的话[21],那么,作为公共文化嵌入的另一重要实践形式——“文化石工程”则是基于标语符号的隐性治理权术。N社区“文化石工程”管理办公室主任FQB告诉笔者,“文化石是新型农村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其目的就是要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十四个字变成的口号和标语镌刻在大大小小的石头上,以不同的字体标注出来,放置在社区比较明显的位置,比如社区广场附件,每个楼栋之间的空地上,这样居民每天都会看到这些口号和标语,潜移默化地就会受到影响,自然而然也会参照这些标准去实践”。显然,“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让农民进社区后通过文化石的熏陶和浸染并采用一种喜闻乐见的方式构建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村规民约,内化为居民群众的道德情感,外化为社会服务的自觉行动,从而达到文化治理的行政他治向自我治理转型。而关于文化石上究竟镌刻了哪些标语和口号,笔者通过梳理将其大致分为两大主题:感恩和修身。感恩党和国家的发展带来了如今的幸福家园和美好生活;而修身则是通过自觉执行社区行为准则和公民道德,维护社区形象,为社区增光,报效党和国家的恩情。笔者摘录部分标语和口号以供读者体会,比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用感恩的心完善一切,用行动为党增光”“紧跟党走,迎难而上,勇挑重担,为国分忧,为民解困,甘于奉献”“做每一件事都要对得起党,对得起群众”“支部职能高效有力,乡邻之间彬彬有礼”“爱岗敬业、遵纪守法,家庭和睦,诚信致富”“办事要节约,勤俭是美德,人人讲道德,个个讲文明”等。中国问题专家安德鲁·华尔德(Andrew Walder)在《共产党社会的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一书中认为,工人对企业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依附、工人对工程领导在政治上的依附以及工人对直接领导的个人依附共同作用产生了一种“权威制度文化”(Institutional Culture of Authority),而其核心作用机制是施恩回报逻辑,这种特殊供给制度下个人对组织的“总体性依附”也是单位制的典型特征。但事实上,所有现代社会都是延续与变化的整合体,既受传统社会结构的影响,又是现代工业化的结果[22]。虽然后单位制时代已成为城市社会治理的常态,农村基层社区建设中仍然部分程度延续着传统单位制中的施恩回报逻辑,尤其在财政能力欠缺的部分农村社区,项目进村俨然成了一种类似单位社会里的特殊供给制度,而N社区正是国家制度供给和政策运作的产物,加之中国传统社会运作法则——“报”的文化传承[23],感恩政党、报效国家就显得那么顺其自然、水到渠成,正如某块文化石上的文字显示的,“用感恩的心完善一切,用行动为党增光”。
因此,就治理功能和实践成效而言,公共文化嵌入能够有效缓解“农民上楼”后产生的认同危机和整合困境,如“文化石工程”基于标语符号的隐性治理权术成功实现了居民自觉执行社区行为准则,维护社区形象,为社区增光添彩以回报党和国家的恩情,有利于社区认同和社区意识的形成。一言以蔽之,实践中的他治型治理具有增强社区认同、培养社区意识的治理功效。
四、结论与讨论
基于“文化治理”理论分析框并以豫北N社区为例,从乡土文化延续、公共文化嵌入两个维度系统性考察农民集中居住区社区文化治理的实践逻辑。
首先,作为自治型自我治理机制的乡土文化延续。作为社区文化治理实践之一的自我治理机制,乡土文化延续在N社区实践中主要体现为“迁建三神庙”和“家中过会”。一方面,从“迁建三神庙”的实践者角度而言,试图通过社会记忆的选择性建构实现“心灵的集体化”并使得宗族文化和村落历史得以传承和延续;同时,从功能主义角度而言,中国人的神灵观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应对日常生活中的不确定性,换言之,家中过会就成为跨村落或村落庙会行好逻辑的地域性延伸。因此,通过乡土文化的历史延续和民间信仰的乡土传承——“迁建三神庙”“家中过会”有效应对了社会空间转型和文化空间消失导致的本体性不安和个体化焦虑,从而实现了农民集中居住区这一特定社会空间的文化自治理。
其次,作为他治型行政治理机制的公共文化嵌入。作为社区文化治理实践之一的他治型行政治理机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嵌入在N社区实践中主要体现为“电影进社区”和“文化石工程”。一方面,农民集中居住区首先是一个需要实现文化治理的社会空间,无论“电影进社区”抑或“文化石工程”都在用一种本土化的方式实现社区公共文化体系重构,从治理主体上看是一种他治型文化治理机制,从治理资源角度而言,用行政手段激发了传统乡土社会文化资源;另一方面,在“文化下乡”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中,“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文化整合功能和社会教化意图更是展现得淋漓尽致,知恩图报的传统美德在后单位制时代的基层农村社区又使得感恩话语、增光行动充斥着居民日常生活的每一处细节。因此,通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重构和“文化下乡”——“电影进社区”和“文化石工程”在实现社区文化公共领域和社会生活公共空间重构的同时,也基于多样化隐性运作技术实现柔性治理再生产出国家——农民关系的施恩回报逻辑,从而有效发挥了文化治理功能并促进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形成,最终奠定了国家政权合法性的社会基础。
第三,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治理的实践逻辑。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治理的基本逻辑,即将文化——包括传统乡土文化和现代公共文化视作基层社区治理的资源规则和实践对象,基于现代新型社区治理网络和组织体系,通过“乡土文化延续”的自我治理模式和“公共文化嵌入”的行政治理体系,充分发挥文化作为自我规训手段和隐性治理权力的机制和功能,并与政治治理、经济治理形成有机协调和功能耦合,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最终促成社区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形成。
最后,正如费孝通所言,“社会问题起源于文化失调”[24],社区公共意识匮乏和认同感缺失正是当前社区文化无法有效发挥引领作用并实现治理绩效的重要原因;又如西里尔·布莱克((Cyril Black)在《比较现代化》一书中指出的,“在任何社会中都不存在纯粹的现代性和纯粹的传统性,相反,现代化进程中是传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在功能上对现代化的要求不断适应的过程”[25]。质言之,基于文化治理理论视角,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治理实践既是作为“小传统”之农民文化的自我治理和自主服务,也是作为“大传统”国家公共文化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作为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的重要地域社会类型的农民集中居住区,若要形成以邻为善、以邻为伴的良好社区氛围和团结协作、守望相助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基本目标,那么,必然无法忽视文化这一重要治理资源及其治理策略,且唯有通过自治和他治的机制衔接,形成传统乡土社会本土文化与现代公共文化的功能耦合,才能真正能实现文化治理、政治治理和经济治理的多元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