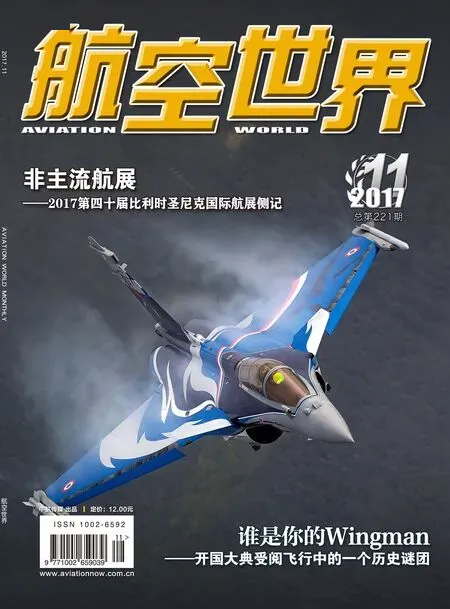负重翱远志半酬
——肖特SC.5“贝尔法斯特”略史
文/俞敏

归于重运公司旗下的“贝尔法斯特”
被国内网友昵称为“胖妞”的运20军用运输机在网络和航展的自信亮相,标志着中国在军用大飞机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该机对于未来的海外兵力投送、物资运输、人道救援和多用途空中平台改造,都有着非同一般的里程碑意义。
而在半个多世纪之前,美苏争霸在所有军事技术领域全面展开的冷战鼎盛期,另一个老牌帝国英国也曾踌躇满志地在大飞机领域极力寻求突破。尽管当时该国内部环境和其他诸多客观条件俨如四处南墙,那些为此目的奔走出力的军界和航空界人士撞得惨不忍睹,但从今天来看,这一努力的消极结果并不代表整个过程毫无意义。实际上,这种比美国C-130“大力神”略大一号的四发中远程运输机,各项性能指标和技术参数在当时说它领跑全球也并不为过。

英国装备的KC-130加油机。皇家空军更为倚重成熟可靠的“大力神”
被忘却的大鸟
由地处北爱尔兰的肖特兄弟公司开发的SC.5“贝尔法斯特”,其地位与今天的A400M大致相当。两者同样采用4台大功率涡桨发动机。和目前所有战略运输机清一色采用涡扇发动机不同,当时喷气发动机技术还处在发展早期阶段,尤其在大型飞机上的应用存在较大限制。可以说在1963年之前,英国皇家空军从未装备过远程战略货运飞机。部署在海外殖民地的武器装备和各类物资主要依靠强大的海运手段,空运以人员投送为主,“约克”系列运输机就已经绰绰有余。肖特兄弟公司当时已经被选中为皇家空军开辟第二条“布里塔尼亚”涡桨运输机(布里斯托尔公司设计)生产线,布里斯托尔从1950年开始就一直是肖特公司的控股方,肖特公司一共生产了23架军用型“布里塔尼亚”。
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该机的灵感也确实源自于稍早问世的“布列塔尼亚”四发涡桨和加拿大航空的CL-44货运飞机。至少从一开始,其暂定名为应该叫做“布列塔尼克”,正式的名称为PD18。这个方案在1957年3月提交小册子给军需部,实际上就是上单翼的“布列塔尼亚”。肖特公司一直在酝酿采用“猎户座”发动机(也是布里斯托尔开发的)的远程运输机方案,希望藉此获得皇家空军的另眼相待。这种飞机能够为陆军运送诸如“蓝剑”导弹系统和大口径火炮等重型装备,除此之外它还能一次搭载200名左右的武装人员等。

布里斯托尔的“布列塔尼”对SC.5的设计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SC.5该机最初的设计目的就是运送特种武器装备,服役后隶属于空运指挥部
竞标方案的机翼、尾翼和主起落架都是现成的,动力则暂时定为4台“猎户座”。从市场前景的角度看,另起炉灶风险很大,比较稳妥的途径是尽量沿用现成布列塔尼亚的零部件,不过在后来的具体实施过程中,肖特兄弟却走出了一条全新的道路。最重要的就是用于布置巨大货舱的机身(容纳3.69米3的货物),必须根据所载导弹的需要量身定制,圆筒状截面是唯一选择。机身分成8段,为了节省厂房空间,简化施工程序,采用垂直装配的方式,多数肋骨和纵梁都轧制成Z形部件,承受载荷的部件都制成盒形梁,货运地板为工字梁挤压件构成,顶部则是蜂窝板材,其余部分都是标准截面或是普通的板材。
与其同台竞争的另两个方案,其中之一是布莱克本的B.107,该机采用罗罗公司的泰因发动机,还有一个是汉德利-佩吉从“胜利者”轰炸机设计衍生而来的HP.111。不过这两个方案皇家空军从一开始就不看好。皇家空军的作战需求其实有过一些调整,尽管如此,装载3万磅载荷(13.6吨)飞行3600英里(5760千米)的要求却是明白无误的。为此,肖特兄弟也及时放弃了“猎户座”,改用和B.107一样的泰因发动机,同时更换了机翼中段,使得翼展增加了5.05米。这一改动果然奏效,军需部在1959年1月正式宣布肖特方案胜出。当然基础构型还需要不断修改,C.D.哈顿(C.D.Hatton)在1958年被任命为总设计师,负责服役之前的整体设计定型。
继续沿用“布列塔尼亚”后续名称的做法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布列塔尼克”-I先是演进成为-IIIA,同时被赋予了SC.5的公司编号。最后经过磋商,就以肖特兄弟公司及哈尔兰工厂所在的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为其命名。项目为北爱尔兰提供了将近5000个工作岗位,由哈顿担任服役前阶段的总设计师,麾下团队人才济济,力量雄厚,最多时总人数达到350人,另外还有200人是专门和分包商打交道的。因为飞机虽然是肖特公司主持设计,但有几个主要部件分包给了其他的公司,比如后机身和载货坡道是桑德斯-罗的产品,货舱门这块是英国气垫船公司生产,动力装置由维克斯负责,短舱则是和博尔顿-保罗签订的合同。特定采买的设备都在合同中详细写明,主要的零件都需经过苛刻的筛选,确保其兼容适装性达到最佳标准,安装之前所有的硬件设备都必须通过验收。
根据初步统计,肖特公司总共开发了4个分型号,当然大部分都未获投产。因为出于政治需要,英国人更倾向于从美国获得廉价而成熟的军事装备。第一种是SC.5/10,从1959年2月开始设计,同年10月就生产出原型机,采用罗罗公司泰因RTy-12发动机,1964年1月5日完成首飞,2号机在5月1日升空,先后一共生产了10架,被皇家空军赋予编号“贝尔法斯特”C.1。与之对应的民用型号是SC.5/10A,突出运载能力,取消了自动着陆和空中加油系统以及军用电台和某些导航设备,空调设备也比军用型更为简化,作为客机能搭载147名乘客,而载货模式下可搭载大型货盘和重型民用车辆等等(可载运22.68吨货物飞行4825千米)。
另外还有两种远期改型,也就是SC.5/13和SC.5/41,皇家空军对它们毫无兴趣,原型机自然想都不用想。SC.5/13其实变化不大,最重要的一点是改用了大直径螺旋桨,使得飞机起飞重量增加,在载重不变的条件下,能够携带更多燃料(43.54吨),最大起飞重量超过了113吨。由于这样一改飞机的航程有了显著改善,于是设计者马上想到了海上巡逻改型。当时皇家空军的“沙克尔顿”系列已经过于老旧,每年的故障率也不断增高。最后一个改型的提出是为了实现英国人大型喷气运输机梦想的,称之为SC.5/41。这个数字实际上暗含着要和美国洛克希德公司C-141“运输星”较劲的意思。它计划采用全新设计的机翼翼型(讽刺的是,还需要洛克希德公司提供),改造成T形尾翼,换装RB.178涡扇发动机,最大起飞重有望达到190吨(军用载重预计在54吨左右)。该机预想可以适应多个型号的发动机,包括罗罗的康威550、布里斯托尔-西德利的BS 100甚至还有普惠的JT3D,但最后却不了了之。
设计单位的失望和愤怒是可想而知的,这与他们数年来雄心勃勃的构想判若云泥。这杯水车薪的采购数量只能算“上级部门”象征性的恩赐,连抵消前期投入都做不到。军方言之凿凿的性能指标看来只针对国内厂商,肖特尽管全部满足,结果还是被一个根本不受条条框框束缚的外来户挤到了一边。当然反过来说,肖特公司可能也过高估计了皇家空军拥有远程运输机的决心。
大身材 大容量
和外形粗短的C-130相比,SC.5身材肥硕修长,机身中段所占比例较大,尾部弧形上翘过渡更为圆滑,其48.42米的翼展超过机长(41.58米)许多,同样带有弯弧前掠的垂尾净空高度为14.33米,最大载运能力接近36吨,占起飞总重(104.32吨)的比例超过1/3,远超“大力神”的20吨。
卵圆机头前端为铰接上翻式电介质雷达罩,内部装有搜索雷达盘状天线,驾驶舱空间和座椅都很大,玻璃框视野完整,厨房后部还有床铺可供6人休息。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减轻机组成员的长途飞行疲劳感。另外,舱内仪表遵照英国航班飞行员协会的建议进行布置,完全没有头顶仪表盘。5人制机组包括正副驾驶各一人,加上飞行工程师、领航员和一名装卸长(或者通信员)。当然这并非雷打不动的固定搭配,具体多少人要看飞行指挥官的安排。飞行工程师在整个飞行阶段负责4台发动机的油门操纵,所以驾驶员实际上只负责滑行阶段的油门控制。机组成员首先进入货舱,走过所谓的“吟游诗人走廊”来到宽敞的厨房,这里足够容纳十多人搞一个茶话会。

SC.5/41的编号暗含着要和美国C-141“运输星”较劲的意思。图为洛克希德公司的C-141C(近处)和C-141B
机翼前缘带有明显后掠角,后缘相对平直,和“布列塔尼亚”的主要区别是主扭力盒还兼用于一体化油箱。而“布列塔尼亚”则使用普通的内部袋状油箱。另外新飞机的襟翼增加了2.4米,其双缝襟翼效率更高,行程节省5°,液压驱动系统比“布列塔尼亚”的电作动筒更轻巧。尾部结构基本照搬“布列塔尼亚”,只不过面积稍大,尾翼翼展19.81米。常规前三点起落架设计,主轮距5.89米,前主轮距14.91米。
双轮前起落架向前收起,可左右转向50°。主起落架系统沿袭了“布列塔尼亚”的设计风格,每侧4对并列轮组,一共为16轮,起飞后向前收入大型的长条形非加压整流罩内。除了用以容纳起落架,整流罩内还装有辅助动力和空调系统。由于起落架间距偏窄,因此滑跑的时候千万要小心,不能过快,否则的话很可能造成飞机两边摇摆,引起轮胎过热甚至起火。在侧风条件下该机也需要特别留神,因为侧倾力矩要比一般飞机大得多,方向舵在80节左右(148千米/时)就不管用了。

CG模拟显示的“贝尔法斯特”双人驾驶舱

机翼后缘与机身上表面连接处

从正面看,“贝尔法斯特”与“大力神”十分酷似
货舱内部总长26.15米,最大高度4.09米,宽度为4.90米,舱门高度1.98米(宽0.88米)。货舱中间部位可以放下长19.49米、宽3.66米的大型货箱,而其余散货一般靠近尾部斜坡存放,其前端配备一台电液卷扬机,机上还有标准的空军侧向引导设备和传送带系统。载货空间非常可观,和当时英国的一套标准住房相当,可以载运特大型货物,这方面甚至超过了波音747飞机。搭载士兵正常状态为150名(去掉可拆卸天花板则还可容纳100人)。陆军大型车辆甚至“酋长”这样的重型坦克也能装下,还可装载雷达设备或是“北极星”导弹等,而换算成直升机则是3架威塞克斯,或者4架“旋风”,而更小些的“黄蜂”和“侦察兵”一次性可装6架!
泰因发动机的安装方式大致借鉴了“前卫”客运飞机的经验,不过有些地方则是体现了全新的理念。发动机短舱实际上是采用了一种非穿透式的半悬吊方式,与机翼面保持一定距离。这样做其实就形成了一个比较理想的“推进方位”,在气动面角度保证了机翼的完整性。发动机本身为钢管构造,驱动4叶4.92米直径的霍克-西德利公司液压自动传动恒速螺旋桨(铝合金实心结构),单台功率为5730马力(4213千瓦)。飞机最大航速为马赫数0.65(7300米高),最大巡航速为566千米/时,经济巡航速541千米/时(7315米高),实用升限9144米(单发7925米),最大着陆重量下失速速度180千米/时,海平面爬升率323米/分,最大着陆重量滑跑距离1065米,起飞至35米高度滑跑距离2195米。机翼每侧3个油箱,容量分别为13024升、7955升和1955升,内部总容量45868升,最大燃油航程8528千米,最大载荷航程1609千米,为了进一步增加航程,机头顶部还装有一支前伸式受油管。

被选作主要动力的罗-罗泰因涡桨发动机
慢慢变得更快
西德纳姆机场编号XR362的1号机(军方绰号“参孙”)首飞因为等不到合适的东风,耽搁了大约12天,最后安排在了1964年1月5日(周日),丹尼斯·泰勒带队的机组成员包括副驾驶彼得·勒韦在内总共6人。试飞的降落目的地是阿尔高夫,而不是返回西德纳姆,过程一切顺利,不过当天降落时高度有些偏高,速度也没有控制好,结果“飞过头”了,只能重新绕一圈。庆功酒打开的刹那,泰勒眉飞色舞,他对于飞机评价很高,认为飞机不光外形漂亮,而且驾驶过程是极大的乐趣。在国外测试期间为了避免引起过多关注,原型机涂上了G-ASKE的民用标记,到了5月份2号原型机XR363出厂,而在当年9月的航展上,观众总共看到了3架原型机,其中第3架(也出现在1965年的巴黎航展上)是专用于自动着陆系统测试的。

“贝尔法斯特”1号原型机的首飞可谓好事多磨
研发的脚步进一步加快,不过并非一马平川。XR362上首先发现了航向稳定性问题,结果就把方向舵拔高,搞成了突角平衡设计。如此一来,前机身就需要通过特种拖车来抬高,这样才能让尾翼不至于碰擦机库门沿。前5架原型机都存在最大载荷/航程方面性能的不足,这是后机身和斜坡和装货门轮廓形成的诱导阻力造成的.加上为了消除偏航力矩,在后机身还布置了附板。后来机翼前缘增加了能够在进入失速之前发出气动警告的缓冲片,不过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飞机的失速特性也很糟糕,哪怕只有18°的迎角都可能让飞机陷入失速(需要通过加装涡流发生器维持副翼效能)。当然,飞机在机头高高抬起的状态下,有时候能达到23°,这确实让人有些提心吊胆。BAC1-11和“三叉戟”这类T形尾翼布局的飞机在这个状态就有可能陷入深失速。原来的后机身附板虽然取消,但出于降低阻力的考虑,其安装位置比原先更高,另外为了降低横滚,还在方向舵上方加装了伺服片。
令公司感到遗憾的是,交付计划没能及时完成.最大问题是高载荷状态3发飞行测试不尽人意,因此必须针对高山上空飞行制定操作规范。当然后来换用了功率更大的发动机和直径19英尺(5.85米)的螺旋桨,飞机的性能一下子又提升了一个台阶。但克服所有短板,真正满足皇家空军的要求则迟至1972年后。在这之前它不但没能达到军方标准,而且公众形象也始终不佳,被媒体讥评为“白象”(意指大而无当之物——编者注),甚至给它取了个诨号叫做“贝尔慢”(英文里,贝尔法斯特Belfast中的fast是快的意思——编者注),而且难听的不止这一个。在空军能走多远成了个问题,赢得民用航空公司的青睐更是想都不用想。

放下起落架准备着陆的“贝尔法斯特”
按照空军的说法是,3万磅(13.6吨)载荷远程运输飞行,带有足够余油状态下完成3450英里(5552千米)航程,阻力超过预期。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因素,是笔直无内敛的后机身及其巨大的装货跳板形成的鸭尾,造成气流分离并产生吸入效应,导致涡流阻力的产生。这样。。再加上为了消除着陆进场过程中的横滚倾向而增加的挡板条,使得问题更加严重。板条经过了1∶35的风洞模型试验,和方向舵上的突角补偿器相配合。麦克卢内为首的肖特气动设计师经过一番研究,找到了有效对策。他们去掉了原先的偏航减振板,将其位置移到了平尾下端。按照麦克卢内的说法,其功能如同长条三角翼,同时机身和平尾之间的整流段有效降低了后机身的上仰角。改动之后在范堡罗和博斯康比唐的皇家飞机中心的风洞进行测试,发现阻力显著降低,只不过巡航速度稍稍下降。这套技术被专门申请专利,从第5架“贝尔法斯特”开始实用,后来推广到所有的SC.5上,以前的慢吞吞变成了急匆匆。
军队生涯
皇家空军的飞行测试活动从1963年步入正轨。第一个驾驶该机的皇家空军飞行员是彼得·贝克利,到1965年还组建了一支由4名训练机长和两名民航飞行员组成的项目组。在这段期间飞机阻力过大和性能不佳的问题才逐步得到解决。在公司试飞员和中队队长共同登机驾驶,经过了大约10天例行的检测之后,牛津郡布莱兹·诺顿的第53中队在1966年1月20日接收了肖特公司总裁库斯贝特·朗翰(Cuthbert Wrangham)亲自交付的XR 367号飞机(绰号“赫拉克勒斯”),“贝尔法斯特”的空军服役生涯总算是拉开了序幕。到了5月1日中队搬到了菲尔福特,因为当时布莱兹正在建造一个新的大型机库,这不光是为了“贝尔法斯特”,还要满足“布列塔尼亚”和VC-10等同级别的大飞机。

降落在某殖民地机场的8号机(绰号“斯巴达克斯”)
博斯康比唐的飞机和武器试验中心在1966年1月初的一份报告中,将该机(主要根据XR 363的驾驶经验)形容为一种“胜任愉快”的出色平台。随着航线适应和人员培训速度加快,到了1967年第53中队上上下下也都对这种飞机赞誉有加,“贝尔法斯特”开始定期执行海外任务(比如飞往亚丁)。第一次实战飞行是在1968年10月初,空运指挥部的1310小队全部的设备,包括3架“旋风”直升机,需要从圭亚那搬到菲尔福特,其他各种典型载荷包括路虎装甲车、“喷气教师”教练机。定期航线的目的地除了中东、婆罗洲等原殖民地,还包括美洲大陆。XR 366和370交付后该中队还执行了将欧洲埃尔多火箭(ELDO)和发射器从英国本土送至12000英里(19312千米)外的澳大利亚武迈拉,算是创造了该机群的早年纪录。
前后两批交付的10架飞机初始状态是不一样的,因此XR362~366必须送回厂方进行性能升级,以达到和后续5架(到1969年全部服役)相当的标准,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了1971年。所有的飞机都部署在布莱兹,这里也自然成了皇家空军最重要的空运基地,集中了最先进的训练设施和“贝尔法斯特”模拟器。交付最晚的XR 364号实际上是用作自动着陆系统的测试平台,从1967年5月到9月之间完成了226架次的成功着陆,据说把跑道柏油路面都给压塌了。实际上,最早进行自动着陆试验的是一年前的XR 365号,地点是在皇家飞机中心的贝德福。

皇家空军所用的“贝尔法斯特”可安装受油管以增加航程
这之后“贝尔法斯特”开始接连创造飞行纪录。XR362号在1968年3月从新加坡一次运送7万磅(31.8吨)药材抵达越南支持美军;在1969年4月的北约演习中又创造了一次起运7.2万磅(32.7吨)的纪录。翌年7月XR370号从博斯康比唐飞往布莱兹,机上装有两门阿伯特自行火炮,载重总量达到了英国飞机的上限:7.8万磅(35.45吨)!当然这些都是虚的,并不代表实际水平,真正体现价值的是从利比亚的一次撤退,大部分设备都是“贝尔法斯特”从塞浦路斯运回英国的,其中的大件包括活动房屋和一台波音747模拟器。北爱尔兰1969年出现政治危机时,5架“贝尔法斯特”在10天内起降28架次,向北爱地区运送了大批部队和装备,其中1架的运量相当于两架C-130和1架大商船!
单件最大载重,是1971年曾经装运的一台23.6吨重的碎石机,航程从阿联酋沙迦飞至马西拉岛。实际上,只要在载重范围内,基本上什么都能运,这也是最让机组人员感到兴奋的。飞机的航程也还算不错,1974年1月XR 367创造了最长的不落地飞行纪录:从阿尔贝塔的冷湖带着一架完成了寒区测试的直升机飞回6880千米外的布莱兹。除了特种任务,还有些是涉及到政治局势的敏感,需要抢时间完成。比如1971年的北塞浦路斯撤侨行动,95架次飞行航班中,“贝尔法斯特”占了将近2/5。据粗略统计,第53中队人均每日留空时间为1.5小时,任何时候都有20人以上保持执勤状态,每年飞行总里程24万千米,相当于绕地球7圈!战略任务由国防部直接分派执行,首先确定轻重缓急,采用的是民航飞行标准(包括驾驶流程和导航手段),不过真的拿来飞民用航线,则又完全是另一套了。
原先还会有一周左右的勤务飞行,即经由阿克罗蒂里和冈岛(马尔代夫)飞往新加坡.但后来的航班基本限于欧洲境内,经停原联邦德国威登拉特、德奇莫曼努(萨丁岛)和马耳他,另外还有定期飞往伯利兹的航行。有时候会有临时远程任务,机组人员不会预先得到通知。当时第53中队可算是空军司令部的香饽饽,不少任务只有该中队才能承担。但这样的好日子并未持续多久,到了1975年3月,政府拿皇家空军的运输力量开刀,“彗星”“布列塔尼亚”和安多佛等型号纷纷退役。“贝尔法斯特”虽然没有立即撤装,但可以预见这一日子不会太远。

从后机身货舱门装运威塞克斯直升机
英国人急于从海外殖民地抽身是当时的大背景。皇家空军在1976年6月宣布进一步削减运输力量,第53中队将在9月份解散。皇家空军负责人威尔比洛夫(James Wellbeloved)力劝首相沃尔(Patrick Wall)裁撤“贝尔法斯特”,认为这样做从经济角度来说最合算,能省下不少开支,也不会对其他军事计划产生损害。但陆战队军官出身的沃尔表示怀疑,对于这根皇家空军的特种搬运工独苗,他有点舍不得下手。毕竟SC.5是当前皇家空军唯一能运送自行火炮和轻型坦克的运输机,可藉此向北翼快速投送两栖力量,就这么退了实在有些可惜,也必将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没有了SC.5皇家空军大型运输机仅剩下VC-10和C-130,威塞克斯和“美洲豹”直升机可以拆散了运,但现有的“大力神”机群无法一次性运走,有些直升机只能自己飞往战区。
可是在裁减空军力量方面即便是首相也无力回天,第53中队还是在9月14日正式宣告解散,5天后完成了最后一次跨大西洋飞行,然后将所有在原联邦德国居特斯洛的设备运回英国。9架飞机集中在了肯布尔,而只有XR 366号(绰号“阿特拉斯”)留在布莱兹打算吸引潜在客户,其最后一次军用任务就是向空军瓦雷基地运送一套全新的“鹰”式教练机模拟器。截止到此机群总飞行时数达到82000小时,总航程为3703万千米。这一数字也决定了它们今后还能发挥多大的余热。转售军用客户的概率微乎其微,因为目标市场基本已经被瓜分殆尽,而且对于这样运力级别的飞机,一般中小国家没有特别需求。
新的上岗证不好拿
幸运的是,这些飞机并未闲置多久。到了1977年2月传出消息:美国泛非航空工业旗下的泛非空运公司(总部位于华盛顿)已出资将其全部买下,用于西非低成本货运网络。SC.5的新任务是运送西非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所用物资,还包括出口国外的蔬菜和水果,但航程一般都不太长。拥有这批大型涡桨运输机使得泛非空运跻身于世界航空货运公司前列,新招募的人员中相当一部分原来曾在皇家空军服役。这批飞机的售价一直没有对外透露,一种说法是单价100万美元,还有报道说每架光是保险费就得200万。不过后来才知道,实际上是过了个手,为泛非空运下属的伦敦办事处也就是欧洲-拉丁商业公司(以下简称欧拉)采购的,泛非空运自身缺乏足够资金。
这批飞机计划日常停驻曼斯顿(位于肯特郡),最终将会带有利比里亚注册号,计划两架编一组,分别用于南美、非洲、远东和欧洲等境外航线。公司储备了大量零备件,包括30台泰因发动机.英国本地的因维克塔国际公司开始着手将座舱更改为3人驾驶,同时还计划对航电系统进行升级,人员培训将从1977年10月开始。谁也没有想到,此时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跨零经空中货运(简称TAC)早就盯上了这批重型飞机,但在竞价环节却败了下来。其实他们收购这批飞机不是为了继续运营,而是为了拆卸上边的发动机用于CL-44飞机维持飞行。在与欧拉的谈判中,TAC副总经理麦克哥德瑞克提醒对方,这些飞机没有民航资质,无法在那些非洲和拉美国家展开商业运营。于是,产生了戏剧性的一幕:欧拉公司和TAC控股公司之一丘纳德合资组建了一个新的TAC-重运公司来开拓海外民用运输市场。
重运公司暂时拥有5架飞机,其中两架就是欧拉提供的SC.5。不过最紧要的问题是拥有独立的飞行资质,这是麦克哥德瑞克比较担心的。后来果不其然,母公司(英国货运航空)在1980年3月倒闭,重运公司要想继续使用“贝尔法斯特”,必须获得自身的民航运营资质,而且必须是正轨的英国国内执照,不能是那种国外的‘廉价野鸡证书’。不过正如前文所提到的,SC.5的失速性能不佳是导致其不受民航市场欢迎的重要因素。麦克哥德瑞克研究后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肖特公司没有从一开始就为其装上推杆,否则早就在航空市场大卖了。可是改造推杆代价不菲,同时代的波音727-100曾被要求改造推杆,算下来每架得花费100万,逼得航空公司最后游说国会取消了这条规定。
好在肖特公司曾经专门为该机开发过自动着陆系统和先进的三余度自动驾驶仪,能够适应任何天气条件。麦克哥德瑞克想到,如果将自动驾驶仪的一条通道拉过来作为推杆,应该就能满足认证要求,至少能解决失速问题。肖特公司答应帮忙,认证机构也承诺加快资质审核,也就是从以前未通过的部分开始,否则推倒重来将耗费大量时间。丘纳德和欧拉的谈判就此顺风顺水,资金也很快到位。可是这时候肖特公司突然变卦了,说到底就是要重运公司出钱买下飞机的所有专利权,然后自行动手改造。TAC有点不信邪,一样花钱买几架民版“大力神”(L-100)不更好。可这么一来还得重新走英国飞行认证的流程,算下来花费更多。洛克希德同意降价,但要求采购量翻倍,那还是算了吧!

曾经一袭白衣的XR 365号
认证过程从1979年7月开始,剑桥马歇尔斯公司提供了技术支持,也就是进行整体设计和必要的改装,由索森德的一个特别小组负责这项工作。试飞对应的是B级认证项目,两架飞机一共要经过120小时的试飞,基本是由马歇尔斯的试飞员道格拉斯·佩吉和鲍勃·雷诺兹驾驶。另外,重运公司的首席飞行工程师巴里·法内和马歇尔斯项目工程师麦克·米尔内也在飞机上。尽管TAC一再强调飞机的失速性能很“柔和”,而且空军已经解决了失速问题,只要增加一个音响警告就足够了。但民航管理部门不理这茬,仍然坚持要求必须装推杆。胳膊拗不过大腿,装就装吧,时间不晚于1981年1月,型号选的是史密斯工业公司的产品,这算是民航管理局和TAC相互妥协的结果。
飞机根据A类特殊C条款投入运营,满足3类仪表降落系统要求。尽管允许3人驾驶,但机上将增加1名成员,专门负责在关键阶段进行速度监测。军标的改变并不很多,只不过导航和通信器材都换成了民用设备。原先气象雷达显示器只有驾驶舱右侧一个,现在多了一个备份。同时还需要增加飞行数据和驾驶舱声音记录仪,史密斯Mk 29自动驾驶仪从三余度降低到单套。“游吟诗人走廊”和前方货舱的上层板可以容纳19名操作人员和乘客,可根据需要拆去,进入到认证阶段则被强令拆除。收到可以升空许可的当天,TAC就迫不及待地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向媒体展示公司手里的“新飞机”。
特种搬运生涯
飞机交付的时候都带着空军的标识,第一架投入运营挣钱的是“爸爸E”(1980年3月),之后是“爸爸S”。重运公司总共改造了5架,同时保持出航最多3架。还有两架飞机归罗罗所有(泰因发动机当时是稀罕货),实际上用来作为零备件来源,买来一直存放在索森德,那里也是唯一能够起降该机的地方。日常维修则转包给了英国航空转运公司(BAF),后者使用的是原先改造过卡维尔(Carvair)特种运输机的机库。不过对于“贝尔法斯特”这样的“巨人”,还是显得有点小,只能把机头抬起压下垂尾才能通过机库大门,翼展也超过了支架的宽度,所以首先需要后移再前移。后来干脆把门拆去一块,总之为了把飞机塞进机库花了整整一天。人员培训倒是相对简单,因为多数以前就是第53中队的成员,发动机可靠性一度受到质疑,但运行了一段时间,还是比较理想的,即便发生空中单发停车,仍旧可以靠着其余3台返回基地。

ATL 98卡维尔特种运输机
按照重运公司的习惯,每次出航路上所带的补给品,都是在当地超市采购,机长说了算,没什么挑挑拣拣的余地。当然,做菜还得看厨师的本事。飞机上没有专职的大师傅,一般都是装卸长代劳。曾经在重运公司驾驶“贝尔法斯特”并担任过调度员的资深飞行员特里·托泽尔对于该机充满了留恋,认为这是自己的飞行生涯中最独特、最值得回忆的一段经历。飞机并不比美国的C-130逊色,而且装载量更大。但与此同时,托泽尔对于该机也给出了与先前皇家空军和航空与武器研究中心完全不同的评价,这从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时代标准的进步造成的。托泽尔在重运公司毕竟只待了一年,对于这种20世纪60年代产品的看法难免有失偏颇。
在托泽尔看来,飞机过于笨重,而且动力不足,系统复杂却效率低下,和当时许多英国自行设计的飞机一样,根本无视人机工程学。尤其是乍看黑科技爆棚的座舱仪表,实际上凑近了看无非是用螺栓拧到一块儿的一摞摞盒子,就和“即拆即用的灯泡没什么区别”。驾驶舱天花板就和老式拖车的上的纸板箱差不多。飞机的起飞性能在托泽尔看来也很糟糕,当初如何满足皇家空军要求简直不可思议,甚至莫名其妙会有发动机熄火的感觉。最让他感到绝望是飞机的爬升率,根本就是灾难,飞越大西洋的旅途中只能维持在3100米高度左右,再高怎么也上不去。
驾驶过SC.5的“老司机们”都能说出一大堆“千奇百怪”的飞行经历。但在托泽尔看来,不过是因为没碰上真正的严重事故,刻意编排出来的所谓“奇遇”而已。发动机故障并不少见。碰上坏天气而偏偏预报有误,比如把逆风报成顺风,有时候飞机即将抵达某机场才发现那里浓雾弥漫。起落架放到一半放不下来也很要命,应急系统都不管用。有一次飞行,为了充分利用机内空间,起落架整流罩那里堆满了汽车发动机。偏偏这次就遇上了起落架放不下来的故障。空中机械师只能在忙乱中打开地板口盖,找到连着上位锁的管线将其拔出。这时候空管雷达却指示飞机飞往盖特维克机场,于是刚刚放下的起落架干脆也不收起就风风火火赶了过去,结果勉强在那里落地。

夜间特种装运作业
焕发新生的“贝尔法斯特”还曾在1985年巴黎航展上高调亮相,这在当时可以说是特别照顾。因为巴黎航展是比较典型的商业航展,一般不接受早已停产的飞机占用展示空间。不过重运公司需要依靠这种老飞机来自我宣传,客舱内的“游吟诗人走廊”正好派上用场。公司人员就在这里摆上餐桌用餐,还招呼观众上机品尝美食。不过,光靠复古风显然无法带来实实在在的主顾。公司销售代表文茨·西格尔为了打开市场四处联系,忙得脚不沾地,不放过任何一丝商业推广机会。机尾有大面积货舱门,可以运送诸如发电机组、钻探设备、飞机机身等非常规尺寸物件。虽说运送超大件物资不是什么全新概念,也并不是SC.5的独家专长,但是在同等能力之下,还得比价格,比运行成本,比出勤率和可靠性。
不少公司认识到,一些大尺寸物件的空运反而要比海运更便宜更安全。用SC.5运送某些大型物件可以省下不少特殊包装成本和保险开支,不用担心港口拥挤的情况,周期也可大大缩短。这些正是重运公司着力强调的优点。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1981年3月总算是获得了一次宝贵的机会——将第一套意大利航空公司生产的波音767尾翼组件,从那不勒斯运至西雅图。波音公司看中的是SC.5可以从尾舱门装卸,货舱地板较低,同时又不需要专门的装运设备,这些都使其成为最佳选择。就运载特种物资而言,重运公司可以说是欧洲第一个吃螃蟹的。可惜直到今天,依然有人对公司花费巨资成立这么一支老爷机队的做法颇有微词,只是当初的负责人麦克格德里克却对自己的决定充满自豪。
按照公司高层的设想,理想的飞机利用率是每月150飞行小时。当然,空运市场也有旺季淡季之分,有些时候闲置是不可避免的,效益也一直不算太高。不过总体来说飞机还是得的了充分利用。大规格的特种运输,包括将重达20吨的煤气厂部件从慕尼黑拉到沙特达兰,这据说是当时民用飞机运过的最重的单件物资;而货物清单中最常出现的是整架直升机,比如把“海王”运到印度,还有一次性将3架“旋风”送到尼日利亚;大部分Bae 146的机翼,也是该机从纳什维尔运到英国的(通常需要占用6~8周的时间)。这曾是机队最忙的一段时间。
除了民营企业,实际上英国国防部也是重运公司的重要客户。不过公司拒绝被军方“长期包养”,只答应签订短租合同。但是运送军火是有一定风险的,比如某次一口气运了35吨的鱼雷,结果发动机起火,如果没有成功控制住火势,后果难以设想。很多读者可能都并不清楚,1982年南大西洋局势日趋紧张之际(指英阿马岛战争——编者注),SC.5也被用作向该地区紧急调运重要物资,目的地是阿森松岛。起初是3架轮班倒,后来减少为每周1架专飞。这种合作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当然之后也没闲着,因为随之而来的海湾战争又让英国国内的航运公司有的忙了,只不过很少有人注意到SC.5的存在。苏联解体之后,西方市场上出现了大批廉价的“空中搬运工”。伊尔-76虽然不见得能够运送超大尺寸部件,但载重量更占优势。好在“贝尔法斯特”也确实该彻底退休了,尽管重运公司的零备件还很充足,但这些也都是七拼八凑的结果。

肖特兄弟公司不仅设计过“贝尔法斯特”这样的巨无霸,图中左上角笨拙可爱的SC.7“夏尔巴”人也是他们的杰作

皇家空军最后1架贝尔法斯特

在重运公司服役的G-HLFT号,此时编号为9L-LDQ
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商人尼克·利奇在2003年买下了G-HLFT号及其零备件(来自2001年3月退役的“西尔雷爸爸”号),并就此成立了重运货物公司(Heavylift)。这架飞机挂籍塞拉利昂,编号为9L-LDQ,后来又转入菲律宾籍RP-C8020。运营状况还算令人满意,包租的客户不只是澳大利亚国防部,在2005年东南亚海啸救援中它还曾被用作救灾物资投送。但从2010年后该机基本就很少活动,一直停在位于昆士兰州d凯恩斯机场无所事事,报价98万美元打算卖掉也无人接盘。G-BEPS(XR 368“提休斯”)号在2008年10月报废拆毁,G-HLFT(XR 365“赫克托”)后来倒是还在飞,不过近况不详。位于考斯福德的皇家空军博物馆收藏了唯一一架较为完整的“贝尔法斯特”,也就是最后出厂的XR 371“恩克拉多斯”号,设置在国家冷战厅。它是1967年6月首飞后不久便交付第53中队的,积累了9229飞行小时后于1978年卖给罗罗公司,之后不久便进了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