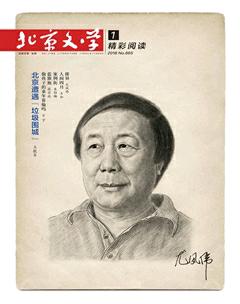去颍西湖
苗秀侠
冬日的颍西湖,水波安宁,麦田碧青。通往陵园的柏油路面上,排满了大小车辆,给平日阒静的陵园,带来一些热闹。陵园门口一排商店,摆放着大同小异的祭品,男男女女走进去,买黄表纸、金元宝、大盘鞭炮,脸上表情肃穆。有打闹嬉戏的孩子,跟在大人身后跳跃。
随着祭奠的人群,进到陵园,走上那条红砖甬道。甬道两边的小柏,在岁月高举着的尖锐年轮里,旺旺地成长着,尽管它们是离生死最近的植物,却有着昂扬的姿势。只有红砖甬道,消瘦如昨,仿佛承载太多泪水的浸染,不愿意长大。那些祭奠时飘飞的炮灰纸屑,把甬道的砖缝,填塞得满满实实。
西8区5排3号,女儿的家址。西8区在陵园的最西侧,一条小沟之外,便是无际的田野。女儿萱萱刚在这里安家时,西8区尚显荒芜,绝大部分墓穴都空在那里。如今的西8区,已是满满当当。
扫干净萱萱墓碑前的落叶、灰尘和纸屑,打开那捆纸,划亮火柴。柔软的黄表纸,金色的元宝,在火光里打着滚。已经成年的萱萱,站火光背后,微微笑着。熔化成蝶的纸屑,漫天飞舞。
一切皆缘于一个爱情。这个爱情,在18岁的春季,滴落在贫瘠的皖北平原上。那个在江南齐山脚下读书的少年,用三年时间,一天两封信、两天一封信,生生把一千多个日子,织成爱情的十字绣。这个给我爱的男人,让我对人生没有第二种选择。便离开故乡,随他到江边而居。
居处不远,有条叫幸福的河。汛期的幸福河,宽宽亮亮的水面,走着机帆船和手摇小民船。早春枯水期,河床高的地方,便露出鲜黄的河底,骀荡的春风,把河底吹起一层翘翘的泥瓦瓦。河两岸的居民,再不用花费三五毛的船费,迈开大脚板,嘎吱有声蹚着河底的泥瓦瓦,走亲戚串朋友。也喜欢去早春的河底,踩着泥瓦瓦走,两人的脚步,一轻一重。重的脚是我,女儿萱萱已经七个多月,安静地住在我的身体里。
五月五日,阳光明媚,大地芬芳,女儿萱萱呱呱坠地。她来到尘世,带来欢乐和喜庆。因为这一天是立夏,升格为父亲的他,为女儿取名夏萱。
居所是一所中学,建在一个叫罗山头的山坡上,离镇六华里,四周被稻田圩堰和野湖所围。这所傲世而独立的学校,四季美景流转,足以喂饱贫瘠的身心。从此的日月里,散步的堤坝上,是三人的影像。有个小人儿,或被我的膝所托,或在他的臂弯里依偎,她咯咯笑着,清澈的眼眸,装着远山远水远逝的船帆,装着满坡满坝的青草和蝶飞。三人的日子,被江边野荷的香气熏染得芬芳四溢,被围堰稻谷焦熟的气浪裹挟得醉意朦胧,被放鸭人粗朴的山歌拉拽得忘了今夕何夕。萱萱会坐了,萱萱会站了,萱萱长牙齿了。萱萱跟我们嬉闹时,嘴巴里无意识发出的笑声呼声里,突然多了一个“爸”字。
“爸爸爸,爸爸爸”,她手舞足蹈的嬉戲里,她摇晃小铃铛,抓着小风车的显摆里,她的不满和抗议里,“爸爸爸”是她用来表达的唯一方式。做爸爸的好生得意,八个月的女儿,先喊他爸爸了。
元月三日的夜晚,罗山头被北风狂拍了半夜,薄弱的土墙壁后面,几排站立着的老沙松,水牛般的低吼声,几乎穿壁而来。蓦地,一阵犀利的呼哨声,猛然把我拽醒。慌忙拉亮灯,第一眼要看的是萱萱。她小手从被窝里挣出,握成小拳,双目圆睁,鼻翼夸张抽搐着,一声紧连一声窒息般的呼哨,正从她嘴巴里汹涌而出。怎么了?怎么了?两人大声互问,他猛然揽过小摇床里的被子,连同萱萱一起,裹进怀里,朝门外冲去。我紧随其后。劈头盖脸的冬风,利如刀剑,裹挟着罗山头四周的黑暗,横贯而来。几乎没得商量地,一起奔赴一座村庄。穿行在岗地、松林和坟山之间,忘却脚下的磕绊,对坟山松岗没一丝惧怕。四五里的路程,我们走得像飞人。惊慌地拍击着小诊所的木门,村医半披着大衣,于睡眼惺忪中,给不断抽搐的萱萱,打了一针镇静剂。
萱萱即刻安静了下来。我们的胸腔里,长长呼出一口气。看着女儿熟睡的样子,以为是上苍给我们开了个玩笑,让我们体味夜半狂奔的艰辛,尝透初为人父母的责任。
村医谨慎地给萱萱量烧,陪我们说话,分析病情。天光渐亮,看着沉睡不醒小脸烧得通红的萱萱,村医催促:赶紧送往县医院,在他这里,已经束手无策。
我们的心,再次陷入冰窖之中。
孩子爷爷连忙喊来村子里的至亲,绑了一只竹晾床,把萱萱裹在棉被里,放竹床上抬着,朝县医院飞奔而去。
苍茫的丘陵原野,枯瘦的棉花秆,遒劲的芭茅草,遍地无助的油菜苗,一座连一座的松岗,再无诗意可言。我望着天的尽头,那里长着一座小山,小山给天空画了一个粗硬的轮廓。没有一滴泪,任凭凉风吹透全身。那时,我觉得自己是走在梦境里。
只愿梦醒时分,这一切都是假的。
抽血、做检查、吊水,萱萱顺利住上县医院。诊断结果也出来了:病毒性脑膜炎。
入院的第二天早上,萱萱从昏睡中醒转了过来。两人悬着的心,扑通放下;堵着的泪,瞬间泉涌而出。萱萱睁大那双明亮的眼睛,轮流看围着她的父母,不知道发生过什么。仿佛走了几天几夜的路程,仿佛从战场上归来,她疲倦地递过来一个歉意的笑。
那个倦倦的笑,从此装进我生命存在的每一时、每一刻、每一天、每一年,直至今朝。那是萱萱作为一个健康孩子留给我的最后礼物。
萱萱再次昏迷、抽搐。医生开始抢救。吊甘露醇,吊消炎药水,抽检脊液。四人间的病房,住着三个人。一个老人,胸膜炎,每天从胸口抽出几大针筒积液,他捂着胸,沉默地坐着,脸色灰青,一言不发。一个中年妇女,来治关节炎,侍候她的男人,摔东骂西,女人时有哭泣,男人便骂得更凶。萱萱的床位靠最里,南窗下,天光足,然而,天光、灯光照在病房里,却全无生机。低头看着萱萱一刻不停抽搐的嘴角、鼻翼,再望一眼窗外苍黄的天,内心的疼痛,刀片般飞舞。
病房空出的床位,在门边,很快被一位新病人住上。是个眉清目秀的年轻男子,却比一般人瘦削、苍白。一群人浩浩荡荡陪同而来,最后一名女子留下相陪。男子病情也很快知道个大概。白血病,晚期。辗转上海、合肥救治,如今再回县医院。女子是他新婚妻子,温柔、美丽,坐病床边,给男子喂食稀粥和果汁。夜晚,女子倚靠床头,把男子手握在掌中抚摩,温言软语,絮絮不休。夜晚的病房,被两人窃窃私语的恩爱充盈,竟少了些许悲痛。那个嘴巴不停骂人的中年男,息了声,连走路也轻了许多。
不过三四日,白血病男子陷入昏迷,滴水难进,鼻子出血不止。女子握着一团团纸巾,帮他擦鼻血,轻声啜泣。男子成了纸片人,卧在女子怀里,薄脆得随时都会碎掉。女子紧搂着他,附他耳边喃喃絮语,然而,一个人的热力,哪怕是痴情的爱,已不能让另一个人起死回生。轰然炸开的哭声,在夜半的病房里响起,送男子入院的那群人,风一般地再次拥来,又风一般而去。
那张空着的病床,陡然变得委顿而哀伤。
第一次近距离经历生死,人呆了半晌。再低眉看昏睡不醒的萱萱,一种巨大的哀痛袭来。女儿,你真要长睡不醒吗?
医生劝转到市立医院,那里有专业的儿科,治疗更专业。
住进市立医院时,已进入腊月天。第一场雪花飘扬而下,天地间白茫茫一片。市里的医院比县里好太多,有专门的儿科诊室和病房。我一直陪萱萱住抢救室。那只高高的抢救台,一头睡着萱萱,一头蜷缩着我,半个多月,和衣而眠,就那样挺过来了。
八个多月的萱萱,多日不进食,已经瘦成了小猫。她鼻子里插着输氧管和鼻饲管,医生送一支粗针管给我,一日三次,我把温热的牛奶,通过鼻饲管,喂养萱萱。但愿这些营养给她增强能量,让她一个翻身,突然醒转过来,递给我一个倦倦的笑。但每夜医生巡诊时,总叮嘱我:今晚危险,注意!
又飘来一场雪。四楼的抢救室,玻璃窗很大,雪花在窗外旋转着,铺天盖地,茫茫无边。我突然想到,萱萱还没见识过雪花呢,等她好了,一定告诉她雪花飘舞的样子,雪花融化的样子……
渐近年关了。医生找谈话。出院吧,别让孩子再受罪了,也要过年了。尽管见惯了生死,医生的脸色和声音依旧温和,充满怜悯。
把萱萱包在小被子里,坐上回家的民船。小民船一路西行时,天空落起了雨夹雪。江面苍黄一片,江心洲残存的芦苇花,在风雨里摇荡,一江的水,都发出呜咽之声。
萱萱人生的第一个春节,在千家万户的喜乐里到来了。年炮在窗外炸响,而萱萱,她依旧沉睡不醒。微弱的呼吸,毫无知觉的身体,使她像一只做蛹的蚕茧。跪在床边,手抚着她软软的发丝,万般无奈中,轻轻呼唤着她名字,用小匙蘸着牛奶,一点点润到她双唇间。热乎乎的牛奶,带着生命的热力,带着初为人父母的决绝和执拗,一星点、一毫毫,穿越紧闭的齿缝,渗透到她的肚腹里,她天远地远的长睡里。
苍天眷顾我们!三个月后,萱萱终于睁开了眼睛!
四肢依旧沉睡,嘴巴无动于衷,只有那双眼睛,传递着茫然和无助。手举在她眼睛边,甚至触摸到眼皮和睫毛,眼波还是静止的。
她的眼睛没有光感,没有视力!
她的牙齿仍紧紧咬着。
要让她好起来,腿脚动起来,眼波流转起来,声音叫出爸爸爸!再一次为萱萱求医找方。
县城里有家头针医院,治好了不少脑炎后遗症的孩子,便抱着萱萱,住了进去。医生给萱萱做了全面检查,听力、视力、肢体的敏感度……“植物人”三个字,第一次撞击脑门。
小病友们的治疗效果非常明显,而扎在萱萱头上的银针,仿佛柔弱的草,毫无用处。一月时光倥偬而过,无奈地回到罗山头。夏荷在四周的野塘里开放。望着天边被小山画出的轮廓,想,天恩之下,人间就没有出路吗?我不要太多,我只要萱萱能走路,会吃饭,哪怕她傻,哪怕她痴……
萱萱3岁了,萱萱4岁了,萱萱5岁了……
仿佛一千年一万年的等待,我看见流动的白云彩,在萱萱的眼睛里飘动起来;我听见四季的花朵,开放在她的嘴角;我听见了猫一样的叫声,从她唇边冲出……她终于张开了嘴巴,虽说吞咽能力有限,但她能在汤匙的触碰中,主动张开嘴巴接食;她的眼睛,可以跟着我手指的晃动而转动,虽然焦距不准,甚至会跑偏,但证明她有视力了;而她的面容,也有了笑模样……我们的女儿,终于回到了我们身边,和我们相依为命!
因为营养跟不上,萱萱瘦弱而多病,高烧成肺炎,几乎隔不久就来一次,每一次,萱萱都处于危险边缘。看医生,吊水,四处奔波……家里的老人,熟识的医生和朋友,不止一次劝我们放下这个孩子,别让她再受人间的罪。每当有这样的话说出,我们便决绝而蠢钝地抱紧萱萱:不,我们一定要治好她!这时候的“治好”,就是要她不再发烧,要她慢慢地吞咽牛奶,要她的眼睛再一次跟着我的指头转动!我已经不指望她一丁点的回报,不指望在衰朽之年看到她的风华正茂,我只要她躺在我的臂弯里,偶然给我一个傻笑,听我的絮絮叨叨……
费尽周折,终于回到我的故乡,那座皖北小城。虽说在城市里蜗居条件窘迫,但救治萱萱的条件,已经好了许多。
冬天的时候,9岁的萱萱又一次病倒。高烧不退,吊水多日无果。那段时间雨多,每日都叫来人力三轮,在门口接我们去医院。把女儿裹在被子里,听着雨滴叮叮当当敲打三轮车的雨篷,看着街上行人匆忙的脚步,猛然会想到在罗山头,女儿初病时我们的狂奔和哭泣。而如果当初不是在罗山头,是在这座城市里,萱萱会成为现在的萱萱吗?
一个冬天的奔波和救治,家和医院,连成一线。这一次,萱萱的离去那么决绝。她最后留给世上的,只是弱弱的一声哭啼……
阳历年刚刚开始的日子。皖北的冬风,把大地吹得面黄肌瘦,一片萧索。友人陪同著,一起去了殡仪馆。布娃娃、鲜花、一只小小的睡袋,随同萱萱一起,化作一缕青烟,升入高远的蓝天……萱萱睡在小小的木盒里,枕着颍西湖水波的轻漾,开始她另一个世界的时光。从此,那个未知的世界,不再陌生和寒冷,因为,女儿在那边。
而死别和生离,却是双胞胎,它们相依相随,并肩而行。
扫去墓碑上的尘埃,那两行淡漠的字,清晰起来:
九岁生命九死一生怀中日月
八苦世界八载沉疴纸上云烟
字下面是两个并排着的名字。
我们在,你便在;我们活,你便活;你是我们的生命。可是,女儿,你走了,那两个给你生命的人,不久,也走散了。
曾经,我是那么相信爱情永恒的神话,当爱情发生时,我蠢钝地抛却一切,相随而去;当爱女因病成痴时,我又蠢钝地四处呼救,相信奇迹发生;而当爱情发生背离时,我却没有拿出蠢钝的执拗,牢牢抓住。我放手了。因为我的身,已经创伤累累,没有一处可下刀的地方;我的心,也倦到抽不出一丝力气,去为一场无望的爱拼守。那就把爱送到这样的路口,随它去吧。萱萱,我错了吗?在我放爱一条生路时,我给自己一条生路了吗?
我只是把大把的眼泪,攥成坚硬的干冰模样,抛洒在来来回回颍西湖的行走里,让路途变得清洁,让现世回归到当年的明朗。
责任编辑 师力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