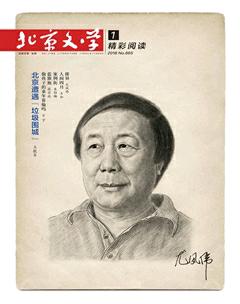他已梦回大唐
吴光辉
一
在我看来,九百年前沿着长江顺流而下的那艘白色小舟,完全就是米芾营造一种梦的意境,它在北宋王朝灰暗色的背景衬托下,显现出些许夸张和变形。这时的江水变得墨黑色的寒冷,天空也如同被泼墨渲染成了阴霾,几只乌鸦像是运动着发出嘶喊的黑点,而长江两岸的村庄全都淹没在水墨般的阴雨之中。那条小舟便扯起了白帆,在这样的长江黑水之上游走。
那条小舟就是米芾创作的一个梦中形象,全身都是白色,白帆白篷白幡白船身,再加上船篷里挂满了白宣书画。那竿随着秋风瑟瑟飘飞的白幡上面,还写着五个斗大的狂草:“米家书画船”。而船舱里端坐着的米芾居然戴了一顶大红高檐帽,穿了一件白色长布袍,像个巫师一般,合掌闭目打禅,全家老小也都不敢吱出声来。
我在想,这条墨黑色的长江肯定就是历史,这只惨白色的小舟肯定就是人生,那顶大红朱砂色高檐帽就是性格,围绕船桅四处盘旋墨点似的乌鸦肯定就是谶言了。它们在一起便组合成一个由水墨渲染的梦境。
米芾确是一个作秀高手,在书画创作和政务活动两个方面,同时将显摆夸张到了极致,将宣传放大到了极致,从而成就了米芾在中国文艺史上书画狂人的形象,“米颠”也就成为他的外号而风行大宋王朝,流传中华书画史。他就是带着这个外号,乘着那艘白色小舟,戴着那顶大红高檐帽,疯疯癫癫地走向他的生命终点。
变形、扭曲、夸张,成为米芾的癫狂个性,也成为他书法艺术的特征。书法是他作秀的一种形式,书法是他发泄的一种表达,书法也是他癫狂的一种载体。狂放开合的书法特色,是一个时代的艺术表达,更是一个知识分子在备受压抑之后的一次又一次情感畅快地吐槽发泄。
他的书法艺术成就之大,是那个时代的共识,甚至有人认为他的书法名列“宋四家”之首。也正是倚仗着这样的成就,他才有了癫狂的资历。他经常被皇帝请去写字,这又进一步增加了他癫狂的本钱。最后,他甚至发展到了在皇帝面前也无法掩饰癫狂本性的地步。因而,在这个时候再有人告他的状,写他的“人民来信”,他还能不倒霉吗?
早就耳闻米芾乖张行为的宋徽宗想看个究竟,便藏在帘后看米芾写字时的癫狂举止,米颠也已发现皇上的偷窥,就更加癫狂起来。只见他头戴红高帽,身系绿袍袖,在桌边跳来跳去,口中念念有词,手中运笔龙飞凤舞,一丁点儿没有收敛的意思,最后写到了高潮时竟然大呼小叫起来。这宋徽宗好在也是一位书法大家,并未怪罪他,反而哈哈大笑地走出了帘幕,和他探讨起 “本朝以书名世者” 的书法高下。这时的宋徽宗倒是不像当今许多领导干部,自己的官职高就觉得自己的水平也高。米颠便是利用最高领导的这种谦虚精神,立马将当时的书法大家全都点评了一通:“蔡襄勒字,沈辽排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当皇上又问他米芾的字写得如何时,他吹自己是“刷字”,居然情不自禁地自我表扬起来了。
一个“刷”字,是“用快笔写”,是在勒、排、描、画之上最为恣肆的挥扫,是八面出锋,挥洒自如,行笔如狂,犹如仙游天外。这一个“刷”字道出了米芾書法的癫狂本性来。我们从现存于湖北襄阳米公祠的米芾书法拓片、碑碣上,还能清晰地看到他当年的癫狂笔意。这些由清雍正年间,襄阳知府高茂选晋谒米家祠时,嘱米芾二十代孙米澍按墨迹摹写,后经广东名匠张源襄历经十八年刻成的碑刻,虽非米芾的笔墨真迹,却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米芾书法“锋出八面”“风樯阵马”的无比癫狂。
也正因为他这样无以复加的癫狂,使他在五十六岁这一年,被贬出京城乘着一条小舟,到边远的淮阳军上任去了。这个淮阳军,在今天的苏北邳州,当时属于边远荒蛮之地。米芾在大观元年六月,“迁礼部员外郎,未入拜而弹章其言,出身冗浊,冒玷兹选,无以训示四方,有旨罢,遂出知淮阳军。”也就是因为他的癫狂,皇上准备提拔重用他,可刚被考察公示,就被人举报,皇上只得将他贬出京城。可叹的是米芾在淮阳军任职半年之后,就病死在工作岗位上。
这时在小舟上,心灰意冷的米芾一杯浊酒狂饮而下,然后飞笔写道:“三峡江声流笔底,六朝帆影落樽前。忽忆赏心何处是? 春风秋月两茫然。”长江三峡的涛声从他的笔下飞泻,杯中六朝的帆影连同血泪一起饮下。此时此刻,他似乎已经预感到苏北就是自己的最后时光。
一笔书写是汗,一句吟诗是泪,一杯饮酒是血。
二
夸张、滑稽、嬉戏。米芾给我们又营造出一幅漫画式的历史画面。
他在公元1103年宋朝的那个灰暗色调的国度,国人早已习惯了简洁质朴的直领对襟,色彩暗淡、拘谨保守的背景下,给京城带来了一股惊艳和狂热。虽然他已经年过五旬,还是刚从外地调到汴京改任太常博士、书学博士的处级干部。只见他摇头摆尾、耀武扬威地穿上几百年前的古人艳丽服装,吆五喝六地行走在首都的大街上,迅速制造出街头巷尾无不议论的头条新闻来。
米芾本身是搞艺术的公众人物,穿着打扮十分另类,平时就喜欢奇装异服,戴个尖头红帽,穿个长袖垂地绿袍,看上去就像个漫画式怪物。这一天,他应同事之邀公款吃喝,更是标新立异一番,穿起了一套唐装。全身上下,色彩艳丽,夺目抢眼,在大宋街头灰暗色调的背景衬托之下,显得格外的醒目。
只见他身穿一件粉绿色宽袖长袍,长袍上朱缘领袖,上面还绣着他亲自设计的富贵红牡丹;内穿一条金边黄丝裤,下面是红袜赤屣,脚踏一双绣花高缦鞋,腰间还佩戴一副玉石双佩。当然,还是那顶高帽子最为抢眼,它是米芾将唐代的通天冠改造创新而来。这大红高帽原本就是唐朝文人雅士郊祀、朝贺、宴会时所戴的礼帽。所以,米芾每当重大活动全都将它戴上。
可是,他今天设计制作的红帽子,上面就像个锥形大烟囱,下部像个圆盘似的帽檐,戴在头上实在是太高了,足足有两尺多高,问题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戴着帽子坐进轿子。他又不肯让秘书拿着,生怕秘书弄脏了自己的高帽子,左思右想,最后竟然命令驾驶员拆去了轿顶,这才坐进轿子。那又高又尖又红的唐代通天帽从轿顶伸出,在大街上招摇过市。一路之上,人们争先恐后去一睹趣事,笑得路人前俯后仰。行到大酒店的门前,正好遇到老友晁以道,晁以道看见成群结队的人跟随而来看热闹,便忍俊不禁地笑道:“哈!米颠呀,你坐的车简直就像监车一般,你就像个示众的囚犯!”
峨冠博带,游走于市,引来无数市人围观,更加激起米芾的表现欲,一发洋洋得意,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居然在大酒店的门前即兴来了一段单口相声。从此,京城市民把米芾当成一个怪物看待,都以为他是个“神经病”。时间久了,汴京城里的男女老少,即使不认识他,也能从唐装上推断他就是米颠。
当然,米颠的红高帽还吸引了首都大批美眉的眼球。米颠是大艺术家,荷尔蒙的分泌想必比普通人旺盛得多,自然对于美女有着特别的兴趣。他的唐装自然也吸引了无数美眉的青睐。我推想米芾曾写过一首《满庭芳》,肯定就是借助品茶去记叙自己的艳遇,词中写的“美盼”“娇鬟”就是写一位芳名叫作朝云的美眉。估计是她见到风流倜傥的米才子,穿上唐装的飘逸潇洒而美目传情。这就引得米颠创作热情高涨,诗兴大作,“轻涛起,香生玉乳,雪溅紫瓯圆。娇鬟,宜美盼,双擎翠袖,稳步红莲”,自然是“频相顾,余欢未尽,欲去且留连”了。可见米芾勾引女人的手段十分高雅,比起当今某些党员干部对女部下霸王硬上弓要高明得多了。
当然,在我看来,米芾穿上唐装艳服,绝不仅仅是一个艺术家标新立异的外在表达,更不仅仅是为了招引美女少妇的青睐目光,而是他面对宋朝软弱无能的国家形象,产生对大唐盛世的一种精神向往,更是一种期望国家强盛“中国梦”的一种行为夸张,这似乎与当今年轻人喜欢穿上印有星条旗的T恤衫有着相似之处。
米芾出生成长在一个充满理想的地方,襄阳的水土培育了米芾理想主义的细胞。然而,他生活的时代让他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使他不得不生存于自己的梦想世界里,让自己穿上唐装,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做大唐公民的强国梦想。
米芾(1051~约1108),襄阳人,本名黻,后改为芾,字元章,自号“襄阳漫士”“鹿门居士”。他自幼聪慧好学,“六岁,日读律诗百首,过目即成诵”,“十岁,写碑刻……自成一家”。在他所作的《书戒》中,我们得知他少年时代便立下宏图大志,可见故乡襄阳是他确立人生理想的一处乐土。
襄阳因位于襄水之阳而得名。襄阳的历史名人对米芾产生过重大的影响,特别是修身济世平天下的诸葛亮。诸葛亮先就读于襄阳城内的学业堂,后躬耕于襄阳城西的古隆中,并与聚集在襄阳的众多文化精英广泛交游。二十七岁时受刘备“三顾”之请走出襄阳,为光复汉室立下汗马功劳。而隐居在襄阳东南鹿门山的孟浩然,则是用诗歌创造了一个令米芾向往的世外桃源式理想世界。
然而,襄阳给米芾营造的这种理想越是美好,与他十八岁离开襄阳后生活的时代越是产生巨大的反差。作为世界经济文化科技第一强国,却又屡战屡败的宋朝,怪事、奇事、变态之事、不可理喻之事,出人意料的多。让文人带兵打仗、不思收复失地、攘外必先安内、莫须有地冤杀忠臣、汉奸多如牛毛,以及女人裹小脚、宣扬“三从四德”,所有的这些都顺理成章地在宋朝发生了。而面对北方金人的不断挑衅,边境报警的狼烟频繁地升腾,整个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国家最高领袖宋徽宗居然能够一心去做文艺潮人,留起了长头发,蓄起了大胡子,带头穿起了奇装异服。在领导的带头下,米芾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思想顾虑了,放心大胆地做一把时装潮人。
当然,与最高领导不同的是,米芾穿上华丽唐装,戴上大红高帽,喜剧般地穿行于北宋王朝,完全是他悲剧情感的一种寄托。
三
“米芾拜石”其实是在煞有介事的癫狂表象之下,不与世俗为伍、纯真自由天性的一种自然流露。根据宋人蔡绦《铁围山丛谈》记叙,年轻时的米芾在新婚之夜,见到新娘子李氏的嫁妆中竟然有一件传家之宝“灵璧研山”,便喜出望外,疯癫之情又上来了,立马摘去红高帽,对着研山石纳头叩拜起来。
这块研台如同一座奇山,有“华盖峰、月严、方坛、翠峦、石洞”,使米芾觉得自己在前世就曾“神游于其间”,而此砚台又“龙池遇天欲雨则津润,滴水小许在池内经旬不竭”。米芾一见便爱不释手,忙问新娘子何得此宝。李氏便将自己是李煜后世之事告诉了米芾,又说这块砚石正是李煜曾用之物。米芾一听更是惊喜,顿觉这块砚石肯定就是李后主笔下描写的一江春水般多情的美人。断言这块美丽多情的研山石就是自己的前世情人了,便将美石揽在怀中,嘴里念念有词,像是与这位玉石美女在互诉衷肠。一直缠绵悱恻到了深夜,最后抱着这块砚石悄然入眠,一觉就睡了三天三夜,居然把新婚妻子丢在一边不闻不顾。
后来,晚年的米芾途经镇江甘露寺时,看到临江有一座省部级高官用贪污受贿的赃款购下的豪华别墅极为喜欢,便在此住下,而那块“灵璧研山”也深受这座豪宅主人的喜爱。高官宅主又托人撮合,在米芾酒后用“灵璧研山”换了这座豪宅。米芾醒酒之后,交易已成定局,便万分悔恨起来。特别是他搬进这座豪宅之后,常思他的“灵璧研山”,竟然到了饭不吃、茶不思的地步,思念到了月夜,更是泪流满面。“研山不复见,吟诗徒叹息。唯有玉蟾蜍,向余频泪滴。”他由此抱恨终生。也正是他思念这位“玉石美人”心切,米芾的著名书法代表作《研山铭》才因此一挥而就,并且流芳千古。
“五色水,浮昆仑,潭在顶,出黑云,挂龙怪,烁电痕,下震霆,泽厚坤,极变化,阖道门。”这幅《研山铭》用南唐澄心堂纸书写的行书大字,正是米芾对那块研山石的情感追念。今天,我们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看到这幅书作时,还能清晰地体会到,米芾痛失美石之后的那种悔恨交加,他将一块石头描写得如此沉顿雄快、跌宕多姿,確如苏东坡痛失爱妻时“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一般肝肠寸断了。
米芾和石头相知、相爱、相伴,他对奇石的鉴赏与理解,绝不是停留在表面的层次上,而且有许多与众不同的感悟。在他的《书异石帖》里,就总结出了相石四字法则,认为“瘦、秀、皱、透”是石头的选美标准;还认为万物有灵,石头也不例外。所以,他常以石寄情,以石励志。他甚至把自己喜欢的石头分出雌雄,放在玲珑剔透的水缸里供养起来,认定这石男石女放在一起交欢,肯定会生出漂亮无比的石子石孙来。
当然,我觉得米芾之所以爱石如命,其根本原因还是他的纯真天性使然。个性张扬,崇尚天真,是米芾“自我”意识的一种表现,与政府机关通行的低调、谦逊之风恰好相反。因此,他的生性率真,行为乖张,言行举止有异常人,得了一个“米颠”的外号也就不足为奇了。说到底“米芾拜石”这样癫狂的作秀,其本质一半是对世俗的抗争,一半是想引起世俗的关注。
正是这种癫狂造就了一个新锐艺术家的米芾,而不是一个平庸官员的米芾;也正是米芾的这种崇尚纯真的天性,促使他天真自然之书风的形成。他在诗中写道:“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这句诗表达了米芾在书法创作时一任感情流淌、不受丝毫世俗束缚的心态。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他书画的巨大成就,使之与蔡襄、苏轼、黄庭坚合称为“宋四家”。
当然,米芾的崇尚纯真,成就了他的书法,却影响了他的仕途。米芾在无为做官时,听说城边河中有一块怪石,当地人们迷信地认为是神仙之石,不能轻举妄动,生怕招来不测之祸。可米芾哪管得了这些,命部下将怪石从水中打捞上岸,然后又沐浴更衣,戴上高帽,出门恭迎。怪石移至政府大院内,又抬上方桌,摆好供品,燃起香火。他便躬身下拜,口中念念有词:“兄长呀,兄长,您好吗?我想见你已经整整二十年了!”其激动之意,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上次是得到一块研山,他视如前世情人;此次是得到一块怪石,他视如今世兄长。就这样,米芾拜石之事被传了出去,有人说他是有失政府体面,米芾因此被人多次来信弹劾告状,真的给他招来一场不大不小的灾祸,最终他就是因为癫狂而被人举报,被贬到苏北地区并且客死他乡。
四
如果说米芾五十七年组成的癫狂人生是大宋王朝的一个象征,那么米芾的洁癖就是那个时代一个含义深远的寓言了。
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皇家宗庙的春秋祭祀大典开幕式开始了。祭坛上高悬起皇家宗祠专用的横批对联,供桌边围上龙凤绣裙,所有祭品也都安放妥当,全猪全羊上架,糖果馔盒、饭羹茶酒等各种祭品全部置于供桌之上。前来出席祭祀大典的皇上皇后、皇亲贵族、满朝文武,全都衣冠整齐、恭恭敬敬地跪倒在地。总司仪宣布开幕式启动,随即鼓乐喧天,唢呐高奏,鞭炮齐鸣,震天撼地,呈现一派热火朝天的动人景象。
也就在主祭宣布开始祭拜的时候,有几个同事向领导打了个小报告,说米芾出席这样神圣的开幕式居然衣冠不整,这是犯了大不敬之罪。皇上听说后抬眼望去,站在干部队伍里的米芾果然穿了一身旧白长袍,居然还戴着那顶大红高帽,在一片灰暗色的干部队伍里显得十分刺眼,立马气得胡子翘得老高。
原来这一年,五十三岁的米芾被招进京任太常博士,就任皇家春秋祭祀大典筹委会成员。而主祭者都有统一的礼服,米芾不穿不行,但他又嫌前任穿过太脏,就将礼服拼命地洗,结果将衣服上的花纹洗掉了,变得又白又旧,因而受到了同事们的联名举报。最后,米芾因此受到撤职查办的行政处分,被赶出了朝廷。
米芾确实有着一种异乎寻常的洁癖,他一天要洗手数次,但又从来不用脸盆,而是特意制作了一把银制的长嘴水壶,让人站在高处往下倒水,自己就着水流洗手。洗好后,也不用毛巾擦拭,嫌毛巾里藏有细菌,干脆用两手互相拍打,一直到手干了为止。不仅如此,米芾的洁癖表现到了极致,朝靴被别人碰了一下便觉得十分恶心,就一遍又一遍地清洗,直到洗破了不能再穿;平时对室内进行反复打扫,器皿反复擦洗,客人坐过的凳子更是要用水反复冲洗。甚而至于在选女婿时,竟然首先考虑的因素也是清洁卫生,因为有个候选人的名字叫“去尘”,便一眼看中将宝贝闺女许配给了他。
我觉得米芾的洁癖是他在故意给自己创造一种清洁如玉的公众形象,与当时机关干部的贪墨腐败正好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而米芾肯定是在有意识地夸大这种对比。我甚至可以说米芾的洁癖,其实就是对机关腐败的一种刻意反叛,简直就是清正廉洁的一种象征。米芾曾在苏北涟水县政府任职,离任告别涟水时,行至半道又转了回来,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他从囊中掏出一捆笔来,一一在池中洗净,并且对大家说:“为官当思地方,笔中之墨乃涟水之物,我不能带走涟水的一草一木。”很明显他的行为已经不仅仅是洁癖了,而是想为自己留下一世的清名。因此,后人有诗赞道:“一泓池水耀清光,犹是南宫德泽长,墨沉浮香传胜迹,人人争说米襄阳。”米芾曾经多次表现出他为民请命、清正廉洁的个人品质。他在雍丘当县令时,见乡村干部催租逼人、民间啼饥号寒而深表同情,对上级领导不顾农民的死活催租行为也是极其不满,心情沉痛地写下了一首《催租》诗,并且愤然辞去了县处级职務。而米芾在“任满之时,归橐萧然”,不像当今许多党员干部往往在任满离职之后就被立案调查。
米芾生活的时代,正是北宋后期,社会变革激烈。王安石变法后,接着就是元祐党祸,权臣倾轧,尔虞我诈,官场一片黑暗肮脏。米芾这种癫狂、扭曲的洁癖,正是在这样畸形官场和变态时代里孕育而生的。这样的官场自然容不得米芾这样的“洁癖”,米芾因此一生仕途不顺,全都干了一些人大政协这类没有实权的虚职。
这一次,米芾被逐出京都之后,举家迁居镇江丹徒,又于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赴苏北“知淮阳军”,派到贫困地区工作,来了个明升暗降,米芾受此接二连三的打击之后就病倒了。
西风萧瑟,夕阳西下。病病歪歪的米芾乘着一条小船,戴上他的那顶大红高帽,载着他珍爱一生的书画玉石,朝着他的人生终点飘然而去。
五
在九百年前大宋王朝的灰暗色背景之上,永远凸现着一个绝世无双的白色灵堂。因为这个告别生死的场所,正是米芾别出心裁亲自为自己精心布置的。这是宋大观二年(1108年)初春,米芾五十七年的癫狂人生终于走到了尽头。
米芾觉得自己很快就要梦回他的大唐盛世,很快就要魂归他的故里襄阳了。因此,他精心为自己设计了一个灵堂。他将整个后院全都披上一层白纱,院墙挂上白幛,庭树高悬白幡,院内撒满白花。而设在后院主屋里的灵堂,更是设计成一个洁白的世界。主屋的后墙上高悬的一个斗大的“灵”字,那是米芾的手书。上面又挂了一块写有“陟岵兴悲”的榜书横匾;两旁则悬着一副由长子米友仁书写的灵堂挽联,上面写道:“痛此日丧未敬礼对灵何以报答深恩,忆往昔生死无善养伏地难襟流血泪。”灵堂里还安放了一张供桌,供奉着供果、供菜、供酒,两旁点燃两支香烛,前面摆着一只燃烧着的香炉。主屋正中摆放着米芾亲自订购的一口黑漆楠木棺材,棺前摆放着几只白布拜垫。一位古筝名师正弹奏着悠扬古远的《高山流水》。
去世一月之前,米芾就已经预感自己大限将至,便开始正式入住这口楠木棺材。在这口棺材里,提前适应这种新的生活環境,就连“签署公事, 坐卧饮食,皆在其中”。每天早晨戴上大红高帽让子孙们前来一一跪拜,上午分别致信与亲友一一作别,下午则逐一焚烧平生收藏的字画奇珍。
米芾生有五个子女,二儿子二十岁就死去,“老来又失第三子”。这时,他躺在棺材里,听着长子米友仁、两个女儿,以及孙子、外孙们前来跪拜哭泣,自然想起了早已死去二儿子和刚死不久的三儿子,心间居然产生一阵喜悦,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到极乐世界,和自己那两个心爱的儿子见面团聚了。想到此,从棺材里爬起身来,戴上那顶大红高帽,对着跪在棺前的子孙们,摇头晃脑地说出一句话来:“众香国中来,众香国中去。”说完便命人端来早餐,就坐在棺材里吃了起来。
米芾少年时代就拜师学禅,在临终时终于大彻大悟,居然丝毫没有悲伤怕死之意。其实,米芾曾怀报国济民的理想,但终因政府内党争不断,官场上无比险恶,他变得“举止颉颃,不能与世俯仰”,也就“仕数困踬”了。米芾大半生都在七八品的处科级职位上徘徊,抑郁不得志,直到晚年才对人生有了觉悟。他在《画史》中道出“功名皆一戏,未觉负平生”,表明他开始确立了以禅悟道、以禅悦心的人生观。
尽管“众香国中来,众香国中去”,可是在临死之前,他还是想起了自己遥远的故乡襄阳,想起自己埋在天边的祖先们,想起自己将要客死他乡,也就不禁潸然喟叹起来。他躺在棺材里,肯定想起了始建于汉朝巍峨矗立的襄阳古城,想起了王粲的仲宣楼和萧统的昭明台,想起了真武山的摩崖铭,想起了岘首山上的杜甫衣冠冢,想起了孟浩然隐居的鹿门山,想起了建于唐代的广德寺和多宝佛塔,也想起了诸葛亮躬耕的古隆中,更想起了自己曾经生活了十八年的故居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想到此,他居然长叹起来,两眼直勾勾地望着棺材板,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他在想,自己只有死后才能魂归故里了。
米芾在去世前七天,就开始斋戒、沐浴、更衣、熏香。临死当天,他又命人请来了所有的同僚亲朋,自己戴上大红高帽,穿上艳丽唐装,端坐在棺材里,高举起拂尘,对着众人念了一首《临化偈》:“众香国中来,众香国中去。人欲识去来,去来事如许。天下老和尚,错入轮回路。”念完扔掉拂尘,合掌闭目。家人见他不再言语,便上前试探,口鼻已无呼吸,居然已死,想必是回他的大唐盛世去了。
米芾就是这样在苏北给自己不同凡响的一生,画上一个异想天开的句号。
他生平收藏的字画在棺前焚烧着,还在散发着袅袅青烟;古筝独奏的《高山流水》,还在如泣如诉地弹奏着天籁。
我觉得,自设灵堂,戴高帽、穿唐装、焚书画、念禅语、别亲朋,绝不是简单的作秀,而恰恰表现了米芾对这个世界的最后抗争。癫狂的米芾肯定是社会的压抑、皇权的变态、官场的扭曲,共同孕育出来的一个畸形人物。米芾的癫狂就是那个社会的一个象征,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寓言,更是那个王朝的一个预言。
他死了,带走了整个北宋,那个畸形的王朝二十年后便宣告灭亡。
他死了,就已经梦回大唐。
责任编辑 王 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