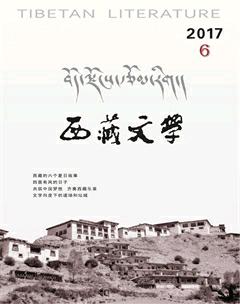西藏的六个夏日故事
赵尧
葡 萄
我2013年到的拉萨,是个志愿者。那时的拉萨比现在要新鲜,特别是人。江苏那一年一共来了三十六个人,个个都是有趣的人,我愿意花三十六个篇幅来讲他们每个人的故事。也许还不止,不过我不愿意得罪人,现在我要讲一个看不到这个故事的人的故事。
他叫叶子,我知道我知道,名字很娘。但是这个人并不是第一眼就让你感觉到娘的人,相反,叶子人高马大,初看你会觉得他是内蒙人,然而他实际上是枚山西汉子。也是志愿者,陕西队的。
具体怎么认识他的,我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大概是除了漂亮女孩以外的记忆在我脑子里都没办法保存三个月吧。依稀记得是在七月份,一个熟识的志愿者离岗,我们这些酒肉朋友自然是要给送个行的。吃吃喝喝也没用多少时间,按照惯例大家就去大昭寺走走。没转一圈大家觉得有点无聊,有个人就说古城里有家盗版的深夜食堂,酒不错。于是刚喝完酒的一群人又屁颠屁颠地跑去喝酒了。我大概就是在那遇到的叶子,也忘了是谁的朋友了,反正大家客套了一番便一起喝酒吃饭了。
他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符合我们现在对于文艺青年的所有定义,不长的长发,会弹吉他,爱好摄影,热爱民谣和摇滚,喜欢异域风格的装饰,与一帮人谈笑风生互相挤兑,开车、骑车、徒步各种折磨自己去看远方的风景,生活在充实与发呆间无缝切换,崇拜卡夫卡、乔伊斯与博尔赫斯,手机有两个,一个最新款一个诺基亚,喜欢写诗和喝酒,画画与弹琴,吹牛逼和高冷装逼,以及哭。
哭不是他的特点,只不过每次我见他总要喝,也不知道怎么了,每次总是稀里哗啦的一大堆。但这不是他的特点,他的特点和其它文青不太一样,他的手脚不太干净,就是喜欢偷东西。
他喜欢乱拿东西的名声比他其它所有的标签都要重。然而他又是一个极具魅力的人,以至于朋友多过我认识的每一个人。于是他的人生在我们看起来有些人格分裂,总是听到说他在哪儿被人打死了,然后一转眼就跟他相遇在酒吧厕所门口。叶子并不是一个抠门的人,也是抢着付账的那群人中的一个,并且总是带动气氛的一个。所以并不像孔乙己,没人会遇到他就开始嘲讽他。他的偷盗就像一个传说一样,他不在的时候仿佛大家都知道,他在的时候大家便都失忆了。
然而有一次真的出事了,晚上将近一点钟的时候,我接到电话,说是人在军区总医院,要住院,但是身上没带多少钱,看能不能去一趟。我听了很震惊,不是他怎么了,而是我真的是头一次遇到他跟我借钱。我自然是连夜赶过去,却看到他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床上,既没有苦主也没有看客,当然也没有帮手。倒是没什么大不了的,胳膊腿也都没断,不过要在医院呆一段时间了。我交了钱便坐着跟他聊天。问他发生什么事了,他就摇摇头。我也不好追问,他就躺在那儿玩着他手里的一个破了的指南针,很明显是今天跟他一起受的磨难。大家不咸不淡地聊了一会儿,我跟他说明天中午我过来再看看他便走了。他大概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我中午会买些饭过去跟他一起吃,一起聊聊拉萨有没有自闭症患者啦,柯南道尔不喜欢福尔摩斯总是想弄死他啦,Don'tcry是不是枪花最无聊的歌啊……
他出院的时候,照例要喝酒,我突然想起来他的一个习惯,喜欢往啤酒里面扔一个葡萄。我问他为什么?他问我,你知道葡萄什么时候成熟吗?我说不知道。他说了句西班牙语,我开始嘲笑他掉书袋。然后接着喝酒了。
他走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像其它来过的人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在2015年的时候收到了一封电子请柬,背景很俗气,是乌斯马尔古城,他未婚夫是个碧眼金发的帅哥,嗯,不是很帅。
雪
从拉萨到日喀则要走三个小时,这是坐火车。拉萨到日喀则的火车是2014年8月份通的车,之前只有汽车,大概五个小时的路程。318国道,经曲水、尼木、仁布,过日喀则机场,拐上艾玛大桥,过了雅江,就进入南木林县的视野之内了。
是的,他就在南木林,我去找他,只是因为他要请我吃肉。
过了桥,沿着湘曲就能到南木林县城,县城不大,三四条街。脚下是山,周围是无边延续的空旷。街道河道都很干净,有气派的政府大楼和中小学校。我经过文化中心门口的时候,接到他的电话,说他住在福利院的旁边,我赶过去的时候,他正一个人在马路边傻站着。
这顿饭没什么好说的,就是找了个小馆子吃了一顿,然而稀奇的是,我们正吃着饭,窗外便开始飘雪了。当时是六月份,六月飞雪说来稀奇,然而这里是西藏,什么时候会没有雪下呢?于是两个人呆呆地看着雪无聊的飘着,然后他好像想起什么事一样,拉着我离开了饭桌。
他带着我去了对面的福利院,一个房间两张床,他径直走向了一位老人,左右反复看看,然后坐下来开始剥桔子。我知道他在等我问他话,可是我偏不,坐在另外一张床旁边,看着一个玩手机的小伙子发呆。
“你在玩什么?”他并不理会我,依旧低头看着他的手机。旁边的基友已经在给老人喂桔子了,不过效果并不好,老人的口水顺着嘴角在向下滴着,他只能再腾出手来给老人擦嘴。
“你会玩游戏吗?”我再次想跟旁边的小伙子搭话,可他依旧无动于衷。“他是個脑瘫,别费劲了。”基友终于把头转了过来,“听话,吃了,老伴就在隔壁,睡完觉就带你去找。”然后接着哄老人吃东西。
“好好睡,下雪了,不能出去了!”“阿佳,我先回去了,今天暖气是不是要开了?”“晋美,想吃什么我回头给你带!”“走吧,还赖在这干嘛呢?”……待他前后吩咐一顿后,我只能跟着他顶着雪跑回了他家。
一人一杯甜茶,围着一个小太阳,哆哆嗦嗦地开始等待。“你知不知道,甜茶这玩意,本来这边是没有的。”我不知道他想说什么,智障一样看着他。“甜茶、藏面都是你们拉萨人的玩意。现在传得到处都是了。”“然后呢?”“然后个屁啊,不知道就不知道,人要有脸承认!”“切!”……又是一阵沉默……“那个老人是个英雄,湖北人。”我喝了口甜茶,听他说起书来。
“老人经历过两次战争。他是1951年到的西藏,本来说是打仗的,结果来得晚了,没打成。然后就被安排在拉萨驻了军。然后就是谈判,谈了好多年,从他在拉萨谈到了日喀则,跟着就和一个藏族的阿姨结了婚。然后,就说是要搞土改,他就被安排到了南木林。那时候哪有个县城啊,办公在前面那个寺庙旁边盖的指挥所里。还没开始搞,就听说西藏高层叛乱了,他奉命去江孜,右腿被打进了一颗子弹。”“然后,就正儿八经的开始搞土改,搞农奴解放,跑遍了整个西藏……”endprint
小太阳的光总感觉有些飘忽,我又给自己倒了一杯茶。“老人家是前年患的痴呆,什么也不记得了,就记得自己的老伴在隔壁屋里做毛毯。我后来发现老人家每个月的退休金只有一千多,我就觉得不对。一去问,照理应该要涨到四千多的,我跑了几趟帮老人家争取到了。唉,又有什么用呢?”
我回去的时候,车子出了南木林便是晴天万里,一瞬间便从冬天回到了现实。后来他给我打了一次电话,说是那个叫晋美的脑瘫儿结婚了。我不知道怎么做到的,不过我再也没去过南木林了。
出租车
如果你来过,那你应该知道拉萨有多小,小到你遇到过的人,一定会再次遇到。
那是2014年的时候,我从仙足岛的酒吧出来,意兴阑珊得很,不愿意走便随手打了个的回学校。小哥是个健谈的人,一路上都在谈自己老婆烧的菜,说拉萨的东北菜全都不地道,还得自己燒,这不,本来是来拉萨开车玩的,他老婆非要留下来,只能租个房子了。然后还是吐槽拉萨的气压低,饭也烧不熟,菜也不好吃,这边的米也不好吃,实在没有东北好……小哥长的并不太像我们印象中的东北人,反而更像南方人,个子不高,有些消瘦,小平头,很精神。
不要误会,我们今天的主角并不是这个小哥。我本来就不太喜欢聊天,兴致又不高,自然没办法欣赏小哥的幸福恩爱了,我要讲的是一个小姑娘。车子经过拉鲁桥的时候,有人拦车,毕竟只有我一个人,小哥便要拼个车,停车问去哪儿。我是坐在前排副驾驶的,招手的在前面,哪知车还没停稳,突然从后面冲过来一个人,拉开后门就爬上了车。小哥和我都被吓了一跳,很浓重的酒味,也不知道怎么了,司机小哥随手换个挡就走了,按理说很多司机都不拉醉酒的客人的。后面的客人应该是个女孩,车子走了几十秒,司机才想起来问去哪儿,后面嘟囔了一个地方,在东郊,并不算顺路。司机小哥说了情况,后面没了声音,似乎是睡着了。小哥等了半天没人应,便靠边停了下来。然而后排依然没有声音,很尴尬的等了两分钟,我说算了吧,先把我送回去,你再把她送回去吧。车子重新发动,相顾无言,车子里很安静,大家突然不知道要聊什么了。就这样过了几分钟,后面的女孩子突然“嗯”了一声,我转头一看,这个女生突然坐起来,把头从后面伸过来,用四川话问了司机小哥一句:“帅哥,你一晚上赚个多少钱撒?”小哥可能是有点紧张,不知道是回答还是不回答,支吾了半天。后面的女孩子好像是要故意揶揄他,伸出手在小哥脸上撩了一下:“说嘛,多少撒?”“大……大概五百吧。”小哥给了我一个很无奈的表情。“好!”小姑娘大喊一声,然后坐了回去,我跟司机小哥都舒了口气。气还没出完,只听后面刷地从包里拿出一沓钱,啪地拍在变速箱上!“今晚陪我,钱给你!”“姑娘,是不是喝的有点多?”“你不想要我吗?”“姑娘,您别误会,我这是出租车。”“我不漂亮吗?”“漂亮。”“要你跟我耍朋友不愿意吗?”“这个……我只是个开出租的,养不起啊。”这一系列对话是在小姑娘躺着的状态下完成的,似呓非语,有一搭没一搭的。我是挺无聊的,突然我发现有些不对劲,忙提醒司机小哥:“怎么回事?你看下后面。”我是从后视镜瞥到了一眼,然后我看了一眼司机小哥,确定我没有看错。是的,没错,后面的小姑娘一边含混说着什么,一边脱衣服。
我跟小哥两个人这时候都蒙了,眼睛盯着前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过了一会儿,后面的小姑娘似乎很满意,好像睡着了。司机小哥一个刹车把车停住,转头跟我说:“哥!你这可不能下车啊,你现在下车我可没办法了啊!”我也有点哭笑不得。“我在车上也没有办法啊。”“哥,你想个主意吧。”“我能有什么主意啊。”“总……总得把她……可她现在……”“不然你看附近有什么宾馆,把她送过去住一晚上?”“她这个样子……说不清啊。”“那……”没人说话了,车子就这么停在路边,前面是两个无奈的男人,后面是一个光着上身睡得很安稳的女孩子。
良久,身子有些僵硬了。“不然把她送到派出所吧。”“好,前面就有一个便民警务站。”拉萨的便民警务站是相当多的,每隔几百米就有一个。不几分钟便到了。我们进去说明了情况,警务站里也只有一个男同志在值班,这种事情他也没遇到过,况且也不方便。最后商议,车子和车里的人就先不动,司机小哥就和警察先呆在警务站里,我自己另外打车回去,警察同志紧急通知一个女同事过来处理。下面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很疲惫,回去便早早进入了梦乡。然而,我没有想到还能再碰到这个姑娘。
我说过,拉萨不大,但我觉得,我再次遇到那个女孩不是因为拉萨的小,可能仅仅因为拉萨的服务业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的发达。
那是在上次那个历险几乎已经不能再成为谈资的一个月后,或者两个月,不会超过三个月,因为我的记忆是容不了三个月的长度的。我和两个朋友吃完饭去洗脚城泡脚。隔壁老王的御用技师不在,我们便随便排着号,一个一个看过去,我本身没什么,隔壁是个无聊的人,非要换到一个符合他审美的给他洗脚。然后她就进来了,我一眼便看出来了,就是那个姑娘。至于我为什么能记住她的样子……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她长得漂亮而已。然后我们便聊起天来。看来她对我并没有印象,我虽然不健谈,但跟漂亮的女孩子总能聊得很多。然而我并不想在这里讲女孩子如何坠入风尘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很多,也很感人,有的也很真实。总之是关于贫穷、天赋、人性和际遇等,我不想讲这样的故事,翻过去吧,就当我没来过。不过真是个乖巧的女孩子,比隔壁黄段子满天飞的强多了。
然而我又遇到过她一次,就在不久之后,在一家烧烤店,她很凶悍地跟老板吵着架,气势很足,不像一个小姑娘,我看了一会儿,转身跟别人去了另一家。
等我再去那家洗脚城的时候,一个小姐姐告诉我86号已经不在了,据说是因为怀孕了。
对了,那个司机小哥后来我也见过两次,最后一次是在半年后吧,一次自行车越野赛上,我好像是看到了他,个子不高,寸头,很精神,我没有打招呼。
还有一次是在一家烧烤店,很凶悍地跟老板吵着架,外强中干,不像一个东北人,我看了一会儿,转身跟别人去了另一家。endprint
竹
我写这段字的时候,拉萨正在过萨嘎达瓦节,校门口的流动摊贩全都被城管藏起来了。我也有些怀念门前的那些黑暗料理,就像怀念你的每一座校门一样。
有时候我觉得故事的地点不重要,故事的时间不重要,故事的因果不重要,但是故事的年龄一定很重要。今天我要讲一个关于青春的故事。
我觉得大学校园皆没有朝气,所谓青春洋溢肯定不是大学生自己形容自己的词语。如果城市之中没有周围的工地,那整个校园确实像一盆精致的死水,不过偶尔会溅起几朵水花。我来这所学校的时候旁边恰好有个工地,就是拉萨的三环路,整体叮叮当当、轰轰隆隆的,说起来并没有什么好处,直到我看到了一节竹子。
竹子是插地上就能长一大片的生物,直到我长大了,有功夫天南地北地闲逛的时候,我才惊讶地发现,北方竟然是没有竹子的。拉萨的海拔三千六,日照强烈,气候干旱,自然是無竹可生的。这节竹子不太粗,撑在煎饼摊上,有点脏,翠绿翠绿的,看得我有点呆。雪域高原上一节孤零零的竹子……总让人感觉有些莫名的、隐约的诗意。摊主是随施工队一起来的,这节竹子估计是从中铁某局的工地捡过来的。摊主非常有活力,让人忍不住想买个煎饼果子,于是我就买了一个,十五块钱一个,很显然,她是来抢钱的。
后来我发现,同样是一个满是淀粉的肉肠、一个不知道什么肉的鸡柳和一堆土豆丝的煎饼竟然只收了我十块钱了,再后来她自己解释说是前期定价不明,可我觉得她就是觉得老师都傻傻的好骗。
三环路修的很快,可是时间也并不短,她一个山东人和我这个江苏人很快就熟识了。但要说真的有什么老乡情谊,我是一点也不信的,她总是透着一股子小生意人的精明和活力,总让人感觉到她摊子上的煎饼果子比马路对面的那家店铺里的要便宜。当门卫说他是山东临沂人的时候,她的头一句话是“我去过临沂,在沂南那卖煎饼卖了半年,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去了。”问及是何原因,答道“沂南什么都好,就是东西太便宜了,我在全中国也没见到论斤卖煎饼的,你知道沂南煎饼卖多少钱一个?”……“一块二!”我当时拿着他们家煎饼在啃着,听了她这话我都不想吃了,感情这是几毛钱的成本?
我爱跟她聊天,在书卷中泡多了的人总觉得世事艰难,斤斤计较的烟火气息很吸引人。生活不过就是算着钱过日子,说来说去还是想先买了房子,孩子暂时还不考虑,等年纪大点,到了二十五六了再说,谁知道下个月又在哪儿呢?我的性格像是一个影子。她比我要明亮得多,据说她还会跳舞,我没见识过,不知道是蹦迪还是广场舞,或者真的有过什么舞蹈的基本功?总之我没见识过。
公路没有通车的时候,她就不见了。后来听说有人遇到过,相互打听,说是她丈夫去世了,赔了一大笔钱,后来终于没人再见到她了。
梦 乡
我小时候就像做梦一样,世界对于我来说就像一个没有边界的神殿。我不记得家乡白天的样子,只有夜晚和太阳下的夜晚。卓嘎感觉有些喝多了,在通往酒吧的路上神秘地跟我讲着什么,我有些拘束,不敢靠得太近。
那个时候觉得世界好大,屋子后边是河,右边是真嘎家,过了很多家还是河。我不经常去那里,也不经常去后面。最常走的路是从前面直走右拐,过了桥一直走可以找到放牛的爷爷,再向右转可以去和另一个村子中间的小学校。学校有两个老师,三个年级,十一个孩子,都小得很。这里面我是最小的一个,跟在真嘎姐姐后面到学校里来。姐姐去上课了,我就一个人爬到墙上,看着小羊吃草。世界很小,我知道外面有更大的世界,但是我从来没有走过那个墙。我最好的朋友是一只小鸟,她叫小拉姆。我怀疑她是彩色的,但是我只能看见黑色与白色。有一天,我的小拉姆死了,我想把她送到天葬台去,我听人家说人死了就要去天葬台。我没有去过,但是我知道在哪儿。首先要往左边走,左边是家,右边是河,黑暗中能听到水的声音和莫啦的念经声。我还不会念经,不然可以给我的小拉姆也念经,或者像真嘎在学校里念的诗一样,也很好听。再往前是树林,树林的声音很可怕,再加上河水的声音,我有些想回家。可是我手里还拿着小拉姆,我知道她是只小鸟,我想把它扔到河里,可是我看不到河在哪里。我想回家,可是我不能拿着一只小鸟回家。我要往前走,我知道再往前是学校的围墙,我要翻过围墙的缺口。我觉得天越来越黑,我却越来越能看清前面的路。可是前面的路我没有来过,我觉得我已经离村子好远好远了。过了好久,我走得累了,便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休息,我不知道天葬台是什么样子的,我也不知道它在哪儿。不,我知道,他们都说在那边,我往那边走肯定能找到,想到这里我立刻起来,我一定要找到天葬台。我走啊走,走啊走,我不知道自己走了多远,也许我马上就找到了!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来,我从石头上起来走的时候,忘了带着小拉姆了!我开始哭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我想回去找我的小拉姆,我又想往前走,前面就是天葬台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于是就坐在地上哭,哭着哭着就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我变成了一只小鸟,但我不知道我是一只小鸟,只能感觉到风在我的羽毛中穿行,云彩把我的耳朵弄得痒痒的。我在飞,可是又不像是我在飞,我挥动着翅膀,但是我并不想往其他地方飞,我好像在找什么。我知道了,我在找小拉姆,我想让她看到我也能飞了。我拼命往前飞,很快我就看到了那块大石头,很快我就能找到我的小拉姆了。
不对,石头上没有小拉姆,躺在石头上的是我自己,我还在石头上睡着。我想落下去看个究竟,可是还没等我飞下去,我就看到了另外一样东西:一条蛇!一条蛇正在咬我的胳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立刻俯冲下去,对准它的眼睛,用力去啄。蛇松开了我的手臂,一个尾巴把我扫下来。我掉在地上,抬起两个爪子就抓向蛇的另一只眼睛。蛇把我紧紧缠住,我开始拼命地不停啄着他,啄着他,啄着他,啄着他,啄着他……
后来我再次醒来的时候,莫啦坐在我的旁边,还有其他好多人。后来爸爸从城里回来,告诉我说我在村外被蛇给咬了,好多人找到了我,他们准备把我抬回家里,谁知道刚到村口就遇到了一个喇嘛,那个喇嘛看了我之后赶紧让人把我送到医院里去,医院的人说再晚点我就没法活了,可还是把我救活了。可是我知道,我是不会死的,你知道为什么吗?我曾经会飞的。endprint
她拿出手机,对着自己的影子,咔嚓,自拍了一张,打开微信,发了今天最后一个状态。
距离那次谈话已经过去了一年,我不记得当时是怎么离开的了,以后的日子里我也没有再见过那个叫卓嘎的姑娘。复述的时候也想不起来这个叫卓嘎的女孩的音容相貌,甚至时间都变得有些错乱,我搞不清这个故事来自十年前还是二十年前。但是我总在幻想那个村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是在那曲,还是在阿里?那座山来自林芝的森林还是昌都的丘陵?是什么将世界的颜色染黑,是巨大的冰川,高耸的山脉还是无尽的草原?冰雪融化形成的河流,终年不化。风声化成水声,在梦乡人的枕中流淌。
后来我走318国道的时候,路过了那个村子。离国道不远,雅鲁藏布江把村子和路隔开了。有座桥,很宽,车子可以开进去。有农田和道路,没有什么人。现在在开发旅游资源,景点是水边的一排青稞磨坊。我走遍了整个村子,既没有学校,也没有雪山。清一色的房子,很漂亮,可能是政府统一建的。我不知道一个孩子的世界是如何分辨现实与幻想的,不过也许我永远也无法知道,这个村庄究竟是不是我梦里的那座。
魔法
考验风的永远都是阳光,当太阳到了天空的另一面,风就统治了整个世界。小桑就是被风选中的人。
他可以借助风飞翔,借助风隐藏,从风中逃遁,带走风里所有的积蓄,吹灭风中所有的幻想。他能利用风打开世间所有的窗户,窥探每个人最深的隐秘。他能将风吹进每个人的耳中,让炎热变得凉爽,让寒冷变得温暖。他在无数人的注目下隔空取物、穿墙过户、凌空飞腾、凭空消失。又在无人注意的地方丈量世界、拨弄时间、描绘因果。
他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他喜欢在风中的生活,即使风中有撕裂的哭喊、有漫天的垃圾、有寒冷与死亡、有无奈和彷徨……他不在乎,因为他知道自己,是风选中的人。
唯一的威胁来自太阳,当太阳来临的时候,他只有躲藏和逃跑。但是太阳太强大了,他总是来不及避开太阳的光芒,交织的光芒会织成坚不可破的牢笼,阳光中的热量会炙烤他敏感的心脏,无处可遁的光明会侵蚀他脆弱的灵魂。他打不开那扇门,纵使他打开过无数的门。他挣不脱精神的捆绑,纵使他摧毁过无数的精神。他被太阳抓住过二十三次,直到他离开了风。
他的离开不是因为太阳,是因为月亮。他爱上了月亮旁边的那颗星星。遥不可及的她是风触及不到的地方,于是风狠狠地鞭笞了他。没有风的力量,他开始变得一蹶不振,他不再能够进入人们的梦乡,不再能够飞翔,不再能够隐藏自己,不再能够指挥他人。他在人群中承受辱骂,在巷道里遭受殴打,在失落中忍受孤独。然后他离开了风,从网吧管理员到电脑销售,从电脑销售到网站编辑,从网站编辑到节目策划……
“操他妈的小逼养的兔崽子!为了一个小婊子……”他最后的话我听的不太清,我要准备去拿我的行李。他叫风,在回拉萨的飞机上,他给我讲了他徒弟桑的故事,现在我们要分开了,风太大,我走得很急。
回家休息了半天,傍晚的时候,我去林廓路的半边山书店装裱一幅画。在去青年路的天桥上,我又遇到了风,头发蓬乱,衣衫褴褛,窝在拐角,前面一个破烂的盆。我绕过天桥的一侧,远远地看了他一眼,急速离开。
谁知道他有没有使用魔法呢?
責任编辑:次仁罗布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