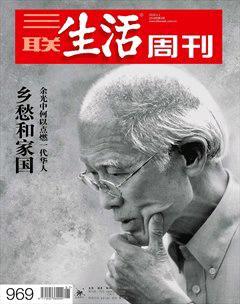樊善标:余光中笔下“文学的香港”
傅婷婷
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香港中文大学在行政区域划分上,还属于沙田区。余光中在这里一住就是10年,开启了他的“沙田文学”时代。
三联生活周刊:1985年,余光中离开香港时,发表了诗作《别香港》:“如果别离是一把快刀/青锋一闪而过/就将我剖了吧,剖/剖成两段呼痛的藕……”余光中对香港的情感,和对大陆和台湾的区别是什么?
樊善标:余光中先生是个很自觉的作家。在《春来半岛》的前言《回望迷楼》里,余光中回顾了他在香港的生活,他说在香港这么多年,好像是把香港当作一个眺望大陆的看台,当他离开的时候,才突然发现他忽略了脚下这个地方。这段戏剧化的自述,变成好多人对他香港时期的概括,认为余光中来香港本来是为了接近大陆的母体,所以80年代开始有“香港”认同感的一些人觉得很不是滋味,也以此批评他。但是余光中很早就在作品中表现出对香港的风景很有兴趣,他在香港的早期有一篇《沙田山居》,把香港中文大学写得很漂亮。
其实,在70年代,香港还没有“身份认同感”的思潮。到了80年代初期,中英谈判的时候,香港才有了一个主体意识,把香港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此前,住在香港的人不太会有命运共同体的感觉。所以,余光中当时没说对整个香港有兴趣,只是对香港的某些地方感兴趣,直到快离开香港时,他才明确说香港作为一个整体对他很重要,这也是很自然的。
在言谈之间,可以感觉到他蛮喜欢香港的。后来去了台湾高雄以后,也常常回来,他对香港政府的效率和一般人的公民意识,都很认可。而他的身份认同感,综合了大陆、台湾和香港。香港的身份他一般很少提到,但是在离开香港前的文章里,他都点出过。
三联生活周刊:从文学创作上来说,香港对余光中有什么特殊性?
樊善标:香港为他提供了一些跟台湾和大陆不同的可能性。
台湾和大陆都是很中国化的地方,但香港人之间的互动,跟大陆和台湾有很大的不同。余光中年轻的时候,生活在大陆。在台湾,他有很多文坛上的交往,但是在香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不会是很强烈的互动,起码表面上不会。初到香港,余光中的人际关系有待重新建立,他可以比较自由和宁静地写东西。所以他说,香港时代是他生命里最安宁的时期。
一方面,香港比较靠近大陆,所以他的心理上跟大陆的关系近了很多。初来香港时,他写诗,听着火车北上南下的声音,就觉得跟他过去很挂念的地方有一种很直接的关系。我猜想,这种心理感受给他带来了写作的气氛,让他常常产生写作的冲动。
另一方面,香港跟大陆的距离比台湾近,很多消息很流通,跟他在美国和台湾听到的信息不一样,消息量也多很多,所以他对大陆情况的理解也比较复杂。因此他作品里面的“乡愁”主题,在美国和台湾时期比较多,到了香港以后,慢慢淡下来了。
三联生活周刊:余光中曾经说,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你如何解读他把香港比作“情人”这个比喻?
樊善标:我没有问过他,但是你的这个提问让我产生了一些猜想。我个人的诠释是,情人和妻子不同的地方在于,夫妻是一种伦理关系,其间有很多责任,而情人很刺激,关系视乎双方的感应。妻子有点像到达目的地的感觉,而情人则常常在动态里。
香港对于余光中来说,应该是一种比较“刺激”的情况吧。第一点是,余光中在“文革”还没结束时来到香港,他的朋友刘绍铭跟他说过,他在香港会受到很多攻击,结果他真的受到很多政治上的批评。第二点是,他出身于外文系,到了香港担任中文系教授,而且来的时候职衔很高,所以任教古典科目的老师会观察他:外文系的人究竟有没有资格在中文系教书?
但是,余光中能够把这些刺激化为创作和学术方面的推进因素。比如,到了香港以后,他的创作题材里有很多中国文化的元素,比如曹操、苏东坡、中国古代的游记、重评五四时期的文学。如果他一直在外文系,大概不会开发这些方向。
三联生活周刊:余光中过世以后,整體上说,香港对于余光中的情感主要是推崇怀念,而台湾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有推崇,也有批评。
樊善标:余光中直到去世之前跟台湾社会各个方面关系很密切,比如,他参与台湾的教育体制讨论,主张课程里不能减少文言文的投入,这是会牵动当地社会的反应的。在他们的评论里,余光中是复杂的,与很多事情有关。
我觉得,这个现象的关键,在于这个地方对他的熟悉程度:因为熟悉,所以有很多意见;因为不熟悉,所以就比较简单。
三联生活周刊:比起余光中的诗歌,你似乎更偏爱他的散文。和大陆读者整体上会被《乡愁》触动所不同,余光中的哪些作品引发你作为一个香港人的共鸣?
樊善标:我最初喜欢他的60年代《逍遥游》系列的自传式抒情散文,后来70年代《青青边愁》里的比如《高速的联想》,我也喜欢。但我作为一个在香港出生长大的人,在感情上最喜欢的是《记忆像铁轨一样长》里的那篇《飞鹅山顶》。
三联生活周刊:《飞鹅山顶》是余光中香港时代的一个作品。创作背后的理念是什么?
樊善标:这要从60年代说起。余光中有一篇参与散文论战的文章,叫《剪掉散文的辫子》(1963),主张“现代散文”需要锻炼出一种强而有力的语言,推倒朱自清、冰心风格那种小品文。
当时余光中为了表达很强烈的感情,常常把现代诗的语言用法引进散文里,打破语法规则,但在《听听那冷雨》(1974)之后,他的语言实验已经成熟,就不需要再大规模的破坏语法。《飞鹅山顶》就是运用这种成熟的语言,但加上了很多像顾问一样的起伏照应,非常细腻,我认为是他散文作品里技巧最高超的一篇。而文章末尾,把大陆、台湾、香港用一个很长的句子连在一起,表达他对这三个地方有同样深厚的感情,更令我从内心产生共鸣。
三联生活周刊:在香港文学圈,在风格上,一度有余光中的“余派”和也斯(梁秉钧)的“也派”之分。他们的创作观念区别是什么?
樊善标:这是80年代后期产生的一种说法。其实,余光中和梁秉钧没有真的笔战过。他们二位对后学都很提拔,所以像是有两帮人壁垒分明地对立,但这种情况早就过去了。
余光中经常表示对语言的美感有强烈的要求。梁秉钧则强调要看用这种语言来表达什么东西,所以主张对事情的看法和视野比用怎样的语言来写更重要。
但是,他们的作品其实比他们的主张丰富很多。例如余光中的《剪掉散文的辫子》没有谈结构,但创作散文的时候在结构上下了很多功夫。梁秉钧虽然不喜欢用成语和那些很古典的意象,但他对语言仍是有要求的,他的语言是提炼过的生活语言。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经提到,余光中对于大陆文学观中的郭沫若、闻一多、戴望舒这些五四经典人物,有不同而独到的看法。他在《青青边愁》和《分水岭上》有写。在课堂上,你是否听到过余光中讲这方面的观点?
樊善标:这些应该是他讲课的心得,而且他在课堂上讲过的作家不止这些。有一点,余光中在文章里写得很清楚,即他对一个作家的语言运用特别重视,所以他评价那些作家的优点和缺点也主要是从语言的角度去看待。比如,他说何其芳的散文有很多语病,但诗歌往往有很好的句子,尤其是在开始和结束的地方。他又指出了朱自清一些有语病的句子,我都很同意。当然后来我也发现朱自清的文章还有他没有谈到的优点。总体来说,他的学问是在五六十年代奠定的基础,他本来读的外文,所以欧美新批评对他的影响很大,他那一辈的很多学者的学问都是这种根底。
回头再说他对这些五四经典人物的批评,其实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他把这些作家放在整个中国,或者整个世界来讨论,用古往今来的殿堂作家,来跟这些五四的所谓重要作家来比。比如,徐志摩的诗、朱自清的散文,能不能跟韩愈的散文、杜甫的诗来比较?他是从这个角度进行批评。
余光中认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其实是在两个高峰之间的低谷,前面的一个高峰是中国古典文学,后面的高峰就是台湾发展得更好的现代文学,五四那几十年的语言还没有达到很好的地步,所以不能把它当成一个永恒的模范。
如果五四是一种断裂,把中国的现代跟古典断开来的话,余光中的立场其实是重新把现代文学跟古典文学连上,我觉得这是余光中在文学史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