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敏如:我在短暂的生命中抓住了永恒
□木匠
杨敏如:我在短暂的生命中抓住了永恒
□木匠
【编辑推荐理由】
2017年,又有不少可称大师的文化名人离开了我们。从一开年就去世了的著名漫画家、《老夫子》的作者王家禧到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的周有光、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再到越剧范派的创始人范瑞娟、新派武侠小说创始人之一的黄易,最后到著名诗人余光中。本以为不会有人再走了,谁想到就在余光中先生逝后仅一天,著名古典文学学者、北师大教授杨敏如先生又去了。
杨先生1916年生于天津,是已故著名翻译家杨宪益的妹妹,已故著名电子与信息学家、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罗沛霖的夫人。中学时代,曾就读于天津中西女中;1934年,考入燕京大学中文系,师从顾随等名师,专攻古典文学,兼研俄罗斯文学;1940年,她在重庆南开中学开始了她长达60年之久的教书生涯;1948年以后,曾先后执教于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1954年,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直到1986年退休。
杨先生“文革”中曾受到迫害。直至2007年,才以90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
杨先生还是第五届全国妇联执委和民盟中央第七届委员、民盟中央妇女委员会第五、第六届副主任委员。
杨先生一生经历可谓丰富多彩,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听过杨先生的一个唐宋词讲座,杨先生上课时,声音洪亮,语调抑扬顿挫,很能抓住学生。最大的特点是鞭辟入里,以情动情,大家风范俨然。如今斯人已矣,斯爱永存!

2017年12月15日,著名古典文学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杨敏如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
名门之后
杨敏如,1916年生于在天津,祖籍安徽泗县(今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
杨家是一个世代簪缨之家,杨敏如的高祖父名叫杨殿邦,是嘉庆十九年进士,历仕嘉庆、道光、咸丰三朝,曾做过山西道监察御史、贵州按察使、贵州布政使、贵州巡抚、山西布政使、太仆寺少卿、顺天府尹、礼部右侍郎和漕运总督等职。他于咸丰三年(公元1852年)卸任后,就在淮安南门更楼以东购置了一个大宅,于此定居了下来。
杨敏如的曾祖父名叫杨仲禾,是杨殿邦的独子,他虽因为有足疾而未能做官,但却生了八个儿子。除老二杨士普早亡外,其余七个都很有出息,其中老大杨士燮、老三杨士晟、老四杨士骧还都考中了进士。杨士燮曾被公派赴日本考察学务,担任过横滨总领事官。回国后,历任江西道监察御使、山西副主考、兵科给事中、平阳知府、大同知府、嘉兴知府、杭州知府等。杨士晟历任江苏无锡知县、崇明县知县、芜湖米厘总办,民国后,任芜湖关监督、苏州关监督等职。
杨士骧是杨家兄弟中官做得最大的,16岁中秀才,26岁中进士,入翰林院,选庶吉士,授编修,从此步入仕途。后被外放为直隶通永道,为按察使,不久,又升任了江西布政使。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十二月,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他接袁的班,成为山东巡抚,在任三年,政绩斐然。光绪三十三年,袁世凯改任北洋大臣,他又代袁成为直隶总督,时,袁为筹办近代新军,需要大量经费,他积极为其筹划,与袁私谊之好,为朝中官员“侧目视之”,成为当时最炙手可热的人物之一。
老五杨士琦虽未考中进士,但也是个举人,初,很得李鸿章的赏识,李在与八国联军谈判时,曾以其为联络员,后因为其兄的关系,亦很受到袁世凯的重用,历任农工商部右侍郎、邮传部大臣、钦差大臣,民国后,为上海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总办、参政院参政等职。
老六杨士钧,不详,一说曾为小吕宋总领事,民初沈阳电报局局长。
老七杨士铨身世不详,据说也是一个举人。
老八杨士骢曾两次担任北洋国会众议院议员。并娶了袁世凯的三女袁叔祯为妻。
不过,杨仲禾很早就去世了,并未亲眼看到儿子们成才。据说杨家一度衰落,幸得“长孙”杨士燮的岳丈吴棠及时伸出了援手,才挽救了杨家(吴把自己的二女儿嫁给了杨士燮,正是这场婚姻,使杨家的处境大为改观)。吴棠也是晚清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早年因剿捻有功,而被擢升为江宁布政使(从二品官),代理漕运总署,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实授漕运总督,四年署理两广总督,五年任闽浙总督,同时加都察院右都御史、兵部尚书衔(正二品),七年调任四川总督、成都将军。而吴早年,杨殿邦对他是有知遇之恩的。后来,吴还把自己的一个孙女嫁给了杨士钧的三儿子。
杨士燮亦也有八个儿子,他让诸子分别到日本、美国、英国等国留学。长子杨毓璋从日本留学回来后,先是在沈阳做了市电话局和电报局的督办,后来又在天津成为了中国银行行长,是中国的第一代银行家。或因为四叔的关系,其与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冯国璋等北洋大员的关系都很密切。
杨毓璋就是杨敏如的父亲。由于杨毓璋的发妻始终未能给杨家生下一个男孩,于是,他又娶了个二房。这个二房,就是杨敏如的母亲,她为杨家生了一男两女,分别是老大杨宪益、老二杨敏如和老三杨静如。
杨家有女初长成
杨敏如兄妹虽然是“庶出”,但毕竟是杨毓璋这一支唯有的三个孩子,特别是杨宪益,又是唯一的男孩,所以他一生下来就由嫡母抚养,全家人都视其为“掌上明珠”。
杨宪益出生时,袁世凯还特意派人送来了一件小黄马褂。过去人迷信,围绕着杨宪益的出生一直有种说法,意思是说其母在怀他的时候,曾有“白虎星入梦”,这是凶兆,会危及父亲的健康,并不能再有兄弟,但也是吉兆,这样的孩子事业会有大成。事实也是如此。大富之家的生活是相当奢靡的,杨毓璋工作之余,喜唱京剧、京韵大鼓,还拉得一手好胡琴(梅兰芳、盖叫天、余叔岩、周信芳、程砚秋等名伶,都曾到杨家献艺),他还爱玩飞镖、斗蟋蟀、抽荷兰雪茄、喝法国白兰地,一派公子哥的作风,不过,其事业倒也做得风生水起,挣下了千万家私,成为天津首屈一指的大户。
为了笼络住杨毓璋这位财神爷,袁世凯以及后来的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徐世昌、冯国璋等都与其过从甚密,乃至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北平、天津一带,只要一提起杨家,很多晚清遗老遗少、民国军政要人都会连声称道、肃然起敬。当时,在杨家的客厅里,一直挂着这样一副对联:“自非北海孔文举,谁识东莱太史慈。”可见,当年杨毓璋掌管的中国银行,也确曾给这些军政要人提供过很大的帮助。然而,就在杨毓璋的事业如日中天之际,一场灭顶之灾降临到了他的头上。1919年,在杨宪益5岁那年,他染上风寒,本来都快好了,可偏偏在这个时候,杨宪益又患上了白喉和猩红热,日夜哭闹不止。一日深夜,他听到儿子又在哭闹,舐犊之情油然而生,遂披衣下床,抱起爱子在家中转悠,结果伤寒复发,竟致一病不起,英年早逝,享年48岁。杨毓璋去世后,留下巨额遗产,作为家中的独子,杨宪益分得的遗产竟比杨毓璋的发妻还多。据杨敏如生前回忆:“父亲去世后,仍由嫡母管家,我母亲因为生了儿子,也分到了不少财产。但没过几年,几个叔叔不知用了什么手段,便侵占了我家的很多财产,房子也卖了,我们这个大家庭也就散了,只留下嫡母、母亲和我们兄妹三人住在出租的房子里。母亲本来并不识字,但与父亲结婚后,父亲教会了她读书识字。我们小时候,她给我们讲故事都是从书上看来的,比如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当时的中文译本名叫《隐侠记》)。她后来一直活到了95岁,晚年仍坚持读书看报……”
杨敏如还说,哥哥没有上过小学,当时,家里给他请了一个国文老师和一个英文老师。到了该读中学的年纪,母亲才把他送进了南开中学读书,他一入学就是班里的优等生,尤其是英文,说得比先生还好。他中学毕业后,就去了英国的牛津大学,主修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古法国文学和英国文学,后来,哥哥成了有名的翻译家,一生翻译过上百种中外名著,既有从英文、德文、法文、希腊文翻译成中文的《荷马史诗》、《奥德修记》、《罗兰之歌》、《萧伯纳戏剧集》等;又有从中文翻译成英文的《史记》、《资治通鉴》、《楚辞》、《长生殿》、《牡丹亭》、《魏晋南北朝小说选》、《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和《鲁迅全集》等。
她和妹妹杨静如则是一到上学的年纪,就进了洋学堂。她中学读的是中西女中。中西女中是一所教会学会,当时在天津很有名,赵四小姐、严幼韵也都曾就读于该校;妹妹杨静如的中学也是在中西女中上的。后来,她考到了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后,转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历任中学教师,南京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翻译。1949年以后,曾任原民主德国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东方语文学院讲师,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教授,也是一位翻译家。
15岁,她遇到了自己一生的挚爱
就在中西女中读书时,杨敏如认识了她一生的挚爱罗沛霖。
罗沛霖,1913年出生在天津,他的父亲罗朝汉是中国第一代电报生,曾任北京电话局局长;舅父孙洪伊是天津早期同盟会会员,曾任大元帅府(广州)内务总长。1922年,孙中山与李大钊就是在孙在上海的寓所里见的第一次面。罗沛霖是杨敏如的堂兄杨缵武在南开中学的同班、同宿舍好友,据传罗沛霖在南开读书时,学习并不好,一次期末考试,竟五门不及格。当时,南开的校长张伯苓到北京为学校筹款,找到罗朝汉时,罗朝汉说:“你都要把我儿子开除了,还来跟我要钱。”张伯苓当场许诺:“可以补考。”罗沛霖毕竟是个聪明人,他从南开中学毕业时,同时考上了北京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杨敏如与罗沛霖的相遇是在1931年的夏天。当时,杨敏如15岁,罗沛霖18岁。那一年的暑假,杨敏如随家人到北京香山避暑,这居然是她生平第一次接触大自然。当时,杨家住在山上别墅中,而罗沛霖与杨缵武就住在香山脚下的电话局办事处。杨敏如对罗沛霖可谓一见钟情,而罗沛霖却在初中二年级时,就被包办婚姻,女方是前大总统冯国璋的孙女,但他一直对这门亲事十分抗拒,也因此“养成了一种落落寡欢、强犟无羁的怪脾气”。当他们熟络起来后,杨敏如还热心地教会他怎么下跳棋、打扑克,而他则会给她“唱歌、讲古诗、辨花木、谈鲁迅和莎士比亚等”,杨敏如听得如醉如痴。此时,杨敏如有两个最崇拜的人,第一个是她的哥哥杨宪益,第二个就是罗沛霖了。罗沛霖虽有婚约在身,但对杨敏如这个小妹妹却越来越有好感。后来,他去了上海交通大学,但仍一直和在天津的杨敏如保持着通信。
杨敏如高三时,收到了罗沛霖寄来的一本他亲手制作的纪念册,上面写着:“幸福的环境往往使人自纵,我常以此自戒。现在我以十二万分的好意,来劝告我十分敬爱的朋友,千万不要让幸福毁损了你纯厚的天性。”当时,大家都开玩笑说:“咱们的小敏如居然都有了自己小男朋友了!”但杨母眼中,罗是订过婚的,因此很反对他们这样的“交往”。
1934年,杨敏如考进了燕京大学中文系。大二的时候,她遇到了自己这辈子最敬重的一位师长——顾随先生(本名顾宝随,字羡季,笔名苦水,别号驼庵。著名韵文、散文作家,文学批评家、美学鉴赏家和书法家,他的学生、红学泰斗周汝昌说他是“一位正直的诗人,同时又是一位深邃的学者”)。据杨先生回忆说:“顾先生的课讲得精彩极了,每次顾先生来上课时,教室的过道里、窗台上都坐满了人。顾先生身体不好,坐骨神经痛,上课时,穿着棉袍子,进了课堂,放下书包,会先抬头用温和的目光扫视一遍坐在台下的同学,再从书包里拿出经他批改过的我们的上周作业,往桌角上一放,然后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他昨天写的一首词,才开始娓娓地谈论起来。当读到一首唐诗,或者一首宋词时,他的兴致来了,眼睛里会放出光来,一片神往的样子。接下来,就会旁征博引,把他的心、神、学问、灵魂全交给我们了。他这哪里是在讲诗,分明是在讲人生,讲做人!他一会儿外文,一会儿古文,一会儿又转到京戏上去了。我在上他的课时,思想从来不敢开一点小差儿,生怕记漏了一句……
“当时,我才开始学填词,竟得到了顾先生的赏识。但我从来不敢登门造谒,甚至不敢到教员休息室,单独求教。”1937年春天,罗沛霖在信中告诉了杨敏如一个对于杨敏如来说,可谓是天大的好消息——他和冯家的婚约解除了。杨敏如幸福得哭了。然而,她还没有从收到罗的这封来信的喜悦中平静下来,“七七事变”爆发了。
“‘七七事变’后,燕大停了半年课。半年后,恢复上课,来到悬挂着美国国旗的燕大,燕园依旧,师生依旧,钟亭的钟声照常响起,但是,风雨如磐,山河破碎,未名湖已失去了它往日的生气。顾先生也一下子老了许多,课上,他讲了很多有着明显的弦外之音的话。他常自称是弱者,并常以此自嘲,来掩饰其内心的痛苦。其实,在我们看来,他才是真正的清醒者和勇者……“由于国事日艰,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半,我始终无法开心起来,当时我的心境,完全可以用秦少游的一句词来形容,那就是‘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
1939年,杨敏如马上就要毕业了。当时,妹妹静如也已去了西南联大读书,此前她曾多次在信中表达了希望姐姐去大后方的愿望,“你还要在灰色的北京待多久?”她原已做好了一毕业就南下的准备。就在这时,时在燕大任中文系系主任的郭绍虞(名希汾,字绍虞。是著名教育家和语言学家)找到了她,建议她继续读研。当时,燕大和哈佛之间有合作关系,燕大的研究生很容易去哈佛留学,这在当时看起来,也不失为一条很好的出路。但是杨敏如在读了半年研究生之后,终于由于忍受不了燕园,乃至整个北京压抑的气氛,同时,也因罗沛霖这时已经到了重庆(他1935年从上海交大毕业后,先去了广西南宁无线电厂工作了几个月,然后回到上海,进了中国无线电业公司,任工程师。1937年8月,日军进攻上海,12月南京陷落。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他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于是,和那个时代的很多进步青年一样,奔赴了革命圣地延安。1939年,组织上把他派到了重庆,以工程师的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在此后的九年中,他先后担任过重庆上川实业公司、新机电公司、中国兴业公司和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无线电厂重庆分厂的工程师,为抗战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所以还是决定要南下。
她说:“我要离开燕园了,临行前,到顾先生家去了一趟。这是我第一次到顾先生家,我告诉他,我要去内地了。先生道:‘走吧,能走就走吧!’
“我终于走了,到了重庆,在重庆南开中学开始了我的教师生涯,那一年,我22岁。刚走上讲台的时候,我还不太会教,怎么办呢,心都跳到嗓子眼儿了。我想,我模仿!模仿谁呀,只有模仿顾先生。他拿学生当朋友,那我也拿学生当朋友;他不讲师道尊严,那我也不讲师道尊严。我的学生们都很喜欢我,但当时我并不知道。直到后来,我80多岁了,他们也都70多岁了,他们来看我,拿出来从前的笔记本给我看,说那时候你讲的内容,你给我们改的诗,我们现在都还记得……
“我在南中一待就是七年,头两年教的是英文,后来才改教文学。南中曾办过一个实验班,学生都是十二三岁的孩子,规定老师必须全英文讲课,看着那群天真活泼的孩子,我是发自内心的爱他们!开始,我给他们上课时,还怀着几分忐忑的心情,边说英文,边用手比画着,没想到竟然成功了,两年的时间,这些学生的英文水平都进步得飞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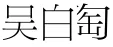

杨敏如的哥哥杨宪益和嫂子戴乃迭

杨敏如和爱人罗沛霖
1941年,重庆,兄妹“双婚”,罗家伦、张伯苓分别为他们证婚
1941年,杨敏如和罗沛霖在苦恋了十年后,终于要结婚了。而此时,杨敏如的哥哥杨宪益也和他的英国女友戴乃迭一起从英国回到了重庆,并正在筹办婚礼。由于罗沛霖当时在国民党当局的黑名单上已属于“注意思想倾向、加紧监视”的类别,上级指示他立刻脱离由著名民主人士章乃器(著名社会活动家和经济学家,救国会“七君子”之一,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创始人之一)主持的上川实业公司,并着手建立和维持一种新的掩护关系。于是,杨敏如就和哥哥商量,想要一起举行婚礼。他们兄妹的感情一向很好,哥哥自然没不同意的道理。婚礼那天,杨敏如和戴乃迭穿的婚服一个绣着梅花,一个绣着凤凰,两位新郎穿的都是丝棉长袍。杨宪益和戴乃迭的证婚人是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罗沛霖和杨敏如的证婚人是南开中学的校长张伯苓(当年,罗去延安时,张伯苓还为他给周恩来写过信)。婚礼办得相当热闹,来了不少名流,燕大的校长梅贻宝和即将担任教育次长的杭立武也都来了。这一年,罗沛霖28岁,杨敏如25岁。
抗战胜利后的1948年,罗沛霖接到党组织的指示,要他去加州理工学院学习。杨敏如在送别了丈夫之后,也回到了天津,任教于南开大学,1951年,又去了天津津沽大学(今天津师范大学的前身)教书,并去西南参加了土改工作,还写了入党申请书,但当时组织上觉得她还是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更能发挥其所长,于是,她便依照组织的希望,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天津解放时,杨敏如接到了罗沛霖的来信,请她代他向上级请示,是否立即回国。组织回复让他继续安心在美国求学,但他还是通过努力,提前拿到了博士学位,于1951年,回到了国内。
罗沛霖回国以后,组织上把他安排在了北京电信工业局工作。1953年,杨敏如也从天津调到了北京,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还写了入党申请书,直到1986年,才以70岁的高龄退休。
杨先生生前是这样回忆她在北师大的执教生涯的:“我来北师大后,开始教的是外国文学,主讲俄罗斯和苏联文学。但我不会俄文,这使我感到很苦恼,又由于我的出身,每次运动来时,我都会受到冲击,因此一度情绪都十分低落。当时,我只有到北京郊区为中学教师授课及在学校中文系教授‘八仙过海’课时,才能些许快乐……
“‘文革’中,我和我老伴都在各自的单位受到批斗,我们被隔离了。那时,有人来问我,还要不要和罗沛霖在一起,每次,我都坚定地回答:‘要!’我那时就总想,罗沛霖是党员,曾经去过延安;抗战时,他去重庆也是党派他去的。不管他出身如何,他一直都是爱党爱国的,所以他肯定会没事的!
“‘文革’后,我终于又可以登上我心爱的讲台了。我要求调到古典文学教研室,校方很痛快地就答应了。于是,我又改教了古典文学,这是我最擅长的,也是我最乐意向学生传授的。”
“我在北师大一直工作到了70岁,才办理了退休手续。退休后,我在家里闲不住,只要有学校邀请我,我就会去给他们上课。就这样,一直教到80岁才不再出去讲学了。但我仍舍不得离开讲台,又在社区居委会的协助下,在社区老年活动中心办了个班,义务为社区里的退休老人讲宋词。他们还都挺爱听我讲的,讲完了宋词以后,他们又让我讲《红楼梦》,讲完了《红楼梦》以后,又让我讲唐诗。书法好的人会事先帮我在黑板上写好板书,居委会的负责人会把我的讲义打印出来,分给大家……”
2011年4月17日,98岁的与杨先生相濡以沫了一辈子的罗沛霖先生去世了。杨先生伤心不已,她曾深情地回忆说:“我老伴平时最喜欢对别人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这辈子就她一个女朋友,她这辈子也就我一个男朋友。’别人听了,就开玩笑地对他说:‘那你可真亏了啊。’他就望着我,傻傻地笑……在我们那个年代,烽火四起,硝烟弥漫,谈爱情真是太奢侈了。如果一定要我来说一说,我和罗沛霖的爱情,那么我的理解就是,我们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对很多事情都有共同的看法,正是这种共同的价值观,促成了我们的结合。我们两个人年轻时都很忙,在一起没有怎么玩过,直到老了以后,才天天待在一起了。每天下午我们都会喝下午茶,他为我冲上一杯咖啡、切上一块点心,便凝固住了我们今生最美好的时光……”
如今,杨先生也去了。一生桃李满天下的她曾经说过:“我在短暂的生命中抓住了永恒。”我想,她的音容,肯定会长久地留在她的学生们的心中。
参考资料:杨敏如《一个教师的生平自述——在短暂的生命中我抓住了永恒》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