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记忆,时间的诉说
曲慧钰

在波兰的某处,有个名叫太古的小镇,它位于宇宙的中心,由四个大天使守护着村落的东南西北四个边界。“倘若步子迈得快,从北至南走过太古,大概需要一个钟头的时间,从东至西需要的时间也一样。但是,倘若有人迈着徐缓的步子,仔细观察沿途所有的事物,并且动脑筋思考,以这样的速度绕着太古走一圈,此人就得花费一整天的时间,从清晨一直走到傍晚。”在这里,人们生活其中,却又无法逾越。那些自以为走出太古的人,不过是在边界处靠着隐秘的墙进入了梦乡。梦醒之后,他们返回太古,把梦境当作了回忆。就这样,人们在太古生生死死,连超越时间的上帝也无可避免地老去。
小说开篇,奥尔加·托卡尔丘克(Olga Tokarczuk, 1962— )就这样将故事的中心置于这座充满奇幻色彩、与世隔绝不受侵扰的“世外桃源”之中;而后用时间和人性的碎片,讲述了同一空间不同时间中一群人的生命历程。84个章节,84块时间的裂片,灵动精巧地复写与重构着变形的历史与族群。在这里,历史变为碎片,融成流体,折射出斑斓的光芒并奔涌至未知的方向。太古这地方就像书中主人公米霞的小咖啡磨,或任何一件物品一样,无数双手抚摸过它,它也旁观着代代更迭的青春、磨难、巅峰和死亡,抒写着关于特殊时期平凡人的尊严,关于爱、欲望和徒然的失去,关于早已谱写的命运和冲破束缚的灵魂。
“百年孤獨”:关于时间的抒写
伦敦时间2018年5月22日,2018年度布克国际奖授予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这位被誉为“20世纪90年代波兰文坛一颗璀璨新星”的女作家,1987年凭借诗集《镜子里的城市》初登文坛,而后接连出版了《书中人物旅行记》《E.E》《太古和其他的时间》等多部长篇小说,曾两度荣获“尼刻”文学奖,近年来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之一。奥尔加善于以碎片化的方式重述历史,在作品中融合民间传说、神话、宗教故事等元素,同时又观照波兰的历史命运与现实生活,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神话。其成名作《太古和其他的时间》便是此种风格的延续。
《太古和其他的时间》(1996年发表,2017年在中国出版)是一本女性写就的时间之书,无穷辽阔也无穷细碎。小说全篇以“×××的时间”命名,通过不同的视角讲述了太古之中各种人物甚至动植物和物件的故事:触摸世界边界的少女、沉迷游戏的地主、寂寞的家庭主妇、咒骂月亮的老太婆、上帝、天使、恶人、椴树、洋娃娃……在这里,非人的时间与人的时间平行向前,交织并进。有多少种存在,便有多少种时间,无数短暂如一瞬的个体融合为一种强大的、永恒的生命节奏。这里的一切都不过是时间的某种变幻方式,就像书中描绘的两条河流,它们时而泛滥,时而清浅,既繁衍无数生命,也摧毁生命无数,最终却汇合在一起“平静地,心满意足地继续向前流去”。奥尔加就这样以一种梦幻般的叙述方式重构了世界,在时间的流淌中,将历史与家族、人与土地、生命的长度与厚度娓娓道来。
故事的时间起点设置于“一战”前夕,以米霞的一生为参照,记录了她从婴儿到女童,从少女到人妻,从母亲到外婆,从出生到死去的整个人生。20世纪的历史下,波兰小村庄中小人物们的生、死、情、恨与万物相交汇,有直接的残酷也有简洁的温暖……在这里,过去、现在、未来都被投入了米霞那小小的咖啡磨中,一圈一圈,弥漫着煮糊的牛奶、老旧的衬衣以及青草和森林的气息。她周围的人和物,她与父辈、孙辈三代人的历史都裹挟在时间的洪流中,共同经历着战争的硝烟、家园的重建、物质文明的侵蚀,最后又迷失于时代通往现代化的路途之中。在这期间,有人出走有人回归,有人离世又有人降生,但太古却是永恒的存在。最后,随着米霞的女儿阿德尔卡的离开,太古只剩下老父亲帕韦乌一人,坐在院子里看着坍塌的房屋,时间仿佛停止于此刻,属于太古的时代随着最后一个第三代人的离去而终结,随之而来的是永恒的沉寂。
从“一战”前到“二战”后,几代人的悲欢离合、年华老去、沧海桑田都在这部时间之书中得到了卷轴般的呈现,三代人的人生故事也折射了波兰20 世纪动荡起伏的历史命运。世界由一个个时间里的故事组成,生命在一个个时间里流逝,碎片的时间拼合成了波兰历史的长流,在这由无数个体碎片组成的巨大时间横流中,很难指明谁才是其中的主角。正如奥尔加所说,她的写作方式是一种“星群小说”,她将故事投入轨道,让读者自行生成对他们而言有意义的形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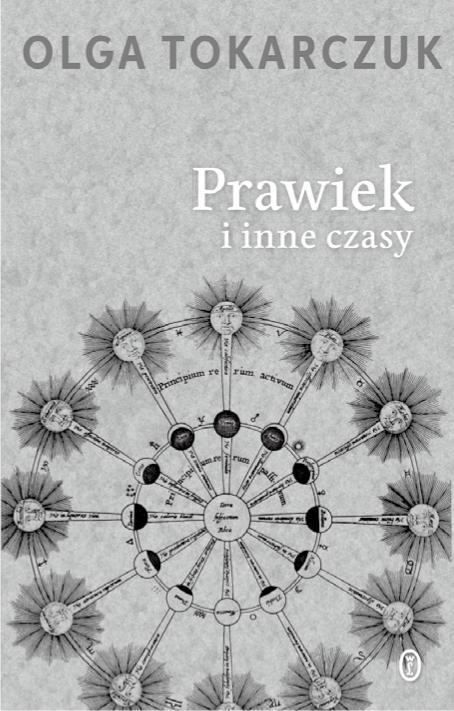
《太古和其他的时间》是一个建立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重复循环的象征框架中的现代神话,时间的轮回重复、命运的类似都使小说隐含了无数大大小小的循环怪圈。奥尔加借用“太古”和村落中三代人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和神话传说来重述民族性,并以超凡的冷静态度记录了两次世界大战对波兰民族的创伤。太古虽然不存在,但其所凝聚的每个人、每株树甚至鬼魂的故事都太真实。时间背后的时间,比人间里的人间更迷人,太古的生民久久徜徉在时光的褶皱里,生息歌哭,日升日落,随着现实与神话的重叠糅合,太古模糊了时空的边界,混淆了人与万物的差别。“上帝在关注,时间在流逝。死亡在追逐,永恒在等待”,先人的脸也会出现在后代身上,上帝的八个世界都是梦。战争过了,交媾过了,太古的人将一切都抹去了,只有梦。
上帝的“八层世界”:信仰与现实的解说
“地主波皮耶尔斯基失去了信仰。他没有停止信仰上帝,但上帝及其余的一切都成了某种缺乏表现力且单调的东西,就如他那本《圣经》里的插图。”于是上帝派来一位矮小的拉比送给他一盒迷宫游戏——《Ignis fatuus,即给一个玩家的有教益的游戏》(Ignis fatuus为拉丁语,意为“难以忍受之火”),这是一个蕴藏造物之谜的游戏棋盒,上帝透过游戏向地主显现自己。在游戏中,上帝创造了“八层世界”。这是一种寻找出口道路的游戏,从迷宫的中心开始,目的是通过所有的层次,从八个世界的羁绊中解脱出来。这“八个世界”看似仅存在于游戏之中,但每个世界的景象又与太古的发展进程共同生息。
在这里,奥尔加运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在创造古老神话故事的同时,又坚实扎根于当下社会,形成了一个充满符号隐喻的世界,令人从容反视生命和爱情的种种。
在“第一世界”中,上帝尚未全然清醒,还无法肯定自己究竟是什么。造物主迷惑且不自知,通过他人理解自己,求知的热望也就随之产生。“斯芬克斯之谜”始于上帝,人便开始了自我探知的旅程。太古就位于这一层的世界之中,这里的生民和谐努力地生存着,在享受自然馈赠的同时,又认真思考着世界的运转。
“第二世界”是上帝年轻时创造的,这里的一切都黯淡而模糊不清,所有东西都更迅速地瓦解并分裂成齑粉。亚伯在田野中杀死了该隐,石头在饥饿的孩子们手上瓦解撒落,战争会永远进行下去。此时的太古也经历着战争的侵扰,成群结队的波兰军队打破了小村落的平静,残酷的死亡开始了它的侵蚀。人们出生,绝望地相爱,迅速地暴死。
“第三世界”是动物的世界,这里既没有上帝也没有人,有欲望而没有理性。动物为了报复而淹死了上帝,在这里“因为什么而战斗,就会因为什么而死亡”。
随后,上帝在狂热中创造了“第四世界”,他狂热地爱着人类,但人却弃他而去,开始寻找新的生活。人们叛逆着,自由意志随之觉醒,在战后的家园重建中努力追赶着时代的浪潮。
在“第五世界”,上帝因孤独而变得烦躁,他开始夺走忠实信徒的一切,而后又以“金钱、欲念、恐惧”归还,于是圣徒约伯那比上帝更为强烈的光辉逐渐熄灭以至于完全消失。此时的太古,私念和欲望开始蔓延,阿德尔卡产生了希望得猩红热的妹妹死掉的念头,因为她们占用了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斯塔霞渴望被爱,而护林员却在发泄性欲之后将她抛弃。自由意志觉醒后,随之而来的是道德的丧失。
上帝在偶然创造“第六世界”后便出走了,人学会靠自己的意志力创造自己,却因冲动而再次陷入混乱。上帝再次归来后,将所有创造物全部摧毁,现在的“第六世界”空无一物,沉寂得有如混凝土的坟墓。地主此时已经被时间的洪流所淹没,他的家族开始振兴,却遗失了上帝和人类的游戏玩具。上帝的缺失标志着“世界之夜”的开始,神性的光芒黯然失色,人们张扬理性却也迷失于此,即使那“第三个人”降临于世,走在身旁,世人也无法将他认出。在这样的时代里,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片“荒原”。

“第七世界”出现了巴别塔之乱,上帝感到了威胁,于是便把人们分散到世界的四面八方,让他们彼此成了仇敌。斯塔霞的儿子最终没能见母亲最后一面;孩子们在米霞死后留下父亲离开了太古;帕苏尔在米霞死后将她的弟弟送进养老院任其自生自灭……在这个世界,亲人产生隔阂,而死亡让留下的人开始后悔。
在“第八世界”,上帝已是垂暮之年,其所创造的世界也令人费解。他停止了活动,凡是不动的,都停滞在原地;凡是停滞在原地的,都在瓦解。离开某一个地方的人开始返回原点,一直停留在原点的人开始踏上新的征程。在上帝之外甚至包含上帝本身在内的秩序里,凡是看似正在时间里流逝、分散的一切,同时也开始了另一种存在——超越时间限制的恒久存在。
在奥尔加的笔下,上帝在游戏的时间里创造了好几个世界,在无穷的时间变化中显现着自己的力量。他存在于所有无定型、起伏不定和容易消逝的事物之中,海面涨落、大陆漂移、冰川融化、種子发芽、胎儿生长、眼角皱纹,都是上帝呈现自己的方式。关于八个世界的设定,关于上帝的猜想,关于光明与黑暗的再创作,传说、史诗、神话、生活就这样和谐完美地交织在小说之中。在新旧交替、世界改变、信仰不在的时代,奥尔加成为乡情和民俗的守护者,她努力体现现代文明的可怕,并对古典、传统、朴素民风和大自然怀有无与伦比的敬意。作者在引经据典的同时,又创造性地改编着它们:在太古世界中,人被驱逐并非出于原罪的惩罚,而是因自由意志觉醒主动离去;与《圣经》原典不同,亚伯将该隐杀死在了田野中,谄媚和欺瞒的自私人性得以显现;被剥夺了一切物质财富的约伯,其精神的光芒甚至超越了上帝,而随后的物质嘉奖却又掩盖了其神性的光辉,物质与精神的难以统一显示了永恒的人性困局。奥尔加清楚地知道这个时代的贫乏,诸神的逝去,使世人失去了庇护,也失去了获得自身本性的能力,于是便陷入一股死亡的绝望气息之中。其笔下黑暗迷失的“人间地狱”不只属于一个人,它属于整个城市,整个战后的世界,整个时代。奥尔加正是以这种方式,书写了东欧的百年历史,同时也创造了一首观照人性、慰藉灵魂的童谣。
背后的小森林:被遗落的原始记忆
“寻根”主题是奥尔加创作的重要内容,在回答波兰《政治周刊》记者的提问时,她就曾表示,写《太古和其他的时间》这部小说似乎是出于一种寻根的愿望:“许多作家都会在某个时刻重返家庭叙事。家庭故事是我们童年记忆中能分享给陌生人的最私密的部分,这部小说确实受到了我祖母的家庭故事的启发。距离它的创作已经过去了20多年,我把它看作我的青春时代的映射。”带着寻根的初衷,奥尔加着意构想了与当代物质文明对立的、充满奇思妙想的原始世界,寻找自己在历史上的定位,而后回归自然,就像太古生民那样,当“世界的磨盘停止了转动,机械损坏,他们在官道上的积雪里跋涉,走向森林”。
奥尔加笔下的太古村庄,是一个古老、原始、远离尘嚣、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神秘国度,在此繁衍生息的人们固守着自己独特的传统、习俗和信仰,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日子。在这里,作者将童年时代的回忆理想化,与社会现代化进程中被污染的贫瘠土地、大都会的钢筋水泥以及城市的喧嚣相并置,因此我们看到这里的每片土地都充满了意义,对自己的居民赐以微笑。太古的象征意义就在于,人们心灵深处都守望着一个被自己视为宇宙中心的神秘国度,在快速变革、大规模迁徙、灾难丛生的世界中,这个角落拥有着人们渴念的某种稳定和足以抗拒混乱的宁静。太古是美好的,并且美得很具体,万物和谐的同时又教会人去跟宇宙打交道,去探寻人生的意义和万物存在的奥秘。整个村落都流贯着一种生命的气韵,融通着人和天地万象的生命境界,透过它能识破天机,看到上帝,看到永恒。
当物质文明随着战争的硝烟踏足太古时,一切的原始美好开始崩塌。政党、工厂、酒宴、狩猎、殷勤的大胸女招待、神父牧场旁新建造的房屋……太古的边界在通往现代化的路途中被渐渐打破,它的每个原始居民都被吞噬在这“文明”的浪潮之中。然而,无论是想要“往高处走,向高处爬”的帕韦乌,还是为了好看的衣裙和高跟鞋而出卖自己,堕入冥王之手的现代帕尔赛弗涅——鲁塔,抑或是对城市生活充满向往,最后逃离村庄的阿德尔卡,都无法摆脱原始的羁绊。在某个醉酒后的不眠之夜,在没有自由的金丝鸟笼,迷失的太古人想起了久违的村庄,感到自己像个被遗弃的孩子,每秒钟都在瓦解成虚无,并且同虚无一起崩溃。这就是现代人的生存危机,在有关死亡命题的新思考中,束手无策地看着自己一步步逼近黄昏,走向空虚与黑暗。
奥尔加通过太古的历史展示了原始村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命运走向,以人道主义情怀杂呈偏远乡村的众生百相,一群不同性格、不同年龄、不同家境的人物,承受着命运的拨弄、生老病死的困扰和战争浩劫的磨练,在生活的甬道里直觉地活着,本真地活着。他们的喜怒哀乐非常直露,家庭纠葛又非常情绪化,他们追求幸福或燃起欲望的方式都散发着原始气息,均为波兰百姓饮食人生的自然写照。生命在此处诞生,死亡在这里轮回,文明在此处流产,暴力在这里重生,爱情在此处萌芽,仇恨在这里生根。村落孕育了文明,暴力摧毁了村落,最后,随着被遗弃房屋的赫然倒塌,太古的一切就此止步。与世隔绝的太古终究躲不过时间和人类的洗礼,有些东西终将逝去,也有一些东西会最终留下。而那些离去的人啊,你们还会不会记起这停泊在现实中的梦?那片被遗忘在房子背后的小树林和那空气中弥漫着的泥土芳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