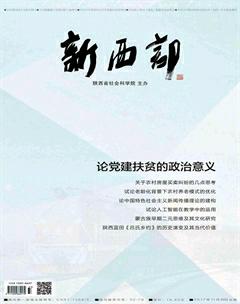浅析阿萨德时期叙以关系的演变
【摘 要】 叙利亚与以色列是中东地区严重对立的国家。经过三次中东战争使得以色列占领叙利亚戈兰高地。哈菲兹·阿萨德执政时期(1970—2000年)三十年间,叙利亚努力实现与以色列的战略平衡,使叙利亚从一个衰弱分散的小国成为地区强国。其间双方就戈兰高地问题多次展开了和平谈判,但是叙以双方态度强硬,在戈兰高地等问题上互不让步。2000年6月随着阿萨德的突然逝世,叙以和谈一切归零,双边关系因格兰高地等问题而毫无进展,从而造成叙以两国无法正常化发展。当前正值叙利亚内战的局势,双方的和谈将在近期一段时间内不会得到解决。
【关键词】 阿萨德;叙利亚;以色列;戈兰高地
哈菲兹·阿萨德(Hafiz Assad)执政前,叙利亚以泛阿拉伯主义为治国理念,坚持与以色列的对抗。阿萨德执政后,叙利亚采取灵活务实的对以政策,努力实现与以色列在军事、政治上的战略平衡。20世纪九十年代叙以和谈启动,但双方在戈兰高地等问题上僵持不下。2000年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ssad)执政后,叙以双方虽有重开和谈愿望,但双方立场分歧严重,随着叙利亚内战的愈演愈烈,叙以双方和平谈判遥遥无期。
哈菲兹·阿萨德执政时期,叙利亚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形势,中东地区自古战乱不断,阿萨德上台后,“在国内大力推进‘纠正运动的同时,在对外政策上做出调整,并开始积极参与中东事务。此后的30年中,在哈菲兹·阿萨德的领导下,叙利亚逐渐成为了中东地区的大国。”[1]在对以关系上,1970年到2000年这30年间,在总统阿萨德的领导下叙利亚与以色列的关系大体经历了战争冲突时期、战略平衡时期、政治谈判时期。
一、战争冲突时期
阿萨德执政后,叙利亚面临严峻的国际形势。“70年代初期,叙利亚采取积极介入中东事務的对外政策,并在与自身国家利益相关的国际冲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这一时期,叙以在对黎巴嫩问题上加以干涉最为典型 ,并且在这一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当时苏联和美国竭力维持中东“不战不和”的局面,避免引起直接对抗。萨达特继任埃及总统后,主张通过战争手段打破当时的局面,此时的叙利亚与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冲突严重,而埃及总统的这一战略思想与叙利亚总统的战略思想不谋而合,因此,叙利亚总统积极与埃及交好,并且希望借助埃及之手夺回失地戈兰高地。
经过战前的积极筹备,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也称“十月战争”)。战争爆发后,埃及和叙利亚两国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支援,战争初期占据了主动权。此时的埃及和叙利亚不采取速战速决地手段,转而求助于联合国进行协商停战,以停战之名从而达到收获失地的目的。这一做法使得以军借此机会进行反击,从而使得埃叙两国由胜而败。面对叙以冲突,美苏大国为了控制局势,从而直接介入中东事务。在美苏的倡议下,联合国安理会于10月22日通过338号决议。决议指出:“交战各方停止所有军事活动,至迟不得超过本决议通过后的12小时,并立即开始执行安理会242号决议的所有部分;各有关方面于停火之日起,在适当方面的支持下,立即开始谈判,目的是在中东建立公正和持久的和平。”[3]
战后,美国逐步调整对阿拉伯国家的政策,通过日内瓦中东和会到基辛格“穿梭外交”,促使叙以双方做出让步。1974年5月,叙以代表在日内瓦签署了脱离接触协议:“以色列撤出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占领的叙利亚部分土地,包括戈兰高地首府库奈特腊城;在叙以军队之间设立1.6—6.4千米宽的缓冲地带,由联合国维和部队驻扎;叙利亚释放以军战俘,交还阵亡士兵尸体等。”[4]至此,叙以敌对状态逐渐发生变化。
二、战略平衡时期
“埃以单独媾和后,叙利亚独扛反以大旗”,[5]考虑到埃及在美国影响下追求和平的政策,叙利亚出于对自身安全考虑,希望本国在综合实力上能够与以色列相抗衡,于是,阿萨德开始进行军事建设,主要通过“大规模军事力量的建设;进一步加强与苏联的合作;加强对近邻国家的军事和政治事务的影响力,包括约旦、黎巴嫩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6]在对外交往中,叙利亚重视与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关系。此外,叙利亚也与俄罗斯相交甚好,以备俄罗斯在必要时给予军事上的援助。
这一时期,叙以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对黎巴嫩的争夺上。“1981年12月14日,以色列议会通过关于在戈兰高地实施以色列法律的法案,非法吞并戈兰高地”,[7]这一做法引起了叙利亚国内对以的仇视,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从而使得叙以在黎巴嫩的对抗升级。1982年6月6日,以色列向黎巴嫩发动名为“加利利和平”的军事行动。其主要目的便是要摧毁叙军在贝卡谷地的导弹基地,进而将叙军从黎巴嫩驱除出境。在反击以色列时,叙利亚遭受了重大的破坏。在美苏的调解下,叙以停止了在黎巴嫩的对抗。以色列不仅在这次侵略战争中重创,而且激起了国内的厌战情绪。当然黎以冲突也使叙军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但是,战后叙利亚在苏联的军事援助下,军事实力超出了战前水平。此外,叙利亚通过黎国内穆斯林的传统亲密关系,在黎巴嫩问题上再次掌握了主导权,促使黎巴嫩局势按照叙利亚设置的方向发展。叙黎传统的亲密关系再次得到了证实,阿萨德追求的叙以平衡发展的战略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但是,“到1985年苏联对外政策开始发生变化,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他几乎立即开始限制叙利亚的军备建设”。[8]1987年4月阿萨德访问莫斯科时,戈尔巴乔夫也明确表示:“依靠武力解决阿以冲突的做法已彻底名誉扫地,莫斯科不再支持叙利亚谋求同以色列达成战略平衡,应寻求政治途径解决冲突。”[9]1988年后,对于叙利亚而言,中东地区的局势也异常严峻,特别是两伊战争中叙支持的伊朗战败后,加之埃及重返中东事务,叙利亚几乎处于被孤立的状态,已经无力与以色列再战,因此,这一时期处理好与以色列的关系变得更加重要。
三、政治谈判时期
政治解决叙以关系的进程主要通过谈判来实现,但是推进叙以政治进程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其关键问题在于叙以双方就具体问题上的严重分歧,虽然和谈对叙以双方来说希望渺然,但面对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叙总统阿萨德通过权衡局势而努力尝试。endprint
1989年后,叙利亚在同以色列的对抗中,军事上不占有绝对优势。苏联领导也对其减少了外交上的援助,此外,两伊战争中支持伊朗从而使叙利亚在阿拉伯世界陷于孤立。因此,叙利亚开始积极与阿拉伯国家交好。
“海湾战争给了阿萨德总统一件礼物,使叙利亚在陷于孤立和与西方大国处于敌对关系后重返中东和国际舞台,并有可能重新回到叙利亚在1970年代曾经有过的、叙利亚自己称之为‘阿拉伯阵线的基石的地区大国地位。”[10]
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在美国倡议下于10月在马德里开启了以主要解决阿以冲突为主题的中东和平谈判。当年9月,布什政府曾在《和平谅解备忘录》中提出:“美国承认戈兰高地为叙利亚领土,但同时承认戈兰高地对以色列安全的重要性。”[11]叙以双方接受了美国的提议,但叙当局表示在戈兰高地问题没有解决的前提下前仅限于参加和会举行的双边谈判。1991年11月,以色列议会通过《捍卫戈兰高地法》,进一步确认了高地为以色列领土。但在1992年9月,以色列首次表明“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也适用于戈兰高地。到1993年近三年内时有间断的谈判约进行了11次,但基本上没有取得进展。[12]1993年双边谈判中,巴以签订了《奥斯陆协定》结束了半世纪以来相互敌对的局面。随后,1994年约以签订《和平谈判》也使得双方的战争状态宣告结束。然而,作为双边谈判中重要的一环——叙以谈判却屡屡受挫,由于叙黎特殊的关系,导致黎以和谈也毫无进展。双方的争论在戈兰高地等问题上僵持不下。从而导致叙以和谈陷入僵局。1995年11月4日,拉宾总理遇刺,1996年6月以色列利库德集团上台执政,这届领导人在叙以争论的焦点格蘭高地等问题上表现的很强势,双方领导人在具体谈判的细节中都互不妥协,从而使得谈判毫无进展。2000年6月10日,随着叙总统阿萨德的突然病逝,叙以谈判从而搁置。
四、结语
哈菲兹·阿萨德执政时期,叙利亚逐渐走向地区强国的位置。阿萨德统治叙利亚30年内的叙利亚,不仅结束了国内动荡的局势,而且在对外活动中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些成就得益于阿萨德在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的前提下,充分把握国内外形势,通过借助以美苏为首的大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进而积极施展叙利亚参与中东事务的热度息息相关。阿萨德灵活的强势治国谋略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除了利用国际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与周边国家发展平稳关系外也与阿萨德本人独特的战略眼光、灵活的外交手段及适度的强硬政策有关。诚然,叙以和平谈判仍然任重道远,关于领土争端也好,宗教冲突也罢,近年来,叙以和平进程随着叙利亚动荡不安的局势而变得扑朔迷离,关于叙以未来的发展学术界目前没有更好的解决之策,只能随着形势的不断演变而进行推测分析。
经过叙以多年的间断性战争表明,靠武力无法解决双方在既有问题上的矛盾。战争的双方在借助外部势力的支援下对抗数年的结果对双方经济及社会的稳定等方面是极不利的。想要很好的解决当前双方所面临的困境,亦或者往后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问题,唯有在政治洽谈过程中的相互包容与互相协作。从叙总统阿萨德执政的三十多年对以政策来看,叙以双方的问题解决进展缓慢,而叙以双方问题之所以呈现这些特点主要使受各方势力的影响,国内外各方势力的干涉导致叙以内外博弈激烈,政治谈判屡遭挫折,政治进程变得漫长而复杂,政治解决前景不容乐观,但是叙以关系的问题将以政治谈判解决的态势仍将持续。
【参考文献】
[1] 王新刚.叙利亚与黎巴嫩[m].北京:商务出版社,2003.286.
[2] 季国兴、陈和丰等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战争全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271.
[3] David E.Long Bernard Reich,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Westview Press,2002,p.243.
[4] 李荣建.阿拉伯研究文集.2015年,第269——270页.转自:刘彦军.阿萨德时期叙以关系探析 [D],2005年硕士研究生.
[5] Anges G.Korbani,U. S. Intervention in Lebanon:1958 and 1982,London,New York Westport Connecticut,1991,p.63.
[6] 尹崇敬.中东问题100[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156-157.
[7] Halena Cobban,The Superpowers and the Syrian-Israeli Conflict,Washington D. C.the Center for the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1991,p.21.
[8] Moshe Maoz,From Conflict to Peace? Israels Relation with Syria and the Palestinians,Middle East Journal,Vol.53,No.3,Summer 1999,p.413.
[9] 新华社开罗,1992年6月25日电.
[10] 徐向群,宫少朋,中东和谈史:1913-1995[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43、244.
【作者简介】
郝红梅,西北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