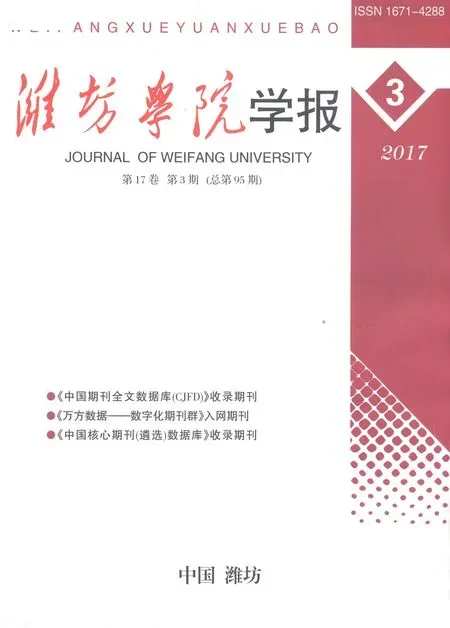诉讼调解合意引导机制研究
赵宣珍
(潍坊学院,山东 潍坊 261061)
诉讼调解合意引导机制研究
赵宣珍
(潍坊学院,山东 潍坊 261061)
正当的引导是诉讼调解合意有效生成的关键因素。但由于“调审合一”模式限制、对抗式思想浸淫、考评指标不当、调解者经验与技能不足等原因,合意引导出现越位或缺位的异化现象,使得调解合意难以或不当生成。为消除诉讼调解合意引导的异化现象,建议调审适度分离,优化调解考评要素,实行调解释明,提升法官与当事人的调解参与度,加强法官及司法辅助人员的调解技能培养。
调解;诉讼调解;调解合意
作为一种“合意”纠纷解决模式,诉讼调解因契合中国传统“和合”文化,具有彻底解决纠纷、修复当事人关系、降低纠纷解决成本、促进社会和谐等诸多功能价值,成为当事人和法官解决纠纷的优先选项,也得到国家法律和司法政策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支持。其中,具有标志性的是,2012年修订《民事诉讼法》时,将“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确立为正式的法律规则。从数据统计看,调解在诉讼实践中也一直得到广泛应用,2013—2016年全国各级法院分别以调解方式处理案件479.8、461.9、498.1、532.1 万件。[1]但是,实践中,由于调解的“合意”无法和不当生成,大量案件最终没有以调解方式结案,许多以调解方式结案的案件,最终的纠纷化解效果也不甚理想,诉讼调解反悔率和申请执行率居高不下。有的法院甚至出现调解结案的民事案件,与判决结案的民事案件强制执行数量基本相同,甚至超过判后强制执行数量的情形。[2]应当说,影响诉讼调解“合意”生成及结果实现的因素有很多,但与当事人相互讨价还价式的自主合意不同,诉讼调解合意的恰当引导,是确保诉讼调解合意生成且有效的关键性因素。笔者将立足提升诉讼调解合意的有效性,探讨如何建立规范的诉讼调解合意引导机制。
一、诉讼调解合意引导的必要性
“合意”是调解的核心要素。有学者认为,合意“是指主体间对实施一定行为所要达成目的之共识”。[3]一般而言,合意的形成,标志着相互对立的当事人就纠纷解决达成一致,也就接受了纠纷解决的方案。在诉讼调解中,合意是调解各方参与人共同努力的目标,调解的一切活动和程序都围绕着纠纷解决的“合意形成”而展开。但由于纠纷解决的方式已进入诉讼阶段,恰当的引导对于“合意形成”就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一)引导是“调解合意”生成机理的本体要求
调解是一种在第三方参与主持下,争议各方当事人达成一致协议的纠纷解决方式。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相比,调解是唯一“第三方参与+当事人合意”的纠纷解决方式。和解与调解均为“合意”形态下的纠纷解决方式,正如日本学者棚濑孝雄所言,“和解、调解等等,凡是最终以当事者的合意来终结纠纷的程序都是‘合意’的例子。”[4]但是,和解中的合意生成,完全是当事人在没有第三方力量作用下,通过谈判或协商方式达成的。而调解中的合意生成,则是在第三方的参与下,当事人才达成的。“如果要说调解与和解的区别,关键就在于第三者的参与能够促使当事人达成合意。”[5]仲裁、行政裁决、司法裁判与调解均属于第三方力量起作用的纠纷解决方式,但是,前三种方式皆为第三方决定纠纷解决的结果,无需当事人的合意。“不站在当事者任何一方的第三者居中说合,帮助双方交换意见,或者在明确纠纷对立点的基础上提示一定的解决方案,往往能够促进当事者双方形成合意。像这种第三者(调解者)始终不过是当事者之间自由形成合意的促进者,从而与能够以自己的判断来强制当事者的决定者区别开来的场面,可以视为调解过程的基本形态。”[6]因此,调解与仲裁、行政裁决、司法裁判的区别,关键就在于存在当事人的自由合意。综合起来,第三方参与,引导当事人自由形成合意,是调解合意生成的内在机理,也成就了调解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不同,以及其在纠纷解决中的独特优势。

不同纠纷解决方式中第三方作用与合意生成比较
(二)引导是消除诉讼调解合意障碍的必要手段
依据矛盾纠纷“自治—调解—裁判”的递进化解规律,进入诉讼阶段,意味着矛盾纠纷解决难度的加大,同时也意味着当事人之间合意难度的加大。“当事人将纠纷提交给第三人(不论是调解者还是审判者)加以解决,就已经表明当事人之间通过自行交涉达成合意的努力已经失败,或者已经预见了这种失败。”[7]矛盾纠纷以诉讼案件的形态呈现,意味着矛盾纠纷在性质、内容上具有较强的复杂性,矛盾纠纷的证据认定、事实评判、法律适用,不仅在当事人之间存在争议,许多诉讼案件因为涉及利益、思想冲突等原因,社会公众也容易产生认知上的分歧。[8]就当事人而言,则意味着进一步强化了双方对抗者的角色,造成了双方的对立情绪的升级。因此,矛盾纠纷进入诉讼阶段,因由矛盾纠纷性质和内容的复杂性,诉讼构造下双方对抗状态的自然加重,使得当事人之间的合意生成存在重重障碍。“对权利人来说,选择调解无异于放弃权利或遭受诉讼的不利益,若没有利益诱导,则很难形成调解合意。”[9]诉讼调解作为设置于诉讼阶段,促使当事人生成合意的纠纷解决手段,调解者必须更加注重做好引导工作,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尽可能为当事人自由达成合意消除障碍。
二、诉讼调解合意引导的异化
一直以来,我国实行的是“调审合一”的诉讼模式,调解法官具有审判者和调解者双重身份,对调解合意的形成起着相当大的影响作用。从司法实践看,大量矛盾纠纷以诉讼调解方式结案,意味着法官或司法辅助人员较好地进行了当事人之间调解合意的引导。但诉讼调解的合意引导也存在着种种异化现象,具体可分为两个类别:第一类为调解者的“越位”引导,表现为调解者对当事人双方合意生成的过度干预,又可分为压迫式引导和引诱式引导两种;第二类为调解者的“缺位”引导,表现为调解者对当事人双方合意生成的消极、不参与态度,又可分为程序不参与和程序或实体上的不干预。
(一)引导的越位
由于“调审合一”的程序设计,加上调解率,以及与上诉率、发改率、服判息诉率等与调解密切相关的法官能力评估与业绩考核指标的设置,导致一些法官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甚至将调解作为规避办案风险的手段,在调解中采用强迫式、引诱式手段,影响了调解合意形成的自愿性,动摇了调解协议履行的基础。
1.压迫式引导。由于诉讼调解的程序特点,调解者的审判者身份本身就对当事人具有潜在的压力。“调解是审判权的行使方式,而审判权本身又具有强制性特征,审判者的身份及其所拥有的审判权对调解中的当事人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10]如果法官再采用“以劝压调”、“以判压调”等方式对当事人的思想行为施加压力,就会逼迫当事人以违背本意的方式接受调解。这种强迫式引导,妨碍了当事人合意形成的自主化,致使当事人虽然有“调解合意”的结果,但心底难以信服、接受,也降低了当事人主动履行调解合意的意愿。
2.引诱式引导。合意形成以当事人信息充分沟通为前提。在调解过程中,当事人信息不对称、不充足情况下达成的调解合意,其合意考虑难以周全,依据是贫瘠的,合意基础不稳定。当事人信息不对称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观方面主要是当事人由于法律知识、诉讼技巧、诉讼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在客观方面,由于调解允许私自会谈,不像审判程序那样要求证据公开、质证,实践中,有的法官乐于采用“背靠背”的方式进行调解,在这一过程中,基于促成调解的主观愿望,法官可能向当事人隐瞒一些对纠纷解决起决定作用的信息,甚至用虚假信息对当事人进行“不实诱导”,促使当事人做出让步,导致当事人在占有信息不全或错误的情况下,达成调解合意。在这种情况下达成的诉讼调解合意,一旦当事人获得更多的信息,或者情势发生变化,很容易引起当事人对合意的反悔。
(二)引导的缺位
由于诉讼对抗式思想的浸淫,加上案件数量成日益剧增态势、调解经验不足,部分法官对诉讼调解持不作为态度,放任当事人调解合意的形成。具体来说,一是表现为程序上的不参与,由此导致的后果是,第三方引导这一调解合意生成的必备要件难以形成;二是表现为程序或实体上的不干预,由此导致的后果是,部分当事人以调解之名,行拖延诉讼、规避义务履行之实。
1.程序上的不参与。诉讼调解没有规范严格的程序,也不以明确的法律规范为依据,使有的法官在调解过程中,完全以一个消极的中介者角色出现,不向当事人进行必要的权利引导和法律释明,导致合意摸索的长期化、复杂化、低效化。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形成合意,也会因为成本过高成为一种低效益或负效益的合意,与诉讼调解节约诉讼成本的功能优势相违背,从而会引发当事人对达成诉讼调解合意的不满。
2.程序或实体上的不干预。有些当事人同意调解,并不是基于解决纠纷的目的,而是出于投机心态,企图通过虚假调解谋求非法利益。在该情形下,法官以调解为当事人自由处分权为由,对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调解行为不加干涉,就使得当事人滥用调解成为可能,造成对另一方当事人甚至国家、社会第三方利益的损害,也会极大地破坏诉讼调解的正面价值。如有的当事人没有调解诚意,只是将调解作为拖延诉讼的诉讼策略,无节制的提出调解请求;有的当事人将调解当作恶意规避判决、减轻义务的手段,抓住对方当事人急于解决纠纷的心态,不仅要求减少支付,而且要求分期履行,到最后仍然不主动履行调解书内容,即使对方提起申请执行,却只能申请执行让渡后的给付内容。
三、诉讼调解合意引导的规范
诉讼调解“合意”的生成,需要作为调解者的法官或司法辅助人员积极、正当的引导行为。针对诉讼调解实践中引导越位与缺位并存的现象及发生原因,笔者将从以下四个方面提出规范诉讼调解合意引导的建议。
(一)减少法官对调解程序的过度控制,防范合意压迫化
我国“调审合一”调解模式,容易造成调解者对当事人明确或潜在的“控制力”,是形成合意压迫化的重要原因。逐步改变“调审合一”调解模式下法官“控制力”的倾向,赋予当事人更大的调解程序选择权,使法官权威在调解过程中更多地体现为“影响力”,是防范诉讼调解合意压迫化的最佳方向。对此,一是要对现有“调审合一”模式进行改善,探索建立“调审适度分离”的诉讼调解模式。具体而言:设立审前调解程序,在审前对适合调解案件进行调解;保持现有调解制度和程序的稳定,赋予当事人对调解者身份更大的选择权,在当事人选择调解程序后,由其再对调解法官从审前调解法官和审判法官中进行选择。这样,根据当事人意愿选择确定的调解者,自然会得到当事人更大的认同。二是要对现行考评体系导向予以纠正,从调解率转向调解质量与效果。如前文所述,虽然大部分法院不单纯以调解率对调解工作进行考核,但是考评中的服判息诉率、上诉率等都与调解率有很大关系,致使法官对于调解结案仍然相当看重,在办案过程中的具体表象就是对于调解程序过分的控制。因此,对于调解工作的考评,并不是单纯“去调解率”化的问题,而应进一步对考评要素进行明确,特别是将能够反映调解效果、质量的一些因素,如当庭履行率、自动履行率、调解申诉率、调解申请再审率作为重要参考,这样才能防止其他考评因素对调解考评的不当影响,减缓调解法官对调解过程和结果控制的压力和冲动。
(二)推进诉讼调解公开,保障当事人对调解信息的知情权
公开可以“使公正的司法行为转化为社会公众的‘经验感受’,无疑会增加和积累公众对司法的信心和信任。”[11]诉讼调解公开,是消除当事人和社会质疑的有效方式。针对诉讼调解中,一些法官基于促成调解的意愿,对于调解程序、调解权利、调解信息等进行隐瞒或误导,致使当事人达成的合意依据不足、内容贫瘠,当事人难以履行的状况,应着力推进诉讼调解公开,以公开拉近与当事人的心理距离。对此,一是要向当事人充分释明调解的“权责能”。调解释明包括对调解权利、义务以及风险等诸多方面,以确保当事人在充分权衡基础上作出抉择。具体包括:调解权利的释明,对调解权利进行充分告知,既要告知有利权利信息,如程序选择权、程序处分权以及申请再审权利等,也要告知不利权利信息,如调解案件无上诉权;调解义务的释明,即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恶意调解以及不履行调解协议、调解书义务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调解风险的释明,就调解可能存在的自身权利的让渡、履行不能等问题予以说明;调解内容的释明,调解过程中当事人声明或表述不清楚、不充分时,法官可以给予必要提醒;等等。二是以“面对面”为主推进调解。目前,与透明度更高的“面对面”调解方式相比,“背靠背”调解方式受到了更多批评。“在实践中,这种方式常导致法官与当事人讨价还价,甚至对当事人哄骗、说好话以说服当事人接受调解,法官的中立地位与尊严也难以得到维持。”[12]但是,“背靠背”调解可以避免当事人双方针锋相对,平复当事人激动情绪,容易提高调解的成功率。因此,从当事人接受诉讼调解的角度出发,不能简单地禁止采用“背靠背”方式,应坚持“面对面”原则为主,由法官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灵活掌握,并在征求当事人同意的基础上适用。
(三)增强互动性,提升法官与当事人的调解参与度
当前,我国诉讼调解仍然是一种职权化的调解模式,法官主导地位凸显,在调解信息流向上呈现出法官向当事人的单向传输,当事人表达意见渠道不畅通,法官与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当事人之间信息交流不足,与诉讼调解“平等——接受”的方向不一致,也影响了诉讼调解的效能。为此,在调解过程中,应坚持三方互动的原则,建立法官与双方当事人充分参与沟通的机制,赋予当事人更大的意见发表权和辩论权,“确保当事人能够在自由、平等的氛围中,就与纠纷有关的事实和法律问题,进行坦诚而理性的对话……在双方充分的信息交流基础上寻求并达到某个形成合意的契机”[13]。要实现这一愿景,需要法院对于诉讼调解参与氛围的积极营造。诉讼调解程序相对于审判程序,更加强调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的充分参与,更有利于信息全面、准确的沟通与交流。在这一过程中,调解法官应当更好地发挥桥梁作用,“在沟通双方意见方面,在双方当事人中架起沟通的桥梁,传递双方掌握的案件信息和意见,避免因双方情绪对立而形成沟通上的障碍。”[14]同时,赋予当事人更多的发表意见和获得倾听的权利,因为“一个人在对自己的利益有着有利或不利影响的裁判或者决定制作过程中,如果不能向有权做出裁决的人或机构提出自己的意见、主张,不能与其他各方及裁判者展开有意义的论证、说服和交涉,就会产生强烈的不公正感。”[15]
(四)加强技能培养,提升法官及司法辅助人员调解合意引导的能力
调解与审判对于法官在知识、能力方面的要求大不相同。调解更多地是依据情理和当地的风俗习惯,对法官社会经历和经验要求很高。然而,当前我们的法官在能力培训中,更多地是侧重于法律知识、法律技能的培训,对于调解知识、技能的培训有相当差距。从法官个体而言,目前大量经过现代法律系统训练、法律专业的毕业生进入法院,法官队伍呈现专业化、年轻化倾向。这些“学院派”的年轻法官,在现代西方司法理念的影响下,更愿意“追求在办理疑难案件中通过主持对抗性的庭审弘扬司法的权威。因此,他们往往对调解不感兴趣。同时由于自身在调解技巧和经验方面的欠缺”[16],开展调解的意愿并不高,在调解能力培养方面也不会用心。致使一些法官对于调解过程中当事人的不良动机,由于调解能力不足,难以认清,也无从防范。根据日本学者棚濑孝雄的观点,诱导合意形成的根据可归纳为,社会常识、法律规范、事实关系和潜在的合意。因此,法官调解技能的培养也应是综合性的,不仅包括法学功底,还需要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而且社会常识、常情、常理以及调解技巧对于调解合意形成至关重要,这需要长期的调解经验积累来获得。可以多采取以老带新、案例分析、经验交流等方法,加强这方面的交流学习,促进年轻法官调解能力的尽快提高。
[1]数据来源于2014、2015、2016、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2]胡夏兵.调解案件进入执行程序的现象值得重视[N].人民法院报,2013-08-26.
[3][14]唐力.在“强制”与“合意”之间:我国诉讼调解制度的困境与出路[J].现代法学,2012,(3):87.
[4][6][日]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M].王亚新,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2001:62.
[5]赵旭东.纠纷与纠纷解决原论—从成因到理念的深度分析[M].u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46.
[7]何石.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和谐价值[D].海口:海南大学,2009:8.
[8][11]赵宣珍.诉讼案件社会答疑制度研究[J].潍坊学院学报,2016,(5):46-47.
[9]唐力.诉讼调解合意诱导机制研究[J].法商研究,2016,(4):122.
[10]尹力.中国调解机制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120.
[12]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361.
[13]闫庆霞.法院调解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156.
[15]李季宁.民事诉讼程序正义论[M]//诉讼法论丛:第二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417.
[16]范愉.调解的重构:上——以法院调解的改革为重点[J].法治与社会发展,2004,(2):118.
Research on the Guiding Mechanism of Litigation Mediation
ZHAO Xuan-zhen
(Weifang University,Weifang 261061,China)
Proper guidance is the key factor for the effective generation of litigation mediation agreement.But because of the reason of the mode of mediation and trial limitation,adversarial thought,evaluation index,improper steeped mediator skills and experience lack of consensus guidance,alienation or absence of offside,the mediation agreement is difficult or inappropriate.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alienation of litigation mediation agreement guide,we recommend the moderate separation of mediation and trial,optimization evaluation elements,interpretation,and suggest improving the judge and the parties mediation participation,strengthening judges and judicial support staff mediation skills training.
mediate;litigation mediation;mediation agreement
王玲玲
D925.114
A
1671-4288(2017)03-0041-05
2017-03-24
本论文得到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国内访问学者项目经费资助
赵宣珍(1974—),女,山西平陆人,潍坊学院法学院讲师,法律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