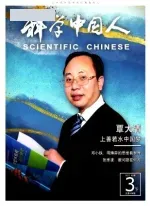医学与医德
——白岩松在2017中国整合医学大会上的报告整理
医学与医德
——白岩松在2017中国整合医学大会上的报告整理

白岩松作报告
最近一段时间,我越来越觉得,我在中央电视台是兼职,做与健康有关的工作是专职。前天,我在参加“健康中国说”的活动;昨天在鸟巢参加“三减三健”活动的启动;今天来到这儿;今天晚上,我周刊的节目关注的是107篇医学论文的流程有假的问题,但我的出发点不是批评医生,而是谁制造了这样的环境。做1000台优秀的手术,都比不上1篇不那么真的论文。
精神抚慰是最大的治疗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为医生说话?第一个,因为我跟医生一样都姓“白”。第二个,我是卫生部的健康宣传员,到现在已经10年了,昨天李斌主任又给了我一个证书,又给10年。第三个,当然是最重要的,我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更是一个患者,替医生说话是因为我还不傻。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医患关系,表面上你骂两句医生,今天好像受委屈的是医生,明天受委屈的就会是我们自己。
中国只有两个职业是带“德”的,一个教师,一个医生。为什么?你看其他职业,用职业道德笼统地涵盖了,而这两个职业是单独计算的。原因在于,教师要负责人们的精神健康,而医生要负责人们的肉体健康。其实还不止,教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教书容易,育人难呐!医生要肉体治疗,还要有精神抚慰,肉体治疗相对好评估,但是这个精神抚慰如何做呢?“德”字就在精神抚慰和教书育人之间诞生了。
什么是“医德”?我觉得任何解释都是苍白的。我讲两个故事。100年前,协和招生。其中一个考场在上海,福建的一个小女孩想当医生,去了上海考试。最后一科考英文,协和对英文要求极高,她答了几笔,考场里面一个女生晕倒了。没想到,这个考生放弃了自己的考试,出去救助这个女生,等她救助完女生,考试已经结束了。她没有任何怨言,明年再考吧!
但是监考老师看到了这个过程,把此事告诉了协和,协和调看了她前几科的成绩,最后决定录取她,因为她拥有当一个好医生没法教的最重要的“德行”:宁可牺牲自己,也要照料别人。这个福建女孩的名字叫林巧稚,也就是郎主任的前辈。严仁英讲了林大夫的一个细节,他说,产科病房里由于病比较重,是哀嚎、是不安、是凄凉。但是林大夫来了之后,一边治疗,一边跟患者聊天,突然一瞬间,病房里呈现出极其温暖的安宁。我觉得,这就有超越技能的、需要我们思考的东西。
再比如,有一个大夫叫华益慰,我在做“感动中国”的时候他是获奖者。看他片子的时候,我的眼泪哗地就下来了,不是因为高超的医术,而是一个小小的细节。打他当医生开始,每天早上查房之前,都要先把听诊器放在自己的肚子上焐热,才进病房,他一辈子没让患者遭到过一次凉的听诊器。

报告现场
武警总医院的急诊中心主任王立祥,给我讲了他的一个经历。一个孩子,出现了紧急情况,送到了他们急救中心。王立祥刚要开始救,发现没法救,孩子已经没了。但是病房外,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全都跪在那号啕痛哭。急啊!要救这孩子!王立祥觉得,如果现在立即就告诉他,孩子没得救了,可能会出事儿。他要给家属接受的时间,他又给这个孩子做了一个多小时完全无用的治疗。但是在这一个多小时里,有很多的大夫在外面劝家属,给他们讲很多事情,让他们慢慢有一个缓冲地带。一个多小时之后,这个无效的治疗结束了,但有效地治疗了这个家庭。
我谈的这3个故事,都与医学的技能和治疗本身无关,但是谁能说这不是一个更大的治疗呢?
医生也有普通人的烦恼
我们每个人生、老、病、死,全要跟医生打交道。所以,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医生是界于普通人和佛之间的一个职业,这句话要分两个层面解读。
一方面,每个医生都是普通人。他们有喜、怒、哀、乐,有自己的挣扎和抱怨,他们是普通人。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的工作是面对别人的生、老、病、死,他就天然地具有了佛和上帝的某些属性。
现在加拿大的总理叫特鲁多,他是帅哥,天下粉丝很多。但是我认为他再帅,都不如100多年前那个去世的加拿大人帅,那个医生叫特鲁多。因为那个特鲁多的伟大,不仅仅在于他是第一个提炼出结核杆菌的人,更重要的在于他墓碑上的那3行字“偶尔去治愈,经常去帮助,总是在抚慰”。
现在的医生委屈很多,我做着如此伟大的事情,为什么人们还骂我?我替各位想了几个原因。第一,人们对你的依赖大,期待就大,抱怨自然多。做任何政府部门调查、年终评议,最后发现好感度和坏感度最高的都是人们需求最旺的部门。一般跟人关系不大的部门好评度很高,因为反正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点个赞嘛!
2015年的时候,中国的门诊人次接近80亿,想想看在这当中能不出问题吗?千万不要认为只有中国才有医患矛盾,全世界都有,只不过呈现的方式不一样。在美国,每家医院外面都有律师递小广告给患者,“有事找我,我来给你赢医生”。
有一个段子,在天堂里,医生找上帝,发现上帝特忙。他说:“你忙什么啊?”“哎哟!今天有一个律师要来。”这个医生生气地说:“好嘛!我们医生在天堂还要住上下铺,为什么一个律师来还要铺红地毯?”上帝说:“没办法,天堂里到处都是医生,律师是我当上帝以来第一个见到进天堂的。”这是美国人编的段子,也反映了美国式的医患关系。
第二,对这件事情还有另外一种解读。过去,人由于对死亡无法掌握,所以把它交给了宗教。所谓“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过去人们不抱怨,如果得了病或者病没治好死了,这是天意。现在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人们产生了一种幻觉,认为“医学无所不能”。因此,出了问题他就不再怨命、怨上帝,他就怨医生。但其实现代人对健康更在意,对死亡更恐惧了,但是又产生了“医学无所不能”的幻觉,可是事实并不是如此。于是,这种反差和矛盾使现在这种冲突变得更多,人们不再像以前一样心平气和地接受事实。
很多医生委屈,我做这么大的好事为什么还有委屈呢?从来都是这样,好事多磨大家都听过吧?我去台湾专门求证这件事,我跟台湾慈济的证严上人聊天,我问他:“为什么做好事还要受难?”他很平静地回答:“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你不觉得被磨的石头才亮吗?”医生就是被磨的石头,您见哪块宝玉,您见哪个伟大的东西不是被磨才亮,最后才成为最有价值的东西。
另外,我觉得大家要有一个警觉。虽然现在的大数据无所不在,但是对医生的一个重要的挑战就在于,你的挑战永远是动态的。大数据永远不解决个体问题,因此您不管拥有了多伟大的数据,您治了多少病人,新来的患者都是全新的。
刚才我看的那篇报纸上写,钟南山院士跟王辰院士跨境为一个特殊的患者做会诊,最后艰难地拿出一致的意见,你看哪一个个体能用大数据来解决?所以我们正在面临一系列这样的挑战。
医德问题是制度的产物
社会上对医德的要求极高,但我的观点是,任何站在道德基础上谈论道德都是无效的。不能指望我们的医生都是圣人,道德归根到底是由外在的环境和制度决定的,如果环境和制度是糟糕的,好人也会变成坏人。
我推荐大家看长篇小说《曾国藩》,小说讲过一个细节,曾国藩很廉洁,但即便这样,他也要干很多灰色的事情,为什么?晚清时候,官员腐败。为什么腐败?科举考上了京官,官家不出路费,到北京需要一千多两银子,全部需要自筹。他怎么自筹?只能说我现在要当京官了,只能挨家挨户地求,让他们给我点钱,将来替你办事儿。到了北京,京官的薪水一百两银子多一点儿,但是维持最低的生活需要三百多两银子,那二百两银子哪儿来?不腐败哪儿来?请问是清朝的官员腐败,还是晚晴的制度腐败?
所以,前些天北京医改,我当天就做了节目。我说了一句话,从此我们可以对医生产生更大的信任,因为让有些医生变得不得不糟糕的环境正在松动和改变。过去医生要替医院创收,要有药品加成,要开更贵的药,医生不做能行吗?这是涉及整个医院的生死存亡啊!现在取消药品加成,我对这次北京医改说了4个字叫“人涨物降”——与人有关的价格要上涨,与物有关的价格要下降。中国的医改必须加速,必须快速行进才能把医生从道德的窘境中解放出来。
现在我们的医生在替迟迟无法有勇气推进的医改在背黑锅!因此,如果环境清朗、制度明晰,再出现医德的问题,那就是我们从业者当中要有一定比例的接受度,哪一个行业都会有自己的败家子儿,但我们现在的败家子儿大比例是由环境和制度逼出来的,所以整个社会要去反思这个事情。
最后,我要讲一个和自己有关的故事。我在好多场合讲过,我最近几乎不讲了,但是今天这个场合比较大,我还是想讲一下。在1970年代,我父亲总咯血,去天津出差,我妈就说,办完公事看个病。我爸办完公事当天晚上要走,下午去天津医院看病,结果医生一看,坏了,癌症。
但是他不好当面和我爸说,就说:“不行、你必须要住院。”我爸说:“怎么可能?我晚上就要走。”医生说:“那不行,你这个必须得住院,需要详细观察,得治疗。”我爸拿出车票说:“你看,我都买了今天晚上的车票回海拉尔!”“不行、不行,你必须留下,让主任回来劝你。”那医生就去找主任了。我爸一看,撒腿就溜了。
晚上,在天津火车站候车室里,突然大喇叭里传来这样的声音“黑龙江来的***,请到门口有人找……”我爸以为是天津的同事,结果到了门口看见一辆救护车,还有下午的那个医生。原来那个细心的医生记住了我爸的车次,然后我爸被送上了救护车,送到了医院。虽然1976年我父亲去世了,这个医生没有治好我父亲的病,但是他治疗了一个家庭。
1989年,当我大学毕业要回北京工作的头一天晚上,我妈把这个故事完整地讲给了我。到现在我都没有细聊过,为什么我妈要把这个故事讲给我,我猜想这里有一种信任,有一种对社会的善良,有一种感恩。我还会把这个故事继续讲给我的孩子们听,我想有无数个医生都会像那个医生那么做。但是,我妈有一句话当天还有点刺激,她说:“如果现在的技术加上那个时候的医生,也许你爸的病可以治好。”
我觉得我要修改成“如果现在我们制度与环境松绑之后,让蒙在医生身上的那些灰尘都被剔除掉,那些扭曲都被剔除掉之后,再加上现在的技术,很多的患者都会得以治疗”。更重要的是,好的医生不仅仅是我给你治病,还要带动患者一起参与到健康的流程当中,非常感谢各位,谢谢!
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