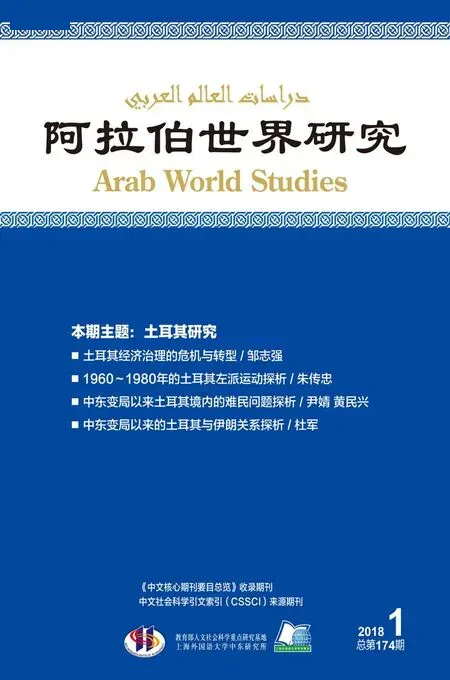印度洋视域下的中东海洋安全合作研究
方晓志 胡二杰
中东地区位于印度洋的北端,重要的海域包括阿拉伯海和波斯湾(又称阿拉伯湾),通常被称为“印度洋北部的弧形战略地带”*宋德星、白俊:《“21世纪之洋”——地缘战略视角下的印度洋》,载《南亚研究》2009年第3期,第32页。,被列入“大印度洋”的地理范畴,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诚如美国学者卡普兰所言,“如同欧洲勾勒出了20世纪的世界格局轮廓一样,大印度洋(西起非洲好望角,途经阿拉伯半岛、伊朗高原和印度次大陆,一路向东延伸至印度尼西亚群岛)可能构成对新世纪来说具有象征意义的世界格局图景”*[美]罗伯特·D.卡普兰:《季风:印度洋与美国权力的未来》,吴兆礼、毛悦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从全球地缘战略格局来看,该地带构成了欧亚大陆柔软的腹部,是欧亚大陆唯一面向温水海洋的地区,且拥有苏伊士运河、红海、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等多条海洋交通要道。所以,控制该地区不仅意味着可以从海洋方向上掌控整个印度洋,而且还有助于在陆地方向从“边缘地带”向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渗透。随着全球能源需求和海上贸易的逐年递增,该地带已不仅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战略区域之一,还因为区域内根深蒂固的矛盾和难以调和的利益冲突,成为世界上爆发冲突风险最高的地区之一。
一、 印度洋视域下的中东海洋安全历史演进
从19世纪中期到二战结束前的一个世纪里,印度洋是“大不列颠的内湖”,地区海洋安全主要由英国维护。贯通东西半球的苏伊士运河开通后,其沿岸地区成为英国军力部署的重心所在。二战后,国力衰落的英国迅速从印度洋地区收缩力量,其留下的权力真空被美苏两国竞相填补。在这场权力角逐中,美国竭力加强对波斯湾的控制,极力遏制苏联力量的进入。冷战结束后,美国调整军事战略,在波斯湾等地投放强大作战力量,并依托迪戈加西亚基地等强化对印度洋的军事控制。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洋海权“美国独霸”的权力结构开始松动。面对中印两国的崛起,美国奥巴马政府提出“印太(Indo-Pacific)”战略概念,试图通过印度洋将东亚和中东连为一体,以便更好地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
(一) 19世纪中期到二战结束前: 英国主导的“大不列颠内湖”
15世纪末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开辟通往印度的新航路后,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法国等欧洲列强即在印度洋展开角逐,对沿岸国家进行掠夺和殖民。英国自17世纪开始努力构建以印度为战略支撑、涵盖整个印度洋海区的“东方殖民体系”。在1805年特拉法加海战后,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进一步巩固,在印度洋的势力范围迅速扩展。英国人在1820年抵达波斯湾,1824年吞并新加坡,1839年抵达亚丁。至19世纪中叶,英国几乎控制了印度洋所有的入口,占据绝对优势。印度历史学家潘尼迦对此这样描述道:“至于印度洋,这就比别处更像是不列颠的一个内湖了。诺大的印度洋面,其他欧洲国家一点好处也沾不上手,就是在海洋附近的地方,亦复如此。”*[印度] K.M.潘尼迦:《印度和印度洋——略论海权对印度历史的影响》,德隆、望蜀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69页。这种主导地位一直持续到二战,英国基本维持了印度洋的海上安全,实现了所谓“英国治下的和平”。
在英帝国主导时期,对于中东地区而言,苏伊士运河的竣工具有跨时代的意义。1869年运河开通,中东海域贯通东西半球的咽喉要道作用凸显,成为无可取代的世界海路交通枢纽。恩格斯曾作如此评价:“由于交通工具的惊人发展——远洋轮船、铁路、电报、苏伊士运河——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4页。虽然运河最初由法国人修建,英国却在19世纪70年代通过巧取豪夺,逐渐控制运河,并在1882年通过武力占领,完全掌握运河的所有权,随后在运河沿岸部署重兵。欧洲其他列强不满英国的垄断地位,联手争夺运河的自由通行权。1888年,德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西班牙、荷兰、奥匈帝国等国共同签订《君士坦丁堡公约》,旨在确保所有国家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使用苏伊士运河。1904年,英国加入该公约。
总体而言,自19世纪中叶以来,“印度洋实际上一直是英国的一个湖泊,而且在某一时期大部分沿岸国土都是大英帝国的组成部分或在大英帝国的保护下。”*[美]E.B.波特:《世界海军史》,李杰、杜宏奇、张英习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743页。但进入20世纪后,英帝国开始由盛转衰,尤其是经历了惨痛的两次世界大战后,其国力遭受重创,全球殖民体系土崩瓦解,从印度洋地区进行力量收缩已是大势所趋。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以埃及实现运河国有化而告终,英法继续控制该地区的殖民主义努力遭到了沉重打击。1964~1968年,英国经过痛苦的决策过程,最终决定在1971年底以前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出全部军力,此举是英国一流大国地位终结的重要标志*参见张新利、翟晓敏:《20世纪70年代美国对波斯湾的“双柱”政策》,载《世界历史》2001年第4期,第54页。。二战后兴起的“侧翼大国”美国和苏联旋即成为印度洋地区的主要利益角逐者。
(二) 冷战期间: 美苏争霸逐渐让位于“美国独霸”
早在二战期间,美国军舰就开始频繁在波斯湾活动。1944年,美国临时组建驻守中东的第五舰队,虽然这支部队在战后遭遣散,但战时“美国在阿拉伯、中东、巴林群岛的油权,表明了它同印度洋区域的经济联系正在大大增长……美国将从目前的战争中形成全球的而不是半球的战略思想,所以必须想到美国作为一个主要海军强国进入印度洋的可能性”*[印度] K.M.潘尼迦:《印度和印度洋——略论海权对印度历史的影响》,第84页。。1946年,美国迫使苏联从伊朗北部撤军,开始填补地区力量真空。之后,美国迅速打破英国在海湾地区的优势地位,至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伊朗的石油公司已占油田总股份的40%以上。*刘金质:《冷战史(上)》,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70页。
二战后,英国开始战略收缩,美国乘虚而入,试图成为印度洋的新霸主。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美国与盟友英法立场迥异,美国坚决反对英法诉诸武力,以免苏联乘机在阿拉伯世界扩展势力。美国的影响因此进一步扩大,“英国和法国在中东地区的历史地位被占夺后,美国发现中东地区势力均衡的责任已经责无旁贷地落在美国肩膀上”*[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525页。。为填补地区力量真空,美国在1966年向英国租借迪戈加西亚岛用作军事基地。该岛位于波斯湾东南大约2,500海里处,在战略上易守难攻且便于向东西半球投送军力。此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印度洋海洋秩序的主导者,为西方国家保护来自波斯湾的石油和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战略原料。到1980年,日本、西欧和美国使用的石油中,分别有73%、63%和15%是依靠油轮从波斯湾输入。*[美]E.B.波特:《世界海军史》,第743页。
美国不仅在波斯湾地区部署本国军力,也积极扶植伊朗和伊拉克等地区盟友以供驱使。伊朗自1953年摩萨台政府被推翻后,便成为美国在波斯湾地区最重要的盟友之一,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均受到美国的渗透和控制。1979年秋,亲美的伊朗巴列维政权在伊斯兰革命中被推翻,革命领袖霍梅尼提出“不要西方,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的主张,美伊关系一落千丈。同年12月,苏联大举入侵阿富汗,试图开辟进入波斯湾地区的陆上通道。美国对此反应激烈,“卡特主义”随即产生,卡特政府表示:“任何企图控制波斯湾地区的外来势力都将被认为是对美国根本利益的侵犯,我们将采取任何必要手段,包括武装力量在内,反击这种企图。”*梅孜主编:《美国总统国情咨文选编》,北京: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656页。从非洲之角到阿富汗的印度洋西北边缘地区也被卡特政府描述为“危险弧形地带”*[美]托马斯·巴尼特:《五角大楼的新地图》,王长斌、汤学武、谢静珍译,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44页。。
中东地区的形势变化迫使美国寻求更为迅捷的远程投射能力和更靠近波斯湾的印度洋军事基地。美方寻求军事基地的努力获得了阿曼、肯尼亚和索马里三国的积极响应。美国立即接受了与阿曼和肯尼亚的合作,并在一番犹豫后最终接受了索马里以军援换取港口使用权的提议。在获得三国的基地后,美军开始进行兵力部署。1981年2月,美国快速反应部队开始进驻新基地。美国的地区盟友体系也发生了较大变化。1980~1988年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和伊朗背后分别得到美苏的支持。这场战争对两伊而言胜负互现,对美国而言则借机进一步稳固了对中东地区安全的主导权。
美国逐步成为印度洋新霸主的同时,其主导地位却面临另一超级大国苏联的强劲挑战。在1945~1946年的伊朗危机中,苏联虽因美英的压力而被迫撤军,但美苏在中东地区较量也随之开始。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苏联积极支持埃及将运河收归国有,借机打击西方在中东的势力。苏联的行为赢得了不少阿拉伯国家的好感,为其进一步介入中东地区提供了良好契机。20世纪60年代后,国家综合力量不断扩展的苏联希望分享中东和非洲地区的资源,通过成立印度洋分舰队,与美国海军分庭抗礼。阿拉伯海、波斯湾和亚丁湾地区成美苏争夺的焦点。
1968年,在英国确定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军后,苏联舰队在北印度洋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巡航。此后,苏联舰队持续不断地在印度洋地区出现。苏联不仅着意显示海军实力,也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与印度、南也门和索马里签署了互助友好条约。这些条约使苏军得以使用印度洋港口。早在1963年,苏联就以军援为名获取索马里的摩加迪沙、基斯马尤港的使用权,并在亚丁湾南侧援建了柏培拉港。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曾将索马里视为“亚安体系”*“亚安体系”全称“亚洲集体安全体系”。1969年6月7日前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提出这一计划,该计划旨在通过分化和控制亚洲国家,取代美国成为亚洲盟主,实现苏联称霸亚洲的目标。但这一主张和设想遭到大多数亚洲国家的拒绝和反对,一直未能实现。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表示:“我们的目标是争取控制西方所依赖的两大宝库——波斯湾的能源宝库和中非与南非的矿产宝库。”*[美]E.B.波特:《世界海军史》,第745页。苏联于1968年成立隶属于太平洋舰队的印度洋分舰队,1969年又获得也门港的使用权,并在阿拉伯海与亚丁湾连接处的索科特拉岛扩建海空军基地,逐步将触角伸向阿拉伯海和北印度洋。不过,苏联尚无力直接对抗美国在印度洋的强势地位,只能采取有限的兵力介入,同时利用地区国家间的矛盾,扶植亲苏势力。1977年,苏联盟国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爆发欧加登战争。苏联在权衡利弊后,决定转而向埃塞俄比亚提供军援和支持。苏联因此失去了拥有三百万人口的索马里盟友和柏培拉海军基地,却获得拥有三千万人口的埃塞俄比亚盟友和马萨瓦港海军基地。1979年,苏联大举出兵阿富汗,并扶植起傀儡政权,旨在从陆上打开经波斯湾南下印度洋的通道。
然而,苏联受总体实力与海军兵力结构的制约,在与美国的印度洋竞逐中逐渐落入下风。尽管苏联军舰时常在印度洋重要海域游弋驻足,却难以获得制海权优势。苏联海军核潜艇部队规模庞大,但大型水面舰艇数量有限,在与美国海军的较量中难有作为。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里根政府奉行“新冷战”政策,开始对苏联的海上扩张进行全面遏制。苏联则陷入了阿富汗战争的泥潭,已无力与美抗衡。至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的印度洋分舰队在包括中东海域在内的印度洋地区已难觅踪影。
(三) 后冷战时期: “美国独霸”逐渐过渡为“多国存在”
伴随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美国在印度洋地区几乎掌握了绝对“制海权”。1990年8月,伊拉克突然入侵科威特,对美国中东霸主地位构成挑战。美国随即发动海湾战争,重创伊军,迫使后者撤出科威特。海湾战争意味着美国军事战略思想开始转变。海军上将威廉·欧文斯(William A. Owens)在战后感慨道:“对于美国海军来说,沙漠风暴是变革的助产士。”*William A. Owens, High Seas: The Naval Passage to an Uncharted World,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5, p. 4.1992年,美国海军发布《由海向陆——为美国海军进入21世纪做准备》战略白皮书,宣告海军战略思想开始转变。波斯湾地区成为美国海军实践“由海向陆”、进行前沿部署最重要的区域之一。1995年7月,美军重建第五舰队,统辖波斯湾、阿曼湾、阿拉伯海、亚丁湾、红海地区的美国海军部队,受美国中央战区司令部指挥,成为美国控制中东海域的重要工具。
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洋地区的“美国独霸”结构开始朝着美、俄、日、印、英、法等“多国存在”的方向发展。*楼春豪:《印度洋新变局与中美印博弈》,载《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5期,第27页。虽然美国在战略和军事上仍占显著优势,但其综合国力出现颓势,对印度洋的主导权有所削弱。为了维系在印度洋的主导地位,美国积极拉拢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并炮制所谓中国“珍珠链战略”*2005年曝光的美国国防部秘密报告《亚洲能源的未来》指出,中国正在建立从中东到南海的海上通道沿线(“珍珠链”),从而保障其能源利益以及实现广泛安全目标。参见Bill Gertz, “China Builds up Strategic Sea Lanes,” Washington Times, January 17, 2005.,作为鼓噪“中国威胁论”的依据。美国通过各种方式对所谓的“珍珠链”国家进行威逼利诱,以最大限度地限制中国在印度洋的影响和发展。
2009年1月奥巴马上台后,美国积极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并提出“印太”战略概念,新两洋战略逐步成形。美国决策者认为,把“印太”地区视为一体并作为地缘战略重点,有助于消除美国的内外政策困境,保持自身伟大强国地位。*《美澳印打造“印太”地区各有所图》,载《参考消息》2012年12月14日,第4版。美国不仅继续加强中东军事部署,还通过多种手段不断提升中东盟国的军事能力。2015年3月,美国军方发布《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聚焦于海上力量的全球投送能力以及与盟国和伙伴国的安全合作。根据计划,美国将进一步强化在“印太”地区的海军前沿部署,适度增加在中东地区的海军前沿部署,并着手向非洲地区部署海军力量。*U.S. Navy, U. S. Marine Corps and U. S. Coast Guard, “A Cooperative Strategy for 21st Century Sea Power,” The United States Navy, 2015, http://www.navy.mil/local/maritime/150227-CS21R-Final.pdf,登录时间:2017年5月2日。
二、 中东地区海洋安全的现状
中东海区不仅向外输出大量的能源与资源,更是连接东西方航运的海上生命线,对全球影响巨大。然而,自20世纪中期以来,由于大国在印度洋和中东地区的博弈和中东国家内部矛盾突出,中东海洋安全始终处于纷扰不断的状态。进入21世纪之后,海盗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凸显,中东海洋安全状况不稳定因素进一步增加,集中体现在能源与资源、非传统安全威胁、地区国家间的矛盾冲突等领域。
(一) 能源与资源问题
在过去的百余年里间,能源与资源是大国地缘政治博弈中的重要因素,并在当今的中东地缘政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作为全球首要能源供应地,中东地区通往其他大陆的陆地通道却非常狭窄,海运航线特别是通往印度洋航线的意义变得异常突出,因此成为攸关全球经贸安全的重要议题。该地区最重要的水域有霍尔木兹海峡、苏伊士运河和曼德海峡。其中,位于阿联酋、阿曼和伊朗三国之间的霍尔木兹海峡,是连接波斯湾和印度洋的必经要道,日石油通行量高达1,700万桶(2013年)。美国能源信息署(EIA)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迄今是全球最为重要的咽喉要道(对于石油贸易而言)”*“World Oil Transit Chokepoints Critical to Global Energy Security,”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December 1, 2014, http://www.eia.gov/todayinenergy/detail.cfm?id=18991, 登录时间:2017年5月2日。。苏伊士运河连接东西半球海运,是亚太国家、印度洋沿岸国家与欧洲最为直接的海上通道,进入21世纪以来运河通行船舶数量不断攀升。亚丁湾的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与阿拉伯海的关键水域,这条宽约30公里的狭窄水道被美国能源信息署视为石油贸易的“关卡”。
在能源与资源储备方面,中东地区拥有丰富的油气、矿产和渔业资源。其中,波斯湾地区是全球最大的石油产地,年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1/3,已探明石油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一半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编:《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13)》,北京:地质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该地区的沙特等五国位居全球十大原油输出国之列。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截至2015年,沙特是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拥有全球第二大探明石油储备,占全球总量的16%;伊朗、伊拉克、科威特和阿联酋的探明储量分别排名世界四、五、六、七位。至于已探明天然气储量,伊朗、卡塔尔和沙特分列全球第二、三、五位。*U.S. Department of Energy, “U.S. Crude Oil and Natural Gas Proved Reserves, Year-end 2015,”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https://www.eia.gov/naturalgas/crudeoilreserves/pdf/usreserves.pdf,登录时间:2017年5月10日。由于中东地区丰富的油气、矿产和渔业资源以及独特的地理位置,其能源安全问题成为世界大国关注的重要焦点之一。
(二) 非传统安全威胁
非传统安全威胁是目前中东海区最严峻的安全挑战之一。从中东延伸到亚洲沿海地区的印度洋北部边缘地带有“不稳定弧形区域”之称。*Stephen J. Flanagan, Ellen L. Frost and Richard L. Kugler, Challenges of the Global Century: Report of the Project on Globalization and National Securit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2001, pp. 16-17.这里恐怖袭击频繁,海盗活动猖獗,自然灾害、非法移民、海洋污染等事件屡屡发生,这些威胁近年来在中东海域表现明显。
1. 海盗问题。印度洋东西两端的战略通道都面临海盗威胁。1994~2004年间,海盗活动最猖獗之地在印度洋东北部的马六甲海峡—印尼海域。2005年之后,印度洋东北部的海盗案件数量开始逐年下降;相反,印度洋西北部的索马里—亚丁湾海域海盗案件却急剧上升。*许可:《印度洋的海盗威胁与中国的印度洋战略》,载《南亚研究》2011年第1期,第2页。这种变化与印度洋西北沿岸地区动荡的安全形势密切相关。印度洋西北部的海盗多数来自索马里,该国从1991年后一直处于部落纷争引发的内战中。*汪戎、万广华:《印度洋地区研究(2012/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4页。印度洋海盗的犯罪动机主要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据世界银行估算,自2005至2013年间,索马里海盗共劫持过往船舶149艘,所获赎金约3.15~3.85亿美元,*刘中民、朱威烈主编:《中东地区发展报告(2014年卷)》,北京:时事出版社2015年版,第66页。而国际社会因此承受的经济损失和安保支出要远超此数。统计资料显示,近年来海盗事件数量已经大为减少,但无法根绝的海盗威胁仍给国际社会和高风险沿岸国带来沉重负担。*伊民:《上半年全球海盗活动有所减少》,载《中国海洋报》2016年8月10日,第4版。
2. 海上恐怖主义。海上恐怖主义行为通常指非国家行为主体在海上采用暴力或者激进方式来制造恐慌、胁迫政府或危害航运,从而实现其特定目的的行为。海上恐怖主义在中东海区易于滋生却难以防控,这主要是因为该地区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威胁异常突出,地区海上反恐机制却比较薄弱。近年来的叙利亚内战以及伊拉克和也门的局势动荡加剧了这种威胁。在埃及,具有反政府、反西方倾向的伊斯兰极端势力不断壮大,已对苏伊士运河的正常运行构成了现实威胁。2014年6月以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兴起成为全球恐怖主义的新力量,其分支机构分布于中东的伊拉克、叙利亚、沙特、也门、埃及,活动范围趋于扩大,并与当地的恐怖组织和海盗纠缠在一起,对中东海洋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3. 海洋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伴随中东海域航运不断增加,船舶伴生污染和生态破坏随之增加。此外,还有沿海工程建设、岸上工业污染、战争破坏、石油泄漏、污水排放、过度捕鱼和损害性旅游业等问题。这些现象在红海、亚喀巴湾、波斯湾等海域都有明显表现。据国际环境规划署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该地区国际河流较多,水污染问题存在跨国传播风险,地中海、红海、海湾地区等中东地区的海洋水质也受到陆源有害物质、农业化学物质和人类生活垃圾的污染,石油泄漏造成的污染情况也比较严重。*国际环境规划署:《全球环境展望》,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4页。中东海域海洋生态系统非常脆弱,却承受着多种环境风险,不仅造成负面经济效应,更对海洋生态环境构成严重损害。
(三) 地区国家间的矛盾冲突
中东地区汇聚了众多国际热点问题,地区国家间的矛盾冲突连绵不断。2010年底以来,中东变局席卷整个西亚北非地区,埃及、也门、叙利亚等国均出现了内部动荡,有的甚至发展为内战。局势动荡和冲突频发对地区海洋安全的威胁不容忽视。
1. 海湾阿拉伯国家与伊朗的深刻矛盾。长期以来,伊朗与波斯湾阿拉伯国家间的矛盾根深蒂固。波斯湾阿拉伯国家极大地依赖美国的安全保障,并通过海合会力求在重大安全问题上保持一致。伊朗则长期与美国关系不睦,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形成安全对峙局面。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经济贸易高度依赖海运,军力迅速发展的伊朗被它们视为海洋安全的主要威胁。早在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就屡屡打击科威特油轮,并试图在波斯湾进行海上封锁。两伊战争后,西方的经济制裁促使伊朗更加注重非对称战法,这也使得对手的反制行为更为困难。2011年底以来,伊朗在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的军力增加和军演升级,引起了美国及海合会国家的高度关注。美国海军借机增强地区部署,据称“既为了应对伊朗军事活动的升级,也为了应对其令人不安的政治言论,特别是关于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Rupert Herbert Burns, “International Naval Activity and Developments in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in 2012,” Stimson Center, Spring 2012, http://www.stimson.org/content/stimson-center-maritime-security-briefing-2-indian-ocean-naval-activity-spring-2012-0, 登录时间:2016年12月20日。。如今,随着伊朗与海合会国家关系持续紧张,波斯湾地区的海上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2. 红海—亚丁湾沿岸国家局势动荡。2010年底以来的中东变局浪潮影响深远,已经在埃及、也门等地区国家导致政治动荡、政权更迭乃至内战爆发。在红海—亚丁湾沿岸国家中,索马里的状况最为糟糕,该国政局动荡是当地海盗难以禁绝的主因。也门和索马里情况相近,自1990年以来,也门历经内战、反政府叛乱以及恐怖主义活动摧残。2011年以来,也门国内出现政治动荡,发生低强度内战,同时面临“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组织等恐怖主义势力的严峻威胁。也门动乱既源于国内教派之争,更源于外部大国的介入和干预。从地缘战略视角来看,也门局势攸关亚丁湾—曼德海峡—红海国际航道的通行安全。也门的安全形势使得红海—亚丁湾地区的海洋安全面临更多的风险。
3. 地区国家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由于中东海域资源储量丰富,国家间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更加难以解决。例如,红海和亚喀巴湾的13起边境领土争端至今悬而未决。2016年4月,埃及和沙特虽已签订蒂朗岛和塞纳菲尔岛的归还协议,*张凯:《地缘视角下的蒂朗海峡协议》,载《公共外交季刊》2016年冬季号,第23页。但归期难定。在波斯湾地区,伊朗与伊拉克和阿联酋均存在岛屿归属纠纷,而巴林和卡塔尔之间的领土争端目前已经提交国际法院。除油气资源外,该海域的渔业和矿产资源同样成为地区矛盾的潜在诱因。一些争端问题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单纯的国家管辖权,还可能影响其他国家的通行权利。譬如,埃及、沙特、苏丹和也门各自对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解读,可能会限制他国军舰在红海南端的无害通过。埃及还根据海洋基线原则,将苏伊士湾划为封闭的内水。这些过境问题会对所有使用地中海—红海通道的国家产生影响,在出现危机时可能会影响到国际航运的整体安全。
4. 地区国家海军力量比较与军力对峙。中东国家发展海军力量一般有三个主要动机:一是作为国家身份的体现,二是作为国家机器的必要组成部分,三是用来支持政治军事战略。*David N. Griffiths, Fred W. Crickard and Edward L. Tummers, Regional Maritime Security: Four Case Studies, Halifax: Centre for Foreign Policy Studies, 2002, p. 64.囿于多重考量,中东地区国家未将海军置于首位,但仍在不断提升海军力量。在波斯湾地区,伊朗和沙特海军占据优势。通常认为,伊朗海军要强于包括沙特在内的海合会国家的海军,尤其是伊朗拥有较强的潜艇部队,而海合会国家尚不具备独立的反制战力,主要依赖美国的安全保障。在红海—亚丁湾地区,埃及和沙特的海军力量占据优势,其他国家的海军力量非常有限。埃及海军主力部署在地中海沿岸,只有少数部署在红海沿岸,且装备落后;沙特虽然拥有总部位于吉达港的西部舰队,但其海军主力也部署在波斯湾一侧。近年来,从叙利亚内战到也门冲突,沙特与伊朗之间的军事角力日趋激烈。2015年3月以来,沙特牵头组建多国联军,打击也门胡塞叛军,后者据称得到了伊朗的暗中支持。*《也门胡塞遭沙特空袭伊朗是否会袖手旁观?》,新华网,2015年3月28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3/28/c_127628074.htm,登录时间:2017年4月1日
三、 中东海洋安全合作的主要内容
中东地区的海洋安全合作进展显著,主要的合作内容包括地区国家开展的区域安全合作和联合军演,以及国际社会和区域国家为应对海盗、海洋环境污染等非传统威胁而建立的多项安全机制等。
(一) 举行区域安全合作和联合军演
1. 波斯湾地区。始建于1981年的海合会是当前海湾地区最重要的政治经济组织,旨在通过合作实现自强,其正式成员包括沙特、阿联酋、阿曼、巴林、卡塔尔和科威特六国。海合会国家联合的核心驱动力在于安全防务问题。成立迄今,海合会国家不仅在两伊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等重大地区事件中实现行动协调,还相继签订了《联合防御条约》(Joint Defense Treaty of GCC)和《安全条约》(Security Treaty of GCC),组建“半岛盾牌”联合部队,使集体安全机制不断完善。海合会国家经常举行联合军演,成员国在联合指挥、情报共享和反恐等方面的军事合作达到了较高水平。海合会国家推动的地区合作进程无疑有利于促进地区海洋安全,但成员国与伊朗的矛盾根深蒂固,两者经常举行针锋相对的军演,容易加剧地区局势紧张,对地区海洋安全产生负面影响。
2. 红海—亚丁湾地区。红海的亚喀巴湾是沙特、埃及、以色列和约旦四国的海上边界交汇之处。根据1979年埃以和约,埃及和以色列均未在亚喀巴湾保有海军力量;沙特的军力部署以波斯湾为核心,在亚喀巴湾海军力量很少;只有约旦拥有一支规模较小却相当专业的海军力量。目前,经过蒂朗海峡进入亚喀巴湾的自由航行权由域外国家的舰船来监控和保障,自1980年以来就设立了多国部队和观察员。近年来,沙特非常注重发展与红海—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军事合作。2016年2月,沙特举行了号称“该地区史上最重要、规模最大”的联合军演,汇集了来自西亚北非等地区的20个国家参加。沙特官方表示,此次军演显现大西亚北非的伊斯兰国家将“团结一致应对区域内所有挑战与维护和平稳定”。*《中东史上“最大规模”军演剑指何方?》,新华网,2016年2月19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2/19/c_128731184.htm,登录时间:2017年4月5日。在红海—亚丁湾地区,沙特尤其看重与埃及的军事合作。2013年3月,埃及应邀参与沙特打击也门胡塞叛军的多国联军,并配合沙特实施海上封锁行动;同年9月,沙特资助埃及购买先进登陆舰,旨在加强在红海—亚丁湾地区的两栖登陆能力建设,以应对也门乱局等危机。
3. 泛印度洋区域。成立于1995年的环印度洋区域合作联盟(2013年更名为环印度洋联盟)是环印度洋区域唯一的经济合作组织。截至2016年1月,有21个正式成员国(其中伊朗、阿曼、阿联酋、也门、索马里等国为中东沿海国家)和7个对话伙伴国(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埃及)。该组织设立的初衷在于促进地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但此后关切的领域逐渐扩展。2012年11月,联盟第十二届部长理事会会议通过《古尔冈公报》(Gurgaon Communiqué),强调海事安全成为未来十年的合作重点。会议决定于2013年召开印度洋航运安全会议,并研究建立印度洋航运安全信息交换和海上形势监控机制。2013年11月,联盟第十三届部长理事会会议通过《环印联盟关于和平、生产性和可持续性利用印度洋及其资源的原则》(Principle of IOR-ARC on Peaceful, Productive an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Indian Ocean and Its Resources)。2015年10月,联盟第十五届部长理事会会议通过《环印联盟海洋合作宣言》(Declaration of IOR-ARC on Marine Cooperation)。近年来,环印联盟为区域国家间及与域外国家的对话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但在应对海盗等地区威胁上的作用尚不显著。澳大利亚、印度、印尼等主要成员国因此希望推动联盟建设,使之成为重塑地区政治、经济和安全格局的重要机制。
(二) 构建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国际和区域安全机制
1. 打击海盗的国际努力。为治理索马里海盗问题,联合国自2008年以来先后通过了五个专项决议,授权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派军打击海盗和执行护航任务。欧盟、北约、中国、美国、俄罗斯、印度和韩国等先后向亚丁湾海域派出军舰开展反海盗作业。2009年1月,“索马里海盗问题联络小组”成立,成员包括6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负责协调国际社会打击海盗的努力。欧盟自2008年12月起开展为期一年的“阿塔兰塔”(Atalanta)行动,旨在震慑和打击索马里海域的海盗和武装抢劫行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也多次开展打击海盗行动。中国海军自2008年底起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开展常态化护航行动。截至2016年12月,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完成了近6,300艘的中外船舶护航任务,其中外国船舶为3,242艘次,并积极承担了10艘次世界粮食计划署船舶的护航任务。*张腾飞:《亚丁湾护航展现中国担当》,载《解放军报》2016年12月23日,第4版。国际社会还设有一些联络组织和信息情报机构,如国际海事组织海盗报告中心、英国海上贸易组织、“非洲之角海上安全中心”、北约航运中心等,为过往商船及军舰提供海情资料、船舶定位、军舰护航、船只遇袭等各类信息,统筹和协调商船和军队的反海盗行动。这些机构的背景、性质和工作重点各不相同,但都以保护航运安全为宗旨,为地区海洋安全发挥积极作用。
2. 应对海洋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区域合作机制。在中东地区,应对海洋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区域机制已经建立,但效果不尽相同。在红海—亚丁湾地区,埃及、厄立特里亚、约旦、沙特、索马里、苏丹和也门均是“红海—亚丁湾环境项目(PERGSA)”的成员国,项目秘书处设在沙特的吉达港。在波斯湾地区,巴林、伊朗、伊拉克、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和阿联酋等国于1978年签署“科威特协议”,决定建立地区海洋环境保护组织,总部设在科威特。虽然该组织因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遭受破坏,但其执行机构“海洋应急互助中心(MEMAX)”迄今仍然发挥着协调区域监督、培训、信息交换和应急计划的作用。该地区还有其他一些双边和多边海洋环境合作机构,如埃及、以色列、约旦和沙特四国合作建立位于亚历山大港的中东区域协调中心,专门负责环境应急反应和准备事务;在亚喀巴湾,埃及、以色列和约旦三国开展了一项应对原油泄漏的合作项目。这些环境保护和应急机制几乎涵盖了地区所有国家,为中东国家间的海洋安全对话提供了重要渠道。
四、 中东海洋安全合作的制约因素
虽然中东地区的海洋安全合作取得显著成绩,但仍面临多重挑战,主要表现为受到美国企图独霸中东、国际社会难以长期持续投入、地区国家维护海上安全能力薄弱以及滋生安全威胁的根本问题难以解决等因素的制约。
(一) 美国的地区霸权
在中东海域,美国试图对某些海上战略通道实行排他性控制,对中东海上安全构成重大潜在威胁。21世纪以来,为增强对中东地区的掌控,美国先后发动了两场反恐战争,以此彰显自身军事实力和巩固地区同盟体系。目前,美军的军事基地遍布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曼、吉布提、阿富汗等国,在海湾地区已形成了弧形的“珍珠链”。*孙德刚:《美国在海湾地区军事部署的“珍珠链”战略》,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年第5期,第16-29页。中东海域的霍尔木兹海峡、苏伊士运河和曼德海峡均属于美军宣称在战时要予以控制的十六个海峡之列。2016年4月,美国牵头举行了迄今中东最大规模、有30余国参加的国际海上反雷演练,演习指挥官凯文·多内甘(Kevin Donegan)中将一方面高调鼓吹演习旨在“保护商业的自由流动,使其免受海盗、恐怖主义和水雷等一系列海上威胁的侵害”,一方面又念念不忘“该地区拥有全球三大海上关卡,显然对全球都很重要”,*“World’s Largest Maritime Exercise Underway in Middle East,” Navy, April 4, 2016, http://www.navy.mil/submit/display.asp?story_id=93996, 登录时间:2017年2月8日。实际上是强调该地区对于美国维护在中东地区霸权的重要性。长期以来,美国护持中东霸权的努力使得地区国家间矛盾丛生,紧张对峙,其中阿以之间以及海合会国家与伊朗之间的矛盾最为突出。美国不仅在该地区部署强大军力,发动数次战争,还持续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暗中煽动“阿拉伯之春”,*安惠侯:《阿拉伯世界政治和社会动荡的原因及影响》,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第5页。其所作所为加剧了地区政治动荡和安全恶化。虽然许多事态在陆上发生,但安全威胁最终会传导至海洋,不论是国家间军备竞赛与军力对峙,还是海盗和海上恐怖势力等。美国图谋掌控的中东海上要道都是印度洋国际航线的必经之地,一旦付诸实施,将对全球航运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二) 地区国家维护海上安全的能力薄弱
鉴于国际社会难以持续投入,维护海上安全的长久之策应是加强区域海上安全力量建设,由西亚北非国家在邻近海域开展巡逻与护航,应对各类海上安全挑战与突发事件。尽管国际社会屡屡呼吁地区国家发挥作用,后者的配套能力建设却乏善可陈。在中东地区安全事务中,海洋议题较之于陆上议题处于次要位置,并且地区各国对空军的重视通常也要超过对海军的重视。目前,不少中东沿海国家连捍卫本国海洋主权的能力尚不具备,遑论远程投射军力,应对敌国海上威胁,或打击海盗和巡逻护航。地区国家不仅海上安全防卫能力有限,而且缺乏健全的地区集体安全架构。地区国家间矛盾错综复杂,缺乏建立海上集体安全体制的基础和动力。譬如,伊朗积极参与国际社会打击索马里海盗的行动,自2008年11月起便派军舰在亚丁湾海域巡航。*“Iran Upgrades Maritime Security,” Arabian Supply Chain, November 25, 2014, http://www.arabiansupplychain.com/article-10667-iran-upgrades-maritime-security/, 登录时间:2017年2月8日。然而,伊朗的举动却被沙特等海合会国家视为在红海—亚丁湾区域进行势力扩张,后者甚至采取了针锋相对的防备措施。可以说,如果没有联合国、国际社会及主要大国的推动和协助,建设一支有效的区域海上安全力量几乎难以实现。
(三) 域外大国持续介入与竞逐
域外大国在印度洋地区的持续介入与竞逐,也掣肘着中东海洋安全。除美国在印度洋推行“前沿存在”政策,依托迪戈加西亚基地和巴林基地等前沿存在,加强对中东地区的军事控制外,印度、俄罗斯、日本、英国、法国等国也持续加大对印度洋和中东地区的介入和竞逐。印度由于自身地缘优势,早已萌发控制印度洋的强烈愿望。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印度综合国力的提升和海空军力的强化,主导印度洋的梦想也逐渐付诸实践。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海军建设步伐坚定而迅速,成为印度洋的主要竞逐者之一。中东海域被印度纳入安全边界之内,2001年印度国防部年度报告即指出,“鉴于印度的规模、位置、贸易往来和广泛的专属经济区,其安全范围延伸到西部的波斯湾和东部的马六甲海峡”。*汪戎、万广华:《印度洋地区研究(2012/1)》,第32页。2007 年,印度外交部长普拉纳布·慕克吉对印度海上利益主要区域进行了描绘:“北起波斯湾,南至南极洲,西起好望角和非洲东海岸,东至马六甲海峡……和印度尼西亚。”*Pranab Mukherjee, “Speech for the Admiral A.K. Chatterjee Memorial Lecture,” Kolkata, June 30, 2007.如今,印度一些思考海洋事务的人士又将“印太”作为涵盖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地区的概念,从而使得印度在中东地区的安全角色不断合法化。*Pradeep Kaushiva and Abhijit Singh, eds., Geopolitics of the Indo-Pacific, New Delhi: Knowledge World, 2014, p. 8.此外,英法日俄等国在中东地区仍然保持着传统的军事存在并有不断加强的趋势。英国虽早已撤出苏伊士运河以东区域,但仍在地中海建有军事基地,部署有约三千人的军事力量。2014年12月,英国与巴林签署军事合作协议,将在巴林塞勒曼港建设立海军基地。这是英国43年前从中东撤军以后在中东地区建立的第一座永久军事基地。2016年11月,英国正式启用该基地,主要停靠英国皇家海军的驱逐舰、护卫舰及扫雷艇等,用于辅助针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并防范有关国家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英国商船进行阻挠,确保英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灵活性”*桂涛:《英国将启用巴林永久军事基地》,环球网,2016年11月3日,http://world.huanqiu.com/ hot/2016-11/9631259. Html,登录时间:2017年1月8日。。法国在吉布提和阿联酋均拥有军事基地,与其在北非和地中海的军事基地遥相呼应。其中,法国吉布提军事基地是其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海外基地,已经存续约150年之久。*孙德刚:《法国在吉布提军事基地的绩效分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年第5期,第28页。日本和俄罗斯分别在吉布提和叙利亚拥有一处军事基地,并部署有数百人的军事力量,前者主要服务于执行护航任务的日本海上自卫队,后者主要服务于支援叙利亚政府军的俄军。这些前沿军事基地为英法日俄等国扩大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提供了重要便利。
(四) 国际社会力量投入难以持续
自21世纪以来,在亚丁湾、波斯湾等中东航运高风险区,由于迫切的海上安保需求和地区国家的有限能力,国际社会不得不承担维护中东海洋安全的重任。迄今为止,国际社会维护中东海洋安全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面临无法持续投入的现实难题,最为突出的是财政支出问题。中东海域的海上安保行动所费不菲,尤其是在欧美国家近年来因经济困境而压缩国防预算的大背景下,仅2012年巡弋亚丁湾的欧盟与北约部队就花费10.9亿美元,*李华强:《中东与北非的海上安全战略评估(下)》,载《尖端科技》2015年第6期,第90页。使得国际社会和相关国家承受了较大的经济代价。近年来,欧盟“阿塔兰塔行动”和北约部队都已缩减在中东海域的力量部署。从投入和产出的效率比看,长期部署国际部队并非最佳选择,代价高昂的联合巡逻也难以根绝海盗威胁。
五、 余论
印度洋是联结中国与中东、非洲及欧洲国家的重要贸易和能源通道,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在不断上升,处于印度洋西北边缘的中东国家与中国在资源、资金和市场潜力方面具有高度互补性,成为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柱之一。目前,国际社会维护中东海洋安全的努力虽然有所成效,但造成地区海上安全形势持续动荡的根本问题并未解决,维护中东地区海洋安全,首先必须要缓解中东国家间的矛盾,解决和预防地区冲突。
对于中国而言,中东海洋安全实为印度洋海洋安全的重要部分和关键环节。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成为中国关于新时期亚欧非区域经济合作的最新主张。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把“一带一路”建设和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经济建设和全方位外交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陆钢:《一带一路搭建国际合作新平台》,载《人民日报》2017年11月5日,第5版。。中东地区地处“一带一路”交汇处,该地区国家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合作伙伴。其中,中东沿海地区局势的稳定及中东海上交通线的畅通,是关乎中国“海上丝路”构想持续推进的关键。中国的经济安全有赖于中东地区的资源和能源,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中东海洋安全紧密相连。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拥有广泛影响力的大国,中国在缓解乃至解决中东地区矛盾方面具有自身优势,也有望发挥更多建设性作用。譬如,在旷日持久的伊核问题谈判中,中国发挥了独特的建设性作用,特别是在谈判陷入僵局等重要节点,中方总是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路径和思路,成为劝和促谈的重要力量。中国在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协助解决地区国家间的矛盾,减少这些矛盾对中东海洋安全的负面影响。此外,由于非传统安全威胁是影响中东地区海洋安全的重大风险因素,而在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中,海盗和海上恐怖主义是当前中国在中东海域所面临的现实而紧迫的威胁,对中国的航运安全构成了较大压力。为此,中国正积极参与亚丁湾护航的国际合作,与多国共同打击海盗及海上恐怖主义,为全球安全贡献自身力量,将在亚丁湾等中东海域开展的反海盗行动作为展现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良好平台。除此之外,中国还积极谋划利用“丝路基金”等机制,帮助相关国家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和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国际机构合作关注该地区的海洋安全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从未来发展来看,中国将与印度洋沿岸和中东地区国家一起,追求共同利益,应对共同威胁,在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中实现合作共赢,从而共同维护中东海洋的长久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