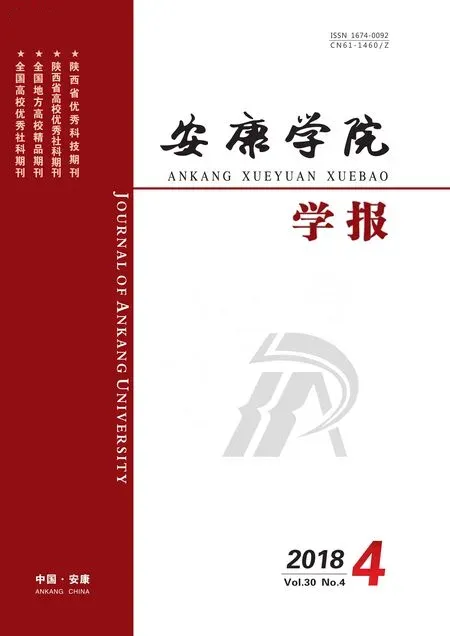论新历史小说《褒姒》的后现代主义精神
王 平
(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00)
对于褒姒形象的认识,一直存在两极分化的现象。在史书中,褒姒几乎是周幽王亡国的祸因,而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与民间传说中,除了祸水形象,也有将褒姒塑造成善良、纯洁女性形象的一面。《汉中府志》所引《虞仙录》中的褒姒是汉水女神形象。《中国民间故事集成·陕西卷·汉中民间故事集成》中,褒姒是热爱汉中的美丽可爱女子。宁慧平女士的《褒姒》一书,对这一文学传统有所继承,从个人化角度重塑了褒姒的一生,力图揭开历史的重重迷雾,还原出民间叙事中的历史真实。与此同时,也表现出了新历史小说的某些特征。新历史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受后现代理论影响,从其兴起便与“颠覆”“消解”等带有后现代色彩的话语紧密相连。后现代主义是当代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思潮。“总体上看,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世界文化意识领域掀起了一阵阵‘话语转型’旋风。这一转型旋风在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信仰上,造成了传统与现代话语的断裂。”[1]这里的“转型”即是说明后现代主义思潮中颠覆性精神的存在,具体体现在《褒姒》一书中主要是对“烽火戏诸侯”的历史消解,对“红颜祸水论”的文化颠覆,以及对人性情感的诗意书写。
一、“烽火戏诸侯”的历史消解
在传统历史小说中,历史是不容更改的客观存在,但在新历史小说家们的笔下,历史的客观性被消解,变为个性化、主观化的历史。黄发有先生认为这种“‘新历史’的历史表达,仅仅是经过作家们的思想过滤和心灵折射的历史印象”[2],意在批驳,但不可否认的是新历史小说打开了文学创作的新局面,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多角度、多层面发展都有开拓价值。《褒姒》一书在对待“烽火戏诸侯”这一历史事件上就采取了新历史的书写,对正史进行了消解,其叙事方式极具后现代主义精神。
对于“烽火戏诸侯”这一历史事件,在《史记·周本纪》中有记载:
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说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3]148
周幽王为了取悦不爱笑的褒姒数次戏弄诸侯,最终丧失了诸侯对王君的信任,是为了博美人一笑而进行的政治儿戏。
到了《褒姒》一书中,第四十七章改为“骊山烽火试诸侯”,对史书记载进行了个性化的消解:
太室结盟,天下震动;大小诸侯。心态各异;申国沉稳,不见异动;西戎挑衅,持续不断。幽王心海翻涌,疑虑重重,结盟的诸侯能与寡人成一体吗?当真能言出必行、依盟约而行吗?
尹球、虢石父看出了幽王心中的隐忧,其实这也正是他们所担心和难以把握的。权衡利弊后积极建议幽王:“太室结盟已成,各诸侯究竟心归何处,尚不得知,王上不妨烽火一举,也算是一次军事集结,试探一下,看看诸侯是否闻“烽”而动,便知忠诚与否。
幽王深以为然。[4]P259
在《褒姒》这本小说中,将“戏”字改为“试”字就代表了作者的态度。作者首先将“烽火”与“诸侯”的关系变为政治试探,而且将史料记载的几次“烽火”事件改为一次,这就将这一历史事件由荒诞变为合理。接下来,作者改变了几个人物的形象,第一个是周幽王,幽王由历史上荒淫无度的暴君变成为国事忧虑的君主。第二个是虢石父,“幽王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石父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王用之”[3]149。按照一般性的评价,虢石父本是奸臣,但在小说中却有了对国君忠心耿耿的意味,而且用“烽火”召集诸侯的主意也变为是他与尹球为王上分忧而献的计谋,那么这件事即使是错的,也不是幽王自己的计谋,幽王的过错最多是用人不当。尤其要注意的是,作者将这件事的起因与褒姒完全脱离了关系。只在结尾处点明是诸侯见褒姒大笑(此处大笑是为幽王得诸侯之心而笑)而心生嫌隙,误认为幽王耽色误国。
《褒姒》一书不仅修改了史书中“烽火戏诸侯”的起因,而且对其结局也进行了改写,据史书记载:
又废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3]149
在这段记载中,“烽火戏诸侯”的结局是幽王失去诸侯的信任,又因为幽王独宠褒姒废了申后与太子惹怒了申侯,申侯联合少数民族的势力共打了王城,杀了幽王,俘虏了褒姒,并立故太子宜臼为平王。但是,在《褒姒》小说中,作者不仅修改了过程,而且结局与史书大相径庭:
骊山烽火,天下皆知,国势强盛的几个诸侯,各怀异思,担忧王师若灭了申国,下一个可能是自己,采取观望的态度,只令整顿军马,不起兵相助。
……
幽王怒斥道:“宫湦无能,辱及宗庙社稷,辱及九鼎神器,愧对列祖列宗,愧对天地百姓也!我堂堂大周天子,岂容尔等戎丑凌辱!”讲完将剑转向脖颈,一股鲜血喷涌而出。[4]P271
在幽王命人点燃烽火之时,竟无一人一马支援而致使兵败,兵败的原因由史书记载的君王昏庸变为了诸侯不守信义。而且更改了幽王的被杀的结局,改为英雄式的自刎,并在死前发出自己愧对祖先、愧对百姓的感慨,树立了一代明君的形象。
《褒姒》一书秉承着后现代主义精神,不再遵从历史的权威,而是试图用个性化的历史视角颠覆传统历史的叙述。“‘历史’的概念受到了从未经历过的严厉的打击,他们不是反思或质疑某个历史事件的真实性,而是干脆把历史本身当成质疑的对象。历史真实被视为是不存在的。……他们首先强调的是恢复文学的虚构性质。将它从历史的压抑和禁闭中解放出来,或者干脆以文学的名义去反抗或质疑历史的合理性。”[5]宁慧平女士以独特的新历史书写技法,使文学摆脱了历史的禁锢,使文学书写达到了自由的最大化境地。
二、“红颜祸水”论的文化颠覆
在史书中,褒姒几乎是“红颜祸水”的代名词。在男权社会这种论调并不在少数,妺喜、妲己、赵飞燕、赵合德、杨贵妃等等都是“祸水论”的牺牲品。但是,在新历史小说中,女性的地位得到尊重并提高。在《褒姒》一书中,作者通过重塑褒姒的美好形象对“红颜祸水”论进行了文化颠覆。而且,小说中的褒姒虽然生于男权中心的社会背景之下,但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男性的附庸。虽然最开始她入宫为妃是为了报恩,是家族利益的牺牲品,但在作者细腻的笔触之下,读者能够感受到幽王与褒姒之间刻骨铭心的爱情。小说中多角度的女性心理描写,让读者深切体会到女性丰富的内心世界,这也是文学作品中女性不再是附庸的重要标志。
在史书中,褒姒的“祸水”形象从其出身便以决定:
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龙止于夏帝庭而言曰:“余,曪之二君。”夏帝卜杀之与去之与止之,莫吉。卜请其漦而藏之,乃吉。于是布币而策告之,龙而漦在,椟而去之……至厉王之末,发而观之。漦流于庭,不可除。厉王使妇人裸而噪之。漦化为玄鼋,以入王后宫。宫之童妾既龀而遭之,既笄而孕,无夫而生子,惧而弃之。宣王之时童女谣曰:‘檿弧箕服,实亡周国’。于是宣王闻之,有夫妇卖是器者,宣王使执而戮之。逃于道,而见乡者后宫童妾所弃妖子出于路者,闻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妇遂亡,礶于褒。褒人有罪,请入童妾所弃女子者于王以赎罪。弃女子出于褒,是为褒姒。当幽王三年,王之后宫见而爱之,生子伯服,竟废申后及太子,以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太史伯阳曰:“祸成矣,无可奈何!”[3]147
但凡“妖物”必有一个匪夷所思的非正统出身,史书以满含神话色彩的文字与极富虚构性的情节来贬低褒姒的出生。褒姒是龙的唾液变换为蜥蜴之后由宫女所生。先是二龙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其后周厉王昏庸不持祖训,还命女子不着寸缕面对龙的唾液大喊大叫,不敬荒淫。唾液幻化成的蜥蜴所遇宫女才六七岁,使得事件再次蒙上不道德的色彩,后来褒姒又为这名宫女所生,宫女地位低贱,也就暗示褒姒不仅出身不吉利而且不高贵。其后更有民谣证明其祸水的身份,幽王废后与太子的行为更是坐实了褒姒作为妖妃的形象,连本该公正客观的太史伯阳都感叹,幽王宠爱褒姒,灾祸已经无可避免。
小说《褒姒》改写了褒姒的出生,她不再是被遗弃在褒国的弃子,而是商王后裔岐山求孕得来的婴孩,是天赐与人间的生命。其父是贵族公子姒柱,其母温婉贤淑。她是仁义书香之家的孩子,其名为婉婧,“婉”是温顺美好,“婧”是纤巧有才品。后来是褒国太赐名为褒姒:
褒国太语带笑意:“姓褒,字婉婧,名姒。褒是国名,姒是个好字,相传夏禹之母吞薏苡而生禹,因姓姒氏。周文王的正妃,周武王之母,太姒就是姒姓。太姒天生姝丽,聪明贤淑,分忧国事,严教子女,尊上恤下,深得文王厚爱和臣下敬重,被人尊称为‘文母’。姒字是个有担当的字,以褒为姓,从今儿起,你就叫褒姒可好?”[4]57
女主人公的名字由“婉婧”变为“褒姒”,不仅是身份地位的变化,也是展现了其性格与责任的发展演变。当她是婉婧时,她的主要性格特征是单纯烂漫。变成褒姒后,她还有政治使命与历史责任,不仅担负了褒国府的命运,而且对国事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小说中,作者特别将褒姒名字的由来和周文王的正妃即周武王之母作比,这既是提高褒姒的地位,同时也是为幽王后来立褒姒的孩子伯服为太子埋下伏笔,并肯定幽王行为的合理性。
作者为褒姒的“正名”打破了史料记载中的出身妖子的魔咒,也推翻了诸如《列女传》记载的“兴配幽王,废后太子,举烽致兵,笑寇不至,申侯伐周,果灭其祀”[6]因幽王沉迷褒姒美色而儿戏诸侯的说法。《诗经·小雅·正月》中也曾有这样记载:“《正月》,大夫刺幽王也。”[7]706点明诗歌主旨,更在诗中云:“赫赫宗周,褒姒灭之”[7]714,将周灭国的原因归咎于褒姒。除此之外,作者通过褒姒知恩图报,为了褒国府而舍己入深宫,被人陷害依旧真诚、善良等描写,将褒姒塑造成了一个聪慧隐忍大度的美人形象,颠覆了史论中的“红颜祸水”论。
曾艷兵教授曾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中指出中国后现代精神的特征之一就是:“传统文化重负中的反传统。”[8]也就是带着某些传统文化的烙印对社会对文化进行解构,小说《褒姒》坚守着传统文化中忠臣大义的美德,却消解了“红颜祸水”论的文化观念,这是后现代主义精神的折射,也是作者继承新历史小说精髓的生动体现。
三、人性情感的诗意书写
在后现代理论的影响下,新历史小说的书写把“人”与“人性”的解构与重建作为文学创作的中心议题。在新历史小说《褒姒》中,人的情感欲望被释放并予以肯定,人的多面性与复杂性取代模式化的人物形象。作者凭借女性独特的视角与细腻的情感体验、丰富的内心世界,其语言技法与叙事技巧使得人性情感的书写富于诗意。
在小说《褒姒》中,有几组人物之间的情感闪烁着人性的光芒,是伦理道德、爱情、善意与恩情的交织。
姒殷氏与里尹——尘世欲望纠葛。在这一感情中,人性的欲望跃然纸上,里尹对姒殷氏一见倾心,虽然文中几次通过梦境曾朦胧暗示姒柱的死似是人为,但情节中还是将其死以打猎出现意外进行了处理,作者没有否认里尹占有姒殷氏的想法,这就写出了里尹人性中恶的一面。姒柱死后,孤儿寡母生活艰难,作者笔下,里尹夫妇多有帮衬,而且在草棚大雨之后,“里尹对姒殷氏母女嘘寒问暖持续不断,打柴送物、安排人手耕种田地。里尹仿佛知道姒殷氏的心思,每次前去必携妻前往,他必在门外不进房门”[4]11。在这样的描写中,里尹身上又体现出君子之风。姒殷氏后来也终因自责自己贪恋肉欲抑郁而终,伦理道德意识一直在其心中回荡。作者笔下的人物鲜活灵动,运用比喻象征手法描写两性生活,含蓄蕴藉,语言极富美感,是将人性欲望诗意化的典型。
褒姒与洪德——政治欲望缘浅。褒姒与洪德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回环的变化过程,褒姒进入褒国府之时,洪德与褒姒是棋手与棋子的关系,不管披上什么温情的外衣,也都只有利用与被利用。日久生情,两人是英雄与美人之间的惺惺相惜,最终褒姒不得不为了褒国公入宫,洪德与褒姒最终回归各自的本位,尤其是后来洪德为了褒姒入宫,命人教她“枕上风情”,要她“熟悉娼技”,没有哪个男子愿意让自己心爱的女子做出这样的选择,这是褒国府政治欲望迫使下的结果。即使是谦谦君子洪德,在作者笔下也有政治家的狠辣,摆脱了模式化的书写。两人的感情一波三折,经过对倾心、纠结、苦闷、牵挂、释然的内心世界的刻写,揭示出政治欲望与爱情理想不能两全的矛盾。
褒姒与宫湦——夫妻恩情绵长。虽然是作为政治权力的绝对权威,宫湦与褒姒之间的相处超越了君主与妃嫔之间等级森严的制度化模式,在很多时候更像是普通民间的恩爱夫妻,比如幽王给褒姒肚中孩子讲述周氏祖先的起源时的温情流露,比如两人十指相扣谈论“连理枝”的场景。尤其是在幽王兵败话别褒姒之时,堂堂一国之君许下诺言:“若有来生,唯愿你我生于庶民之家,淡薄桑麻,尽享生趣”[4]270。两人的感情可谓是宫中生活的一片净土,伉俪情深,感人肺腑。
此外,诗词的大量引用与创作,以及景色描写为小说蒙上了浪漫的诗意色彩。诗词与人物活动的场景完美融合,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以幽王册立太子之时的乐舞为例,作者选取了《诗经·周颂·清庙》作为乐,以八佾为舞,不仅符合周天子的身份,而且和祭祀祖先,祈求庇护的主题相切合,将诗文完美融合到创作之中,秉承了诗意的书写方式。
纵观《褒姒》全书,宁慧平女士以严谨的写作态度进行创作,其参考书目涉及历史、地理、典章制度、诗文艺术、考古发现、医学药理等各方面,对于周代的礼乐制度、妃嫔等级、宫廷生活等作了认真考察,是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虚构。在此基础上,作者以敏锐的眼光,独特的视角,不仅重塑了褒姒的形象,更为新历史小说与后现代主义精神的结合提供了范例。白璧微瑕,女主人公褒姒性格起伏变化不大,宫斗描写未脱窠臼,在情节的起伏设置上可以加大创新力度。但瑕不掩瑜,作者饱满的感情深深吸引了读者。文中洋溢着对褒姒故里——汉中的热爱,对于发扬汉中精神、扩大汉中的文化影响力都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