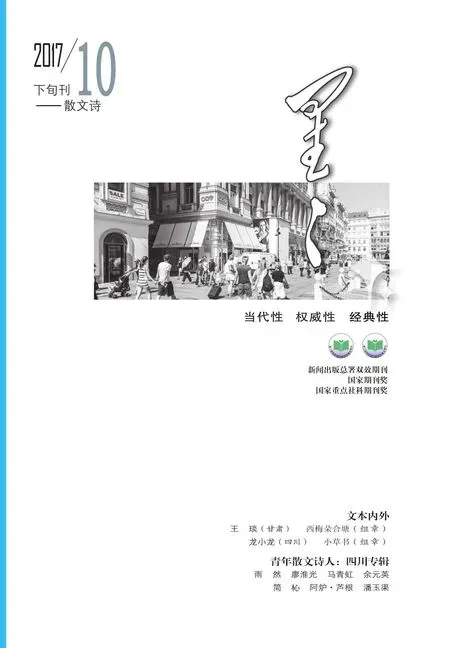破碎的时光(组章)
陈海容(福建)
破碎的时光(组章)
陈海容(福建)
万物行走在光阴的轨道里
万物都行走在光阴的轨道里,交错聚离在瞬息之间。
快乐的和伤感仿佛也有自己运行的轨道,自顾自地进入和离开我的身体。我像一个被提着线的木偶人,属于我的一切都无法指挥,只能睁着或闭上眼睛,在心里惋叹。
“哇”的一声飞鸟疾速地掠过天空。突然涌出的悲伤,也来不及捂住,只是一瞬就从我的内心逃逸了。
追循岁月的轨迹,交错的线如乱麻缠绕成茧,轨迹影影绰绰远去,如儿时看的社戏,在锣鼓声中又记得不太真切;如宇宙洪荒中来自血脉的呼号,暗示那潜藏的不可说出的秘密;各个陌生的事物却有怪诞的熟悉感,一切未发生的现象仿佛早已经历过。
暗黑张开宽广的怀抱,容纳光和暗,生和死,聚与离。也将无家可归的人纳入怀抱。而我知道,暗黑将命运的轨道拉回早已预设的程序里;而我知道,暗黑滋生光明滋生万物,又伸出巨手将其一一打碎。
所有激昂的、奋勇的、悲伤的、无奈的暗流最后终会熄灭。
在星球爆炸陨落之后,沿着光阴交错的叶脉,我虚构了那些已不存在的事物,渐渐虚拟形成万事万物,补缀了接近完整的世界,用以安慰我和像我这样怀旧的人。
一切终将成为废墟,些须从远方传来的微光逐渐消散而去,而我愕然无言。
住在时光家里
有多么爱光阴,你就有多么恨光阴。
时光擦不净往事的生字本,在时光面前你一直都是个小学生,展开天真无邪的笑容。世事轮番出现,你趴在课桌下找出半块橡皮擦用力擦去,以及涂改,企图擦去你不愿意看见的人和事,你将整本历史书折腾着面目全非,还比不上母亲用力地擦掉自己总擦不干净的鼻涕,很痛,你像是躲母亲的手一样躲着光阴。最终你只能对它苦笑,不能更换或撕破这本书。
起初你不愿久呆的家。
脚步落下的地方就是你的故乡,时光就是你永远的家。年轻时你渴望离家出走,年老时你渴望叶落归根,你像背着家的蜗牛四处寻找着你的家,走了一圈又返回原地。几十年的光阴啊,仿佛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就过去,你开始惶惑着,时光与家园多么像一对难兄难弟。
后来你开始思念的家。
从小到大,你离开了无数次的家门。也搬过好几次家,从乡村搬到小县城。时光苍白了记忆,时光和你的家,早彼此已经习惯的等待和被等待,至今不变。
如今你渴望归回的家。
倘若可以,你多想穿过时光之门回到儿时的旧厝,去拾回放在窗台上的旧蝉蜕,床底下的玻璃珠,还有一串搁在门口的脚印。
这是你又爱又怕的家。
时间的截面
终其一生,我们总是在和时间拉力赛,从光阴的一个节点向另一个节点。
从孩童跑向青年,跑向中年,跑向老年,我们被时光打磨得垂垂老矣。奔跑吧,终其一生的奔跑不过消耗几十年光阴。
是的,时光正将我们引入一个未知的深渊,有人勤快地翻读完自己的一生,有人勤快地把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痕迹抹净。而我不知道,我该怎么用完属于我的时光,岁月的渊薮要用什么填满?
或许有大神通,在某些让我们沉醉、感慨、欢愉、发呆的片刻,它们是一把利刃切入光阴,剖取一个个时光的截面,用于记忆。
通过这些剖开的截面,得知时空是个循环体,生命是个循环体。
与其说是时光苍老我们的身体,不如说是我们用时光磨洗自己的内心。
这其实很危险,用一个比喻来说明一个道理。
不必企望作为一个先知先觉者,在这时空交错的岁月,我们不必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们需要八面埋伏着,渴望着挣脱离自己的身躯,用于孤零零地面对一场场未知。
我们所谓的身世,浮于光阴表面。
有些时候,我们就坐在时光里发呆,呆萌地怀念那些故人故事,让没有冷暖的时光在怀念中沾染一些温情。
这样连缀时光的一个个节点,最终,每个人都是一部自己的断代史。
像蚂蚁一样筑巢
在地下构建一些幽暗回环的通道、巢穴,直至成为一座自我的城堡。蚂蚁需要,人类也需要。
年少时在旷野行走,总爱将土坡上堆得高高的蚁巢一脚踢倒,却对地下错综复杂的城堡束手无策。匿于九地之下的蚁穴,难以追寻。人类和蚁类如此相似,筑穴、群居、夜伏昼出。本质上说,人类也是造物主眼中的蝼蚁?
无尽的时间长河里,有谁能摆脱蝼蚁的命运?我们亦只是卑微而庸凡的蝼蚁,循着单调重复的日子漂泊,命运早已被安排,正行进在这速朽的生涯中。
钻木以取火,挖掘内心深处的巢穴也可以取出火,用以观望属于内心的另一个世界。行走在大地和天空之间,我们的内心怎能不深入大地,从中汲取力量?
生活如此厚重,多年后才发现曾经的愿想有如肥皂泡的轻盈不可触碰。生与死如唇齿相依,在万物生灭的交替中你逐渐悟生之命定。
将日子过得低些,再低些,低到雨水之下,低到植物根部,低入尘埃,低入内心的巢穴。
让鹰隼划过长空,让潮汐退回海洋,我们怀抱着一个时代的沉默,在内心的巢穴里进出,从巢穴汲取力量,并以此拥有涉入地狱般深渊的勇气。
而后,让尘埃掩盖自己曾被读起的名字,忘却来路归途,不断分解和重构另一个恢宏浩大的心灵世界,让最终的我得以返回最初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