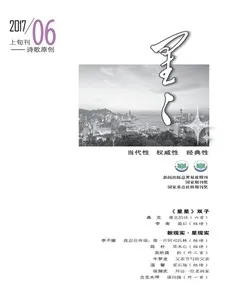抄自故乡的单词(组诗)
红 薯
一个安静的梦想家:它躺着
在隆起的土堆里睡上一个秋天
接着在地窖里冬眠
从童年到中年,我从来没有打听过
它梦到的,是不是与我一样多——
一个喻体:它的成长史
与我约略相同。父亲腿上的泥巴
母亲手上的柴火,无尽的阳光雨露
围着它一年四季不停地转
却只有一点清香报答苍天大地
一个故乡的词根:关于土地和时代
它反复验证的年成,折射宏大的
叙事背景:农耕文明的衰退
生产关系的变幻,在原始的农具下
它的面孔陈旧而新鲜,像人类生活本身
一个可靠的预言:永远吃不透的根系
大地周而复始的绿色。生命从泥土中诞生
到人间流浪,岁月的馈赠不多也不少
水 陂
我热爱它的干净。浣衣的人已离去
泥巴沉入水底。阳光照着人间的幽微之处
除了多出来的几粒鱼虾,沧浪之水
保持了山中的模样。水边的乡村
像树木的影子不见瑕疵——但我也热爱
它的肮脏。洗菜的人捋起了衣袖
丢弃的叶子开始腐烂。锄头把泥土的咸味
吐进水中。粪桶将剩余的营养
留给岸边的水草:这热闹的一切
酿造了乡村醇酒一般的黄昏
我还热爱它的枯竭,一种坚持到底的意志
像饥馑年代,乡亲们难以迈过的坎
但过不了多久,春水就涨起来
归还它源远流长的梦想——一直以来
我渴望着像它一样丰富和成熟
生命的停顿和流淌,融汇着人类的希冀
但我又向往它的单纯:冬天的清晨
清浅的水面上薄雾散去,几只鸟吃过的柿子
咚的一声,就让它记住了大地的恩情
民 宿
最先是一位戴眼镜的人,像医生,又像画家
反复打量着这些废弃的土屋,他用青山绿水的
目光,发现乡村另一种笨拙的美
接着是一批工人。像面对一位年迈的病人
用减法和加法开始手术:把发黑的灶台
拆除,把零乱的柴薪搬走,把断腿的木凳
清理,把腐败的檩子更换,把原汁原味的生活
掏空。然后为门窗房梁上油,为石器,木器,竹器
除去尘埃,归置一隅,并标注名称。而房前屋后
小径铺上了卵石,青竹掩映着清池,仿佛迎接
归来的隐士——但入住的,是一批衣着光鲜的
过客。他们看完了村里的山水田园,吃过了
农家菜蔬,却并不走进现代气派的宿处
他们把灯光打开又关上,走到小院里在青瓦之下
一弯新月斜挂,钩沉乡村往事。就像改造的民房
在月光下辨認自己的前身
河 滩
在诗人的故乡,这些河滩,丘陵,田园
按照另一套修辞进入深沉的内心
它的荒凉和粗粝,只沿着一条线路
展示神秘的美学——当夕光
镀亮了茅草,这时光的分泌物
又一次侵蚀村庄破败的砖墙,倔强的树木
石桥苍老的脸上野花摇曳,透露了多少
一闪而过的明眸皓齿。流水哗哗地
冲刷河堤,四十年前的烟柳繁华
隐匿于浪花之下——这就是诗人的故乡
艺术完成了加法和减法,与本体完全重合
的确,更多的美停留在生命源头,与诗人一起
固守单纯的情感取向,拒绝别人的参与
但我相信诗人跳跃的语调。相信他额上的
一根白发,蕴藏着鲜为人知的红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