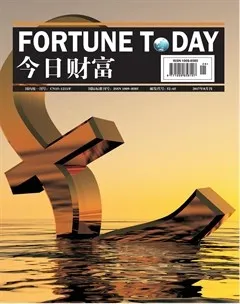中美竞争下东亚各国安全政策分析
随着中美在东亚乃至全球的竞争越来越显著,受其影响的东亚各个国家不得不在这种环境下进行困难的抉择,尤其是在安全领域。各国依照其原有的结盟体系,国家实力和国内政治因素,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中国崛起速度的加快,在全球主要在东亚区域,中国与美国的实力对比逐渐接近,其影响开始大致相当。东亚原有的以美国为首的安全结构开始出现松动,中国提出了与美国不同的安全主张,使得东亚区域各国在中美之间开始了新的安全政策选择。
一、中美实力接近,东亚安全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经过十多年的反恐战争和2007年以来的次贷危机、全球金融风暴,美国的综合实力在全球和东亚出现了下滑,不再具备本世纪初一览众山小的绝对优势了。主要体现在经济规模优势缩小,按照世界银行购买力评价统计,中国在2016年全球GDP排名中位列第一。图表1 世界主要国家GDP(购买力评价)2016
美国在全球的贸易主导优势也在逐步丧失。到2012年,中国就取代美国成为很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这其中包括了韩国,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国。美联社的分析表明,2006年,美国是全球127个国家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这一数字为70个。如今该现象完全逆转,2011年中国是124个国家最大贸易伙伴,美国则是76个。美国现在收到经济危机影响,其财政能力也受到极大限制。美国的财政预算赤字越来越高,联邦债务也不会减少。但美国庞大的预算赤字必须要用联邦债务来进行弥补。这导致赤字越大,联邦债务越高。而联邦债务越高,带来的财政负担也会越来越大。最为严重的就是美国军事投入会受到极为严重的影响。2012财年开始,国防部已经受到了4870亿美元预算的影响。2011年的预算控制法案(Budge Control Act, BCA)创立了一个持续的削减经费机制,即在未来十年每年削减50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1]
与此同时,中国综合实力全面提升。除了在GDP(购买力评价,以下均值这一指标)超越美国之外,在制造业规模和水瓶,全球投资、贸易主导地位等方面都取得了极为显著的进步,这给中美在东亚的竞争带来了基础性的资源。
中美在东亚这一区域整体而言,美国还是占据相当优势的,但中美实力更加接近平衡则是未来的大趋势。中国在经济领域的追赶效应最为明显。尽管中美综合实力在全球范围并没有达到同等量级,但在东亚区域,两者之间的实力差距是很小的。
二、决定东亚各国安全政策的外部因素
与中美的战略安全关系是影响东亚各国安全决策的重要体系变量。在一般情况下,安全利益排名第一,这是其生存的最低也是最重要的因素。
不同的安全关系决定了这一国家的行动选择自由度。有学者认为,结盟有三种不同的构成方式,等级制,共识凝结式,以及混合式。美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盟友是分为不同类别的。日本是战败后被美国占领,在美国主导下确立了日本宪法和管理模式。美日同盟是非常典型的等级制。美韩关系则是在二战后美国主导下建立的,朝鲜战争之后由于冷战对峙,美韩同盟关系也呈现出显著的等级制。日本和韩国一个是被占领国,一个是被保护国,所以这两个军事结盟都是等级制,也就是说美国在这种关系中具有最高最直接的决定权。
对日本来说,日本同盟是日本所有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的基石,这是不容也不能被改变的。这也是日本在执行对外政策的时候总无法突破的天花板。因此对日本政府来说,利用好日美同盟关系,提高日本的国际战略地位,获取更多的国家利益,就成为日本制定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在涉及东亚的重要战略问题上,日本都会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在中美两极化进程中,日本在安全结构中从初始条件到进程变化中几乎没有发生改变。
对韩国而言,其安全政策选择是极为狭隘的,尤其是在萨德部署问题上。萨德系统是末端高空防御体系,对于防范所谓朝鲜导弹威胁根本没有实际意义,反而对于窥探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导弹发射及其性能侦察是严重的威胁,这会进一步加剧中俄对韩国的战略敌视。无论是朴槿惠政府还是文在寅政府,都无法自主的改变这一决策。这也是美韩同盟对韩国自主决策权的限制的典型表现。
而与美国没有签署正式安全条约的伙伴国家则有着相当的自由程度。但还是与美国保持程度不一的联系和合作。比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等。
中国的新安全观则让东亚区域避免出现冷战时期的极端对峙态势。2014年5月,在上海举行的亚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新安全观,那就是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亚洲安全观。[2]此后,在2015年9月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讲话中再次指出,要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中国最高领导关于新安全观的提法、内涵和全球视野,与美国单边、排斥、利己、不可持续的安全观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战略观念与现有东亚两极化进程是能够相互映照的。
三、东亚各国安全政策的选择趋势
在中美两极实力均等,战略关系转向对抗竞争性进程中,东亚各行为体内部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偏好则决定了各自对外政策的方向偏好和价值排序。这其中执政者及周围集团对于自身利益考量和意识形态思考是最为关键的变量。而不仅仅是所谓的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和冲突。
对于日本来说,其政治右倾化和日本自身实力的衰落驱动日本政府更加倚美抗华。在钓鱼岛、东海防空识别区、反导等领域进一步加剧了安全争端。而韩国的“朝鲜恐惧症”决定了韩国将被美国安全战略所绑架,在面临国内外巨大压力之下,朴槿惠政府仍然批准了萨德系统的进驻,文在寅政府也没有改变这一决策。
东盟国家无论是哪一个,在中美面前都是小国,因此,他们普遍追求不受大国控制,同时能够获取大国带来的好处。因此,很多东盟国家都表示欢迎中国永远不称霸的宣言。但是,它们又特别害怕在中国崛起历史进程中可能发生的权力转移所带来的冲突和不稳定,又特别需要依靠大国来解决安全与稳定问题。所以说大部分东盟国家都没有采取“制衡中国”的政策选择,只有菲律宾在阿基诺三世执政期间采取了与中国对抗的政策,杜特尔特执政后改变了这一选择。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都采取了所谓的平衡性政策,即在中美之间尽可能保持中立,而不不是做出被迫的选边决策。泰国虽然是美国盟友,但泰国方面对于美国干涉内政尤其是军事政变后美方的言论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其中立政策也不会改变。越南虽然与中国存在南海争端,但越南政府更更加倾向于与所有主要国家建立伙伴关系而不是盟友关系。新加坡最近有着与中国的政策和南海问题的分歧,但最终选择了调低调门,修复对华关系,总理李显龙还访问了北京。
这些都充分表明,东亚各国在安全领域并没有如同美国期望的选择站在美国一边“制衡”崛起中的中国。这也让美国“重返亚太”“亚洲再平衡”战略面临极大的困难。(作者单位为贵州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