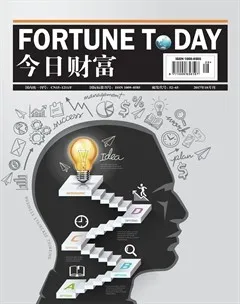未成年人入罪问题的研究
当前未成年犯罪高发,而且形态、情节也更加复杂,当前基于对未成年人保护政策,往往因年龄限制不能入罪,只能由家庭、学校间来平息,肇事者得不到有效的惩罚和教育,成本极低已经对不能适应当前的社会发展,不能起到保护和预防的作用,要想适应当前社会发展必须从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区分恶性及主观心理,增加社会调查、交流评估程序,以及增加对监护人、学校进行适当的惩罚等几方面来共同解决。
一、刑事责任年龄的问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知识进步、科技教育水平的提升,未成年人的成长成熟也进入了高起点、高速度的趋势,未成年人思想性格成型,认识对错辨别是非的能力已经提前,当今发达的网络媒体更是缩小了见闻渠道的限制,他们可以不像80后90后那样经历和年龄基本是匹配的,12、13岁左右我们眼中的孩子基本上能接受各种媒体画面、社会百态的冲击,而当前各类偏激的、利已的思想已经在部分未成年人思想中传播、滋生,甚至根深蒂固难以清除,而年龄的增长并不能像以前我们设想的那样能给未成年人多少改变。而结合近年的案例,我们也可以观察到未成年人犯罪的情节、心理、形态也有很多变化,已经不是原来的由于激愤的情绪、偶然的环境、过失的过作,大多是在常期的恶习下转化为一次不计后果的犯罪,个别案例中本应还是孩子年龄,却心性残暴,案件令人发指。
另一方面考虑到未成年人在特定年龄时确属脾性未定,尚有回归社会的可能,同时减少社会负累不易一概追责,所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宜以社会发展为基础,不能无限制降低,应以13、15周岁为界,划分相应犯罪的刑事责任范围。
二、增加未成年人犯罪成本
当前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多以学校、家庭教育为主,有时候低下头,认个错也就过去了,即便过了风声依然我行我素,不思悔改,在法律制度上也是无可耐何,这种不痛不痒式的惩罚,经历过的多了,可能会被视为被纵容,甚至有些未成年人在犯罪后直言“我是未成年人,我不负责任“,这种明知思想是对被害人的嘲笑,对法度的无视,所以必须要增加未成年人犯罪的成本,其一强化对监护人的惩罚,例如:暂时交纳与监护人收入水平相适应的保证金,使得他们对孩子的教育认真起来,而不是现今的有些家长似的“管不了就不管了”,或“花点钱平息了就万事大吉了”,结果事了了,孩子就不想着教育了,根本没把一次错误当回事,认为孩子只是顽皮,不予重视。树立全社会家庭生子、育人是责任的意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即使在未成年人犯罪后,其父母在多数情况下也是最易接近未成年人身心的人。其二必须要建立学校责任制,当前学校的重心在学习成绩上,衡量孩子也只以成绩为标准,而忽视了学校是要将每个孩子陪养成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之人的社会责任。在这种思维下最终相当顽劣、成绩差的未成年学生可能遭到学校和自我的双重放弃,结果可想而知,其二学校内的暴力往往得不到校方或者老师的重视,校方和老师普遍认为孩子之间的只存在打打闹闹,平时总是受欺负的孩子如果向校方反应问题反倒是被认为是小题大作或是认为被欺负者自身性格懦弱,最多对欺辱他人的人只是象征性的说教一下罢了,这样下来一方面欺人者学会卖乖,更加隐蔽,被欺者呢无处救济,而存在这种现象的学校、班级内的同学们往往要比给老师和学校更加清楚,老师和学校却成局外人,事情得不到控制,演变成犯罪后校方、老师也只是受到不良的影响而已。所以当前必须建立学校、老师的责任制,师者真正起得传道、解惑,要求老师将孩子间的简单初级的暴力记录,针对存在暴力行为的孩子与家长沟通,共同教育在萌牙状态消除孩子的倾向,对于只关注孩子成绩,对班级内暴力现象不管不问,怠于处理的老师给给予记过或降薪处分,取消评优。
三、未成人入罪时必须区分主观恶性
当前社会上存在的另外一种未成年人犯罪或是接近犯罪的行为,这种行为已经不是以往简单的、偶然的孩子间的过当行为,常常是无底线的欺辱他人,手段越是残暴、伤害越是深重,他们越是兴奋,他们年龄都在12、13周岁,却已麻木别人的乞饶和痛苦,他们肯定能够明白他们的行为是会剥夺别人生命、健康的,他们只是在笑,这种麻木和残忍的故意行为在法律上被原谅,只是因为年龄仅差一岁而已,可能在情理不能接受,所以在法律规定存在两面性的矛盾下,即不能一味地强调保护未成年人施暴者而忽视对受害者的保护,也不能只站在保护受害者的立场一味地动用法律惩罚施暴者,所以引入主观恶性区分机制对待未成年人入罪,具体衡量个案辨别未成年人入罪出罪是合情合理的,建立一整套评价机制,对未成年人的情况综合调查、结合案情情节辨别主观心态,同时谈话探究真实心理,作为案件主要评判标准。(作者单位为辽宁省铁岭市调兵山市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