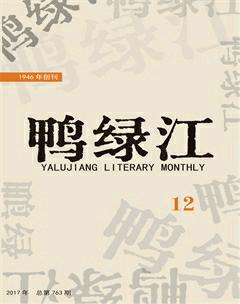雷锋与我的人生起跌浮沉
“雷锋与我的人生起跌浮沉”——当我为这篇回忆文章写下这样一个题目时,立刻想到,看到这样的题目,人们一定会产生疑惑:你的生平、经历和职业,好像与雷锋关系不大,怎么会与你的“人生起跌浮沉”有牵连?难道你与雷锋还有什么纠结处?莫非你曾经是学雷锋的先进人物后来倒退甚至“落魄”了?或者你曾对雷锋有过什么不敬而遭到应有的批评?如此等等——但都不是。
世人有所不知,原来我是上世纪1963年,普及全国、影响至今的雷锋报道与学雷锋活动兴起的“第一线”直接当事人。关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现在有点众说纷纭,或略去真实的情况不说,或语焉不详,或张冠李戴;甚至在正式的“历史文件”性的报道中,也不免有失误之处。虽然早些年《辽沈晚报》有过一篇于铁同志写的简略是“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文章,略述过历史的真实;还有哈尔滨《新晚报》2009年3月4日记者李玥报道《三十三岁记者笔下雷锋这样走来》,其中写道:“彭定安,这个普通的新闻工作者,通过一篇《永生的战士》的报告文学,第一次把雷锋带入国人的精神家园,由此雷锋这名普通的战士,成为全国人民的学习榜样。”但它们的内容既简略,影响也很有限。以后的一些报道,人们或者是未能看到,或者竟是“未予采信”,所以“依然故我”。我在几处雷锋纪念馆参观时,解说员开首介绍雷锋和学雷锋活动的渊源,也都是语焉不详,不明来龙去脉。我总是站在她们面前,耐心地谛听她们“不明究底”的介绍,含笑不语。我知道,在这种场合,要是我站出来,试图“真人说明真相”,人家反倒一定不相信,甚至会以为是来了一个骗子,或者目我为疯老头子胡吹。
以后,我在中共党史学会主办、以“揭示历史真相,展现世纪风云”为宗旨的权威性历史性刊物《百年潮》上,发表了《学雷锋活动是怎样兴起的》一文,才算是正面和稍微详细地述说了原委。但由于刊物的性质,公众面上知道得仍然很少,社会影响也很有限。现在,历史的真相似乎就要消失于时代的飘风中了。因此,为了还历史以真实面貌,为了澄清误传,也为了“立此存照”,我愿“连细节的真实”都尽量保留地来“钩沉”史实,纠正误传,恢复五十四年前的“历史现场”。我这样做,还有一个意念,就是要为当年(1963年)所有为雷锋报道和“学雷锋活动兴起”做出了贡献的有关人士留名,他们都已经作古了,自己不能说了,只有我还存活,能够为他们“说话”。这不是为他们“争功”,而是“还历史以真实面目”。这是唯物主义的应有态度。这些人士是:原辽宁省委常委、抚顺市委书记沈越,原辽宁省委常委、《辽宁日报》总编辑殷参,原《辽宁日报》副总编辑邢真,原《辽宁日报》政教部副主任霍庆双和政教部军事报道组编辑赵徐。——这里暂且只提他们的姓名,以示珍重。他们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做的工作,容后叙述到有关事宜时,再具体介绍。
1962年。那年我三十三岁。我1948年离开家乡,其时已经十五年未回过故土,已近中年了,为了乡愁,为了探望老母,我请准半个月探亲假,定在12月下旬举家回故乡鄱阳(当时易名“波阳”,现已恢复原名),火车票已经买好,只等到时候启程了。就在登车前夕的晚上,突然接到《辽宁日报》分工主管政教报道的副总编辑邢真的电话,召我立即去报社编辑部,接受重要的紧急任务。我赶到报社邢真办公室,他匆匆对我说:“先进战士雷锋牺牲了。报社决定大报道,分三个组。写长篇通讯的,写社论和言论的,整理选发雷锋日记和笔记的。”交代完毕,他接着说:“现在,决定长篇通讯由你来写。给你一周时间,你是快手,要按期完成。具体事宜,霍庆双会给你布置安排。”他又说:“我知道你要回乡探亲。你把车票退掉,完成任务再走。”邢真从部队转业不久,还保留着军队作风,行事果决痛快。说完这些,他又唠嗑式地说一下:“这次让你采写,是殷参同志点将。”这一点,我从他交代任务时,在“启用”我这个“隐形人”上,不是期期艾艾,而是果决的神态中,已经感觉到了。因为,此前他为了让我乘飞机突击采访,受到过批评。那是一年多前,锦县农村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附近的海军某医院及时全力抢救,效果很好,事迹感人,沈阳部队空军领导机关决定派运输机急送物资和药品去当地,并邀请《辽宁日报》派人采访。邢真闻讯,也是在下班后,电话召我授命。他急令我马上出发,跟随部队同志,乘运输机去采访,并赶写大通讯。他布置完任务后,出去了。过一会儿回来,对我说:“让你坐飞机采访,遵佗同志批评我了。”——那时,“记者坐飞机采访”是破天荒的事体,怎么能够让一个“摘帽右派”享受?王遵佗的批评是有理的。她是当时《辽宁日报》副总编辑、总编辑殷参的夫人,延安来的老报人,位居常务副职,“高人一等”吧,故可批评另一位副总。我听了,连忙说:“那我就不去了。”邢真却说:“已经定了。遵佗同志问我,‘你跟他说了吗?我说,已经布置了。她说‘那就算了吧,下不为例!”接着又说:“你可要好好完成任务啊!”言外之意是:你要是没干好,我就更不好交代了。所以,这次如果不是殷参的决定,邢真是不敢造次“破例”的。
在这个细节上,现在就出现了一个误传。在一篇正式的关于《辽宁日报》的雷锋报道的文章中,就写成是殷参接受沈越的建议后,打电话给总编室的范敬宜,要他打电话给我布置任务(《<辽宁日报>是如何宣传雷锋的》,见《辽宁日报》2013年3月5日)。这就完全是误传了。事实上,当时范敬宜不但不在《辽宁日报》总编室,而且不在《辽宁日报》,而是在它属下的《辽宁农民报》工作,怎么会出现上述那种事情呢?而且,即使他在总编室,按工作程序,也不会是总编辑让一个一般人员给另一个一般人员打电话布置重大任务,更不要说,那时彭、范二人都是“摘帽右派”,绝不可能发生这样不可思议的怪事。这种误传,虽然把范敬宜同雷锋报道以及学雷锋活动联系起来了,但对他一点意义也没有,也许还有负面的影响。故在此对一个误传的历史细节加以订正。
這里还需要补充一下这次大规模雷锋事迹宣传的原委了。原来,雷锋在驻抚顺的工程部队中牺牲后,在省委委员、抚顺市委书记沈越的指示下,在抚顺就展开了大宣传,在《抚顺日报》上,连载雷锋事迹的报道,并开展了热烈的社会性学雷锋活动。同时,他还建议同是省委委员的《辽宁日报》总编辑殷参,在《辽宁日报》上展开全省的宣传。殷参接受了他的建议,并作为重大报道来亲自抓。这样,就有了上面所说的邢真向我布置紧急采写任务的事。
再说我从邢真处出来,就按他所说,去找霍庆双同志,他是這次重大报道的一线指挥,所有采访活动均由他安排,所有稿件也先交他初审过关,然后呈邢真审阅定稿付排。我见到霍庆双,他先交给我一份油印稿,他说:“这是雷锋生前所在团的俱乐部主任写的,关于雷锋的详细材料,你可以参考。”又说:“已经联系好你去雷锋部队采访,现在,你先去工人文化宫参观雷锋事迹展览。这也联系好了,他们会为你特意开馆。”我拿了那份油印材料,便直奔工人文化宫。果然为我一个人在中午休息时开馆。于是我得以独自个儿,在寂静中,注意地、仔细地、漫漫地,巡阅、观看,细读雷锋日记和笔记,并选要摘录以备用。我在这寂静的展览馆里,默默地观看、认识、理解雷锋,并酝酿初步的腹稿。当我走出展览馆时,我心中闪过两个意念:“雷锋不死,能当将军”和“雷锋永生”。这后一个意念,后来化作了雷锋报道的题目。应该说,这两个意念,并没有错;至于霍庆双给我油印材料作参考,更是新闻工作中常规、常见的事情。但是,真个是“天意从来高难问”,历史的发展却是:这两件事,让我给自己种下了祸根。
我在结束采访之后,觉得材料已经很丰满了,只是,未见其人,未见其事,缺乏现场感和直观的感受。于是我想起了那位俱乐部主任,他是雷锋生前战友,他能够提供这方面的鲜活见闻。于是我约见他。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我们在《辽宁日报》编辑部的二楼我的办公室里会见,他还带了一位年轻的女友同来。我们交谈了约莫一个多小时。他提供了一些有关雷锋生前音容笑貌的材料,有助于我想象活着的雷锋的形象。我们欢快地握手言别。
在结束采访之后,我进入写作阶段。此前,关于活着的雷锋的报道,陆陆续续累积已经很多了,他已经拥有了“红色战士”“毛主席的好战士”的光荣称号。不过,那些报道,大都是一个时期的事迹、一个阶段的表现或者一个事件的出现等等的报道。综合的大报道也有过,但一是仍然不够详尽,二是影响有局限。而现在,雷锋牺牲了,再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报道,就要求更为全面详尽地书写了。因此,我确定以“拟传记”的形式、规模和歌颂性的笔调,来全面地、系统地、综合地、总结性地,报道雷锋生前事迹;特别是提炼、概括出“雷锋精神”的精髓是当时提倡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共产主义风格的具体实现,这就是“助人为乐”——处处、事事、时时,主动热情地帮助人,做好事,而且隐姓埋名。于是我决定以“传略”体式来写,即按苦难童年→解放、参加工作、参军→一系列事迹表现→不幸牺牲,这样一个叠进式进程来写。基于这种“创作设计”,我拟定了这样的有连缀性、系统性,循序而进地表现发展进程的小标题:《血泪九年》→《新生》→《启蒙》→《斗争》→《熏陶》→《苦学》→《功业》→《入党》→《向前进》→《谦逊》→《永生》。
通过采访,通过参观展览和阅读雷锋大量的日记、笔记,在丰富的鲜活材料基础上,在了解了活着的雷锋的种种感人事迹的基础上,我产生了对“传主”的热烈而深厚的感情,也产生了对雷锋思想、精神的理解和诠释的理性概括。我理解,雷锋由于在旧社会遭受了种种苦难,对它具有超乎常人的恨,因此,对新社会,对共产党、毛主席,就具有超乎常人的爱,这种发自内心深处的爱,化为日常行动,就是在工作和生活中,那些超乎常人的先进行动和事迹。他工作上无论何时何地,总是热情、积极、主动,总是超等地完成任务;在社会上,就是总想为他人做点什么,奉献热诚、尽力帮助,而不留姓名。而此时,正是大力宣传“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共产主义风格的时期,这更增加了雷锋做好事、帮助人的理性和自觉性。它的这种精神和行为,凝聚成通俗而容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的话语,就是“助人为乐”。
这样,我怀着对雷锋的这种理解和理性概括,带着对雷锋的热爱之情,怀着激动的心情,开始撰写通讯。我有意摆脱一般新闻通讯的格局和笔调,而尽量使用文学笔法、形象语言,“笔锋含情”地书写。进展很顺利,语意流畅、叙事翔实,逻辑和情感一致,流泻而下。一天多时间,就完成了八千多字的长篇通讯,而由于其行文具有一定的文学性,叙事方式、整体结构和段落间的顺畅衔接,实际上它成为一份报告文学的篇章。给我一周的时间完成任务,我五天就完成了。
行文至此,我觉得需要也应该暂断叙事,而对这段“历史事件”或称“新闻史”做一点“史的解读和诠释”,同时,也是“同步”批驳现在一些对于雷锋和学雷锋活动的造谣、污蔑。从以上的事实可以看到,雷锋之成为先进典型、英雄人物,是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是他的长时期的具体行动累积起来的。他当工人是积极奉献的劳动模范,参军之后,在部队里,他各方面都有超越他人的积极表现,同时,在社会上,又隐姓埋名做了许多好事。这样,他的模范事迹,先先后后,在军内报纸和地方报纸上,都有及时的、分别的报道,日积月累,他获得了“红色战士”“毛主席的好战士”等光荣称号。这可以说是积少成多、集腋成裘、实至名归。他因公牺牲后,首先是在他部队驻地的抚顺市,在市委书记沈越的关注和指示下,展开了大规模宣传,并在市内开展了群众性的轰轰烈烈的学雷锋活动。尔后,在沈越的建议下,殷参又在《辽宁日报》上展开了更大规模、更大影响的宣传。事情就是这样一步步发展、提高、升格的。这里,丝毫没有谁在事先定下一个什么“政治目的”,然后制造事实,弄出一个“人造模”来。至于所谓“为什么他隐姓埋名做好事,却又有那么多事情被人知道、被宣传报道了”,这也很好解释和理解。雷锋做好事、帮助人之后,往往在被询问姓名时,回答说:“我叫解放军!”虽然如此,人们的往往事后会去部队追索、表示感谢,这就露出了真名。就像现在有的护士在路上抢救了急病人后悄然离去,但事后人们还是追查找到她一样。事实上,雷锋所做过的好事还很多,报道了的,为人所知的,应属少数。更多的是不为人知的。
现再接续中断的叙述。
我写完通讯稿之后,按照参观展览时“雷锋永生”的感受,写下了题目:《永生的战士》,同时署上了那位提供了油印材料的俱乐部主任的名字。我拿去交给一线指挥霍庆双,我记得很清楚,我是在走廊里碰见他,把稿子交给他的。他接过去一看,就说:“你写的稿子,怎么署了他的名字,却没有你自己的呢?”他说完,我们对视一下,立即彼此明白:我是“隐形人”,可以写新闻、通讯、评论、社论,甚至为省委主要领导起草文稿,但必须隐姓埋名。他于是说:“那——署个笔名吧!”我因为马上要回故乡波阳(现恢复原名鄱阳),急切间回答说:“好,那就署个‘波阳吧。”他便在第一署名后面写上了“波阳”。关于这件事,霍庆双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详细记叙过,他写道:
老彭的一生是历尽坎坷的……让他写文章,但不让他的名字见报。而他毫不计较名利,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且干得极其认真,总是很出色地完成任务……雷锋的宣传便是一例。
1963年我在政教部负责政法摊的工作,殷参同志交代了雷锋宣传的任务后,社论由我起草,通讯由谁来写呢?这时就又想起了老彭,于是把他抽出来搞通讯的采访写作。他二话没说接受了任务,开始进行采访。……沈阳军区搞宣传的……提供了一份宣传材料,老彭便参考这份材料,吸收采访中得到的材料,带着深厚的感情写出了长篇的深刻、生动、感人的报告文学《永生的战士》。在发稿时他没署自己的名字,我问他:“你写的为什么不署名?”他说:“不用署名。”我说:“不用真名,那就用个笔名吧。”这样,《永生的战士》就用波阳的笔名发表了。(《超越忧患的求索·说说老友彭定安》,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
霍庆双接过稿子后一边往办公室走,一边对我说:“我正赶写配发的社论,赵徐正在整理、挑选雷锋日记、笔记,准备发表。就等你的通讯了。”他的话,表明了“长篇通讯”是这次报道的主体部分。我也了解到,还有其他同志在为这次的报道用功出力。
稿子经霍庆双初审后交副总编辑邢真审定发稿,又经总编辑殷参终审,一路未作任何修改,全文照发。文稿小样出来后,我寄了一份给那位非合作者的“合作者”,征求意见。他阅后给我打电话,说:“文章写得很好哇,我提不出什么意见;可是我没有写,还署了我的名字,很感谢!”(附带说一下,我在发稿稿签上注明:稿费一半寄合作者,我的免发。稿费是送达了的。)
《永生的战士》于1963年1月8日见报,占第三版一整版。这天一早,我就接到《辽阳日报》吴非的电话,他是我在《东北日报》的老同事,后调《辽阳日报》工作,他说:“《永生的战士》写得好,我一看文笔,就知道是你写的。很感人、很轰动。我们这里反响很大!”这是我听到的第一个反映。
当晚,我就携全家登上火车,奔向南归省亲的路。在鄱阳度过春节,半个月后回到沈阳,即听说在这短短的时日里,发生了许多事情:《辽宁日报》的雷锋报道,在全国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在军内的影响也很大。总政特别邀请《永生的战士》作者去北京作报告。我这个真正的作者,自然不能去,而是由未着一字、不是我的合作者的“合作者”去了。他正好以“雷锋生前战友”的身份去给部队同志作报告。由此,他改变了退伍的命运,而继续留在部队,以后,则几乎可称为“宣传雷锋第一人”,并以此为终身职业,在这方面,他做出了可贵可赞的贡献;而职务也不断升迁,达到高层。同时,在这些时日里,新华总社、《人民日报》都来向我约稿,《人民文学》编辑部更为我申请半个月创作假,为他们撰写长篇报告文学。这些邀约,自然也都以“众所周知”的原因,被婉拒了。而从此之后,我与雷锋,就毫无关联了。在他人,也许就因此“一举成名天下知”了吧。但我没有,连一句褒奖的话语都未曾听到过。
但我内心还是深感欣慰的。回忆自1950年学新闻专业结业,服从分配,出关来东北,先在《东北日报》做编辑工作;1954年大区撤销,转入《辽宁日报》,继续担任文艺编辑工作。到此时,新闻从业生涯,已经十三个春秋了,虽然写了许多通讯、消息、书评、影评以及文学评论、短论、社论,数量不少,但是至今并无可观成绩,也就数这篇产生了全国影响的报告文学,算是“突出成果”了;再有,就是1956年为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在《辽宁日报》上连载的《鲁迅的一生》了。已经“微近中年”了,其时虽然隐姓埋名工作,但能有机缘写了这么一篇报道,也算“堪慰平生”吧。
那时,还发生了一件与此相关联的事情。我的朋友,也是《辽宁日报》的记者李宏林,因被错划右派,此时在行政科卖饭票。他约我一同写表现雷锋的电影剧本。我欣然同意。他本是有出息的剧作家,我熟悉雷锋事迹,我们的合作,定有成效。那时候,在班上是绝对不允许干本职工作以外的任何事情的,我们都在晚上秘密写作。我们分工,我写前段,他写后段。我们很快就合作完成了电影文学剧本《雷锋》,并立即寄给长春电影制片厂。不久即获通知,“接受剧本,立即筹拍”。这可以说是真正的第一部反映雷锋的电影文学剧本了。我们那时都还年轻,剧本未必很成熟,但正当其时,时代感、鲜活性、蓬勃朝气还是蕴含其中的。但是,一到调查作者状况(这是当时必做的政审),事情陡变。长影的调查电话打到省剧协,得到的回答是:“两个作者都是摘帽右派,这涉及什么人占领舞台的问题,绝不能采用他们的作品。”于是第一个写雷锋的电影,便胎死腹中,化为泡影。
在此前多年军报、地方报纸众多关于雷锋的陆续报道的基础上,《辽宁日报》这次在雷锋同志牺牲后大规模的、系统的、全面的、详尽的、总结性的报道,在全国产生了轰动性的巨大而广泛的影响。在这里,不能不说到前面提到的,那些为此付出了辛劳、做出了贡献的人。首先,是抚顺市委书记沈越,他率先在抚顺大规模宣传雷锋并发起学雷锋活动。尔后,他又建议殷参在《辽宁日报》大规模宣传。而殷参则不仅接受建议,还准确地把握了雷锋宣传的要旨,做出了大规模报道的战略性决策与规划。然后,副总编辑邢真,作为战略实现的战役总指导,又是积极地、有效地具体实现战略意图;至于霍庆双,作为战役一线指挥,具体地、认真地一一落实报道要求。还有赵徐,默默地从雷锋大量日记、笔记中,选出重要的发表,这是第一次“摘要选用雷锋笔记”,它是以后各处选用的基础。所有以上诸位,都是与有功焉的,是“历史的实现者和实践者”。历史不能假设,但是,我们不妨设想,如果没有沈越的触发和建议,如果没有殷参的积极、富有思想的大规模宣传構思和战略计划,以及邢真的有效执行、霍庆双的具体实践和实行,还有赵徐的默默工作,那么,当然就不存在雷锋的全国性影响,更无领袖的题词,而学雷锋活动也就不可能产生。雷锋和他的事迹,也许就湮灭在历史存档中,消逝于历史的烟尘中,而不为后人广知了。
《辽宁日报》的雷锋报道在全国产生巨大反响之后,《中国青年报》于1963年2月5日,予以转载;转载时略微删去了一些文字,把作者名移到文末,用括弧括上。十几天后的2月16日(或17日),《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思想教育组几位编辑,在编发准备发表雷锋事迹报道的“学雷锋专号”这期刊物(1963年第五、六期合刊)时,考虑如何在其他报刊已有宣传的基础上,做到“后来居上”,就设想请毛主席为雷锋题词。于是给毛主席写了呈请信函。过了两三天,毛泽东主席的题词仍然未收到。因刊物出版在即,编辑部便打电话向到毛主席办公室询问:毛主席是否同意题词,如果同意,是否能够在2月25日前赐予。一天,毛主席休息起来,秘书林克提起雷锋题词一事,并呈上已拟好的十几个题词稿,他看了均未采用,便自己提笔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这个题词。3月4日,新华总社向全国发通稿;3月5日,全国报刊发表了毛泽东主席的这个题词。一场学雷锋活动于是在全国兴起。
这个过程,从《中国青年报》转载,到《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请毛泽东主席题词,也是延续前述各节发展过程,一步步发展过来的,普及全国、轰轰烈烈的学雷锋活动也就是这样兴起,并一步步发展起来达到高潮的。这里,完全没有什么“事先确定一个政治目的,制造一个假英雄,让全国学习”这回事。
当全国掀起学雷锋热潮的时候,我的那位“合作者”自然是“当仁不让”的“宣传雷锋第一人”;而一个真正的作者,却隐姓埋名、继续以无人理睬的“隐形人”的身份,埋头工作、低头做人。
事情如果到此结束,在我也就算是幸运了。而在我内心,我做了,产生积极社会影响了,整个报道成功了,我也就心安理得,生命潜在的意义得到了,无褒无奖、默默无闻,又有何妨?
但是,事情并不止于此。历史有时很严峻,个人命运有时很曲折。
三年之后,“文革”风起。我立即成为首先被揪出的“《辽宁日报》第一个牛鬼蛇神”,定性为“死不改悔的右派分子”。缘由(用当时的语言说应为“罪行”)是我“利用编辑《星期天》副刊之机,挖空心思疯狂反党反社会主义”。原来,在1961-1963年期间,由于在三年困难时期,按照“物质缺乏,多提供精神食粮”的指示精神,我应领导安排,负责编辑《辽宁日报》的《星期天》副刊,其中辟有“故事新说”专栏,每次讲一则小故事,然后加以简略的意义阐述。每期一则,均是我编写的。另有“科学诗”一栏,均是我依据一些科学常识和科学趣闻,采用诗的形式加以表现。在“文革”中,这个“故事新说”加上“科学诗”,被定性为“辽宁的《燕山夜话》”,这罪名在当时是罪加一等的。批斗中是这样揭露批判的,比如,“故事新说”中有一则源自《百喻经》的故事:一个人想要造三层楼,他对木匠说,我只要第三层,不要第一、二层,省事呀;木匠说,不造第一、二层,哪能造得第三层?“新说”则略微阐释云:人们学习、做学问也是如此,要循序渐进、一层层累积。主题意旨是很明确的。但批判者却指出:“这是攻击大跃进没有基础,是空想。这是恶毒攻击‘三面红旗。”又如,有一首“科学诗”说非洲有一种大蚂蚁,能麇集把大蟒蛇吃掉。这不过是一则科学趣闻,并无深意。但揭露批判却说:“这是号召牛鬼蛇神起来把共产党吃掉!”如此等等。另外,还有我利用十年业余时间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忠王传》,因为戚本禹著文批判李秀成是“叛徒”,这剧本也就定性为“为叛徒树碑立传”了。这是我第二项大罪行。
这样,我就成为报社第一个被停止工作的人,以“牛鬼蛇神”的戴罪之身,在编辑部打扫厕所。
此时,虽然遭此污蔑不实之词批判,定我之所写,均是毒草;但我心中却有一盏不灭的明灯:雷锋事迹报道《永生的战士》。雷锋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先进典型,谁会砍倒、谁能砍得倒?到运动后期落实政策,我为此定能得到正面的助力,而幸获宽大处理。这是我确信不疑的。一盏不灭的明灯,照亮我那黑暗的前程。
但是,这一确信,很快变成幻影。
那是有一天晚上,在《辽宁日报》编辑部三楼,突然出现一张上顶天花板、下达地板的大“大字报”,硕大的标题是:《彭定安的〈永生的战士〉是一株不折不扣的反毛澤东思想大毒草》。其大意是:“雷锋是‘毛主席的好战士,彭定安却污蔑他是什么‘永生的战士;他还胡说什么雷锋是‘积小事而成英雄,这是彻头彻尾的贩卖刘少奇的‘吃小亏占大便宜的修正主义黑货”,最后批判说:“这是疯狂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读完这张大字报,脑子一片空白,心里却被堵塞无隙。我欲语无言,欲哭无泪。那盏心中不灭的明灯,彻底地被掐灭了,那渺茫的求生的希望也幻灭了。我知道,申辩是无用的,而且是不被允许的,还会罪加一等。我只有等候最后的灭顶之灾的降临了。
就在这种绝望之时,又来“雪上加霜”。第二天,又出现一张同样“顶天立地”的大“大字报”,题目是《严正申明与强烈谴责》,原来是我的那位不是合作者的“合作者”的言辞激烈、义愤填膺的“严正申明”。《申明》说:“彭定安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狗胆包天,盗用我的名义,发表污蔑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的黑文……”下文我已经无法忍耐看下去,也无须看下去了。解放军领导同志的严正申明,还会假吗?我毫无申辩之力。“彭定安用心狠毒啊!”人们震怒了。在当时当地,这严正申明,有千钧之重,对一个“牛鬼蛇神”,具有泰山压顶的无穷威力和置之死地的威权。我只有、只有,俯首就俘、引颈受戮,别无他途了。
紧接着,又一张大字报宣布:“沈阳部队领导指出《辽宁日报》走资派让右派分子彭定安去采写关于雷锋的报道,是对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的极大的侮辱!”我在“罪行”之外,又受到真正的人格侮辱。
正当此时,一张简短但分量极重的大字报,适时而出,云:“彭定安这样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用不着再开什么批斗会了,立即逮捕,送法院,审判、判刑。”
这样,我在“处心积虑、千方百计,炮制黑文,疯狂反党反社会主义”和“为叛徒树碑立传”的罪名之外,又罪加一等:反军、反毛泽东思想。
事情到此,已成结局,无可申辩,无可救药。至此,也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吧,我反倒无惊恐、无忧虑,也无冀盼,就干等那一天的到来,心地反而“踏实”了——心死了。
这时,还有一件事“应运而生”。《辽宁日报》造反派组织,也许是为了配合以上诸多行动,还编印了一份“白皮书”,题目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彭定安罪行录》。上述诸多“罪名”罗列齐全。这个“白皮书”,不仅在报社内部人手一份,而且,还在围观在报社大楼周围的群众中广为散发。我就曾挤对在这乌合之众里,眼看着那“白皮书”在传播,深怕有什么人突然认出我来,那就可能立时惨死在愤怒群众的拳脚下。这样的事,幸亏没有发生。
但倒是出现了另一种万难想象的事情。那时正是新年快到的时候,报社大楼要升国旗、挂彩灯,这项任务交给一位烧锅炉的临时工办理。他把在锅炉房劳动的我带上当助手。我们爬上高高的高楼顶层,在狭小的顶层平台上,把国旗悬挂在旗杆上,然后牵电线挂彩灯,很艰难、很费事。中间,我们在小平台上休息,他平躺在地上,闭目养神,享受中午阳光的温暖。我没有敢放肆躺下,只在他身旁坐着休息。半晌,他闭着眼,仿佛自语,却是针对我说的。只听他用很轻的语音,缓慢地说道:“我看了那个小本本……”他停下了,没有再说下去;我不知道他将说什么,那时,随机地、“一对一”单独地批斗“牛鬼蛇神”的事情,是常发生的;他是不是也要就地单独批斗我,显积极、立战功呢?我警惕地、担心地认真谛听下文。他停了一会儿,却接着细声说:“我,决不相信,你是那样的人。”我心头立即涌上一股暖流。这是这个时期从未听到过,也不可能听到的友好的、理解的话语。但我不敢有任何表示,因为,表示同意吧,一旦传出去,就有“死不认罪,顽固不化,妄图翻案”的新罪名砸来;如果表示不同意,那就是不识好歹的浑球。我只能沉默以对。但我感觉到他是理解我的“沉默”的。
我感觉到我们之间的一种默默的心之交流。这位随潮来去的临时工,微近中年,中等个头,平素少言寡语,我对他一点也不了解。但是,这一幕在当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友好的理解和信任,我至今不忘,常常想起,永在的心之温暖!让我衷心地为久违的他祝福!
1969年初,我以戴罪之身到位于盘锦的省干校,一边劳动,一边接受批判。至年末,终于获得宽大处理: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于是在12月29日,在仅给三天收拾的时间内,准备就绪,全家四口,“五带”(带户口、粮食、工资、党员和团员关系)离城,乘坐敞篷车,冒着风雪,翻过大青山,到内蒙古敖汉旗偏僻山村插队落户,完成了“在大雪封山前到达插队地”的“遣送”律令。我们在这个穷乡僻壤困居十个年头,于1978年回到沈阳。我由于自己的坚持,终于获准离开《辽宁日报》,到新组建的辽宁社会科学院工作。
转年初春,我省召开新时期第一届文代会,我幸获代表资格。不意,在这个会上,发生了一件意外而有趣的事情。在小组讨论时,我被分在省直组,召集人正是久违的我的那位“合作者”,但我认不出在座诸位谁是他。我想,只要他作为召集人宣布开会,我就认出来了。果然,他宣布开始讨论,而他,就坐在我身旁!我于是对他说:“我是彭定安。”他转脸看着我,半晌,轻声说:“你受苦了。有什么困难吗?”久别重逢,历经风雨,我完全没有料到他会说出这样内容的话。急切间,我只是说:“没有。谢谢!”以后,我们再没有交谈;而此后,也再没有任何联系。直到1984年整党期间,却又突然出现一件事情。
那是整党期间的一天上午,忽然有两位校级军官来访,我在办公室接待他们。他们说明来意:在整党期间,部队有人揭发我的那位“合作者”,在“文革”时期,因为他的揭发,而使我遭受严重迫害,因此,他的重新登记受到阻滞,故特来外调,求证实情。我未经思索就如实回答说:“我在‘文革初期就被揪出,不是因他的《声明》而获罪;但他的《声明》确实增加了,也加重了我的‘罪行。”他们赶忙说:“如果你能够把这个情况写成证明材料,他就能夠重新登记!”我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并当即写出了书面证言,交给他们。两位军官高兴地接过证明材料,向我致礼,转身离去。
又过了几年,到了1990年代。我的挚友、《辽宁日报》高级记者、著名报告文学家和剧作家李宏林同志,为了替我正名,特意在他担任主持人的一个辽宁新闻界举办的文艺演出会上,安排我和我的“合作者”共同接受他的采访,一起回答关于雷锋宣传和学雷锋活动兴起的缘由和过程。我们俩共同回答了有关问题,说明我们在1963年一起署名发表了报告文学《永生的战士》,并握手言欢。
终于,我们“笑着向历史告别”。
这些,就是我能够提供的“历史真相”的准确版了。历史事件究竟是如何在最初诞生的,其起因,其发源与衍进,是怎样的情景,对现实来说,本不十分重要;主要的是它形成以后的和现实的性质和作用。不过,从发生学的视角来说,事物、事件的起源,往往决定了它的基质与品性。因此,了解它的起因和渊源,对认识其本质,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也许,这篇回忆录,在这一点上,能够提供一点“历史花絮”和供人思索的资材。而对“当事人”的我本人来说,则是难以忘怀的坎坷经历和应予重视的人生体验。
【责任编辑】 宁珍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