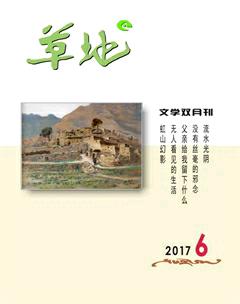父亲给我留下什么
远泰
父亲,就是在老家一位普普通通的乡绅。这个乡绅,是过去的称谓,今天,可以称作知识分子。以我的理解,就是一个有点知识的一份子。
父亲出生的年代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比较动荡的年份。人烟稀少的老家,仅有一座私塾供人们就读。父亲是他们那一代之中最小的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便被送到私塾去了。也正是这个时候,饥饿与灾难在这块土地上横行,并不富裕的家庭因此而很快贫穷下来。聪慧的父亲在私塾堂的成绩很让老师赏识,便在老师的怂恿下,年满十岁的父亲便只身去往成都,在一个皇城边的洋学堂从初级中学读到高级中学。成都解放的那一年,他又转到汶川威州师范就读,随后便回到老家当了名老师。
或许是父亲自身的成长经历时常触动着他的内心,他选择了教师这一职业,自此无怨无悔。教书期间,父亲在县的小学、乡的小学、甚至在村的小学,都会赢得家长和孩子们的感佩。在老家,有一半的居住民是土著汉族,这些土著汉民一些是十八世纪中叶乾隆皇帝征战大小金川时留下的。战乱平息后,有功之臣都得到了皇帝的册封,就地分得土地,于是,便一代一代的生息下来。一部分是近现代时期,经商、经营茶马互市留下的。另一部分,则是藏缅语系嘉绒支的藏族,这一支藏民族,是有着辉煌家族史的一支。他们的祖先叫做木塔尔,木塔尔是为大清帝国立下过赫赫战功、智勇双全的朝廷将军。曾多次在廓尔丹之战中屡建奇功的朝廷要员。至今,在故宫博物院的皇墙之上,悬挂着不下四张他的画像。父亲就是受政府派遣,去教育木塔尔的后裔。在当时,这是一群不懂汉语,也不会说汉话的学龄儿童,他们的交流全部是用的本民族的母语,这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年轻的父亲开始尝试着用嘉绒方言传教孩子们。渐渐地,送孩子上学的家长多了起来,沉静了千年的空谷有了关于读书的声音,本朴的孩子有了快乐的笑声。把自己的歌唱给别人听,把自己的锅庄跳给别人看。父亲让孩子们在自己的歌舞中寻找幸福,又把扭秧歌、打腰鼓教给孩子们。在快乐中学习,在学习中成长。
有一年的夏天,正是胡豆、青稞成熟的季节,也是野猪、老熊等野兽活动频繁的季节。夏天的阳光照在大地上,感觉一阵阵的闷热,学生们挤在一间四十多平米的教室里,腥臭的汗味弥漫在空气之中。下课放学的铃声响起,父亲用嘉绒方言说,孩子们,今天回家大家都要洗个澡,也把你们的老熊掌掌(手掌)洗得干干净净的,明天我要看谁最乖!第二天,绝大多数孩子都干干净净、高高兴兴地来到教室,只有一两个学生怯生生地站在教室外。正待上课的父亲,看着他们害怕的样子,便问道,怎么啦,为什么不进教室呢?一位学生难过地说道,老师,我们没有找到老熊掌掌。看着孩子们干净的手,父亲感到些许的感慨。自此,他除了教学,还不断地加紧民族语言的学习,以尽快适应特殊的教学。完全不懂汉语的孩子们,在父亲的教育下,很快地成长起来。当时的老家,新政府刚刚建立,需要熟悉当地风土人情的各类人才,以适应百废待兴的事业发展。父亲所教的学生,纷纷考上了民族中学,有的当了舞蹈演员,有的做了声乐演员,有的成了医生,有的从事首批驾驶人员。然而,新生的政权并不是一帆风顺,旧制度下的反动残余在老家时有活动,需要更多的人投入到清匪反霸的斗争中。不久,征兵工作在父亲所在的地方展开。父亲班上的学生年龄参差不齐,有一个学生小学毕业时已到了十八岁,他家里不算富裕,父母年过四十,膝下只有一个独子,本以为小学毕业后,回家敬孝双亲,让父母颐养天年。恰逢参军之际,父亲便主动上门动员孩子参军,经过严格的体检和政审,孩子光荣地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喜悦和自豪洋溢在这个普通的家庭,寨子里的乡亲们都为之高兴。没想到,孩子在黑水剿匪战役中光荣牺牲。那是一个黄昏,一对人从林间的弯弯山路上走来,刚吃过晚饭的父亲,听到远处隐隐约约的说话声,说话声由远及近,父亲从房间里出来,看着几个人在山路上正朝学校而来,前面一位穿着一身绿军装,中间一位手上捧着一个红红的东西,后面一位穿着中山服。远远地看着父亲,便站着,气喘吁吁地问道,是范老师吗?得到父亲肯定的回答之后,便加快了步伐。最前那位走到父亲面前,双脚并定,抬头挺胸,举起右手行个军礼。老师,这是您培养的学生,他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了,我们不懂藏语,特请您一起前往烈士家中,安抚家属。此刻的父亲,脑子一片空白,这不是那家的独子吗?去时七尺男儿,回来一把尘土。还没有来得及过多思量,父亲的眼泪就滚淌而下。
其实,在老家这片土地上,曾经有过令人骄傲的历史。在中国近代史上,那一场震惊中外的鸦片战争中,这块土地上的青年男子们枕戈待旦,千里驰援,数千男儿星夜兼程,在宁波保卫战上,以骁勇善战,猱身而上,无所畏惧的英雄主义气慨,演绎了一场共赴国难的壮歌。至今,在浙江宁波的大宝山朱贵庙里,附祀着民族英雄阿木穰和哈克里这群英灵。而今天,面对英年早逝的学生,还有行将老去的学生的父母,父亲心潮难平。从此以后的许多年,每至年节之時,父亲总是搭乘客车到学生家去看望学生父母,直到他行动不方便后,还托人帮带东西,以求心中的慰藉。
由于父亲的杰出表现,在藏区成为第一个使用藏语方言教学的老师。是在上个世纪的一九五七年,父亲的事迹被刊载到了《人民教育》上,杂志用了一页版面介绍了父亲的特别教育方式。从此,父亲就成了老家的红人,三街十二沟的人都知道他的名字。也正是这样,这位民族教育的拓荒者,在一次运动中,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遣返回家务农。
父亲回来时,我还没有出生。当我懂事之后,父亲已是一个右腿残疾的人。据说,是在一次修水沟的劳动中从山崖上摔下来致残的。那时的老家,有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猪圈,父亲总是在我熟睡时掌灯进入,然后从圈梁上悬吊的书中取出一两本,在油灯下阅读。开始我并不知道父亲读的什么书。小学时,才似懂非懂的知道他读的是中医书籍。自小,父亲就有一个梦想,要做一名医生。这个梦想,还是他幼小时深埋于灵魂深处的。那年,老家瘟疫盛行,在这一场流行瘟疫中,父亲险些夭折。渐渐长大以后,身边的左邻右舍时不时有人因疾病夺去了生命,看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被病痛折磨,甚至走到人生的尽头,父亲便立志治病救人。可事与愿违,他却当了一名塑造灵魂的教师。遣返回家后,劳动之余,他有充分的时间捡起他曾经的梦想。于是,他成了老家远近闻名、却没有取得许可的医生,有好多人的疑难杂症、头晕目眩、腰肌劳损都被他医治过。也是在这时,我才开始真正地走近父亲。在他的熏染下,我开始喜欢中医,放学玩耍之后,便拿着医药书读一读。不经意间,我能背诵《药性简要》、《医宗经卷》、《金匮要略》。但那时,更多的是看他藏在圈梁上的四大名著和《子夜》、《屈原》。其实,那时的我,阅读这些书籍是很困难的,繁体字只能边猜边读,每每读到好的作品时,总要回味一番。或许,正是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埋下了要当一个作家的梦的种子。想想这一段经历,因为父亲的陪伴,让我愉快地成长。也因为我的陪伴,让父亲熬过了那段悲苦的日子。也是在这段日子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父亲的正直善良与一丝不苟,并影响我至今。
小学快要毕业时,父亲开始焦虑起来,他深知,因为他的原因,可能影响到我升学的问题。在一个深秋的夜晚,当我从熟睡中醒来,看见父亲在灯影中来回地踱步,手中握着那支与之相伴的钢笔,愁容满面。我抬起头说,您还不睡?这时,他才注意到我已醒来。桌上的煤油灯火在微风中轻轻地晃动,黑色的烟雾弥漫了整个房间。他说,有人告诉他,如果写一封状告别人的举报信,就会摘掉他右派的帽子,这样,他的普通人的身份就会恢复,对我们全家、特别是我的升学有很大的好处。但是,被告的那个人就会戴上叛徒的帽子。我说,那人是不是叛徒呢?父亲说,不是。我说,那不是您就别写。父亲说,不写就要影响你。我说,没得事。父亲惊讶地看着我,眼睛里充满了疑惑、欣赏、感动。这时,窗外投进一丝微白的晨光,父亲的脸色转瞬变得红润起来,慢慢地放下握在手中的笔,吹灭了煤油灯,翻身睡在床上,长长的出了一口大气:不写就不写,这种昧着良心的事不做。又过了许久,我在父亲的鼾声中醒来,太阳已照到窗外的半山上。我的躁动,惊醒了父亲,他翻身下床,把昨天的剩菜剩馍放在锅里蒸热,父子俩分而食之。然后,背着他的背篓,杵着他的拐杖劳动去了。临走时,回头一笑。父亲是我们这个山沟里最有文化的农民,能写得一手好的毛笔字。每到临近春节时,远亲近邻都要去买一些红纸来,请父亲给各自的大门写几幅对联,写的人多了,不免出些差错。记得有一年,民兵连长请父亲写了一幅对联,写完之后发现下联少写了一个字。民兵连长并没有发现,便拿着走了。那时的红纸很贵,只有劳动力相对多一点的人家才能分得更多的钱,我们家是很难拿出钱去买红纸写对联的。那一年,父亲破天荒地给我了五角钱,让我去买了一张红纸,然后,先裁了一个单幅,把写错了的下联重新写了一道,让我给送去。当我送到别人家时,刚好是大年三十早上,连长家的对联已经贴上门框。我说明原委后,连长一看,才发觉真的少了一个字,好在字少了,意思还没有变,不然,破坏的罪名安在父亲头上一点也不过分。其实,我小学毕业后,正是因为父亲的原因没能上成初中。那几年,我在父亲的身边如影随形,虽然,物质上显得拮据和贫困,但是,我们的精神却格外的充实和饱满。
父亲从来都显得谦恭。恢复工作时,他感觉到知识的更新替换日新月异,便不再选择回到教室,回到学生当中。在我参加工作后的某一天,我随父亲在老家的马路上散步,迎面驶来一辆货车。车到我们身边时,停了下来。从驾驶室跳下一位中年男子,走到父亲面前,亲切地喊了一声,老师!父亲掷地有声地应答,我却从他的眼神中读到了此刻的迷茫。老师,您不认识我啦?我叫杨根思。喔,是你啊,没有找到老熊脚板的孩子呀,你都当汽车师傅了。父亲笑着说。杨根思红着脸说,老师您还记得呀,我都跑了十几年长途汽车了。杨根思边说边把父亲搀扶着,老师,我送您回家,好多年没见到您了,我送您,我送您。说着,就把父亲往驾驶室牵去。父亲说,不不,我在散步,几步就回去了,你不送。哦,不,老师,我一定要送。父亲回过头看看我,我用眼睛告诉父亲,就让学生送您吧,路虽然短,可情意深长呀。父亲被他的学生送走了,独自留下我一个人在马路上闲走,我忽然羡慕我的父亲,他一次不经意的相遇,却让他享受了一份美好与崇高,一次被顶敬的褒奖。不久,我从县城调到了另一座城市,陪父亲的时间更加的少了,直到他猝然离世。父亲藏在猪圈梁上的那些书,也被虫蛀得破烂不堪,并随着岁月的更替,荡然无存。父亲未能实现的夙愿:做一名医术高超的中医,医治人間疾病,没有在我们这一代人里实现。相反,我也做了一名教师,选调成了一名机关工作人员。回望这风风雨雨的如歌岁月,父亲没留下点点财富,没留下良田庄房,也没留下锦缎绫罗。只为我留下了一种勤勉的生活态度,一种旷达的人生哲学,一种相伴一世的严谨作风和一种宁静悠远的简单命题。这些财富,让我精神强大,内心饱满。
愿父亲灵魂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