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生长
刘鹏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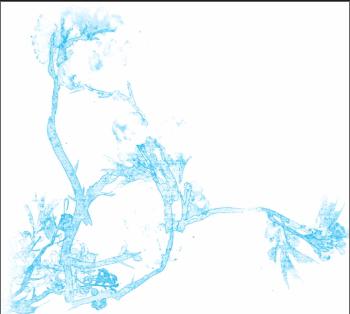
春 省
倏忽一下,春便来了。日子渐渐和暖,河中的水和路边的风都柔软起来,柳条儿拂面,迎春嫩黄,红叶李一树粉白,嘤嘤的有蜂鸣蝶绕。一派大好春光,时尚的姑娘们都拣了窈窕的单衣来穿,只是做母亲的谨慎,生怕乍暖还寒,自己和孩子身上都还裹着厚厚的冬装。然而到底是春天了。一日和儿子漫步在街头,他很惊喜地指着一树绽开的玉兰对我说:“妈妈,看,好漂亮哦。”心中便也欢喜,这小小的男子汉,已对美有了认识,他的世界就要渐渐丰满起来了。我对这个春天充满感激,不仅因为万物生长。
与儿子日日相伴,看到他的乖巧,也看到他的任性;爱他讨喜的聪慧,以及天真的傻白甜;他和每一个健旺的男孩子一样,充满永动机般的活力,也因为这个年纪的精灵跳脱,处处惹人皱眉。我本不是个性子柔顺的人,做母亲有时不免急躁,往往是两个同类项的倔强,必要用一场哭闹来合并。他气恼地叫我“坏妈妈”的时候,我就由着他气恼,并不无逞强地说:“我就是坏妈妈。”到最后,他终于是要回到我怀抱里来的,我端的有恃无恐。
这样的日子一晃就到了六七岁,我有时吼他,有时吻他,有时揍他,有时抱他,拿出做母亲的面孔,恩威并施。小小的他习惯了这样的母亲,并且以为这就是母亲。直到有一日,不经意间被一句话戳中,我忽然对他心生愧疚。
“其实我们一直在欺负孩子。”某亲子教育专家在她的课堂上这样对在座的每一位家长说。“欺负”这个词,带着一语中的的尖锐,我立刻意识到,对一个孩子的照拂,恐怕多半是以欺负为对价的。想来我们在智力和体力上都比孩子强大许多倍,在他们面前,我们充满了对一个弱小个体的优越感。“这孩子真不听话!”“快一点。”“不要哭。”“有什么好怕的?”“这道题都不会,你有没有认真听讲?”诸如此类的责骂一不小心就从嘴里溜出来了,好像不必经过慎重的考量,因为孩子是我们的,我们始终掌控全局。然而这样的相处模式必定是有保质期的,我想,不必等到青春期,我们就会迎来一个叛逆的孩子,随着他渐渐长大,智力上的开发和体力上的增长,日渐衰老的我们将不可避免地陷入无力感。换句话说,局面一旦失控,我们拿什么维护一个长者的尊严?曾听到一个母亲这样描述她七八岁的女儿,“难以管教,无从下手”,因为“你要是敢打我,等我长大了就打你”。亲子关系到了妖魔化的地步,恐怕唯有天怒人怨。
中国的家庭,往往是由一个缺席的父亲、一个焦虑的母亲和一个有问题的孩子组成的。在孩子的问题上,刨根究底是一件高成本而无回报的事。作为母亲,你不可能要求那个“离心离德”的父亲回归,他有一万个理由支持他在家庭以外的轨道上运行,毕竟这样更符合传统的格局和生存的经济。所以孩子有没有问题,父亲是不大负责任的,母亲更自觉地担负起陪伴成长的职能。然而成长势不可挡,陪伴却不一定有效。我们常常看到失望的母亲气急败坏地抱怨丈夫和孩子,好像她的牺牲毫无意义,只换来一对白眼儿狼。天知道她的时间和精力都祭献到哪个空间去了,岁月这个黑洞吸纳了她的青春和美貌,却吝啬地连骨头渣子都不肯吐出來一点儿。
母亲要有足够的智慧。在“欺负”孩子这一点上,她要懂得运用战略战术。毕竟孩子是可塑的,她要把他塑造成哪一种款型,以至于自己落得怎样的下场,全由她说了算。躬身自省,你要吼他的时候,必看到一面镜子,反射出他日后吼你的样子;你打他的时候,也看到他日后怎样打你。又或者我们换一种方法,与他细细地说理,共情,同体验。父亲通常是简单粗暴的,他有限的用来教育的时间,不过是斥骂和拳脚。余下的,都要靠你来完成。要知你的身份是尊贵的,不仅是孩子的母亲,万千个你便成了民族的母亲。所以,时时提醒自己,“母亲”二字何其伟大,她是一个抱持的体式,把婴儿护在臂弯,抱持愤怒,抱持委屈,抱持焦虑,抱持恐惧,抱持那个有缺点的孩子。只有你,才这样温柔而坚定。
其 实
春日的早上,他伏在我的背后,微凉的风从身边掠过,像是一幅幅拂面的丝绸。他的两只小手从我身后穿过来,牢牢地缚住我的腰,使我肌肉紧张的腰背部感受到支持的力量。这么一双小小的手,竟然有这么大的温柔的力量!
每天都是这样,骑着电动车,载着他,穿行在城市的这条路上,看玉兰花开了,谢了;红叶李开了,谢了;樱花开了,谢了……接着是槐花,石榴花,以至于无穷尽的花事。心里满满的,像要溢出来,春风浩荡,十里都是母亲的微笑。
他是可爱的,尽管有时调皮。好像是一夜春风,种桃种李,他一下子长大不少。为了这次成长,他大哭了一场。我不确定植物的生长是否具有某个醒目的节点作为标识,动物呢?小孩子呢?一棵树的年轮代表着它的履历,但在留下这道年轮的那一年里,它生长得可还顺利?是历经坎坷而后一蹴而就吗?还是每天一点向上的力量,心胸渐渐就随着腰围变得宽广了?我们多半还是认同那些看不见的生长。未知未觉间,树就高了,花就开了,叶就落了,人生就圆满了。因为我们不是万物的母亲。
做了母亲之后才发现,这个孩子的生长我是看得见的,呼吸之间,方寸之间,举手投足之间,喜怒哀乐之间……原来一切看不见不过是视而不见,如果你做了母亲,你都看得见。
他用嚎哭来反抗。因为爸爸只看到结果,爸爸对他的指责蛮横无理。
哭倒在我的怀里时,他委屈得上气不接下气,如一头爆发的小兽,一下子瘫软在陷阱里。
“不是爸爸说的那样……是吗?”
他点点头,泪眼模糊,小脸被食物和泪水化了浓妆,沟壑纵横,五色斑斓。
“妈妈知道的……”我安抚着他小小的心灵,那纯洁得容不下一点污垢的美好所在。
妈妈知道的。面对这个孩子,前所未有的温柔,前所未有的体贴,前所未有的宽容之心,一切只是因为,我是这个孩子的母亲。在这个孩子看来,我身材伟岸,胸部伟大,有奶,有温度,有爱,有余地。不管事实如何,他的眼里这就是母亲了,从不和别人的母亲比较,不像成人那样动辄挑剔地来一句:你看看人家。
老师布置语文作业,用课文中学习到的外貌描写来写一个家人。他很雀跃地说,妈妈,我来写你吧。
“我的妈妈黑头发,白皮肤,大眼睛,小嘴巴,她是我心中最美丽的人。”
稚拙的小手描绘出最美丽的图画,尽管那个妈妈的图像一点也不精准,却是每个孩子心中的妈妈。
春天,万物生长。他也在悄悄长大,瞒过所有人的眼睛,却一直在我目光的聚灯下。
今天,他六岁零六个月了。他知道为做错事而感到羞愧,愿意做一个有礼貌的孩子,控制自己的情绪学会冷静,在妈妈生病的时候送上体贴关心的话……春日,花香弥漫,熏风吹动悬铃木树冠漏下的斑驳的光点,在我们的身上跳跃,照耀我的,必也在后一秒钟照耀他。骑行在熟悉的街道上,扑面是熟悉的味道,背后是熟悉的声音,环抱着我的,是熟悉的柔软的力量。
“妈妈,下午我要穿校服,戴红领巾,因为我被老师选上了。”
他很骄傲,脆嫩的语音里透着十分的满足。老师上公开课,恰巧五十个名额,全班有那么几个小朋友被“选掉”了。被“选掉”的孩子不能去多媒体教室上课,只能待在隔壁班级看书、写作业。
“他们都是不听话的小朋友。”他的解释让人觉得好笑,也有些辛酸。在孩子的心中,大人们都喜欢听话的好孩子,所以我也要“听话”,做“好孩子”。这是社会化规训的第一步,也是最基础的一步。有了这样的孩子,大人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有了这样的弱势群体,强权者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我忽然转过身对他说:“其实,在隔壁班写作业也不错。”
故 事
立秋后的一天,我和儿子坐在午后静谧的时光里。暑热渐渐褪了些,我们并肩坐着,安静地做涂色游戏。老外婆在另一间房里发出节奏均匀的鼾声,和着时间滴答的流淌。那套《怪到没朋友》涂色书,成为我和儿子共同致力的目标。往常,这是个精灵跳脱的孩子,如果不是迫他坐下来,他的屁股总不爱和板凳亲嘴儿。现在,他饶有兴趣地坐在桌前,专注地涂抹着时光,倒很让我意外。
“妈妈,我发现这很有意思。可我以前并不喜欢画画呀。”
“当你认真地去做一件事的时候,你就会喜欢上它。”
这是关于色彩的游戏,更多的还是关乎耐心和专注力,我尽量陪伴他,有心保护他的兴趣。在此之前,他从我的爱好里发现了这项略显古怪的趣味,由此打开一扇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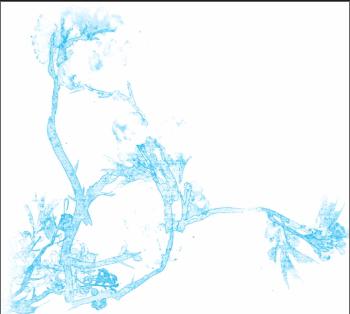
有新鲜的空气进来,完全出乎意料地,我们看到彼此认真的样子。
“有些地方我不想涂上颜色。”他很有自己的主意,把留白叫做“缺陷美”。
“很好。”我颔首。这是另一种想象力。
时间在流淌,有些单调。我想加一点音乐,于是打开手机,音乐汩汩地流出来。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我信口开河。
“怎样的故事呢?”儿子不经意地问一句。但也许他并没有十分往心里去,毕竟这是游戏之外的余兴。
我也就三分玩笑地说:“每个故事都不一样。”
“你和我说说吧。”儿子摆出一副随便聊聊的架势。
手机里正在播放的是港版《天龙八部》的片尾曲《两忘烟水里》。那个年代的粤语歌有种老照片般的怀旧味道,我略整理一下思绪,在脑洞中快速而滑稽地沥了一遍那部宏大的关于轮回的哲学叙事。从哪儿说起呢?无情不孽,有生皆苦。说与一个七岁的孩子,怎样都显得大而无当。但也许从一个母亲的角度,故事可以有另一种讲法。
我撷了一段虚竹的成长经历。这个小和尚的前二十年都是被一笔带过的,但我想这段儿才是人生的重点,尤其是对一个孩子。
“小和尚刚出生就被人抢走了,他的妈妈到处都找不到他。”
“他为什么被人抢走?”
“因为他被认为是个‘杂种。”
我以为儿子会追问什么叫“杂种”,谁知道他“噢”一声,煞有介事地点点头。小孩子的词库真让人惊讶。我继续讲故事,说到叶二娘因为找不到自己的孩子而发了疯,每天要抢一个别人家的孩子,天亮时抢过来玩,玩上一整天,天黑的时候就把孩子杀死。儿子睁大了眼睛。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她的宝宝被人抢走了呀。”
“你是说,有个人的玩具被抢了,他就去抢别人的玩具?”
“她被抢的是宝宝。”我加重了语气,“要是随便抢个什么东西,妈妈可不会发疯。”
儿子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他完全被这个故事吸引了,像是看到一幅从来不曾看到的色彩浓烈的画卷。时间也好像在这里凝固了,琥珀似的,把我和他肩并肩的样子铸在斜斜照进窗子的光线里,晶莹地镀上一层釉彩。
很多年后,也许他还会记起这个周末的下午,一个满嘴跑火车的妈妈和他说了一个形而下下下的哲学故事。苦難的根源在于浓烈的情感,无挂碍故,无有恐怖,但谁能在失去最宝贵的东西时无动于衷呢?
他举起他的“缺陷美”作品让我看。“我画得好不好?”他指着骷髅上的留白。
自然是好的,每个母亲都这样赞美自己的孩子。我只是奇怪,他竟然不惧怕那些具有巨大生命力的东西,譬如死亡。他和我一起画了一下午的骷髅,对于色彩在白骨间的跳跃有异乎寻常的兴趣。他一定不明白涅槃为何意,但他专心地描画着“啊,现在,现在,现在,这唯一的现在,首要的现在,除了你这个现在,没有别的现在,而现在是你的先知”,好像得到了一次天启。
多少年后,当他读到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他还会想到这个周末的下午,母亲坦然地坐在桌前,递给他一张画满骷髅的画稿,一个写满了故事的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