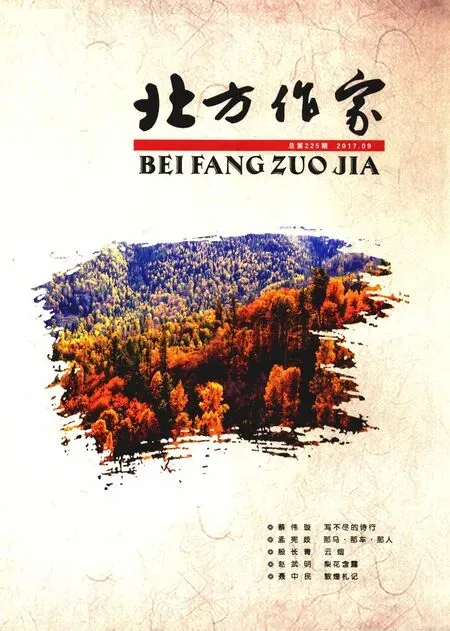梦萦乡愁忆卖花
■王义和
梦萦乡愁忆卖花
■王义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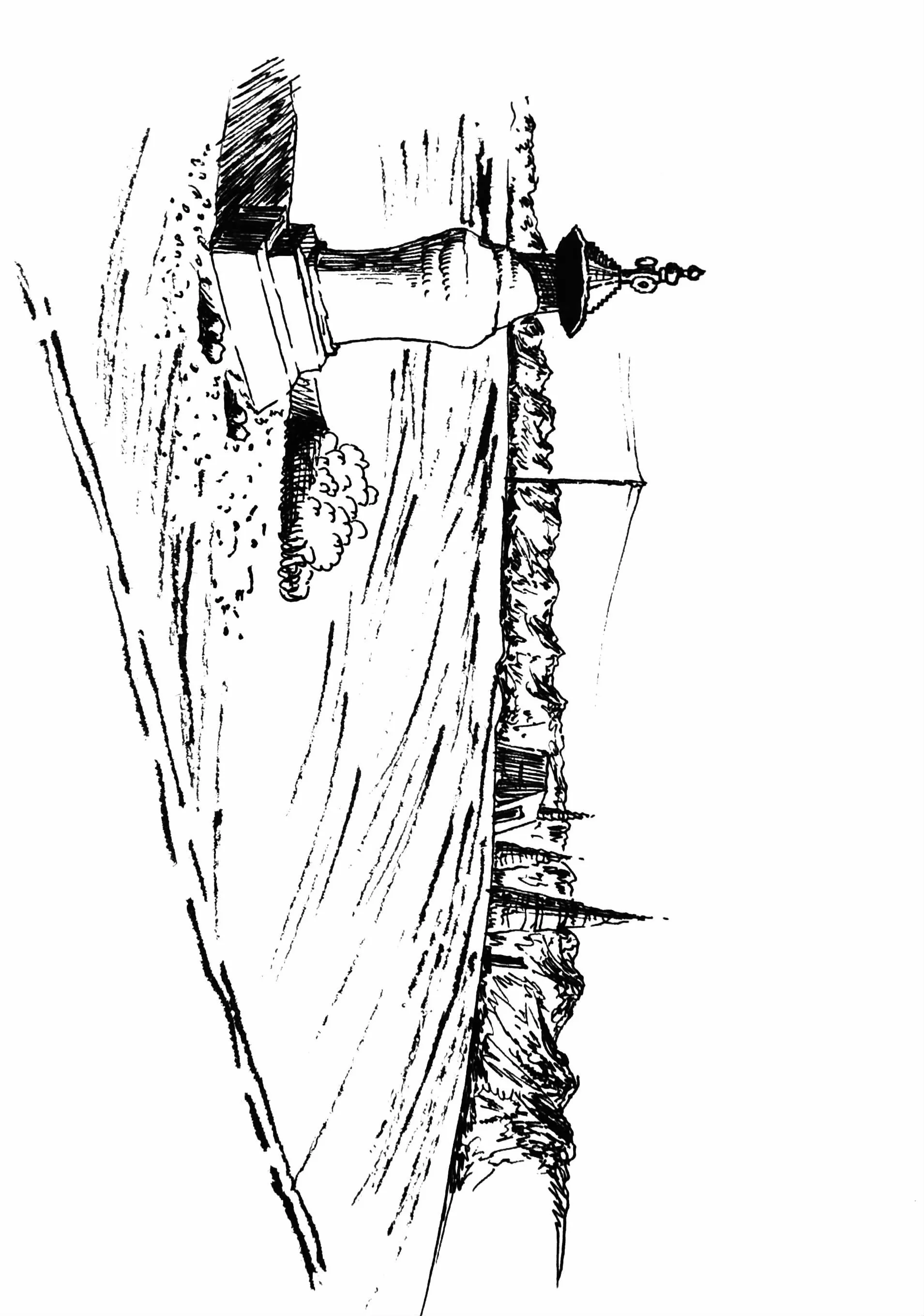
插图/李海霞
故乡的记忆是一缕缕飘逸不断的炊烟,总是在每个寂静的黄昏袅袅升起,像生了根一般,淡淡的,却执拗地牵动我的乡愁,使我不由得回过头去,轻轻翻开那些尘封在岁月深处的破败和苍凉,苦涩而温馨的陈年旧事,进行深情地抚摸,并真诚地歌吟……
三十年前,我师范毕业后,就在家乡附近的一所小学当老师。虽说也吃公家饭,但薪水少的可怜,还时常被拖欠,难以养家,日子过得相当艰辛。迫于生活压力,我不得不利用节假日,为生计奔波忙碌。
那年夏天,正值学校放麦假,我骑车载货独自一人去唐山销售妻子做的纸花。
这是我第一次骑车出远门。出发前,我到书店买了张省交通示意图,把去唐山必经之路上的一些主要村镇熟记在心。为了节省路途花费,我让妻子给我烙了两张面饼,又把一个行军壶灌满白开水,以备路上之需。妻子打开衣柜,拿出一身我只有走亲戚才穿的衣服,说到城里做买卖,穿着不要寒酸,那样会容易被人瞧不起。人家拿你当乡巴佬了,你还怎能做成买卖呢?我默默点点头,似乎突然间明白了许多道理。
望着妻子略显消瘦的面庞,我很感动,也有些酸楚。为了这趟买卖,妻子何曾睡过一个囫囵觉!白天她带女儿下田侍弄庄稼,晚上就坐在灯下用一双巧手娴熟地粘围纸花,几乎连轴转!劳作时,嘴里哼唱着一支无词小曲,哄我们的女儿进入甜蜜的梦乡。她那柔美的歌声飞出老屋,在乡村静谧的夜空里萦绕飘荡。
我两岁的女儿已经很懂事了,在我临行前,把她自己珍藏的两颗糖果硬塞到我手里,说:“爸爸去卖花,爸爸路上吃!”我满眼含泪,不忍让女儿看见,把糖果又偷偷塞进了女儿的衣兜。
皓月悬空,光泻如水,未等鸡鸣我就动身了。我推着沉重的车子,踩着皎洁的月光,悄无声息地上路了。回头望去,妻子站在村口,正默默地目送我远去。我心头一热,满眼盈泪,陡然间生出一种悲壮来,似乎这一去关乎全家人的幸福生活。我暗自发誓,此去即使再难,也要拼一番,做成这笔买卖,盈利而归!我挥挥手,没有说话,我知道妻子深情的目光在注视着我,就像天上的朗月照耀我踽踽独行。
我家到唐山,有两百多公里的路程,我根据图上的比例尺反复计算过。按计划我要先向东走七公里的土路到老堤上柏油路,然后沿柏油路北奔到霸州改走津保国道,再由津保国道往东穿过天津北仓,到达芦台后投宿一宿,估计次日晌午就能赶到唐山了。
附近村子鸡叫头遍的时候,我登上了通往霸州的柏油路。这时夜色渐渐退去,东方露出鱼肚白,继而又变成一抹绯红,路两边的麦田里,涌动着金黄的麦浪,空气中弥漫着麦子的清香。太阳出来了,开始时猴屁股般红,随着太阳越升越高,阳光也渐渐毒了起来。很快,我就冒汗了,汗水浸湿了衣衫。我心里急,只想早一点到达唐山。
来到天津北仓时,天已经后半晌了,我还没有一点食欲,只顾蹬车前行。热辣辣的阳光似乎更毒了,炭火一样炙烤着大地,街面也蔫蔫的没了生气。谁家两只觅食的柴犬吐着粉红的舌头在街头转来转去,不知什么原因,突然在我前面凶猛地相互撕咬起来。我一惊,忙向一旁躲闪,把树荫里一位卖杏老汉的独轮车挂倒了,车上的杏子哗啦啦滚落一地。我吓坏了,慌忙下了车子,连声向老汉道歉。摆摊老人摆摆手,说:“没关系,没关系……”可是我已经在窘迫慌乱中惊出了一身冷汗。往后的日子里,我常常会想起这位仁慈的摆摊老人,从他身上,我学会了隐忍与宽容,即便失意落寞时,也会隐忍做事,宽容待人,恪守善良豁达的胸襟。摆摊老人那个包容的摆手动作,一直清晰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黄昏时分,我到达了芦台。此时,我已经马不停蹄地骑行了两百公里,我艰难地下了车子,双腿像灌了铅似的一样沉重,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我把沉重的自行车靠在路边的一棵杨树上,从后车架拽下遮盖纸箱的帆布雨衣,铺在路边,躺了下来。过了好一会,才感到又饥又渴,我从挎包里拿出妻子烙的半张面饼,就着行军壶里的白开水,香甜地吃了起来。等体力恢复后,便投宿在一家廉价的浴池旅馆,次日晌午准时到达了唐山。
我推着沉重的车子,穿行在唐山的闹市区中,望着来来去去穿着时髦的红男绿女,不知是羡慕还是自卑,心里酸涩而茫然。我无暇顾及这些,眼睛在林立的商铺中间,忙着搜寻那些挂着幌子的花圈铺,我带来的纸花要推销给他们。终于,在一个繁华路段,我见到了一个花圈铺,就像被打了鸡血一样,兴奋得一颗心砰砰直跳。我把车子靠在店铺外,忐忑不安地走了进去,向店主推销我的纸花。店主正忙着整理待售的花圈,我即刻上前打招呼:“师傅,买纸花吗?”那人连头也没抬,只用眼角的余光斜了我一下:“不买!”硬邦邦的回答差点呛我一个跟头。我有些沮丧,只得退出店铺,把希望寄予下一个目标。
我一口气走访了三家花圈铺,却没有卖掉一朵纸花。我的心凉了半截,初始的那股兴奋劲荡然无存。我思忖再三,决定改变一下推销方式。我花五角钱买了一盒“大前门”牌香烟,又来到下一家花圈铺。这回我没有急于求成,而是毕恭毕敬地递给对方一根香烟,并为他点燃,凭借妻子传授的纸花知识,和店主攀谈起来。我对他店内的花圈成品先品头论足一番,接着指出他那些纸花存在的瑕疵,最后把我带来的纸花样品拿给他看,一下子就把他吸引住了。他没有犹豫,也没有讨价还价,把我带来的三大箱纸花全部收购了。呵,我成功了!好家伙,我一共卖了三百元钱,除去纸花成本,净赚二百元,能抵得上我五个月的工资呢!
从花圈铺出来,估摸已是下午六点钟的光景了。我找了个僻静之处,从挎包内掏出半张已经略带馊味的面饼,蹲在地上,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吃得津津有味。我拿出水壶咕嘟咕嘟灌了几口凉开水,马上爽透骨髓。片刻休息后,刚想骑车朝归途进发,忽然,身后响起几位女子怪异的笑声。我不经意地回头一瞥,原来她们是在笑我!我下意识的摸摸后背,并没发现什么,可那几位着装时髦的姑娘笑得更欢了,笑得我心里直发毛,真是莫名其妙!我没再理睬她们,飞身跨上自行车,朝归途猛蹬。轻车熟路,很快便驶离了唐山这座繁华城市。
夏天的天气就像小孩脸,说变就变,刚出唐山市区那会,天空还是晴朗的,此刻猛一抬头,只见从西边天空飘来一片浓重的阴云,在我头顶上空吹气似的膨胀开来,眨眼之间便罩满了苍穹。云层越来越厚,随着一阵带有土腥味的风吹过,雨水就劈头盖脸地浇了下来,尽管我穿着雨衣,但身上还是被肆虐的雨水浸湿。我摸摸内衣兜,还好,花款被塑料袋包裹着,是不会被雨水浸湿的,我冒雨继续骑行,可要命的是雨水还夹裹着雷电,乌天黑地里忽然一条火蛇蹿过,紧接着,轰隆隆的雷声就把整个大地震得地动山摇。我只好推着车子,战战兢兢地前行。不一会雨过天晴,太阳一下子又毒了起来,金子一样的光亮直晃人的眼睛,很快,我湿透的衣衫又被阳光蒸晒干了。归心似箭呵,我恨不得肋生双翅,一下子飞回故乡,和我的妻子一起挥舞银镰收割我家那五亩小麦呢!
暮色上来了,我还没有赶到芦台那个投宿的地方。暮色渐浓,天空仿佛是不断加入墨汁的水,渐渐浓稠成夜色,而我的归途,还在夜的墨黑里无限地延伸着。我实在是累极了,就下了车子,瘫坐在路边休息,这才看清挨着路边有个微微隆起的土丘。我忽然冒出一个念头,想在土丘上过夜,还能省下住店钱,何乐而不为呢?我走上土丘,只见周围长满了苦蓬和杂草,流萤在草丛中划着发亮的弧光,闪来闪去。土丘中央有棵大柳树,茂密的树荫笼罩着一座汉白玉石碑,我这才知道原来这是一座坟茔。我有些犹豫,管他呢,先躺一会儿再说。我把自行车靠在石碑上,铺开雨衣,躺了下来。月亮还没有升上来,闷热的空气里,没有一丝风。就在我昏昏欲睡之际,藏匿在柳树上的一只猫头鹰冷不丁地啼叫了起来,像婴儿的啼哭声,那声音令人不寒而栗,我潜意识中与生俱来的恐惧因此一下子被激活了,仿佛坟茔里潜伏着面目狰狞的鬼魅,绿莹莹的眼睛正不怀好意地窥视着自己。我一骨碌爬了起来,睡意顷刻间全消。就在我一愣神的时候,突然感觉有个什么东西缠绕在我的左脚脖子上,冰凉冰凉的,似乎还在东扭西歪地蠕动。我本能地弯下腰一拽,妈呀,是条蛇!我的魂都要被吓飞了,顺手把它一丢,扯起雨衣,跨上自行车,跌跌撞撞地向前一路狂奔。也不知骑行了多久,当我骑上一个高坡时,眼前出现了一片灯光,像漂浮在浩瀚无际的海洋上。呵,是芦台!我到芦台啦!我的心里倏然敞亮起来,不再惊恐,但留给我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直到今天,回忆起在那座孤坟与野蛇邂逅的恐怖场景时,还令我心有余悸呢!
天又蒙蒙地亮了,我离开了芦台,继续我的行程,直到暮色再一次降临,村舍升起晚炊的缕缕烟柱时,我终于回到了家的温馨的港湾。
见我平安归来,妻子笑了,是焦急后的笑,是等待后的笑,是担心后的笑,笑得有些苦涩,笑得有些酸楚,泪眼对我望着,竟闪出感激的光。我亲了亲女儿,从挎包内掏出一包糖果给她,女儿开心极了,快乐得在屋里蹦来跳去。忽然,女儿指着我的屁股咯咯咯地笑了起来,这时我才发现,我的裤子挨近屁股的地方,竟然被车座磨破了两个大洞。猛然间想起唐山那几位女子对我的嘲笑,我恍然大悟,旋即释然地笑了。
为了这条磨损的裤子,我一连心疼了好几天。
三十年的光阴流水一样的过去了,记忆中的乡村已尘埋在岁月深处,而我所经历的那些陈年旧事,却始终叠印在我的记忆中,魂牵梦萦着我的乡愁。那个骑车去唐山卖花的苦涩日子,如一卷储满欢乐与悲伤的胶片,穿透岁月的苦雨凄风,随着年轮的转动,清晰地映现着那段无法忘怀的时光……
王义合,笔名王义和,男,河北省保定市雄县人,教师,保定市作家协会会员,燕赵文学签约作家,雄县文协副主席。作品散见于《河北日报》《荷花淀》《华夏散文》《现代作家文学》《鸭绿江》《燕赵文学》《福建文学》《长城文艺》《南开文艺》等几十家杂志及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