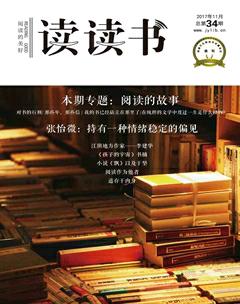读物(三)
经典的意义就在于它们能够给予我们一个海量的经验世界,我们可以不用亲历就得到体验,我们可以面对人类对世界方方面面的感受,超越了我们被局限和被设计的当下生活;通过经典的学习,我们可以逃脱囚笼,仿佛获得第二次生命。
——雅克·巴赞
我说过,在下决心读书之前,我们总是试着继续聊天、打电话,一个又一个地询问电话号码。而一旦听任自已去阅读,我们更愿意选择像布瓦涅夫人的《回忆录》这样的书,它们让我们产生继续访客的幻觉,好像在拜访我们从前无缘得见的客人。
——普鲁斯特
一本书是另一个自我的产物,无关我们在习惯、交往、缺陷中所展示的自我。如果我们试着在内心重新创造,我们就可能成功地尝试并理解这自我,这深藏内心的自我。这是心灵的努力,别无他途。
——普鲁斯特
人文教育之所以与经典作品的学习密不可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个人的成长,本来就意味着个体原有的经验和观念得到不断的修正、扩展和改变。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未来的世界尚未可知可论,而当下的经验又往往显得狭隘和短视,所以那些凝聚了人类已有的经验,又经过历史与文化积淀的经典作品,才会成为人文主义教育最为适宜的资源。
——毛亮
他没有宗教信仰。一个人读书太多且读得太通的时候,已经不需要宗教的慰藉了。这使他不受任何禁忌和清规的羁绊,也使他只能选择与语言表达终生为伴。因为只有语言与思想最接近,只有语言最适合表达思想。
——乔良论博尔赫斯
第一天我问学生:小说应达成什么目的?我们何必花费大把的时间读小说?我向他们说明最伟大的想象之作,目的在于使读者觉得在自己家中却仿佛陌生人。最优秀的小说总是逼我们质疑平常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之事,质疑看似不可改变的传统与期待。
——阿扎尔·纳菲西《在德黑兰读<洛丽塔>》
厄多斯不太相信上帝,但他愿意相信世界上有一本超级的“天书”,那里面包含了所有数学定理的最简洁、最漂亮、最优雅的证明。他对一个证明的最高赞誉就是:“这正是书上证明的。”
艾略特说:“凡是诚实的诗人,对于自己作品的永恒价值都不太有把握。他可能耗尽一生而毫无所得。”
1935年5月10日的夜晚,拥有博士学位的戈培尔在柏林发起随后遍及全国的焚书运动,那些被视为“对我们的前途起着破坏作用”的书籍,如马克思、恩格斯、卢森堡、海涅和爱因斯坦等名人的著作,都被付之一炬。戈培尔向参加焚书的学生们说:“德国人民的灵魂可以再度表现出来。这火光不仅结束了旧时代,而且照亮了新时代。”因此,戈培尔获得“焚书者”的万恶之名。
1938年2月21日,托马斯·曼到达纽约。有人问他流亡生活是否是一种沉重的负担,托马斯·曼回答说:“这令人难以忍受。不过这更容易使我认识到德国弥漫着荼毒。之所以容易,是因为我其实什么都没有损失。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我带着德意志文化。我与世界保持联系,我并没有把自己当做失败者。”
关于世界的两大问题“柏拉图之谜”与“奥威尔之惑”,乔姆斯基如此描述它们:柏拉图的问题是,在可以借鉴的事物极端贫乏的前提下,解释人类如何能够获取如此丰富的知识;奥威尔之惑恰恰相反,他欲了解的是在能够借鉴的事物极端丰富的情况下,人类为何所知甚少。
贝隆执政半年后,博尔赫斯被“升任”为国营市场的家禽和家兔稽查员。虽然是“升任”,但將一位重要作家升为鸡兔稽查员仍然是毫无疑问意味着侮辱。受此羞辱的博尔赫斯决意辞职,他还公开发表了辞职声明,声明中说:独裁导致残酷;最可恶的是独裁导致愚蠢。刻着标语的徽章、领袖的头像、指定呼喊的“万岁”与“打倒”声、用人名装饰的墙壁、统一的仪式,只不过是纪律代替了清醒……同这种可悲的千篇一律做斗争是作家的诸多职责之一。
福克纳曾一直有一种恐惧,恐惧有一天不仅创作的狂喜会消失,连创作的欲望以及值得一写的内容都会消失。这种恐惧只有当他的目光被老作家舍伍德·安德森引导到自己的故乡上才戛然而止。他说:“我发现这块邮票大的故土值得一写,一辈子活得多长也写不完。”
保罗·策兰每天从事翻译,但一直坚持用德文写作。有人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只有用母语,一个人才能说出自己的真理。用外语写作的诗人在撒谎。”
井上靖是一位大量取材中国历史文化的作家,当他如愿以偿,来到憧憬已久的古丝绸之路和重镇敦煌,他感叹:“真没想到敦煌竟与我想象中的这样相像。”“23年前我就写成了《敦煌》,可直到今天才头一次见到它,却一点儿也不觉得陌生。我与中国太相通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