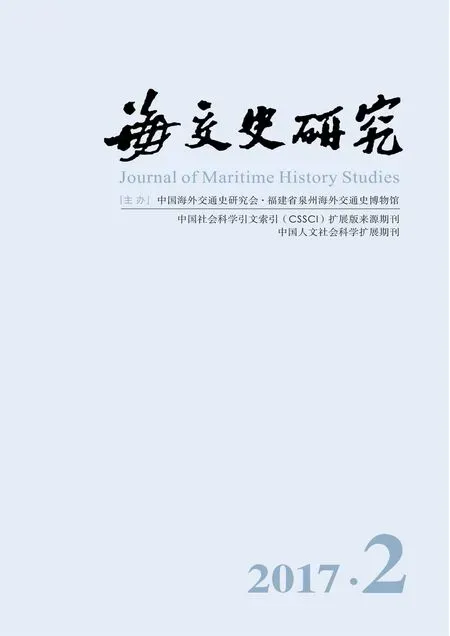澳门开埠之初(1564-1580)葡萄牙人对三次中国海盗活动的应对与处理
汤开建 周孝雷
澳门开埠之初(1564-1580)葡萄牙人对三次中国海盗活动的应对与处理
汤开建 周孝雷
葡萄牙人居留澳门伊始,正值广东地区海盗匪情风起云涌之时。葡萄牙人出于诸多因素的考虑,往往主动协助明廷剿灭沿海剧盗。本文就澳门开埠以来葡萄牙人分别在嘉、隆、万三朝剿灭三股海盗势力(1564年柘林叛兵、1568-1569年曾一本、1580年林道乾)的几次事件开展研究,通过论述葡萄牙人对以上三次中国海盗活动的应对与处理,可以看出葡萄牙人的剿匪行动除了保障自身安全之外,还应当遵循了葡人一以贯之的通过讨好明廷以获得长期居留权的政策导向。
澳门 葡萄牙 柘林叛兵 曾一本 林道乾
葡萄牙人进入南中国海后,即展开了对中国东南沿海各地的海上贸易,为了更便捷顺利的获取海上贸易的利益,葡萄牙人曾多次与中国东南沿海的海商集团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以便达到走私货品的目的。与此同时,葡萄牙人因此也获得了与“海盗”同样的坏名声。*参见汤开建:《明代澳门史论稿(上卷)》,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232页。为了改变这一形象,也为了争取中国政府对葡萄牙人进入中国展开贸易活动的谅解和支持,于是葡萄牙人开始与海盗集团决裂,并以剿灭东南沿海地区的海盗为其主要政策。在澳门开埠前,被葡萄牙人剿灭或葡人参与剿灭的海盗较著名的有Coje Hazem、林剪、何亚八*参见汤开建:《明代澳门史论稿(上卷)》,第111-162页。等,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萄牙人更以“驱盗”之功得以入居澳门。自澳门开埠之后的二十余年间,广东海防压力日益吃紧,而葡萄牙人正利用这一机会,陆续三次出兵帮助明朝剿灭名噪一时的三支海盗集团。明政府则以澳门葡人为“香山海洋”的“屏卫”*(明)霍与暇:《霍勉斋集》卷19,《呈揭·处濠镜澳议》,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清光绪丙戌重刊本,第84页。,“为天朝守海门而固外圉”*(清)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卷下,《澳蕃篇》,澳门:澳门文化司署点校本,1992年,第148页。。虽然中西文献均不乏对早期葡人协助明朝驱盗的记载,但是随着嘉隆时期广东地区海防危机的加剧,广东政府与澳门葡人之间的军事合作也日益频繁、深入,澳门葡人也开始作为一支特殊的武装力量参与到受明朝政府领导的海防行动之中。
中国学者在对早期中葡关系的考虑中,立足中文材料及部分翻译材料,以明朝政府对澳门葡人的防范、管制或利用着手,深入挖掘明朝政府的对澳态度及治澳措施的流变。国外学者虽对这一领域关注较少,但其视角却恰恰相反,往往着眼于葡萄牙的殖民策略、葡商对华政策的调适与应对等方面进行研究,但是对中文材料的使用不足。*关于葡人学者的研究,参见J. M. Braga,The Western Pioneers and Their Discovery of Macau,Macao, 1949 年;[葡]徐萨斯著,黄鸿钊、李保平译:《历史上的澳门》,澳门基金会,2000年;[葡]阿尔维斯著,祁滢译:《澳门开埠后葡中外交关系的最初十年》,载《文化杂志》中文版,第19期,1994年,第70-79页。本文一反以往华人学者偏重中国政府的应对与防范这一传统话题,同时立足本位,充分利用西方学者所短缺的中文资料,结合葡文数据,以葡萄牙人面对澳门开埠初期的三股海盗集团(柘林叛兵、曾一本、林道乾)的应对与处理展开讨论,通过研究,我们不仅可以看出葡萄牙人对广东海警的应对与行动,还可以厘清葡萄牙在澳门开埠初期对华政策的一贯态度。
一、嘉靖四十三年澳门葡人助剿进犯广州的柘林叛兵
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驻守柘林的东莞水兵因不满朝廷一再拖欠粮饷,进而暴动作乱,此即著名的“柘林兵变”。《明实录》对此事起因有较为明确的记载:
广东东莞水兵徐永泰四百人守柘林澳。五月无粮,皆怨望思乱。会领军指挥韩朝阳传总兵俞大猷檄,调戍潮阳海港。诸军益怒,遂鼓噪执朝阳,数入外洋,与东莞盐徒及海南栅诸寇合,进逼省城。抚按官遣人责问乱故,以潮州知府何宠不发军粮对。朝阳亦归罪千户于英。事闻,诏下朝阳、宠、英御史问。夺海道副使方逢时、佥事徐甫宰,戴罪杀贼。*(明)徐阶等:《明世宗实录》卷532,“嘉靖四十三年三月甲寅”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8661-8662页。
关于此事件之始末,郭子章《潮中杂记》则记载更详:
是岁潮州柘林海兵叛,提督侍郎吴桂芳再讨平之。时倭寇久驻潮阳,府藏不继,柘林防守海兵谭允传等以缺饷称乱,扬帆直抵广城。初尤以告粮为名,省中以军门方有事,倭寇在远,径议发兵剿之,大为所败。于是各叛兵横肆钞掠,省会戒严。桂芳闻变,阳布令招之,随调东莞南头九铺水兵,自外洋出,因躬督副总兵汤克宽、参将门崇文水兵自惠阳趣东洲里海而入,合击之,贼腹背受兵,骇奔无措,生擒六百一十二人,斩首不计。已而余党复据大舰不解,桂芳与总兵俞大猷用计破之,复生擒三百九十三人,斩级四十一颗。首贼谭允传、卢君兆等先后磔于市,其船入官,遗孽无存,远近称快。*(明)郭子章:《潮中杂记》卷11,《国朝平寇考》下,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影印本,2003年,第80页。
根据以上郭子章的记载,可以看出柘林兵变过程可分为两段:第一个阶段是两广总督吴桂芳调动东莞南头九铺水兵与副总兵汤克宽、参将门崇文麾下水兵,采用内外合击之战术,重创敌军。第二个阶段,叛军之残存势力固守兵船之中,实力不容小觑,吴桂芳与俞大猷“用计破之”。此处之“用计”,当指时任福建总兵的俞大猷所设诱降之计。根据俞大猷日后的记载,可知当时叛兵余党的规模仍相当可观,共有大乌船30只、白艚船40只,俞大猷先后“差人往抚”,诱使叛兵将21只大乌船“送还官府”,并答应其提出的给与赴潮州贩盐牌照的要求,继而俞大猷趁叛兵剩余船只在岸停泊之机,出其不意,“乃以其送回二十一只船载兵往击”*(明)俞大猷,廖渊泉、张吉昌校:《正气堂全集》,《洗海近事》卷下,《书与巡抚熊及二道》,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97页。,一举将叛军歼灭于东莞三门,此即诸方家所称之“三门之役”。而澳门葡人帮助广东政府剿灭叛军,正是在战役的第二个阶段“三门之役”中进行的。
在论及澳门葡人出兵始末之前,有必要对此时澳门的政治形势和中葡关系作一回顾。柘林兵变爆发时,澳门正式开埠仅七个年头。此时的葡萄牙人正值在澳经营的关键时期,澳门内部的权力结构却暗流涌动。澳门开埠初期的政治权力主要由驻地首领委员会(澳门议事会的前身)行使。此制度发轫于1560年,是年,居澳葡人选出一委员会,由驻地首领(Capitão de Terra)、法官和4位较具威望的商人组成,对澳门进行管理,处理区域内部事务。*Austin Coates, A Macau Narrative, p.25; 吴志良:《生存之道: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澳门:澳门成人教育学会,1998年,第49页。葡萄牙富商迪奥戈·佩雷拉(Diogo Pereira)担任首位驻地首领。佩雷拉及其家族经过在澳门的长期发展,已经基本掌握了澳门的经济、社会与政治领导权,佩雷拉也担任澳门兵头数年之久。
1563年,葡印总督若奥·门多萨(João de Mendoca)认为由于澳门驻地首领的选举并未获得葡王的认同,且过于依赖听命于香山县政府,故于本年下令撤销驻地首领一职。但澳门驻地首领迪奥戈·佩雷拉深得澳门居民的拥护,故这一职位并未被撤销。*Montalto de Jesus, Macau Histórico, Macau: Livros do Oriente, 1990,pp.51—52.同年,刘易斯·梅洛(Luís de Melo)船长带着赴日航行特许状从印度来到澳门港。他到达后十多天内,唐·若奥·佩雷拉(D.João Pereira)也从马六甲到达,并持有葡萄牙摄政王太后御赐的航行特许状。于是,二人就由谁来掌管澳门地方兵头权力发生了争执*[葡]阿尔维斯著,祁滢译:《澳门开埠后葡中外交关系的最初十年》,载《文化杂志》中文版,第19期,1994年,第70-79页。。郑舜功称:“今年,佛郎机夷号称海王者,官市广东龙厓门……复有佛郎机夷号称财主王者,横过海王,俱处其间。”*(明)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下册)》卷6,《海市》,民国二十八年据旧钞本影印本,第6页。此处的海王与财主王当即指梅洛与若奥·佩雷拉。最后,迪奥戈·佩雷拉做出让步,放弃了澳门兵头一职,由唐·若奥·佩雷拉出任兵头。*[葡]若昂·埃斯科巴尔:《关于至高至强之塞巴斯蒂昂国王派往中国的使节团的评述》“澳门,1565年”,载[葡]罗理路著,陈用仪译:《澳门寻根》,澳门海事博物馆,1997年,第108-109页。
除了政治权力和商业利益之争外,此时的葡萄牙为了建立正式的对华外交关系,1563年由葡印总督派遣热尔·戈伊斯(Gil de Góis)以国王特使的身份使华。该使团到澳门后不久即与广东政府联络特使进广州及进京之事,广东巡抚就此事差官下澳调查核实,还检查了进贡的各种礼品,并对贡品表示满意*同上,第106页。。就在戈伊斯信心满满地准备进一步出使广州觐见总督时,却爆发了柘林兵变。这导致使团出使计划暂时搁浅,同时还促使澳门的各股政治势力不得不暂时停止权力争斗,共同解决澳门即将面对的军事威胁。
叛军起事后,从柘林出发,直抵广州城下,但广州城墙高大坚固,叛军未能攻入,他们袭击了广州郊区*(明)叶权等撰,凌毅点校:《贤博编》附《游岭南记》,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4页。。并于6月中旬来到澳门,准备洗劫澳门。据戈伊斯使团成员埃斯科巴尔(João de Escobar)记载,当时澳门只有不到300名葡人,加上奴仆和当地基督徒,约1 500人。当盗匪来到澳门港口时,兵头迪奥戈·佩雷拉指挥山上的石弹炮向盗船发射。停泊在港外的两艘葡舰也向盗船开炮射击。后来又有从帝汶返回的葡船支援,在葡萄牙人猛烈炮火的反击下,盗匪撤退。*[葡]若昂·埃斯科巴尔:《关于至高至强之塞巴斯蒂昂国王派往中国的使节团的评述》,载《澳门寻根》,第110-111页。
此次柘林叛兵给澳门带来的兵燹之害,使得葡萄牙人不得不为澳门港及葡国商船的安全做出相应的防范,但同时也使澳门葡人看到了向中国政府谋求政治外交利益的良机*葡国学者阿尔维斯(Jorge Manuel dos Santos Alves)称澳门向广东政府提供军事援助包括三个目的:1、对叛兵可能做出的封锁粤澳贸易的行动做出预防;2、对叛兵袭击澳门港及葡国商船的行动予以还击;3、对在澳门军队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向中国政府索取政治红利,促使戈伊斯使团成功访华。详见[葡]阿尔维斯著,祁滢译:《澳门开埠后葡中外交关系的最初十年》,载《文化杂志》中文版,第19期,1994年,第70-79页。对于此结论,我们亦表示认同。。叛军撤退后,葡人当即向广州方面表示愿意提供军事援助,当时的葡萄牙人也坦陈,其出兵动机主要是为了获得中央政府的信任,推动戈伊斯使团遣华,进而获准入华传教:“全体都一致认为提供援助是对的,理由有很多:第一,因为我们是在他们的土地上;第二,因为这些强盗也给我们造成损害;第三,因为这样可以加强同他们的友谊;第四,这个理由是最能打动我们及其他处于类似地位的人们的,就是认为这一来,基督教徒就可在他们当中树立声誉和威信,他们就会接受我们的使节团,我们就能如愿进入这片国土去宣扬我主的福音”*[葡]弗朗西斯科·佩雷斯:《弗朗西斯科神父写给龚萨尔维斯神父的信》“澳门,1564年12月3日”,载《澳门寻根》,澳门海事博物馆,1997年,第102页。。本来葡人对此并不抱太大的希望,然而中国政府最终还是答应了葡人的请求:
中国人竟认为还是以接受援助为好,作出这一接受决定的是总兵……他还转告特使,他愿意担负起处理使节团一事之责,并启奏皇上知闻,他愿意担负起处理使节团一事之责,并启奏皇上知闻,目前则暂时可在澳门休息……*[葡]若昂·埃斯科巴尔:《关于至高至强之塞巴斯蒂昂国王派往中国的使节团的评述》,载《澳门寻根》,第111页。
另一位目睹此事的葡萄牙耶稣会士安德烈·平托(André Pinto)亦对中国此番出人意料的决定有所记载:
神父们看到这次出兵增援,对于企图在这片国土上进行的为天主效劳的事业是很重要的,而且他们看到这次中国人对我们抱了信任的态度,而过去是很不信任的,这一来,就可以打开一道门,彼此进行更多的沟通与联系,于是他们就向总指挥陈词,说明同意提供他们所要求的援助,也是我们的人所盼望给予的援助,是多么的必要。*[葡]安德烈·平托:《安德烈·平托修士给印度耶稣会士们的信》“澳门,1564年11月30日”,载《澳门寻根》,第93页。
可以肯定的是,广东当局得以如此顺利地答应葡人军事援助的请求,此事应当与当时的总兵官俞大猷有着密切关系。在俞大猷对葡人的早期的了解中,葡人先进的武器装备给俞大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俞大猷曾多次提及葡人的武器装备,如嘉靖三十一年(1552)俞氏向浙江巡抚王忬呈递的揭帖中称:
二凶(指海寇王直、毛烈)虽猛,孰与佛朗机?曩时佛朗机船数只,久泊玄钟、走马溪。副使何乔等督兵驱之,日久不去,轻视官兵何如耶?*(明)俞大猷:《正气堂全集》,《正气堂集》卷5,《呈浙福军门思质王公揭十二首·议王直不可招》,第164-165页。
嘉靖二十八年(1549)中葡在福建沿海爆发了走马溪之战,尽管明朝海防部队最终打败了盘踞在福建的葡人,但葡萄牙人优良的武器装备也使明军吃尽了苦头。 据俞大猷后来的记载来看,他也亲历了此次战斗。*(明)俞大猷:《正气堂全集》,《正气堂集》卷15,《与两广军门自湖吴公书十六首·论商夷不得恃功恣横》,第383页。在俞大猷的眼中,葡萄牙人是比倭寇还要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但在当时朝野中充斥着“驱澳”呼声的大背景下,俞大猷为何还敢于利用葡人力量打击海寇呢?这应当与俞大猷的政治主张有着密切关系。俞大猷称:
市舶之开,惟可行于广东。盖广东去西南之安南、占城、暹罗、佛郞机诸番不远。诸番载来乃楜椒、象牙、苏木、香料等货。船至报水,计货抽分,故市舶之利甚广。数年之前,有徽州、浙江等处番徒,勾引西南诸番,前至浙江之双屿港等处买卖,逃免广东市舶之税。及货尽将去之时,每每肆行劫掠。故军门朱(纨)虑其日久患深,禁而捕之。自是西南诸番船只,复归广东市舶,不为浙患。……
盖倭人之桀骜剽悍,嗜货轻生,非西南诸番之比。在隋、元之世,为患中国最甚。其地又无他产,仅一刀一扇,非若西南诸番犹有椒木、香料诸货,可资中国之用者也。故祖宗绝之,视诸番特严,而为人臣子者,可不遵守耶?*(明)俞大猷:《正气堂全集》,《正气堂集》卷7,《呈总督军门在庵杨公揭帖二首·论海势宜知海防宜密》,第196-197页。
以上材料可以反映,俞大猷主张有条件地开启市舶贸易,而在他所列举来华贸易“西南诸番”中,佛朗机即是其一。俞氏认为,佛朗机来华不但可以互通有无,更重要的是广东政府得以享受抽分的“市舶之利”,这与同时代的林希元、霍与暇等人的主张相仿。除此之外,俞大猷还将“西南诸番”与日本倭寇进行比对,说明与前者贸易利少弊多,这又在另一个层面上表明,在俞大猷的心目中,葡萄牙人与“桀骜剽悍,嗜货轻生”的倭寇有很大的区别,其与倭寇是属于不同性质的两种海上势力,因此与葡人的合作也非逾矩之事。
据葡人记载,俞大猷在广州会见澳门使者之后,旋即派遣副总兵汤克宽赴澳门商议军事合作事宜,并于1564科斯莫节(9月27日)这一天召开会议*[葡]若昂·埃斯科巴尔:《关于至高至强之塞巴斯蒂昂国王派往中国的使节团的评述》,载《澳门寻根》,第111页。。中文文献对汤克宽下澳谈判之事亦有相应记载:
是年春,东莞兵变,楼船鼓行,直抵省城下。城门昼闭,贼作乐饮酒天妃宫中。汤总兵克宽与战,连败衂,乃使诱濠镜澳夷人,约以免其抽分,令助攻之……*(明)叶权等撰,凌毅点校:《贤博编》附《游岭南记》,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4页。
葡文文献记载更详,还特别提到了谈判地点及仪仗:
那位中国官员就派人告诉若昂说,他将登岸到庙里同若昂会面,把事情办妥,为了不耽误时间,请您也这样做。若昂同意了,就到该地去,那是在居民点的尖端,就对着大海……那位中国官员一看见总指挥到了庙里,就不再耽搁,立即从他所在的帆船登陆。他一动身,许多talicos,有点像我们的定音鼓,就一齐敲响了,像一些古怪的大锅,把整个狂欢节都煮得沸腾翻滚溢出,还响起了莫名其妙的音乐,声音像风笛和歪七歪八的喇叭。*[葡]若昂·埃斯科巴尔:《关于至高至强之塞巴斯蒂昂国王派往中国的使节团的评述》,载《澳门寻根》,第112-113页。
葡方将谈判的地点选择“居民点的尖端”的一座庙里,很显然即是指澳门岛南部的妈阁庙。这里的“若昂”当即指澳门兵头唐·若奥·佩雷拉(D.João Pereira)。经过前一个阶段的战役,余下的叛军就停泊在东莞地区的海湾中,中国政府希望通过趁敌不备,中葡合力偷袭敌军,从而一举歼灭叛军。根据葡萄牙人的记载,此次谈判计划葡人分兵两路进击叛军,汤克宽还为葡人带来了所需船只:
为了使匪贼蒙在鼓里,将他们一网打尽,让他们就停泊在东莞的海湾,满以为总兵会一由他们逍遥法外。我们不使他们对这一用兵之计得知风声,所以我干脆将必要的船只一并带来,以便你们兵分两路,从内从外前往,很快就可以上船。*同上,第113页。
广东方面也为此次会剿行动进行了悉心的筹备,特别是制定了分路出兵的进军计划:
葡萄牙人应分两路进击贼兵,一路应从当中走,取道广州,另一路应从外面包抄,为此,他给从外面包抄的带来了船只,至于取道广州的,可以在广州随意选用船只,但现在去广州也是先乘坐lanteias,这样船他也带来了。路易斯·德·梅洛问他为什么要援兵分成两路,本来大家合在一块儿去会好得多。那位中国官员就回答说,这样做有其必要,因为贼兵们碇泊的地点,只有一个出口可以逃跑,应有从外面包抄的那支船队开到这个出口,这一来,他们遇到从当中走的那支船队的进击要逃走时,就会发现退路口已被切断,这就会使他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为了他们看得清楚些,他叫人送上一张示意图,上面标上了所有各岛屿和海口,并且在示意图上指出了贼兵所在的那个港湾能外逃的航道。*同上,第115页。
此处“外面包抄”的进军路线应指虎门一线入海口的水道,而“当中”一路则为粤澳之间的内河水道。此计划看似是寻常不过的出兵计划,其实内中还蕴含着复杂的中国政府、特别是支持军事合作俞大猷的考虑与试探:
总兵派人来求援时,他对派来的人叮嘱的主要一点就是:要指出葡萄牙人应兵分两路,一路从里面走,一路从外面走,就要注意看他们对此采什么态度,如何回答,如何决定。因为他们如果分兵,就是可靠的、不可怕的、忠心的、真实的;如果拒绝分兵,那就说可疑的、胆小的和存心不良的。他对葡萄牙人单单采用这个测试法,要看透他们的内心世界。*[葡]若昂·埃斯科巴尔:《关于至高至强之塞巴斯蒂昂国王派往中国的使节团的评述》,载《澳门寻根》,第124页。
据埃斯科巴尔称,此段信息来自于总兵“内部最亲信的人”。然而,中文文献中并未有同样的记载。如果此事属实的话,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中国政府已经决定与澳门葡萄牙人展开合作,但出于对葡萄牙人传统的戒心,还是借机试探葡人的目的与动向。也正是由于澳门葡人意识到明政府的这种心理,为了巩固澳门这一远东重要商站的地位,葡萄牙人也不得不时刻逢迎明政府的要求。
中路内河水道进军的路易斯·德·梅洛于1564年10月6日抵达广州,挑选了6艘帆船和两艘lorchas*Lorchas是16世纪50年代在澳门产生的一种新型帆船。这种船型结合了中国传统帆船以及葡萄牙、英国等船式而成,由于在船体上的改进,这种帆船较之中国传统的帆船速度更快,载货更多。,将带去的武器安置到船上。中路进军的澳门葡人整顿完毕后,路易斯·德·梅洛率领的7艘船首先出发,俞大猷随后率领的25艘船尾随其后,驶向东莞三门一带。而在此之前,迪奥戈·佩雷拉已经于10月4日从澳门出发,经虎门进军,提前到达东莞海域。跟随佩雷拉船队的有一位俞大猷从广东派来的官吏(此人不详),他看到佩雷拉船队即将遭遇三门叛兵,而俞大猷和路易斯·德·梅洛的船队尚未抵达,因此要求佩雷拉停止航行,停泊下碇,一边监视叛军动向,一边等待省城中葡船队的到来*[葡]若昂·埃斯科巴尔:《关于至高至强之塞巴斯蒂昂国王派往中国的使节团的评述》,载《澳门寻根》,第119页。。在两支中葡船队进军的同时,另一支由海道副使莫抑率领的船队此时也应出发,驶向三门方向,以阻截出逃的叛军*(明)俞大猷:《正气堂全集》,《正气堂集》卷15,《与莫吉亭海宪书》,第371页。。三路船队分别从不同方向驶向三门,构建了一个严密的战略围剿网络。10月7日,迪奥戈·佩雷拉与俞大猷所率领的船队主力逐次驶达三门口,与叛军展开遭遇战,最终全歼叛军,而战斗仅花费了半个小时的时间。*[葡]若昂·埃斯科巴尔:《关于至高至强之塞巴斯蒂昂国王派往中国的使节团的评述》,载《澳门寻根》,第116页。
三门之役以中葡联军的大胜落下帷幕,此时的居澳葡商及耶稣会士满怀信心,期盼着戈伊斯使团出使北京的任务能够最终成行。在此役的推动下,广东当局同意接见由吉尔·德·戈伊斯、埃斯科巴尔,以及耶稣会士安德烈·平托、弗朗西斯科·佩雷斯组成的代表团。根据埃斯科巴尔的记载,广东右布政使陈暹*埃斯科巴尔仅记载“布政使”接待了他们,而当时在任的广东布政使有左布政使万士和、右布政使陈暹。据吴桂芳《议阻澳夷进贡疏》记载,陈暹在任之时,曾经对佛朗机托称满剌加国入贡一事进行过详细的勘合以及调查,据此推测,此处布政使当为陈暹。接待了他们。然而此行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出使北京一事再次搁浅。其实,早在俞大猷与葡人洽谈出兵之时,俞氏就暗中致信总督吴桂芳,明确表态“其夷目贡事已明谕,其决不许”*(明)俞大猷:《正气堂全集》,《正气堂集》卷15,《与两广军门自湖吴公书十六首·集兵船以攻叛兵》,第369页。。同时,吴桂芳亦对葡萄牙人入贡一事充满顾虑,担心葡人日后逃税,影响广东赖以为继的关税收入,同时还顾虑葡人侵扰海防。因此,吴氏在奏疏中称:“却其贡,则彼必肆为不道,或恣猖狂,然其发速而祸尚小;许其贡,则彼呼朋引类,日增月益,番船抽分之法,必至尽格而不行。沿海侵陵之患,将遂溃决而莫制,其祸虽迟而实大,大难图也”*(明)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342,《吴司马奏议·议阻澳夷进贡疏》,续修四库全书本,集部1660册,第220页。。可见以上两位广东军政最高领导人,出于海防、关税等多方考虑,基本上一致决定阻止葡萄牙人入贡。此番葡人助剿一事,从开端便注定了其只是一场单纯的军事行动,其背后的政治诉求难以实现。然而,尽管广东政府虚与委蛇的态度导致使团一事搁浅,然而葡萄牙人对于出使的热情依旧不减。正如埃斯科巴尔在广州写给澳门耶稣会泰玛诺(Manuel Teixeira)神父的信中称:
这个开端是好的,虽然并未完全办成,但大有希望,可以让耶稣会的神父们凭天主佑护很快地在这片土地上收获硕果,这是因为本地的大官们已经对神父们的声誉产生了信任感。*[葡]若昂·埃斯科巴尔:《若昂·德·埃斯科巴尔给曼努埃尔·特谢拉神父的信》(广州,1565年11月22日),载《澳门寻根》,第129页。
通过剿灭海盗,葡萄牙人收获了中国人的信任,同时还结交了多位地方大员,这在以往的广州贸易活动中是很难实现的。结合日后葡人多次的军事援助可以看出,助剿海盗几乎成为了居澳葡人获取中国政府信任,谋求政治、经济利益的一种“捷径”。
二、隆庆二、三年澳门葡人助剿曾一本海盗集团
关于曾一本集团起事经过,文献多有记录,其中《粤大记》记载其始末:
曾一本者,乃广东潮州人。因倭寇之乱,招亡纳叛,聚党数万,出入闽、广,大肆猖獗,攻城略地。杀虏参将缪印等,直抵五羊,焚我舟师,经年不能平。致厪圣怀,下廷议,推兵部左侍郎刘焘总督福建、两广军务,以兵部员外王俸随军赞画,议于南、北两京帑银内解发十万,以资兵食。四月二十一日入境,督催广东廵抚熊桴、福建廵抚涂泽民,总兵俞大猷、郭成、李锡,参将王诏等,闽、广克期相机会剿。五月十二日,一战于铜山,胜之,六月十二日,再战于玄钟澳,又胜之。二十六日,再战于莲澳,大胜之,生擒贼首曾一本,党伙数千,悉除。是役也,盖两省夹攻之力。然俞大猷建议造舟于闽,身任其事,竟以收功,其算多矣。*(明)郭棐撰,黄国声、邓贵忠点校:《粤大记(下)》卷32,《政事类·海防》,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95页。
曾一本,又名曾三老,广东潮州(一说福建诏安)人,原为海盗吴平的部下,吴平覆灭后,汤克宽曾建议招抚,并安插在潮阳,结果曾氏及其党羽“入则廪食于官, 出则肆掠海上人”*(明)张居正等:《明穆宗实录》卷14,“隆庆元年十一月丁巳”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380页。。曾一本首先由潮州起兵*(明)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342,《吴司马奏议·请设沿海水寨疏》,续修四库全书本,集部1660册,第227页。,招亡吴平旧部,“聚党数万”,不断骚扰闽广二省海疆,“破军杀将,略地攻城,称雄海上”*(明)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308,刘焘:《刘带川稿·总督闽广初上本兵剿抚曾林二寇书》,续修四库全书本,集部1659册,第505页。。其行踪飘忽不定,“胜则兽聚长驱,败则鸟兽散,飘忽瞬息千里,莫可追袭”*(明)张瀚:《台省疏稿》卷5,《参广东失事疏》,续修四库全书本影印万历刻本,第93页。,以至“所向无前,诸将莫敢撄其锋”*(明)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308,刘焘:《刘带川稿·总督闽广初上本兵剿抚曾林二寇书》,续修四库全书本,集部1659册,第505页。。曾一本于隆庆元年(1567)十一月二十一日突袭雷州,参将缪印、把总俞尚志被擒,指挥李茂才战死,雷州守军损失近四千人*(明)张瀚:《台省疏稿》卷5,《参广东失事疏》,续修四库全书本影印万历刻本,第91-92页。。针对此事,杜臻称曾一本“杀参将缪印,遂不可制”*(清)杜臻:《粤闽巡视纪略》卷3,《南澳山》,文海出版社影印岳雪楼抄本,第24页。。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曾一本船队已装备有大量从官军手中抢掠的火器,两广总督张瀚称“其船只利便,及掳得火器渐多,故一见官兵,铳炮如雨,冲突直前,我军遂怯”*(明)张瀚:《台省疏稿》卷5,《查参失事将官疏》,第107页。。葡人记载亦称“对方有三四千人,一千五百多只火枪”*[葡]加斯帕尔·福鲁图奥佐:《怀念故土》,载《16和17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159页。。凭借在潮州及雷州所劫掠的坚船利炮,曾一本异军突起,成为广东地区最大的海盗团伙,具备了与朝廷军队正面抗衡的能力。雷州战役过后,俞大猷调任广东协助剿匪。
此时的广东海防军队面对实力强劲的曾一本集团几乎无计可施,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广东船政连年遭受海盗的侵扰,正处在无船可用境地*对于广东战船经年遭受损失一事,俞大猷曾有详细的记载:“不意十五年前,浙直倭炽。总督军门胡议调广船一百只,皆选其巨者前去剿倭。经三四载,不得毕事,各船因皆损坏于彼,而一只不返广东,船事从此弱矣。继以数年之前,叛兵等贼在海乌尾、横江到处追焚,所余遂无几也,自此而海上之事益多。民间方造得船一二只,尚未得载货之利,未有得载货之利,未有精壮后生在船,官府遂刷以载兵。或为贼焚,或为贼得,或经年载兵不得退还,而各主者钱本亏损,以后造船觅利之念皆灰矣”。(俞大猷:《正气堂全集》之《洗海近事》卷上,《呈总督军门张》,第813页。)可见在曾一本作乱之前,广东船政分别经历了两次重大打击,一是胡宗宪租调一百只大船赴浙抗倭,结果一只未返广东;第二次便是上文所提到的柘林兵变,叛军到处焚毁广东战船,以致主力战船所剩无几。。因此,广东政府正在广州加紧打造战船。同时,为了留出充足的时间打造船只,俞大猷屡屡差人向曾一本招降,“不问有益于事,无益于事,只混款他,以待兵集耳”。*(明)俞大猷:《正气堂全集》,《洗海近事》卷上,《书与李培竹公》,“隆庆二年三月十五日”条,第801页。对于老将俞大猷而言,他对曾一本招降之事并未作过多的期望,只是借招降作缓兵之计,为造船留出足够的时间。但就在此时,曾一本的船队已经从雷州启程,开赴广州。据中文文献记载,隆庆二年五月十三日(1568年6月8日),曾一本集团出现在珠江口西面的上川岛一带:
贼在三洲迟疑,似有内犯之意。福船未造完,乌船又不肯借福兵用,奈何?奈何?*(明)俞大猷:《正气堂全集》,《洗海近事》卷上,《书与李培竹公》,“隆庆二年五月十三日”条,第803页。
“三洲”即澳门西南方向的上川岛。可以看出由于战船尚未造好,军中又政令不一,此时的俞大猷已经毫无办法组织严密防御。但就在曾一本准备开赴省城之前,叛军却首先骚扰了附近的澳门。根据西文记载,就在曾一本集团出现在上川岛后的第五天(即6月13日),海盗开始向澳门进军,1566年起担任澳门兵头特里斯藤·瓦斯·达·维加(Tristão Vaz da Veiga)指挥了此次战斗:
6月12日,一百来艘帆船在距港口一里格左右的海面出现,大概有四十艘大船于第二天拂晓前来登陆。〔当时〕居民点上的葡人不到一百三十个人,其中还有很多老人和孩子。特里斯藤·瓦斯·达·维加打发在港口的〔一些人〕,大概有三十五个或者四十个人,到船上去保护船只,他自己则带领余下的人到居民点外面迎击敌人,走出不远便停下来等待敌人放弃他们的船。看到他们下了船,他立即发动进攻。感谢上帝,对方有三四千人,一千五百多支火枪,而他们只不过九十个葡人和他们的奴仆,却把对方打败了。在那一天曾四次把敌人赶回船上,打死了许多人,还夺取了许多条火枪。因为敌人为了减轻负担把火枪和武器扔下了,争先恐后地逃命,结果有几条船翻了,很多人当场淹死。*[葡]加斯帕尔·福鲁图奥佐:《怀念故土》,第159页。
据葡人战后统计,守城的葡人和奴隶有“十三至十四人被杀死”,“另外有四十至五十人受伤”*[葡]加斯帕尔·福鲁图奥佐:《怀念故土》,第159页。。海盗攻城失败后,开始着力进攻停靠在海湾中的葡人大黑船,这与柘林叛兵之手段如出一辙:
这一天敌人吓破了胆,没有敢再来进攻,只是从远处挑衅。后来他们的船长试图夺取大黑船,与大黑船搏斗了两三天,先是从划浆的船上用火炮轰击,想把它打沉。后来来了六只大船,是他们当中最大的船,用铁索连在一起,试图把大黑船撞坏。但大黑船上的人坚决抵抗,于是对方在海上和陆上都没有占到什么便宜。*[葡]加斯帕尔·福鲁图奥佐:《怀念故土》,第159页。
曾一本集团围攻大黑船的行动也未能占得便宜,两三天之后,便停止了攻击,此次攻打澳门也告一段落。在此期间,兵头特里斯藤·瓦斯·达·维加带着他的人日夜在居民点外面的陆地上警戒,以防敌人纵火焚烧。葡人事后得知,此战曾一本集团“共损失了六百人,敌人包围了八天之久”*[葡]加斯帕尔·福鲁图奥佐:《怀念故土》,第160页。。
曾一本与葡人交战期间,同时还与广东政府周旋,佯装归顺之意。就在曾一本与葡人交战结束几天以后,为了安抚曾一本,广东官员特意下澳知会葡萄牙人和曾一本集团,希望双方停战讲和*[葡]加斯帕尔·福鲁图奥佐:《怀念故土》,第160页。。停战的建议是葡人与曾一本均乐意接受的结果。对于葡人来说,他们担心来澳的船只会遭到就在澳门附近的曾一本集团的劫掠;而对于曾一本而言,遵循中国政府的命令可以使他进一步麻痹广州的守军,同时还获得了重整旗鼓的机会。根据福鲁图奥佐(Gaspar Frutuoso)的记载,曾一本离开澳门港后,来到了“离葡萄牙人居民点七八里格的老麻〔岛〕一带”*[葡]加斯帕尔·福鲁图奥佐:《怀念故土》,第160页。。另据若阿金·萨赖瓦(Joaquim de Sousa Saraiva)主教手稿称“21日,曾一本亦率众离开澳门,转泊于老万(Lamão)岛”*埃武拉公共图书馆及档案馆Cód, CXV I/2—5,转引自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一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6页。。老麻岛即老万岛之异译。前文称曾一本集团6月13日登陆,包围了8日之久,此处21日离开澳门正与前文相合。
就在曾一本赴老万岛休整期间,广州当局也在紧锣密鼓地打造船只,据俞大猷隆庆二年六月初三(1568年6月27日)日写给总兵官郭成的信件称:
贼情反复无常、百有所求,安能一一依之?有一不依,即反,官府安能尽包容之?乞公与培翁议,将福兵照旧发上。广船将已完,冬仔船整搠,并白船俱出泊波罗(庙)待之。或天作飓风,即速收入五羊驿前,亦不迟也,此恃吾有以待之意,乞留神。*(明)俞大猷:《正气堂全集》,《洗海近事》卷上,《书与郭宝山》,“隆庆二年六月初三日”条,第804页。
可见此时的造船计划即将完工。与此同时,葡萄牙人也在华商林弘仲的牵头下准备向广东政府增援。根据两广总督张瀚记载,澳商为增援广东,已集结了2 000人*(明)张瀚:《台省疏稿》卷5,《查参失事将官疏》,第107页。,若此记载属实,那么除了澳门城中原有的130多人及其奴仆,以及刚刚抵达澳门的大黑船中的船员之外,剩余的千余人应当为澳门华商林弘仲等人联合组织的抵抗力量。然而当葡人还在等待广东政府的回复之时,几天之后,由于曾一本突然进犯广州,使未完工的战船遭受到了灭顶打击,一部分被曾一本掳走,另一部分则被焚毁。“半载经营战船杠椇,复为贼烧毁占据。而城外民居,亦遭毁熖。”*(明)张瀚:《台省疏稿》卷5,《查参失事将官疏》,第107页。对于此事,杜臻《粤闽巡视纪略》记载与之相仿,但将失事的矛头指向俞大猷。详见(清)杜臻:《粤闽巡视纪略》卷3,《南澳山》,第24页。杜臻《粤闽巡视纪略》记载与之相仿,但将失事的矛头指向俞大猷:
总兵俞大猷使人诱降,欲生致之。一本觉其意,因藉以愚大猷,挟大艘六十,直趋大朋(鹏)。一把总察其意色非是,言于大猷,大猷始仓皇修战。备陈未定,而贼发投火爇,官船俱尽。一本遂掠直抵广州,题诗海珠寺壁,以诮大猷,扬帆竟去。*(清)杜臻:《粤闽巡视纪略》卷3,《南澳山》,第24页。
广州的失守,使得此次葡人的助剿计划也未能成行。葡人对此亦有记载:
后来他(曾一本)进攻广州城(此城既大又繁华),抢劫并烧毁了该城的郊区,夺取了停泊在河上的整个船队计一百余只船,其中有些船非常大;他选择最好的留下,把其余不用的统统烧掉。此次围攻持续了十五天或二十天之久。*[葡]加斯帕尔·福鲁图奥佐:《怀念故土》,第160页。
此次曾一本的突袭,使得广州的防御力量遭到了极大的打击,对于正在打造的战船无异于灭顶之灾,广东政府一度到了无船可用的境地。曾一本撤离广州后,其残余部队不时骚扰周边地区。就在此时,葡萄牙人再一次抓住机会,向明政府表明,准备提供军事援助。此次助剿计划最终成行,张瀚记载了此次隆庆二年七月初三日剿匪之事:
七月初三日,白艚贼船二十余只突至香山县唐家、九洲地方打劫……各官兵遵奉总督军门催督调度,于初六日在虎头门外,自寅至午,与贼大战十数合,夺获大白艚船九只,冲沉大船三只……头目林弘仲、何中行等部领兵夫夹剿前贼,生擒贼徒二十五名,斩获贼级四十八颗。*(明)张瀚:《台省疏稿》卷6,《海上擒获捷音疏》,续修四库全书本,史部第47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09页。
此处所提“林弘仲”,中文文献中又称林宏仲,葡人称之为Nilao(林老),是澳门开埠初期著名的华商。关于此人最早的记载,应当出自朱纨《甓余杂集》。嘉靖二十七年(1548),浙江巡抚朱纨在《申论议处夷贼以明典事以消祸患事》一文中提出:
卢镗呈称会同巡海道副使柯乔,访得长屿等处惯通番国林恭、林乾才、林三田、林弘仲、李文瑞、林石……,各号为喇哒、总管、舵工、水梢等项名色,勾引夷船贼船。*(明)朱纨:《甓余杂集》卷5,《申论议处夷贼以明典事以消祸患事》,四库存目丛书本,集部第78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141页。
可见林弘仲早在1548年便开始与葡萄牙人接触并开展贸易,故称其惯通番国。此人为俞大猷的“旧熟”,早在三门之战时俞大猷就利用“香山澳船”,并“取其旧熟用林宏仲者数船”*(明)俞大猷:《正气堂全集》,《正气堂集》卷15,《集兵船以攻叛兵》,第368页。如果从时空方面来推测的话,林弘仲在浙闽地区通番经商活动应止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朱纨驱逐双屿港海盗至嘉靖二十八年(1549)福建走马溪之战之间,之后行踪不明,很有可能追随迪奥戈·佩雷拉等人辗转来到澳门。而俞大猷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之前曾担任福建汀漳守备,二十八年(1549)还亲见走马溪之战,之后便辗转广东、广西、浙江等地为官,直至嘉靖四十年(1561)才重回广东(何世铭:《俞大猷年谱》卷1,泉州文献丛刊第五种,泉州历史研究会影印版,2012年,第108-261页)。因此,我们猜测俞大猷与林弘仲相识当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之前。帮助明军征剿海盗,后还曾担任广东政府的名色把总*三门之战前夕,俞大猷召集人力打造战船,其中作为“名色把总”的林弘仲也接到了摊派任务。(明)俞大猷:《正气堂全集》,《洗海近事》卷上,《呈总督军门张》,“隆庆二年七月十二日”,第829页称:“名色把总,一员。林弘仲,造三丈面一只。”至于“名色把总”,并非世袭官职,也非科举选授,而是拔擢才干的庶人中,给与冠带,破格用之,是介于平民与武官之间的一个职位。林弘仲之所以被任命为名色把总,我们以为这与俞大猷“旧熟”的关系是分不开的。对于林弘仲来说,他既是澳门华商的代表人物,又是明政府与澳门葡人接洽的中间人,还是明朝官僚体系中特殊的一员,具有多重身份,这或许是澳门开埠初期华商的一大特点。,以澳商“头目”的身份参与战斗。据记载,林弘仲“十五年来一直同葡萄牙人打交道,自有两三艘帆船”*[葡]若昂·埃斯科巴尔:《关于至高至强之塞巴斯蒂昂国王派往中国的使节团的评述》,载《澳门寻根》,第112页。,此外,林弘仲至少在澳门之时便已受洗入教。据福鲁图奥佐《怀念故土》的记载,1568年澳门攻打海寇曾一本时,澳门当局派去了“五十个葡萄牙人和几个当地的基督教徒及他们的奴隶”*[葡]加斯帕尔·福鲁图奥佐:《怀念故土》,第161页。,由于此役林弘仲亦有参与,故“当地的基督教徒”应包括林弘仲。
郭棐对此次剿匪同样有所记载,但他误将曾一本与“白艚战船二十余只”的小股海寇混为一谈:
一本,潮阳人,本吴平遗孽,乘倭变聚众作乱,执参将缪印杀之,遂率众数千,乘船二百余艘,突至广州,杀掠不可胜纪。外兵入援,乃引去。*(明)郭棐:(万历)《广东通志》卷6,《藩省志六·事纪五》,日本早稻田大学藏明万历三十年刊本,第52页。
葡人对于此次战役的记载更加详实:
此人拥有二十三艘船,经常在离〔葡萄牙人居民点〕很近的地方抢掠,妨碍向本地运送食品。中国官员一再向他求助,派几条船来到本港。特里斯藤·瓦斯给他们当中的四条船派去了五十个葡萄牙人和几个当地基督教徒及他们的奴隶。他们在傍晚时分驶离澳门,凌晨时分与海盗交战,夺取了海盗的二十三艘船中的十一艘,俘获了许多人,并缴获了许多军火。〔其余〕十二艘快船得以逃脱。*[葡]加斯帕尔·福鲁图奥佐:《怀念故土》,第161-162页。
中葡文献对于此次战役的记载虽详略不一,但基本相合,我们也可以大致还原此次会剿行动的进程:关于驱盗主体,中文材料所称“林弘仲、何中行”,即葡文资料所称“当地基督教徒”,以他们作为代表,代指了当时参战的澳门葡商;关于海盗进犯的地点,中文材料称曰“香山县唐家、九洲地方”,此处“唐家”,即今珠海北部的唐家湾,而“九洲”应为伶仃洋北面的九洲洋,以上两地均在澳门附近。而据葡文材料,此股海盗经常在澳门附近的地点劫掠,与中文数据大体相符。关于时间,中文文献记载称时为隆庆二年七月初六(1568年7月29日)寅时至午时。葡文文献虽未指明日期,但也记载了开战的时间为凌晨;关于交战地点,中文文献载之曰“虎头门外”,葡文文献不详,但其提到了船队“傍晚时分驶离澳门,凌晨时分与海盗交战”,交战地点距离澳门数小时航程,基本上也应地处虎头门附近。关于敌军规模与战果,张瀚记载敌船为“白艚战船二十余只”,俘虏敌船九只,击沉三只;福鲁图奥佐称敌船共二十三艘船,夺取了其中的十一艘,二者仅在战果的统计上存在着些许差别。然而在另一位葡萄牙人的记载中,其战果似乎更贴近中文数据。博卡罗(António Bocarro)《旬年史之十三》称:
从前,一名叫曾一本、林道乾(Charempum Litauqiem)的海盗与该省的官员及国王作对。他犯上作乱,准备夺取广州。于是,中国官员招我等前去与他们并肩作战。我们出银两,人手,船只与军火。敌众我寡,但我等毫无畏惧,奋不顾身杀敌,将其全歼并俘获九艘船只。*[葡]博卡罗:《印度旬年史之十三》,载金国平:《西力东渐——中葡早期接触追昔》,澳门基金会,2000年,第288页。
此处Charempum当为中文“曾一本”之译音,而Litauqiem则当为中文“林道乾”之译音。虽然此处博卡罗将曾一本、林道乾两位海盗的名字误认作一人,但博卡罗此处所言之史实仅指曾一本,并未涉及林道乾,因林道乾从未进攻过广州。根据博卡罗的记载,此处葡人“全歼并俘九艘船只”,正与张瀚所言“夺取大艚船九只”相合。
除了隆庆二年葡萄牙人在广州助剿曾一本集团之外,隆庆三年(1569)剿灭曾一本的会战中,澳门葡人还曾在华商林弘仲的带领下,跟随中国船队远赴潮州剿贼。关于此役,《粤大记》称:
闽、广克期相机会剿。五月十二日,一战于铜山,胜之,六月十二日,再战于玄钟澳,又胜之。二十六日,再战于莲澳,大胜之,生擒贼首曾一本,党伙数千悉除。*(明)郭棐:《粤大记》卷32,《政事类》,第895页。
自隆庆三年五月起,广西总兵俞大猷、广东总兵郭成、福建总兵李锡三人分别从三路出兵,围剿盘踞在粤闽交界的曾一本集团,三战皆捷,六月二十六日生擒曾一本。关于此役,俞大猷曾经在船队的参战名录中提到了一条重要信息:“把总林弘仲等四只(船)”*(明)俞大猷:《正气堂全集》,《洗海近事》卷下,《海战军令》,“隆庆三年二月”条,第867页。。前文已指出,林弘仲其人为此时澳门著名华商,与俞大猷交好。在此之前俞大猷在造船的名录中同样提到“名色把总,一员。林弘仲,造三丈面一只”*(明)俞大猷:《正气堂全集》,《洗海近事》卷上,《呈总督军门张》,“隆庆二年七月十二日”条,第829页。。可见澳门华商林弘仲是作为名色把总*名色把总并非世袭官职,也非科举选授,而是拔擢才干的庶人中,给与冠带,破格用之。此例在创设之初,多行之于南方。与名色把总相对应的,当为武举中试之后所授的“钦依把总”。徐阶《世经堂集》云:“诸将升迁,自有资序。乃若壮夫,窃谓宜如南方之例,给与冠带,作名色把总,待又有功,实授官职。如此破格用之,继者必当益众矣。”(明)徐阶《世经堂集》卷24,《复冀康川》,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集部80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135页。率领澳门武装力量参与了剿灭曾一本的战役,此信息他处无载,唯赖俞氏《洗海近事》得以保存,为澳门葡人助明驱盗又多一明证。
自隆庆二年至隆庆三年,澳门葡人及澳门华商先后两次协助明朝政府围剿曾一本集团,最终获得胜利。此次军事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接下来数年间明朝对澳门的政治倾向。明朝官员再一次领略到了澳葡强大的军事实力,时任工科给事中的陈吾德直言不讳地称:“佛郎机、满咖剌诸夷,性之犷悍,器之精利,尤在倭奴之上。去岁曾(一本)贼悉众攻之,夷人曾不满千而贼皆扶伤远引,不敢与斗,其强可知矣。”*(明)陈吾德:《谢山存稿》卷1,《条陈东粤书》,四库存目丛书影印清刊本,集部138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423页。但此时的明朝政府并没有回到清剿、驱逐葡人的老路,而是更为理智地尝试对澳门政治军事管理的初步制度化。其中以广东南海籍文人霍与暇在隆庆五年(1571)所论“治澳三策”最为典型:“建城设官而县治之,上策也;遣之出境,谢绝其来,中策也;若握其喉,绝其食,激其变而剿之,斯下策矣”*(明)霍与暇:《勉斋集》卷19,《处濠镜澳议》,华南师大图书馆藏光緒丙戌重刊本,第83页。。他认为若驱逐澳夷,对于广东地方而言,会产生两大不便,其一是影响澳门贸易抽分所带来了巨大利益,“两广百年间,资贸易以饷兵,计其入可当一大县”,若失去这部分收益,则两广军费难以保障;第二点则似乎更为重要,便是当时群盗滋生的珠江口地区的海防问题,“香山海洋,得澳门为屏卫,向时如老万、如曾一本、如何亚八之属,不敢正目而视,阖境帖然”,可见此时的澳门葡人,在当地官员眼中已然成为了拱卫珠江口的一道坚实的屏障,“若撤去澳夷,将使香山自为守,二不便也。”*(明)霍与暇:《勉斋集》卷19,《处濠镜澳议》,华南师大图书馆藏光绪丙戌重刊本,第84页。。
三、万历七年至八年澳门葡人助剿逃亡大泥、甘埔寨的林道乾海盗集团
林道乾,潮州惠来人,原为吴平海盗集团之部属,吴平死后,即与曾一本分别纠合吴平余部,并各自发展自己的势力,林道乾在闽粤海上活动,为当时著名海盗。乾隆《潮州府志》曾载其起事经过:
林道乾,惠来人,少为县吏,机变险诈,智虑超于诸寇。性嗜杀,所过无不残灭,舟泊处海水尽赤,积尸如山,潮汐为之不至。先是嘉靖四十五年三月攻诏安山南廐下等村,都督俞大猷逐之,遁入北港。大兵不敢进,留偏师驻澎湖守之。道乾不乐居北港,遂恣杀土番,取膏血造船。从安平镇二鲲身遁往占城,复回潮州,掳掠如故。既而就抚,安插潮阳下尾乡,犹与曾一本声援相应。亡赖之徒,相继归往。每悬赏招募人予一金,致十人者予三金,即以其人统之,故附之者日众,为海滨巨寇。连年劫惠来龙溪都无噍类,又犯海丰石帆都。时届宾兴生员李棠束装赴省,途中被掳,其妻卓氏抱子入贼舟赎棠贼,释棠以卓为质,卓于是夜抱幼子赴海死。及榜发,棠登第,因上策请兵剿贼。有朱良宝、魏朝义、莫应敷者,亦纠党入海行刦,与道乾相应。时因地方多事,兵力难分,勉为招抚。既就抚,道乾居招收都,良宝踞南洋寨,朝义踞大家井,应敷踞东湖寨,杀掠如故。*(清)周硕勋:(乾隆)《潮州府志》卷38,清光绪三十九年重刊本,第37页。
林道乾于嘉靖末期骚扰福建沿海,在俞大猷的围剿之下“遁入北港”,后还曾逃往占城,接着返回潮州。在广东政府的招抚下,林道乾归降,被安插在潮州,但林氏四处招徕人手,以致“亡赖之徒,相继归往”,同时依旧从事海盗旧业,“杀掠如故”。曾一本之乱时,林道乾曾经配合明政府打击曾氏海盗集团。在乾隆《潮州府志》的记载中,林道乾是一位“性嗜杀,所过无不残灭”的暴徒,然而在更早成书的瞿九思《万历武功录》笔下,林道乾则又是另一种形象:

根据瞿九思的记载,可以看出林道乾虽同样身为“专以剽略为务”的隆万时期一代巨寇,但同时还是一位“为人有风望,智力无二好”的义匪。除此之外,林道乾还“擅山海之禁以为利”,俨然又是一走私海商。关于海盗林道乾,瞿氏记载“乾自谓不能居人下,居恒欲收招海上精兵,发动举事”,俞大猷同样记载曰“曾(一本)为人愚悍,自无主张;林道乾凡事自决,推诚谕之”*(明)俞大猷:《正气堂全集》,《洗海近事》卷上,《呈总督军门张条议三事》,第794页。,可见林道乾集团不同于传统的愤而起事的贩夫走卒或是土匪盗寇,而是具备较为明确的战略目的海商海寇集团。
由于隆庆年间自张瀚至李迁的历任两广总督对林道乾集团多采取容忍与招抚的态度与手段,故明政府与林道乾集团并未发生太大的摩擦。至采取坚决剿寇态度的总督殷正茂上任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万历元年(1573)两广总督殷正茂率军击破林道乾,林被迫逃遁海外。关于林道乾逋逃海外一事,《万历武功录》有着详细的记录:
制置使殷正茂佯宽假(林道)乾罪曰,令而得以功赎。于是乘传以惠州,阴使参政使刘稳、唐九徳、按察副使吴一介、苏愚、参议使顾养谦及横海将军张元勋、胡震议,议以不意图之。当是时,乾有侄曰茂,先在彭亨国为都夷使,乃以尺一牍约乾,乾竟瞑目张胆,请于参政使陈奎曰:极知制置使意,业已远托异域,不复还矣。……是岁癸酉二月十五也。乾既行至甘浦寨,乃出槖中装五百金,帛五十纯,因阳四送奉寨主……*(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3,《林道乾诸良宝林凤列传》,第532页。
由于林道乾桀骜不驯,且四处招徕亡命之徒充实力量,到殷正茂督粤时期,广东政府终于决定铲除林道乾。然而林道乾提前发觉了殷正茂的意图,于万历元年二月十五日逃离广东,远赴柬埔寨。刘尧诲万历二年《林贼遁番疏》称:“叛贼林道乾投往夷方甘埔寨,近探闻在彼聚粮缮器,添造战船,决回闽广作乱。”*(明)刘尧诲:《督抚疏议》卷2,《林贼遁番疏》,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第32页。
林道乾抵达柬埔寨后,不久又折回闽广沿海。据福建巡抚刘尧诲记载,万历元年林道乾船队抵达福建,攻打沿海卫所,给当地驻军造成了很大的伤亡:
看得海贼林道乾等逃入闽海,窃据澎湖为患,仰将各该将领怠玩偾事录由备行监军道副使邓之屏查报间录,该道已先期入场监试。至九月初六日随据该道呈称,先为飞报紧急贼情事。七月初一日,据万安所报称六月二十六日广贼三十余船突入本所古龙港,百户侯炜督驾兵船五只当被贼抢去。迄七月初七日据福宁州报称,六月三十日贼船三十六只在芙蓉海洋行使,烽火寨哨官鲍尚忠督率捕盗李文清等到,彼对敌不过阵亡。七月十七日据罗源县报称,本月十六日本县鉴江堡被贼攻破,申乞添兵协守。七月十八日据福宁州报称,本月十四日贼众打破北僻塘头堡。七月二十三日据分守福宁道报称,本月二十四日贼船驾到松山后港烽火寨,把总刘国宾统兵救援,对敌不过与哨官钱明俱各阵亡……臣为照广贼林道乾雄踞广潮,威行于内地十年已。一旦大兵压境,援应未周。故浮海而南,焚弃旧巢,以示无复东意,实未尝一日忘广东也。*(明)刘尧诲:《督抚疏议》卷1,《海贼突犯查参失事人员疏》,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第9-11页。
万历六年(1578),林道乾曾短暂返回潮州补充经费,招徕党徒:
戊寅七月,乾自甘埔还潮故巢,居月余发囊所藏银穴,募潮一百余人,与俱南行至琼崖,遇闽中转榖舳舰。乾乃略其金银,及男妇二百人而去。*(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3,《林道乾诸良宝林凤列传》,第533页。
宋懋澄则记载了万历六年林道乾进犯潮州附近的碣石卫:
林道乾者,故揭阳县吏。负罪窜海,有舟千艘,众数万余。通安南、占城、旧港、三佛齐诸国,尝佩列国相印。相小琉球三年,将谋夺其国,国人不从,乃复航海。戊寅春,率舟师四百,突至碣石。碣石者,惠之边卫也。*(明)宋懋澄:《九籥集》文集卷7,《叔父参知季鹰公行略》,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177册,第569页。
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与刘尧诲的信件中称:
昨据闽中报,柬埔寨主言林贼虽投入暹罗,尚往来攻彼寨。*(明)张居正:《张居正集》卷24,《答两广刘凝斋》,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64页。
次年《神宗实录》亦记载曰:
海贼林道乾者,窃据海岛中,出没为患,将士不能穷追。而大泥暹罗为之窟穴,既而逼胁大泥,侵暴暹罗。有通事言彼国愿往擒自效,总督两广刘尧诲议重立赏,格期于必获,部覆为请,从之。*(明)叶向高等:《明神宗实录》卷99,“万历八年闰四月壬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1977页。
此处“通事”究竟为何人?“彼国”又指哪个国家?如果单从材料本身来看,很有可能会误认为是暹罗或大泥。其实,结合其他史料我们可以看出,此处之“彼国”即为一直以来积极帮助明朝打击海盗的佛朗机人。时任两广总督刘尧诲《督抚疏议》一书中有此事更详细记载:
万历七年八月二十四日,据广东巡视海道右参政刘经纬揭报,据暹罗国夷船主握坤哪喇赍到该国国主番书来到,广东布政司译出语意,内称“逆贼林道乾今改名林浩梁,大小船只来到本国海中澳,虏掠客商船只,声言欲会大泥国,同谋攻打本国地方,本国主议欲招抚道乾进来,道乾要我国主发誓,不拿我解广东布政司方听招入,差官往来招安,讲议三月之久。国主思见差来广东船只不得出港,且风期将尽,只得与道乾盟誓,两不相害。道乾方进水口,还不肯信,又要当天滴水发誓,国主果誓,道乾听招,进入头关,来报布政司得知”等因,具报到臣。该臣批行该道,密切译审前情,及往探各夷来船,有无林贼伙党在内。去后九月内,又据广东总兵官张元勋揭报相同,又续据海道参政刘经纬揭称“依奉查得握坤哪喇,系隆庆五年来贡船主,万历二年、三年、四年俱驾船来广贸易。今岁执有罗字二号勘合,来省候领印信,其纳款互市,已为有素,屡奉军门谕访,似无别项隐情。如蒙给牌,谕令国主,谋与夷众,将林贼擒献,傥幸天成,亦为长便。仍乞裁定,将本夷船主先与量加厚赏,以示鼓舞”等因,尤恐不的,时且冬汛,该臣于本年十月内移镇广东省城,本月十八日据总兵官张元勋揭称“名色把总黄元兴等,禀称香山澳报效人吴章等,与佛朗机番人沉马啰及船主啰鸣冲呅呧呶,通事蔡兴全等密报,林贼见在暹罗,章等请给冠带犒赏,自备兵船驾往擒获,仍乞移文入暹,使内外交攻”等因。据此,牌行香山县调到暹罗贡夷船主握坤哪喇、佛朗船主啰鸣冲呅呧呶,及把总黄元兴、通事蔡兴全等二十余人前来军门谒见,译审前情无异,即牌行广东布政司,转行该国谕以尽忠擒贼,果效有成劳,即与题请降∘褒嘉,及叙功给赏,量免该年船税,以示优厚。仍附船主握坤哪喇等赍回宣示,当处给银牌、花段,颁赏各番及通事人等有差,各番夷领受,于本年十二月初三、十五及八年二月二十四等日前后开驾原船,复回该国,去讫为照。*(明)刘尧诲:《督抚疏议》卷9,《题为逋贼投番叵测乞申赏格以劝励人心事》,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第8-13页。
暹罗使者握坤为暹罗语(Ockans)之译音,为暹罗职官名,王宗载称:“其官制有九等,四曰握坤。”*(清)佚名:《暹罗馆译语》,载《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6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761页;陈学霖:《暹罗入明贡使“谢文彬”事件剖析》,载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编:《史薮》第2卷,1996年,第143—176页。暹罗所有官阶都称“握”,“握”为“大”之意。哪喇面见两广总督刘尧诲,并汇报林道乾作乱一事。于是香山澳门人吴章、佛郎机人沉马啰、船主啰鸣冲文呧奴(Bartoloméu Vaz Landeiro)、通事蔡兴全等20余人连续上书要求自己备装去进攻林道乾。关于以上几位葡萄牙人和华人通事,中西史料记载极少,所见仅有啰鸣冲文呧奴一人之葡文数据。此人是一位于16世纪80年代活跃在澳门的葡萄牙犹太船主,从事澳门与日本、马尼拉之间的贸易,是一位非常富有和极有权势的葡萄牙人。1583年2月13日,他还派船将西班牙耶稣会士阿隆索·桑切斯(Alonso Sanchez)同格列高利省代理教区长热罗尼莫·布尔戈斯(Jerónimo de Burgos)修士送往马尼拉*[西]桑切斯:《耶稣会桑切斯神父受菲律宾总督佩尼亚罗沙、主教及其他陛下的官员之命从吕宋岛马尼拉城使华简志》,西班牙塞维亚东西印度总档案馆,菲律宾档79—2—15。转引自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一卷,2009年,第201页。。而上述“沉马啰”,据葡萄牙人学者苏禄修(Lúcio de Sousa)之研究,此人姓名中之“沉马”一词通常为西班牙姓名José Maria之缩写,而“啰殊”则为Rosa之中文译文。可知此人或为一西班牙裔船主*Lúcio de Sousa,The Earlyeuropean Presence In China, Japan,The Philippines and Southeast Asia(1555-1590)——The Life of Bartolomeu Landeiro,Macao Foundation,2010,p.35.。关于葡人助剿,《万历武功录》称:
庚辰八月,暹罗亦使,使者握坤哪喇请予制置使刘尧诲曰:乾今更名曰林浯梁,所居在臣国海澳中,专务剽略商旅,声欲会大泥国,称兵犯臣国。臣国请招徕乾,乾乃欲歃血为盟誓,誓无令汉使得执我也。于是,臣国不得已,佯与乾盟。今乾已行至头关,敢闻。是时,香山澳人吴章,佛朗机人沉马啰,及船主啰鸣冲呅呧呶、通事蔡典全等二十余人,并踵制府上谒,请自治装往击乾。于是,制置使进暹罗使者,庭中问状,因赏赐银牌、花、彩段如礼,曰与我师并击,如令。*(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3,《林道乾诸良宝林凤列传》,第532页。
瞿氏所记载之内容,或参阅过《督抚疏议》一书,然内容多有删减,且频现抄讹,如将暹罗及葡萄牙使者觐见时间错记为万历庚辰(1580),“林浩梁”记为“林浯梁”,“蔡兴全”作“蔡典全”。毛奇龄《后鉴录》则抄《万历武功录》称:
澄海林道乾,嘉靖中为盗,降。继而以兄子茂入彭亨国为都夷使,招道乾。道乾诣军门明白辞去,封还前所给一十七札,竟行。广督殷正茂檄暹罗、安南共讨之。暹罗乃使使者握坤哪喇请曰:“道乾更名林浯梁,在臣海澳中,欲会大泥国入寇,今已统兵向头关矣。”正茂与福督刘尧诲遣香山吴章、佛郎机沉马啰及船主啰鸣冲呅呧呶同击道乾。*(清)毛奇龄:《后鉴录》卷4,续修四库全书本,第432册,第235页。此段记录同样见于万斯同《明史》卷407,《盗贼》,续修四库全书本,第331册,第449-450页。
清人毛奇龄此处所记录的内容与瞿九思之记载存在一定出入。毛氏称剿灭海盗的明朝官员为“正茂与福督刘尧诲”,但此时刘尧诲已经由福建巡抚转任两广总督。
万历四十五年(1617)耶稣会士庞迪我、熊三拔的《具揭》则称:
颇闻林道乾之乱,有在澳商人等自备舡粮器械,协力攻击。督府曾上其功。……欲求海中安靖,中国欲仿林道乾事例,与各国市舶协力擒剿,庶免贻祸将来。*[西]庞迪我、[意]熊三拔:《具揭》,载钟鸣旦《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第1册,台北:辅仁大学神学院,1996年,第71-140页。
葡萄牙人对此事同样有所记载:
从前一名叫曾一本、林道乾(Charempum Litauqiem)的海盗与该省的官员和国王作对,他犯上作乱,准备夺取广州。于是,中国官员招我等前去与他们并肩作战。我们出银两,人手,船只与军火。敌众我寡,但我等毫无畏惧,奋不顾身杀敌,将其全部杀死,并俘九艘船只。我等将船上俘获之物如数上缴官员。后王室大法官获一冠帽、通事获一银牌奖章。因为此次军事援助的原因,中国官方认为我们是好人,并把我们援助一事记录在案。*António Bocarro, Década 13 da História da índia, (ed. de Rodrigo José de Lima Felner), Lisboa,Academia Real das Ciências, 1876, p.729, in Lúcio de Sousa,The Early european Presence In China, Japan,The Philippines and Southeast Asia(1555-1590)——The Life of Bartolomeu Landeiro,Macao Foundation,2010, p.32.
前文已述,此处博卡罗将曾一本、林道乾两位海盗的名字误认作一人,但博卡罗所述驱盗之史实当指曾一本。然而随后“王室大法官获一冠帽、通事获一银牌奖章”的记载,引述的却是打击林道乾之事,与前揭瞿九思“赏赐银牌、花、彩段如礼”之记载相合。万历八年(1580)葡萄牙国王第一次向澳门派遣了王室大法官,当时王室大法官的名字叫路易·马沙度(Rui Machado)。*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Macau Imprensa Nacional,1976,p.8.前引《万历武功录》中的“佛郎机人沉马啰”或即为马沙度。
关于万历八年葡人协助明政府远赴柬埔寨剿灭林道乾海盗集团一役的结果,西文文献均显示林道乾集团是由啰鸣冲文呧奴(Bartoloméu Vaz Landeiro)等人的远征军剿灭。啰鸣冲文呧奴在其自述中曾提及此次征剿林道乾之事:
后来,一支海盗集团崛起,他们盗窃并摧毁了中国沿岸所有的港口,中国政府要求他(指啰鸣冲文呧奴)追击这个海盗并将其逐出这片海域,啰鸣冲文呧奴成功地完成了这个任务,这件事使得他为我们国王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因为他为此次远征调用了两艘他自己的船只,花费了很多经费,此举使中国政府非常满意,葡萄牙的居留地也变得平静安全。*Archivo General de Indias, PATRONATO, 53, R.2,in Lúcio de Sousa,The Early european Presence In China, Japan,The Philippines and Southeast Asia(1555-1590)——The Life of Bartolomeu Landeiro,Macao Foundation,2010, p.246.
除此之外,根据1586年西班牙王国的一份官方调查报告,当时身处澳门、马六甲及摩鹿加群岛的很多人都听说了这个事情。苏禄修教授所披露的这份调查报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事件陈述:
一个中国海上剧盗,装备有数条武装船只,在中国沿海无恶不作,摧毁了许多港口和城镇,(两广)总督对此大为苦恼,并找到了啰鸣冲文呧奴,请求他派遣自己的武装船队搜索这个海盗集团。啰鸣冲文呧奴对此非常感激,这使他有机会效忠我们陛下,同时与总督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啰鸣冲文呧奴带着他自己的两艘武装船只出发,来到了暹罗海域搜索(剿灭)这个海盗。在花费了大量的金钱以及五百多里格的航行后,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原文为“他又为陛下做了很大的贡献”)。*同上, p.250.
第二部分则为证人言论,所搜集到的证词之中,几乎众口一词地承认啰鸣冲文呧奴剿灭林道乾一役之真实性,如船长安德拉德(Francisco de Mercado de Andrade)称:“我在澳门听说了这件事。以上问题中所涵盖的大部分信息,当地居民几乎无人不晓”*同上, p.255.。同样在澳门的巴普蒂斯塔(Juan Baptista Roman)亦称:“我在澳门听说了此事,而且此事在澳门也比较出名,啰鸣冲文呧奴为中国国王所做的这一切,为澳门的葡萄牙人带来了和平”*Archivo General de Indias, PATRONATO, 53, R.2,in Lúcio de Sousa,The Early european Presence In China, Japan,The Philippines and Southeast Asia(1555-1590)——The Life of Bartolomeu Landeiro,Macao Foundation,2010, p.259.;莫拉雷斯(Rodrigo de Morales)神父称:“此事在马尼拉几乎无人不知”*同上。;布里托(Miguel Rojo de Bríto)更是称:“很多生活在澳门和摩鹿加群岛的葡萄牙人,是这一事实的亲历者。”*同上。综合以上西文材料,可以看出,当时在远东的葡萄牙人及西班牙人几乎一致认为林道乾是由啰鸣冲文呧奴所歼灭,也就是说,西文材料认为林道乾死于葡萄牙人啰鸣冲文呧奴之手。
然而,中文材料对于此事记载并不一致。据万历、天启年间担任阁臣的朱国桢所撰《皇明大事记》称:“香山澳人吴章、佛郎机人沉马啰并请自治装往击乾,许之,不果。”*(明)朱国桢:《皇明大事记》卷41,四库禁毁书丛刊影印明万历刊本,史部29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69页。知此次军事活动或未成功。瞿九思则称林道乾:“或曰犹在,或曰被戮杀已死。”*(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3,《林道乾诸良宝林凤列传》,第533页。可见林道乾是否死亡,在当时并无定论。特别是今天的北大年地区还流传着这样的传说:
明时有福建英雄名林道乾(Lim Tao Khiam)者,率大军乘舰至此,一战而占之,马来王震慑,招其入赘而传禅,道乾乃乐不思蜀矣。后其妹林姑娘(Lim Kao Niong)率众踪至,促其兄返唐山(按即中国)不听,妹因起与马来人激战,欲尽歼之,以挽回其兄志。不意屡战皆北,兵败殆尽,妹以羞怯,自缢于猴枣树。其部将五人,亦均从缢于大树殉义,士卒遂散。*(民国)许云樵:《北大年史》,南洋书局,1946年,第118页。
除了林姑娘的传说外,北大年地区还有林道乾造炮的传说*(民国)许云樵:《北大年史》,第119页。。以上内容多为民间附会之词,早在清人的著作中以辨其讹。但众多传说的出现也可看出林道乾对北大年影响之大。
葡萄牙人此次远赴柬埔寨剿寇,是葡人首次离开中国本土打击华人海盗,而且此次中国政府也对葡人义举完全表示赞同,同时还赏赐葡人“银牌花彩段”,在奖励的规格上远远超出了之前驱盗的银两褒奖*如剿灭柘林兵变之后,俞大猷曾经赠与葡人银两以示嘉奖。参见[葡]若昂·埃斯科巴尔:《关于至高至强之塞巴斯蒂昂国王派往中国的使节团的评述》,载《澳门寻根》,第125页。。为何明政府及葡人会对剿灭一个远赴海外的流寇如此重视呢?这要从中葡两方面说起。
对于中国来说,首先,广东当局不能容忍海寇与海外藩国的勾结,早在林道乾出逃之时,时任广西布政使的郭应聘就曾向殷正茂进言曰:
林道乾挟众出海,无非逃生之计。恐目前之流突闽广海澳,未必据投异域。但此党甚悍,非他寇比。为今计可防,而未可图也。门下所示,盖洞烛之矣。倘在近岛,即设法招之,亦无不可。不则果投异域,又将有勾引之患,闽广之忧方大矣。*(明)郭应聘:《郭襄靖公遗集》卷24,《又柬石汀》,续修四库全书本,1349册,第516页。
刘尧诲亦称:
林道乾雄据广潮,威行于内地十年已,一旦大兵压境,援应未周,故浮海而南,焚弃旧巢,以示无复东意,实未尝一日忘广东也。*(明)刘尧诲:《督抚疏议》卷1,《海贼突犯查参失事人员疏》,南京图书馆藏万历刻本,第11页。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流突闽广海澳”的海盗势力并不会给明朝政府带来太大的隐患,因为海盗势力毕竟有限,闽广当局即可退而招降,又可进而剿灭。但若是林道乾流突海外,与海外诸番相勾结,必然会给明政府招致隐患,“闽广之忧方大矣”。
明政府此时乐意接受澳门葡人援助的另一个原因,应当在于此时的两广总督为刘尧诲。刘尧诲原为福建巡抚,他在任期间,曾经于1575年7月18日接见过西班牙奥斯汀会士马力陈(Martin de Rada)所率领的使团,并给与了优厚的接待,同时西班牙人也给刘尧诲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西]门多萨著,何高济译:《中华大帝国史》第2部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81—237页。。除此之外,刘尧诲抚闽期间,曾联合菲律宾的西班牙共同剿灭了与林道乾同时期的粤东剧盗林凤集团,*参见汤开建《隆万之际粤东巨盗林凤事迹详考—以刘尧诲《督抚疏议》中林凤史料为中心》,载《历史研究》2012年,第6期。《明神宗实录》称:
丙申,巡抚福建佥都御史刘尧诲奏报:把总王望高等以吕宋夷兵败贼林凤于海,焚舟斩级,凤溃图遁,复斩多级,并吕宋所赍贡文方物以进,下所司。*(明)叶向高等:《明神宗实录》卷54,“万历四年九月丙申”条,第1264页。
后来出任两广总督的刘尧诲早在万历三年(1575)就与吕宋的西班牙人进行了接触,并给与优厚的接待,同时依靠西班牙人消灭了林凤集团,可见刘尧诲对于此时西方人的印象应该不错。当万历八年(1580)同为西方人澳门葡人请缨剿寇时,刘尧诲欣然接受并回报以厚礼一事自然水到渠成。
对于葡萄牙人来说,帮助明政府剿灭远遁海外的林道乾同样有着出于自身的考虑。首先,林道乾所处之“甘埔寨”及“大泥”,即今日之柬埔寨及泰国的北大年,地处葡萄牙生命线马六甲与澳门之间的马来半岛,亦是葡商东南亚贸易航线的主要对象,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海盗林道乾之存在,犹如扼住了澳门之咽喉,对来往的葡国商船带来了极大的威胁,这自然是澳门葡人所无法容忍之事。
除了维护自身的商业利益之外,葡萄牙人助明剿寇还应蕴含了以往向明朝示好这一政策的考虑。随着澳门周边走私、接济的问题日益盛行,此时明朝日益加强了对澳门防范的力度。万历六年(1578),两广总督凌云翼同福建巡抚刘思问联合提议,对闽、广下番船实施挂号给告制度,由海道副使挂号,验其丈尺,审其货物,当出海回籍后,俱照数盘验,不许夹带违禁货物。*(明)叶向高等:《明神宗实录》卷81,“万历六年十一月辛亥”条,第1724-1725页。此举意在打击沿海走私、接济等问题。另外,据(乾隆)《香山县志》记载,凌云翼在平定罗旁诸贼后,还曾派遣王绰驻兵澳门:
初,番人之入市中国也,愿输岁饷,求于近处泊船,绰乃代为申请。其后,番以贮货为名,渐结为舍宇,久之成聚落。绰以番俗骄悍,乃就其所居地中设军营一所,朝夕讲武,以控制之。自是番人受约束。绰卒,设位议事亭,番人春秋供祀事焉。*(清)暴煜:《香山县志》卷6,《人物·人物列传·武功·明》,中山文献影印乾隆十五年刻本,第785-786页。
关于此事,西文材料亦称1587 年以前,明政府“曾经派遣一位官员驻守澳门,‘承皇帝之旨,管理该城’”*[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46页。。王绰驻兵澳门,这是明朝政府第一次派兵进驻澳门,足见当时凌云翼对澳门问题的重视。明朝派兵驻扎澳门,再刺激了澳门葡人关于自身地位的考虑,为了巩固澳门这一据点,葡人不得不再次采取行动证实自己效忠明廷之心。作为当时远东葡萄牙人中的实力雄厚的一位船主,啰鸣冲文呧奴自然认识到了这一点,主动请求消灭林道乾集团以换取明廷的信任。正如他在任务完成后所说的那样:“此举使中国政府非常满意,葡萄牙的居留地也变得平静安全。”*Archivo General de Indias, PATRONATO, 53, R.2,in Lúcio de Sousa,The Early european Presence In China, Japan,The Philippines and Southeast Asia(1555-1590)——The Life of Bartolomeu Landeiro,Macao Foundation,2010, p.246.
结 语
本文分别叙述了澳门开埠初期,葡萄牙协助明廷剿灭三股海盗之始末。除了以上对三次清剿活动的史实考证之外,通过中葡双语原始文献记载的驱盗史实,我们同样可以一窥当时明朝政府与澳门葡人之关系之流变。
以上分别发生于嘉、隆、万三朝的海患,对于葡萄牙人来说,其出兵追剿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维护其自身居住地的安全及远洋贸易通道的畅通。由于澳门位于珠江口西翼,一方面是阻挡外洋船舶进入广州的一道重要的屏障,另一方面则是万商云集、财富积聚之地,因此意图进击广州的海盗团伙,往往首先攻击澳门。如柘林叛兵和曾一本集团,在他们进击广州之前,均曾劫掠澳门未果。而马六甲与澳门之间的航线,是澳门远洋贸易赖以生存的一条重要航线,远遁南洋的林道乾集团盘踞于此,同样严重地危害到了澳门的贸易利益。
葡人剿灭海盗的另一方面的考量,就在于意图获取中国政府信任,进一步稳固澳门的地位,谋求政治、经济利益。葡人东来伊始,由于中葡双方缺乏了解,中国政府往往将葡人视作与倭寇别无二致的海盗,双方相继在宁波双屿港和漳州走马溪爆发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经历以上两次事件后,葡萄牙人认为:“华人同我们和平相处的基础是牢固、可靠的,但只要我们像我们的先辈一样胡作非为起来,他们就会镇压我们,但愿上帝保佑,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葡]费尔南·门德斯·平托著,金国平译:《远游记》,澳门基金会,1999年,第701页。。而要摆脱海盗这一形象、获取中国政府的信任,最为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打击海盗势力。同时,这一系列打击海盗的行动也为葡萄牙人谋求政治、经济利益提供了方便,如葡人得以入居澳门便与打击海盗密切相关*参见汤开建:《明代澳门史论稿(上卷)》,《佛郎机助明剿灭海盗考》、《葡人驱盗入居澳门新说——以委黎多<报效始末疏>为中心》,第111-162页。。
就以上三次驱盗行动中明朝政府的应对来看,明朝政府对于葡人的态度也日益改善。嘉靖末年柘林兵变之时明朝政府对葡萄牙人尚存芥蒂,以致处处提防、监视葡军动向,而到了隆庆时围剿曾一本一役时,明朝政府已经开始主动要求葡人联合出兵。至万历剿灭林道乾集团之时,明朝政府更是对葡萄牙人远涉重洋打击海盗之义举表示赞赏,并赏赐银牌花红彩段等物。可见,明朝政府与澳门葡人的军事合作日益密切、深入。而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嘉隆时期广东地区的海防危机日益加剧,而广东政府海防力量薄弱,船政废弛,无法应对大规模巨盗。另一方面,则在于此时明代朝野士人对待澳门葡人态度的转变。自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人大规模入居澳门以来,朝野士大夫针对葡人的去留问题产生了分歧。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朝政府也日益转变了对葡萄牙人入居澳门的态度,虽然明政府治澳政策偶有反复曲折,但明中叶以来对待澳门葡人以及治澳政策总体上呈现出由分歧至趋同、从激进到冷静、自感性而客观的演进历程,对待澳门的政策基本上由清剿、驱逐葡人向容留、治理转变*参见汤开建:《明代澳门史论稿(上卷)》,《明朝野士人对澳门葡人的态度、策略及流变》,第270页。。
东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苏禄修Lúcio de Sousa为本文提供了ArchivoGeneraldeIndias的翻译资料,南京博物院的马根伟先生以及浙江大学的李庆博士为本文提供了《督抚疏议》中的材料,在此致以真挚的感谢!
作者汤开建: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
周孝雷: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博士候选人
Macao became a settlement of the Portuguese, at a time when Guangdong was suffering from rampant pirate attacks. Out of various considerations, the Portuguese settlers used to help the Ming Court to defeat pirates.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Portuguese settlers' defeat of Chinese pirates (Zhelin rebels in 1564, the rebellion of Zeng Yiben in 1568-69 and the rebellion of Lin Daoqian in 1580) during the reigns of Emperor Jiajing, Longqing and Wanli of the Ming dynasty. Based on analysis of Portuguese settlers' responses and management of these three incidents, we can conclude that the Portuguese were not just concerned about their own security, they also followed a consistent policy that sought to obtain long term residency in Macao by pleasing the Ming Court.
Macao; Portugal; Zhelin Rebels; Zeng Yiben; Lin Daoq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