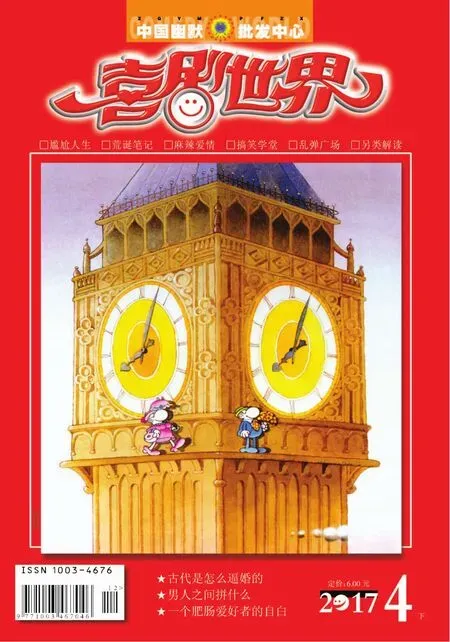一个肥肠爱好者的自白
★文/李 舒
一个肥肠爱好者的自白
★文/李 舒
肥肠爱好者自有暗号,当他们在江湖夜店里相聚,眉眼间带着笑,似乎邻座的都是旧相识,诚然吾道不孤矣。
因为肥肠,我吃过好多亏。亲戚吃饭、朋友小聚,点菜时,只要我一提“肥肠”两字,座中就有人或“啧啧”两声、或“哇哇”不迭:“啊,这种过屎的东西你也吃!”“胆固醇含量多高,不能吃点健康的吗?”“点了你吃哦,反正我们不吃!”
有人介绍相亲,据说特点是“神似吴彦祖”。临走时,我妈再三叮嘱:“淑女点!注意形象!不该说的话不说,不该吃的东西不吃!”一见面,只有几个字可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老鼠掉到米缸里!”当时心里那个小鹿怦怦跳啊,苍天啊,大地啊,这么多年,终于也让我遇到一次颜值高的相亲对象!吃的是日式料理,边吃边聊,翩翩君子侃侃而谈,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风花雪月花鸟鱼虫,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两个人聊得天昏地暗,简直觉得遇见天下第一号知己,仿佛很快就可以一起看雪看星星看月亮去了。服务员端着一份熟悉的食物经过,飘过一阵异香。我那时说到兴起,忘乎所以,一把拉住服务员说:“啊,这不是烤肥肠吗?快给我也来一份!肥肠就酒,越喝越有!”
快要沸腾的世界冷却下来,星星月亮和诗词歌赋都消失了,男神皱着眉头看我手舞足蹈吃那盘烤肥肠,花容失色,端酒的手都有些颤抖:“你怎么会爱吃肥肠啊!”
然后,便没有然后了。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也曾在暗恋的学长面前大肆宣讲,我吃过一道云南名菜“大肠套小肠”,其实就是医学上所说的“肠套叠”病症;我还殷勤拉过上司去吃全城最火的大肠面,他下午就进了医院,急性胆囊炎发作……
这世界要没有肥肠,真的实在无趣。张大千请张学良吃饭的菜单里,还不忘一道色泽金黄、外酥里嫩的“软炸扳指”,那是把肥肠蒸熟切段、入油炸成;三年自然灾害,傅抱石率团到成都公派写生,被招待吃肥肠粉,饿了很久的画家们一拥而上,一碗接一碗,怎么也不肯放手;在西安肥肠的别称葫芦头,朋友告诉我一句贾平凹的评语:“生了痔疮的葫芦头最有味,最耐咀嚼。”
幸亏有这些前辈们,肥肠爱好者顿时觉得:“吾道不孤矣!”
肥肠的做法,最家常是卤。怕麻烦的,就在小区菜场的熟食店里买,拿回家用大蒜叶或青椒丝炒了,便是一道宜饭宜酒的好菜。父亲不喜欢买现成的,嫌弃处理不干净,总买生肠回家。做肥肠,关隘不在做法,而在收拾。收拾得太干净,肥肠便徒剩薄薄的肠壁,甚至有时候会有些发苦;收拾不干净,留着脏气,更难下口。父亲的绝招,是先用盐搓揉一遍,冲洗之后,将肥肠翻转,用面粉再冲洗,这个步骤要重复两遍。处理好的肥肠,内壁尚留着油花,卤水汁最好用些老卤,不行就拿花椒老姜八角茴香干辣椒草果和酱油配,虽然会少一点醇厚。做好切上来,灰褐与雪白,层次分明,暗香涌动,吃一口,烂糯而厚腴,无上美味。关于处理肥肠,唐鲁孙曾经写文揭发,说广州饭馆把猪大肠最粗的肠头切下来,用粗绳一道一道地勒出横纹,放卤水里泡三天,拿出来浓油赤酱红烧,一点吃不出大肠味——当然,饭馆也没打算把这菜当猪大肠卖,这玩意儿对外叫“红烧象鼻”。
肥肠爱好者的乐园,绝对是在成都。从一碗冒节子肥肠粉开始的早晨,有粉蒸肥肠和豆花肥肠陪伴的中午,到了晚上,还可以趁着月黑风高,去吃最重口味的脑花肥肠。最喜欢去一家公然以肥肠为招牌的苍蝇馆子,里面20多种肥肠的做法,肥肠爱好者在这里相聚,眉眼间带着笑,似乎邻座的都是旧相识,那一刻,只想感慨:
肥肠虐我千百遍,我待肥肠如初恋。
(摘自《悦食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