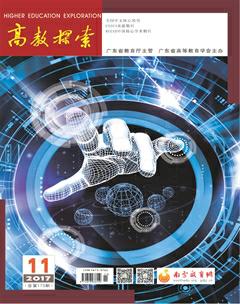大学知识治理的现实审视与理性实践
黄文武++徐红++戴雨婷

收稿日期:2017-07-19
作者简介:黄文武,长江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徐红,长江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戴雨婷,长江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湖北荆州/434023)
*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重点项目“社会转型背景下高校教师角色适应研究”(14D317)的成果之一。
摘要:知识生产模式经历着从模式1到模式2再到模式3的转型过程,知识的分立性、异质性特征及知识势差的存在促使大学进行知识治理,将自身知识活动与政府、企业、市场等知识生产主体的知识活动联合起来,实现知识共享与整合。大学知识治理包括“对知识进行治理”和“用知识进行治理”两个方面。通过交互创新平台的建构、运行与保障机制的建立及共治文化的营造实现大学知识创新发展。
关键词:知识生产模式;知识治理;知识分立性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生产模式经历着从模式1到模式2再到模式3的转型过程,大学不再是知识生产的单一主体,政府、市场及企业、公众及公民社会都成为知识生产相关主体,形成“大学-政府-市场及企业-公众及公民社会”的“四重螺旋”知识生产创新系统。大学必须通过知识治理有效联合各主体间的知识活动,通过外部知识的获取及内部知识的整合实现知识创新发展。
一、知识生产模式由模式1到模式3 的转型
(一)从模式1到模式2
自洪堡以“學术自由、教学与研究统一”思想创办柏林大学以来,科学研究被纳入大学体系,大学形成教育与科研相结合的功能。以大学为中心的知识生产表现为一种自容性活动,大学教学和科研共同为追求永恒真理而服务。学界一般将这种“第一次学术革命”下的知识生产模式称之为“洪堡模式”或“模式1”,模式1下的知识生产方式强调“为知识而知识”的理念,知识生产遵循严格的组织规则和学科范式。大学是唯一的知识生产者,并与市场、企业等社会部门划分出一条明显的分界线。
随着知识社会的发展,知识生产从大学蔓延出来并越过组织边界,打破了“以大学为中心”的藩篱。传统的以理论为尊、学科内部驱动、以大学为核心的知识生产模式即模式1正在被新的知识生产模式2所取代。[1]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价值与作用愈发凸显,知识生产成为由大学、政府、企业等多种因素、多元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政府、市场、企业对大学科研成果转移和商业化抱有强烈的需求,各主体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对大学知识生产的引导和干预。同时,政府和企业为了充分掌握知识的实用价值纷纷设立研究所、实验室进行知识生产,这就进一步打破大学知识生产的垄断性,迫使大学走出象牙塔并围绕知识生产与政府、企业开展广泛的交流与合作。知识生产从模式1到模式2转变意味着,在学术情境中进行的以认知为目标、由兴趣驱动的知识生产转向在应用情境中进行的由任务驱动的知识生产;从知识生产参与者单纯性转向生产主体异质性与组织多样性;大学知识活动的价值评价由同行评价转向质量控制标准多样化,并且知识质量的监控由系列的标准决定,这个系列标准反映了知识生产过程扩大了的社会构成。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表明大学或许不可能在知识生产过程中遗世独立,而应积极与各知识生产主体展开广泛合作促进知识共享与整合。模式1下的知识生产呈现出“大学基础研究-相关组织应用研究-政府、企业接纳与运用”单向线性创新模式,大学处于知识生产的上游;在模式2中,大学、政府、企业之间由“三元分立”转变为非线性的链环结构,知识生产横向联合趋势更加明显。
·教育管理·大学知识治理的现实审视与理性实践
(二)从模式2到模式3
在模式2中,各知识生产主体的立场不同,所追求和专注的知识领域也必然有所不同,大学注重高深理论知识的探寻,而政府、市场及企业更注重知识的实用性,致力于发展技能性知识和应用性知识。知识主体间知识存量的差异导致了主体间的知识差距,也就阻碍了知识的进一步发展,这客观上要求加强各主体间知识交流与融合。同时,模式2着重大学、市场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却忽视了公民社会实体(公众)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公众和公民社会是知识生产的用户群体,与知识生产及运用具有高度的相关性,理应成为知识活动行为主体。
华盛顿大学教授伊莱亚斯·卡拉扬尼斯(Elias G.Carayannis)与坎贝尔(David F.J.Campbell)首次提出并系统论述了“知识生产模式3”及其应用性情境,模式3是对模式1和模式2的逻辑拓展,是“分形创新生态系统”的内核。“分形创新生态系统”主要是指具有多形态(Multi-modal)、多层次 (Multi-level)、多节点(multi-nodal)、多主体(multi-agent)等特质的创新生态网络。[2]模式3的核心要素是“创新网络”和“知识集群”,“强调大学、产业、政府、公众及公民社会之间分形协同创新,并以竞合(co-opeting)、共同专属化(co-specializing)和共同演进(co-evolving)的逻辑机理驱动知识生产资源生成、分配和应用过程,最终实现知识创新资源优化整合”[3],如图1所示。
模式2以“大学-政府-市场/企业”的“三重螺旋”创新系统为适应性情景,而模式3则在“三重螺旋”创新系统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知识生产的边界,将公众及公民社会纳入知识创新系统演变为“四重螺旋”创新系统,从模式1到模式3揭示了大学知识生产的动力多元化,大学、政府、企业及公民社会共同组成知识生产的动力场,从以大学为载体学科分布式知识生产到社会分布式知识生产,预示着大学知识活动必须在与各知识主体的有效联动中实现知识创造。
二、知识生产模式转型框架下大学知识治理的内涵及其必要性分析
(一)大学知识治理的内涵阐释
知识治理的概念最早由格兰多里(Grandori)提出,他认为知识治理是对组织内或组织间知识的交换、转移、共享等知识活动在内的治理,即知识治理就是对组织相关知识活动过程的治理。[4]随后知识治理这一理念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但在其早期发展中知识治理并未被视为一个特定的理论范畴,关于知识治理的具体内容及手段还只是一般组织活动的简单迁移。后继学者对知识治理内容进行了拓展延伸,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伯斯坦(Burstein)将知识治理与知识管理战略结合起来考虑,认为知识治理侧重于合理分配资源及决策权,以审查、规制、监督和修正知识管理过程,进而促进知识管理战略有效实施。[5]福斯(Foss)从知识生产活动与组织实践关系的角度指出,知识治理是治理知识的过程,即选择治理结构(如市场、混合形式或层级制)以及治理和协调机制(如协议、指令、奖励计划、信任机制、组织文化等),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组织结构或机制的安排以最优地选择、创造、共享和利用知识。[6]他还明确提出知识治理的三个问题:一是动机与知识过程,鉴于动机的复杂性,不同类型的激励对知识共享、整合与创造的影响;二是配置何种的知识治理机制最能促进组织间及组织内的知识共享、整合与创造;三是考虑知识活动中的风险,如何配置治理机制以规避这些风险。[7]endprint
大学作为学术组织的一系列活动都是围绕知识及其生产展开的,在知识生产模式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作为知识集合体的大学不再是知识生产的唯一主体。大学外部组织如政府、市场、企业等广泛从事知识生产活动并积极介入大学内部知识活动。大学应努力在知识生产“大学-政府-市场/企业-公众/公民社会”四重螺旋创新系统中取得主动权,而知识在量上的增长和质上的创造需要通过对知识主体行为的协调强化组织内外知识及行动的相容性和互动性,消除知识在各知识生产主体之间转移、使用、整合等方面可能引发的矛盾。
大学知识治理是指大学由协同参与情境的创设,将政府、市场、企业及公众等知识主体纳入自身知识活动中,通过各种协调保障机制的设立,使各主体在遵循“和而不同”的沟通原则下保持知识差异的同时相互协作与联合,从而弥补大学自身知识及经验的“缺口”,促进内外部知识资源的有效整合与共享,使大学形成知识获取、累加、创造利用的螺旋上升形态。具体而言大学知识治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知识进行治理”,即通过组织结构、激励制度、决策权配置、沟通、信任、文化等正式和非正式机制安排影响大学知识获取、知识整合、知识内化、知识创造等活动。一方面大学在外部知识的获取与整合中快速了解知识发展的最新动态及知识应用领域的需求变化和前景规划;另一方面大学通过对各类知识的内化增强自身知识吸收能力,实现知识的持续积累和创造。二是“用知识进行治理”,即有意识地利用知识来解决组织问题的治理形式。[8]理性的知识确保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协调政策的协商以及对复杂问题的解决做出长效决断,促成大学高效的知识行动。
(二)大学知识治理的必要性分析
1.知识的分立性。以哈耶克为代表的经验理性主义强调任何单一的组织都没有能力把深嵌于社会秩序中的所有信息和数据收集起来,并把它们组合成一个知识整体,知识总是分立于不同组织之中。在知识的分立当中,包含一个基本的内在规律:一方面,不投入到特定的局部里去的组织是无法获取任何知识的;另一方面,投入到特定局部里的组织不得不依赖于其他组织(在其他局部里)的“经验”。[9]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突出了知识分立性特征,知识分散掌握在各组织之中,不可能由某一个人或某一权威组织全盘集中。这就指明大学独自进行知识活动时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和“无知”,大学知识积累和创造在于追求其目标时能够使用较其自身所拥有的更多的知识,大学能够从其自身并不拥有的知识中获益并超越其无知的限度。[10]
2.知识的异质性。在知识领域“分类”的认知方式及大学依据知识进行的专业划分都是知识异质性的表现形式。知识异质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知识主体异质性,大学、政府、企业等构成了知识活动的多元主体。在知识活动认知价值观念上,大学推崇对高深理论知识的探求,致力于科研学术水平的提高,而政府、市场及企业的多数知识活动着眼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大力发展实用性知识。多组织跨边界知识合作由于缺乏共同理解和共享认知,使得知识的协调利用较为困难[11],这大大增加了整个社会知识活动的成本。二是知识本身异质性,各知识活动主体由于不同的价值理念和活动目的,所关注的知识领域是不同的,使得各主体掌握的知识存在异质性。并且各主体对知识的关注及研究力度的不同使得各自所掌握的知识在程度上也表现出异质性。异质性知识的有效整合为大学知识创造带来无限的可能性,设计并建立一个良好的协同机制实现异质性知识的交互创造成为大学知识治理的关键。
3.知识势差的存在。知识活动领域和发展方向不同决定了各主體积累的知识存量各异,也表征着组织间知识需求的差异,知识活动的非均衡性必然使得不同主体间产生知识势差。知识存量势差表现在知识的数量和知识的质量上,知识的数量指知识的多元性,即组织掌握知识的广度;知识的质量指主体在某一方面的知识专注程度,即知识的深度。知识存量的广度和深度的差异直接导致各组织间的知识距离,从静态方面理解,由于知识网络中某一组织的知识不足而导致知识活动多重螺旋创新系统整体创新效益显著降低,造成“木桶效应”[12],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知识生产和创新水平。从动态方面看,这种势差是各组织间知识转移与整合的动力,引发主体间的交互作用,形成持续的互补关系,促进大学与各知识生产主体异质性知识的耦合。知识势差也表现为各主体间知识需求势差的存在,各相关主体由于立场不同,对知识价值的看法及知识生产活动的期待就不同,从而导致需求势差的形成。大学专注于理论知识的探索,提升人类精神境界;企业、市场则更多追求知识的实效和利益;公众的知识需求更为复杂,或是为提升知识素养以丰富精神世界,或是通过知识的掌握提高自身行动能力以改善生活。知识势差的存在必然影响大学知识活动,大学必须有效回应这种知识势差以应对环境的变化,增强自身知识生产能力。
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下的大学知识治理理性实践
(一)通过知识治理交互创新平台的建构促进知识共享
在知识社会,知识生产主体的多样化形成多渠道的知识流,加上知识本身的分立性和异质性,使得组织之间联合行动能力不强,阻碍了知识的创新发展,这就需要大学建构容纳政府、市场、企业等多元主体的知识治理交互创新平台。在知识组织之间的战略层面,大学应建构知识共享与整合的物理平台、虚拟平台及心理平台。物理平台是组织间知识融合的空间分布场地,比如联合建立创新实验中心、创新实训中心等,在这一空间中大学与各知识生产主体共同规划知识活动并联合进行知识生产。虚拟平台是指根据知识情境建立支持分立性知识源进行知识处理和协调的信息系统平台[13],有效的信息交流和沟通程序能够促进各主体间知识行动的协调,克服彼此之间的组织距离。心理平台可以帮助大学塑造“众推共传”的知识共享文化,营造知识交互创造“自利的利他主义”氛围,并营造各主体间都适用的知识分享惯例以公平配置知识活动权益,心理平台建设对于维护知识联合网络的稳定意义重大。大学知识治理交互创新平台的建设有利于改善大学内外部组织之间的社会关系以更好的适应知识生产环境,形成大学与外部组织之间的“强联系”,促进以大学为主的知识密集度增加。在这一平台中,大学坚守着“象牙塔”的传统,又肩负起“服务站”的责任;坚持以学术知识生产与创新为导向的探究式、突破式创新,又兼顾外部组织知识需求的渐进式、利用式创新。endprint
(二)经由知识治理运行与保障机制的建立维护知识网络运行
大学只有建立健全各种知识治理运行与保障机制才能实现与政府、市场、企业及公众团体之间知识活动的良性互动,推动知识创新系统持续发展。运行机制为知识治理视域下的大学与外部组织间知识共享、整合的实施提供支持和引导;保障机制是为保障知识治理视域下的大学与外部组织间知识共享、整合的顺利实施而采用的方式方法。[14]大学知识治理运行机制包括激励机制和协调机制,保障机制包括学习机制和评价机制。激励机制的建立在于明确知识创新成果及其效益的分配原则,大学按知识生产贡献大小对各组织或个人知识共享行为进行物质或精神激励。协调机制可分为任务间协调机制和任务内协调机制,任务间协调机制针对某一任务可分解为多个具体任务并在不同组织间分别进行,大学应建立对不同组织专业知识准确把握的知识交互记忆系统,定位各组织专长领域的位置,建立知识目录实现对知识活动的有效分工[15],提高问题解决和知识创造的效率。面对不可分解的复杂性任务则应对任务进行整体协调,大学将各组织人员、环境、设备等有效组织起来,形成正式化的知识活动流程,制定共享的行动进程计划,使得各组织及个人的行动彼此融合。学习机制是为促进大学与各组织间经常的学习互动,提升组织知识吸收能力,有利于知识在各组织间的流动与融合。大学应积极实行开放式办学,帮助各组织培训组织成员,或是将其纳入自身知识活动。同时大学人员广泛参加外部组织的知识生产活动,丰富彼此的交流。评价机制的建立在于规避知识活动过程中的机会主义倾向和利益分配道德风险。大学通过组织各种评价,对知识联合行动的及时反馈,避免不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消耗,规范知识活动。
(三)依托共治文化的营造实现大学知识创新
知识生产模式变革下的大学在知识生产中能否占据制高点,引领社会发展,关键在于大学是否具有或生产有价值的、稀缺性的、不可替代性的知识资源。大学是学者最为集中的地方,学者是大学知识活动最重要的人力资本,大学人力资源优势的挥发程度决定着大学能否实现知识创新最优化。一方面,在“对知识进行治理”上,只有学者最了解学者自身活动,最了解知识活动规律,并且人力资本与载体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率取决于个人意愿及努力程度。大学教师不仅是学术权力的载体,也是公民权力的行使主体,而不只是大学知识生产的工具。大学教师应在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及公民权力的协调互动中推动大学知识治理。另一方面,在“用知识进行治理”上,教师不仅掌握着专业理性知识,更具备丰富的情境性知识。每个大学教师都是所处特定时空情形下的在场者,这种在场体验是一种极其珍贵的知识。只有通过将决策权赋予在场者,使无以计数的分散的行动者将零散化、情境化的知识协调起来,才能构成整个复杂的大学组织系统得以运行的知识基础。[16]大学应努力营造支持开放和参与式的组织文化,注重知识活动权力的重新配置,搭建代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教师群体与代表行政权力的行政人员群体之间的协商、咨询、共同决策平台,并通过各种激励措施激发教师参与大学知识治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此外,学生也是大学知识活动的另一参与群体,是知识的受用者,作为社会成员,学生的公民民主权力应得到充分尊重。大学知识活动应本着对学生负责的理念,各项知识活动计划和政策的制定倾听学生的意见,将学生纳入知识活动之中,最终形成行政人员、教师、学生共同参与大学知识治理的局面。
參考文献:
[1]Gibbons M.Limoges, C., Nowotony, H.,Schwartzman,S.,Scott,P.and Trow,M.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M].Sage,London:1994.18.
[2]Carayannis E.G.,D.F.J.Campbell.Open Innovation Diplomacy and A 21st Century Fractal Research,Education and Innovation (FREIE) Ecosystem:Building on the Quadruple and Quintuple Helix Innovation Concepts and the“Mode 3”Knowledge Production System[J].Journal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2011,2(3):327-372.
[3]Carayannis E.G.,D.F.J.Campbell.Mode 3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Quadruple Helix Innovation Systems:Twenty-first-century Democracy,Innovation,and Entrepreneurship for Development[M].Springer New York,2012:29.
[4]Anna Grandori.Neither Hierarchy nor Identity Knowledge-Governance Mechanisms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J].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2001(5):381-399.
[5]Zyngier S,Burstein F,Mc Kay J.The Role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Governanc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Strategy[R].IEEE:Proceedings of the 39th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 Sciences,2006:104-115.endprint
[6]Nicolai J Foss,Joseph T Mahony.Exploring knowledge governance[J].Center For Strategic Management and Globalization,SMG Working Paper,2010 (04).
[7]Foss N J.The Emerging Knowledge Governance Approach:Challenges and Characteristics[J].Organization,2007,14(1):29-52.
[8]Van Buuren,Arwin,and Jasper Eshuis.Knowledge Governance:Complementing Hierarchies,Networks and Markets?[M].In Knowledge Democracy:Consequences for Science,Politics and Media.2010.
[9]汪丁丁.走向边缘:经济学家的人文意识[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124.
[10][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M].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19.
[11]M L Mors.Innovation in A Global Consulting Firm:When the Problem is too Much Diversity[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0(31) :841-872.
[12]廖志江,高敏,廉立軍.基于知识势差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知识流动研究[J].图书馆学研究,2013(1):79.
[13]黄昱方,范芸.基于情境管理的创新网络跨边界知识治理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3(19):148.
[14]姚伟,刘建准.竞争情报协同的运行和保障机制——基于知识治理的视域[J].情报杂志,2014(1):16.
[15]詹一虹,熊峰,丁冬.交互记忆系统理论在虚拟团队中的应用研究[J].管理世界,2011 (4):180-181.
[16]庞正,李丹.哈耶克法治思想背后的知识观探析[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4(2):68.
(责任编辑赖佳)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