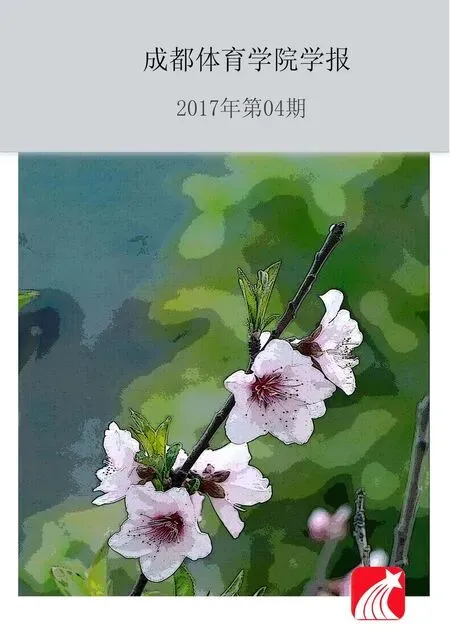也谈体育赛事转播权法律性质界定的二分法
——与冯春博士商榷
欧阳爱辉
也谈体育赛事转播权法律性质界定的二分法
——与冯春博士商榷
欧阳爱辉
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法律性质界定一直存在较大争议。从多元复合化属性下的权利动态流转视角思考该问题具备一定新颖性,但也有着相应缺陷,且对界定体育赛事转播权法律性质的传统二分法存在误读。较之当前国内外其他主流观点,传统二分法仍更具合理性。针对传统二分法的局限,对它做了有限度修正。在直播权意义上转播权属于赛场准入权,在字面意义上转播权属于广播组织权。
体育赛事转播权;二分法;无形财产权;广播组织权;赛场准入权
体育赛事转播权即体育组织或比赛主办单位等举办体育赛事时,转让或准允他人通过电视、互联网等各类媒体利用体育赛事资源来获取利益的一项权益。随着体育产业在现代社会的蓬勃兴起,体育赛事转播权之重要价值也愈发凸显。不过体育赛事转播权在法律性质上究竟该界定成何种权利,长期以来我国学界一直是众说纷纭尚无定论。《法学论坛》2016年第4期登载了广西大学冯春博士撰写的论文《体育赛事转播权二分法之反思》(以下简称“冯文”),全文非常详细的论证了当下我国学界在体育赛事转播权法律属性上的各种争论,尤其是对已获国内学界一定程度认可的体育赛事转播权二分法(以下简称“传统二分法”,即将体育赛事转播权分成直播权意义上的转播权和字面意义上的转播权,前者系主办方让渡给转播机构产生的无形财产权,后者系其他转播机构向获得直播权的转播机构购买直播体育赛事节目产生的和著作权相关的邻接权)进行了详尽分析*体育赛事转播权二分法最早系蒋新苗、熊任翔二位学者提出,随后得到了不少国内学者的认同。具体可分别参见蒋新苗、熊任翔:《体育比赛电视转播权与知识产权划界初探》,载《体育学刊》2006年第1期;或乔泽波:《2010年广州亚运会赛事转播权的法律性质分析》,载《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张玉超:《体育赛事转播权法律性质及权利归属》,载《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11期。。该文指出,体育赛事转播权并非一成不变,应从权利转换角度思考其性质。在主办方手中属于无形财产权,通过转让合同等让渡给转播机构后则具备了知识产权特性。冯春博士由权利流转的动态新视角去剖析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法律性质,无疑为我们能更全面认识体育赛事转播权多元化属性进而实施相关侵权行为法律规制大有裨益,但其论证思路仍存值得商榷之处。故笔者特借此机会就体育赛事转播权法律性质界定的二分法阐述一些自己的不成熟观点,以求教方家。
1 冯文基本观点概述
长期以来,由于体育赛事转播既带有播放广播电视节目的组织色彩,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又具备着服务合同特性,兼之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很大程度展现出表演者表演意味,体育赛事转播权自身便凸显了一种多元复合化属性。而正是这类交错重合的多元复合化属性,方才令国内学界在其法律性质界定上人言人殊。“……法律是调和、协调、这些彼此交叉和冲突的利益的努力。[1]”同样,冯文对体育赛事转播权法律性质界定以及就传统二分法提出反思也是建立于多元复合化属性思辨上完成的。
1.1 冯文的法律性质界定视角:多元复合化属性下的权利动态流转
从广义上说,冯文对体育赛事转播权法律性质界定依旧属于一种二分法,即一部分为无形财产权,另一部分为知识产权。不过冯文界定基础不同于传统二分法,在这一点上实可谓传统二分法的批判性重建。冯文基于权利动态流转的角度认为,多元复合化的体育赛事转播权法律性质不是一成不变的。当转播权在体育组织或比赛主办单位手中没有通过转让合同等方式让渡给电视、互联网等各类媒体转播机构时,它是静态的,表现为无形财产权;当其通过转让合同等方式让渡给电视、互联网等各类媒体转播机构时,它被动态化的转让出去了,表现为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45条确认的广播组织权从而具备着知识产权特质。
在冯文看来,这种权利动态流转视角进行的多元复合化体育赛事转播权法律性质界定非常具备实际意义,它能很好的就各类相关侵权行为加以认定与规制。譬如冯文以2015年哈尔滨腾翼队和贵州智诚队之间进行的一场中国足球甲级联赛比赛为例,因贵州智诚队主场无电视直播信号,视频网站PPTV便为哈尔滨球迷提供了网络直播技术帮助哈尔滨球迷得以顺利在互联网上观看到了本场比赛。由于中国足球甲级联赛主办方系中国足协,哈尔滨球迷和视频网站PPTV未征得中国足协准许擅自转播比赛就构成了对足协无形财产权的侵害;至于体育赛事转播权通过转让合同等方式让渡给电视、互联网等各类媒体转播机构后,转播机构依靠节目制作和信号传输获得了作为邻接权的广播组织权。若社交网站私自播放转播机构制作的赛事节目,就构成了对转播机构广播组织权之损害;若某些大型体育赛事中的主办方将某地区的转播权授予某电视台独家所有,某本地区社交网站或其他电视台盗播了其他地区转播机构的赛事节目,就同时构成了对主办方无形财产权和本地区独家转播的电视台广播组织权之侵害[2]。
1.2 冯文批判针对的目标:多元复合化属性下传统二分法之缺陷
冯文指出,基于体育赛事转播权的多元复合化属性,其法律性质界定的传统二分法尽管有效避免了单纯知识产权或财产权属性说易出现之逻辑错误,但依旧存在新问题:第一,传统二分法将“转播”划分成了“现场直播”和“转播”,这不符合国人日常语境中对“转播”的认定。即便是体育赛事转播权研究极其发达的欧洲国家,也没有任何一个学术流派和国家立法为了能够解释体育赛事转播权多元复合化属性而强行割裂概念的;第二,传统二分法对“直播权意义上的电视转播权”究竟归谁所有,未给出明确答复。因为传统二分法既认为该权利归体育赛事主办方所有,又认为电视台等转播机构可以向主办方购买此项权利。那买到手之后,按逻辑推导是否也应属于“直播权意义上的电视转播权”(无形财产权)呢?若属于,那为何又要将其列入“字面意义(转播权意义)上的电视转播权”(和著作权相关的邻接权)呢?这会导致转播机构权益无法辨识;第三,传统二分法对体育赛事转播权与播放者权的划分过于绝对化。因为当电视台等转播机构购买体育赛事主办方的转播权后应当就享有了相应播放者权,体育赛事转播权和播放者权会合二为一,可传统二分法却认为此时此刻体育赛事转播权与播放者权并不存在重合;最后,一些支持传统二分法的学者因考虑到体育赛事转播权基本不涉及到和体育赛事主办方的交易,研究价值不大,这样一来便很可能导致二分的体育赛事转播权又退回到了单纯无形财产权之一元论调[2]。
2 对冯文基本观点的质疑
毋庸置疑,冯文站在权利动态流转视角下,对体育赛事转播权法律性质的划分显然给我们开展相关研究和司法实务工作提供了新思路,也一定程度修正了现有理论不完善之处,帮助我们看到体育赛事转播权产生过程内的静态和动态变化。不过,任何一种理论观点都难免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依笔者拙见,冯文对体育赛事转播权法律性质界定以及就传统二分法提出的反思亦有若干难以自圆其说和误读之处,或许这还待日后加以改进。
2.1 冯文对体育赛事转播权法律性质的界定有待进一步完善
从前述可知,冯文对体育赛事转播权法律性质界定系基于多元复合化属性下的权利动态流转角度,在广义上可谓传统二分法的一种修正。当转播权在体育组织或比赛主办单位手中没有通过转让合同等方式转让给转播机构时,它是静态的属无形财产权;当通过转让合同等方式让渡给转播机构时,因被动态化转让出去了属于邻接权中的广播组织权。不过笔者认为,这种权利动态流转视角下的二分法修正,仍然未能较圆满诠释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法律性质。
首先,冯文认为当转播权在体育组织或比赛主办单位手中没有通过转让合同等方式让渡给转播机构时,它是静态的属无形财产权。但无形财产含义非常广泛,知识产权、债权等等也可能构成无形财产权。这样一来,动态层面的体育赛事转播权作为邻接权中的广播组织权同样可纳入无形财产权范畴。静态和动态层面的权益岂不失去了轮廓鲜明的界限?况且,无形财产权形成的关键是无形财产本身要具备市场价值,若根本没有价值或者非常低,那自然谈不上无形财产带来的权益。例如风靡全球的美国NBA职业篮球赛,激烈对抗程度、高感官刺激和明星效应无疑导致其市场价值巨大,但迄今仍处培育期一些鲜有人问津的赛事(如中超预备队联赛、个别少数民族体育项目等)市场价值极低,又焉能在当下构成无形财产权?冯文自己也指出,“在它没有销售和转让之前,它没有任何价值。[2]”此时此刻,电视台、社交网站等转播机构进行这些鲜有人问津的比赛转播,往往系出自推动青少年体育事业发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社会公共利益需要,社会公共利益固然广义上也算作赛事主办方希望获取的“利益”,但显然不能将它们笼统视为无形财产权。
其次,冯文认为当通过转让合同等方式让渡给转播机构时,因被动态化转让出去了,体育赛事转播权便属于邻接权中的广播组织权。主办方转让体育赛事的原始转播权,的确可谓一动态过程,在理论分析上显然是有意义的。不过就实际操作来说,作用不大。毕竟直播权意义上的体育赛事转播系赛事主办方转让或准允某转播机构(电视台、社交网站等)将现场体育比赛场景通过设备制作成节目传输出去,字面意义的体育赛事转播系其他转播机构将获得直播权的转播机构制作好的体育比赛节目二次传播给广大受众。侵犯体育赛事转播权实质上往往大多发生于字面意义转播环节,由于传统二分法也将字面意义转播权视作邻接权中的广播组织权,那么司法实践操作中它和冯文权利流转动态划分就无太多差别,实际意义不大。
2.2 冯文对传统二分法的批判存有一定程度误读
冯文对传统二分法的批判给我们日后不断完善体育赛事转播权法律性质相关理论给予了很大启发。但不得不指出,冯文某些批判还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首先,冯文认为传统二分法将“转播”划分成了“现场直播”和“转播”不符合国人日常语境中对“转播”的认定,在相关研究居领先地位的欧洲国家也没有类似提法。诚然,根据汉语语境的通常解释,“转播”一般被认为是“(广播电台、电视台)播送别的电台或电视台的节目”[3]。但我们应看到,体育赛事转播权毕竟乃一个外来词。“转播”的英文表述“broadcast”指的是“广泛传播”,它既包括现场直播“live transmission”,也囊括着播送他人节目“retransmission”。所以从转播的本源意义来说,它无疑覆盖了“现场直播”和“转播”(即播送他人节目)两种类别。我们决不能简单以其不符合国人日常语境对“转播”的认定而抹杀了将二者区分的作用。至于体育赛事转播权研究在世界居领先地位的欧洲国家也无类似提法,这一定程度是各国语言表述不同所致(如中文“转播”和英文“broadcast”之巨大差异),况且我国和欧洲国家长期都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伦理道德范式及法律规定,草草以欧洲国家为依据不免略欠周详。
第二,冯文认为因传统二分法既主张转播权归体育赛事主办方所有,又主张电视台等转播机构可以向主办方购买此项权利,购买之后从逻辑上推导,转播机构也有可能获得了“直播权意义上的电视转播权”(无形财产权)。但它若获得了“直播权意义上的电视转播权”,传统二分法再将其列入“字面意义(转播权意义)上的电视转播权”便会令转播机构相关权益究竟是什么难以辨识。笔者认为,这纯属冯文的误读。尽管电视台等转播机构可以向主办方购买体育赛事转播权,主办方享有的是“直播权意义上的电视转播权”,但能够购买获得“直播权意义上的电视转播权”的仅是最初将现场体育比赛场景通过设备制作成节目传输出去之转播机构。“字面意义(转播权意义)上的电视转播权”是其他转播机构通过向获得直播权的转播机构购买直播体育赛事节目传输出去而取得的。它们虽然同为体育赛事转播机构,但前者系向体育赛事主办方获取转播权,即最初转播机构;后者系向最初转播机构获取转播权,彼此泾渭分明。所以,这种划分并不会造成转播机构相关权益难以辨识。
第三,冯文认为传统二分法对体育赛事转播权与播放者权的划分过于绝对化,当转播机构购买体育赛事主办方的转播权后应当就享有了相应播放者权,体育赛事转播权和播放者权会合二为一。笔者认为,这也是冯文的一种误读。因为播放者权多指广播电视部门对其编制的广播电视节目依法享有的许可或者禁止他人进行营利性转播、录制和复制的权利。尽管转播机构购买体育赛事主办方的转播权后就拥有了相应播放者权,由于字面意义(转播权意义)上的转播权和播放者权此刻享有的主体均是电视台等转播机构导致主体相同发生重合,可上述两种权利针对的客体终究存在差别——字面意义(转播权意义)上的转播权客体系体育赛事,播放者权客体系将体育比赛通过设备录制好的体育节目(含剪辑、回放、特写、解说、制作集锦等等)。类似于刑法学中的想象竞合犯概念,虽然此刻两类权利主体相同,但客体毕竟不一致,若发生了侵权行为自然同时损害了两项权利,只不过责任追究按照一个侵权责任处理罢了。“法律推理是一个集合性标签,它表征许多产生法律决定的智力过程。[4]”所以,体育赛事转播权和播放者权此刻仅是侵权责任追究的实务操作中发生了混同,但权利性质依旧差别迥异未造成本质的重合。
最后,冯文还担心因体育赛事转播权基本不涉及到和体育赛事主办方的交易,研究价值不大,就很可能导致二分的体育赛事转播权又退回到了单纯无形财产权之一元论调。笔者认为这种担心不免多余,即便体育赛事转播权关键在于通过电视台、社交网站等转播机构令无形财产经济权益得以实现,但前提条件毕竟是体育赛事主办方作为神经中枢转让或准允转播机构利用赛事资源,没有它无形财产经济权益的实现就俨然成了镜花水月。更何况某些体育赛事转播还具备着浓厚社会公共利益色彩。所以纵观当下国内学界各类著述,尽管迄今体育赛事转播权法律性质界定尚无统一定论,但支持传统二分法的大多数学者都没有简单将二分的转播权退回到单纯无形财产权一元论上去。
3 余论:对传统二分法的有限度修正
根据前述对冯文观点的分析,不难发现冯文观点具备一定创新性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判断体育赛事转播权法律性质,可自身也存不少缺陷,对传统二分法之批评亦有诸多误解。其实传统二分法虽有个别难自圆其说之处,但相较国内外其他主流观点,反而能更科学完整地看到体育赛事转播权多元复合化属性。
目前在国内,除二分法外对于体育赛事转播权法律性质界定大体上有如下几种观点。其一是契约权利说,即认为体育赛事转播权缺乏现行法律的明文规定,主要是一种依照协议或章程形成的合同权利[5];其二是商品化权说,即认为该权利是本身不具备商品属性的体育赛事因蕴含的某种抽象物被转移到商业领域继续创造需求而形成的权利[6];其三是物权说,即认为体育赛事转播权是体育赛事这一服务产品形成的所有者收益权[7];其四是无形财产权说,即认为体育赛事转播权属于财产权中的无形资产[2];其五是著作权说,即认为体育赛事和电影一样均符合著作权法中的作品界定,其转播权理当构成著作权[8];其六是邻接权说,它又包括两种意见。前者主张体育赛事虽非作品,但体育赛事转播权系运动员等体育工作者劳动成果表现形式,构成邻接权中的表演者权[9]。后者也主张体育赛事不是作品,但体育赛事转播权系制作、转播体育赛事的相关机构享有之权利,构成了邻接权中的广播组织权[10]。至于在国外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对于体育赛事转播权法律性质界定则主要有三类不同观点。其一是企业权利说,即体育赛事转播权乃组织者和参与者作为“企业”享有的财产权益;其二是赛场准入权说,即体育赛事转播权乃允许他人进入比赛场地之权益;其三是娱乐服务提供说,即体育赛事转播权乃转播机构像观众观看比赛获得娱乐需付费一样产生的权益[11]。
就上述国内外主流观点而言,应该说都从某些视角看到了体育赛事转播权之特性,但均有自身不足。譬如按照契约权利说笼统认定为契约合同权利,表面看貌似很圆满,但由于民事法律关系最广义层面都可以视作契约或者合同,其实质即简单抹杀了电视台、各类网站等转播机构在制作体育赛事节目过程中的特殊性;根据商品化权利说认定为商品化权利,毕竟体育赛事主办方依靠转播权获得之利益乃广义的,既包括商业经济利益也涵盖社会公共利益。假设该项比赛目前在市场中缺乏相应价值(例如个别少数民族运动项目),电视台、社交网站等转播机构转播该赛事仅仅出于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并无商业价值,那又何来商业领域的商品化权利之说?同理根据物权说,假设该项比赛在市场中缺乏价值转播机构仅出于社会公共利益目的录制体育赛事节目播放,物权上的所有者收益便很难成立;若根据无形财产权说,一则无形财产含义过于广泛,知识产权、债权也可能构成无形财产权。况且如果比赛缺乏市场价值仅是基于社会公共利益转播,财产权益就很难说存在;若按照著作权说,因体育赛事一直具备严格的程序和规则,除部分艺术性竞赛(如花样游泳)外独创性相对较低,显然很难构成作品。而体育赛事不构成作品,著作权便不成立;若采纳邻接权权说,一来运动员等体育工作者在比赛中虽有一定程度展示精湛技艺表演意味,但他们毕竟是严格按比赛规则竞技,视为表演者未必公允,如此这般显然表演者权就难自圆其说;二来广播组织权主体系播放自己节目的机构,不包括体育赛事主办方。这样主办方岂非不享有任何转播权与体育赛事转播权概念明显背离?此外对于国外流行的企业权利说和娱乐服务提供说,它们只看到了可能产生经济效益的体育赛事属性,可那些缺乏市场价值的赛事就根本谈不上相关企业经济权益或娱乐付费权益。而赛场准入权,虽然避免了体育赛事究竟有无市场价值能否产生经济效益之困扰,但它笼统将全部转播机构对体育赛事的转播也视为赛场准入,又一定程度无视了转播机构并非赛事主办方难以控制赛场的特殊背景。
因此,传统二分法将体育赛事转播权法律性质区分成直播权和字面意义两层面进行思考,显然更多考虑到了体育赛事转播权的多元复合化属性。较之其他国内外主流观点,也更具备可取之道。不过,传统二分法在两层面的思考某种程度又乃无形财产权说和邻接权说的结合,自然无形财产权说和邻接权说本身缺陷也难免影响到了二分法。故笔者主张,我们宜在坚持传统二分法基础上,对其作出有限度的修正:
第一,针对直播权意义上的体育赛事转播权而言,它应被界定成一种赛场准入权而非无形财产权。尽管有学者指出,赛场准入权说作为西方国家早期的一种体育赛事转播权性质界定观点目前在欧洲已远不如企业权利说和娱乐服务提供说盛行。该观点强调主办方对场馆的绝对化控制,运动场馆外的马拉松和公路自行车比赛就很难谈得上主办方对纯开放性赛场的管控[6],也体现不出体育赛事转播权巨大经济价值。但笔者认为,将直播权意义上的体育赛事转播权视为赛场准入权仍然是比较科学的。因为就比赛本身权利而言,在最广义层面即公民体育权之集合体。毕竟体育比赛受事先设定的严格竞赛规则束缚,除部分艺术性竞赛(如花样游泳)外大多独创程度相对较低,难以视为作品形成著作权。不过,体育比赛自身权利无疑乃参赛运动员和组织者体育权的集合体。所谓体育权,系公民在各项体育活动中依法享有的相关权利之总称*当然目前国内学界对于体育权的界定尚无统一定论,甚至个别学者还对体育权持否定态度,但主流观点大多肯定了体育权的存在。具体可分别参见黄鑫:《作为基本权利的体育权及其双重性质》,载《体育学刊》2016年第2期;或杨腾:《体育权:权利泛化语境下的虚构概念》,载《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它既包括运动权利,也囊括了其他和运动关联的权利(如财产权、健康权等)。由于体育比赛是公民作为运动员积极参加并得到组织者大力引导、配合才形成的竞技活动,体育比赛自身所有权利自然均源自参赛运动员和组织者的体育权。这些体育权有财产权性质(如职业运动员参加比赛获得的可观收入),也有纯粹公益性质(如普通民众参加比赛锻炼身体)。那既然体育比赛自身形成的体育权并非全然带有财产权性质,依托体育比赛权益产生的转播权自然也不例外。如此一来,赛场准入权就更说得通了。直播权意义上的体育赛事转播权乃主办方转让或准允某转播机构(电视台、社交网站等)将现场体育比赛场景(具体化的体育权)通过设备制作成节目传输出去获取利益的权利。假设主办方不授予转播机构直播权意义的转播权,也即意味着电视台等转播机构不得进入赛场,就体现着赛事主办方对赛场之绝对控制力。即便是在运动场馆外进行的马拉松等露天性质比赛,主办方很难实现开放式赛场的全方位控制,但电视台等转播机构要采集信号、接入信号和布置摄像机对本项赛事实施全面报道,必然要得到主办方密切配合与准许。换言之即依旧处于主办方控制下,否则它想顺利完成转播只会变得困难重重。至于那些缺乏经济价值,纯粹系出自推动青少年体育事业发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增强体质等社会公共利益需要进行的比赛直播权意义上的转播显然也是在转播机构获得主办方许可,主办方具有赛场控制力情况下展开的,它决不会像无形财产权说那样因此刻的转播无市场价值缺乏财产权益而陷入尴尬境地。另外,赛场准入权的判定还能克服无形财产含义过宽泛的缺陷。因为赛场准入权范围比无形财产权要小,人们不会将知识产权、债权等也纳入到赛场准入权中。
第二,针对字面意义的体育赛事转播权而言,它应被继续界定为邻接权中的广播组织权而非其他权利。传统二分法将字面意义的体育赛事转播权视作邻接权中的广播组织权,笔者认为这是完全合理的,我们理当继续坚持。因为字面意义上的体育赛事转播权是其他转播机构通过向获得直播权的转播机构购买直播体育赛事节目(具体化的体育权)传输出去而形成的权利,获得直播权的转播机构在制作体育节目时往往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不论高清晰的体育比赛现场画质画面、灯光音响、精彩回放、运动员特写、字幕设计、摄像机选角度、赛场评论和解说、观众互动以及策划监制,都凝聚了诸多智力和体力劳动成果。而邻接权中的广播组织权乃广播组织对自己编排和播放的节目所享有之权利[12],获得直播权的转播机构录制体育赛事节目无疑便具备了相应广播组织权。依照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45条:“广播电台、电视台有权禁止未经其许可的下列行为:(一)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转播;(二)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录制在音像载体上以及复制音像载体……”,拥有直播权的转播机构就可有效捍卫自己字面意义的体育赛事转播权。另外有一点需着重指出的是,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各类网络媒体等新兴转播机构尤其是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的体育赛事点播回看功能日渐兴起,而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仍处反复修改酝酿中,对此类网络实时转播方式造成之侵权能否纳入到现行著作权法第45条规定的“广播、电视转播”中尚缺乏明确规定。对此笔者认为,未来我国著作权法应跟紧时代步伐,及时扩大现行著作权法第45条中广播组织权之设定,从而更妥善地保护字面意义的体育赛事转播权。
4 结语
综上所述,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法律性质界定尽管因其自身的复杂性多年来难有统一定论,但将其划分成直播权意义和字面意义分别予以判断的传统二分法很明显还是有较大科学合理性。不过正所谓“符号系统实际上规定着我们对自己和社会的理解”[13],针对传统二分法的个别缺陷仍需进行适当修正。直播权意义的体育赛事转播权应属于赛场准入权,字面意义的体育赛事转播权则属于邻接权中的广播组织权。我们唯有树立起正确的权利观念,方可确保体育赛事转播活动能在法律框架下有条不紊进行。
[1] J·M·凯利.西方法律思想简史[M].王笑红,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345.
[2] 冯春.体育赛事转播权二分法之反思[J].法学论坛,2016,31(4):126-132.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Z].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709.
[4] 张民全.法律推理的概念辩证[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7(5):84-91.
[5] 张志伟.体育赛事转播权法律性质研究——侵权法权益区分的视角[J].体育与科学,2013,34(2):14-17.
[6] 张玉超,曹竟成.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法律属性研究[J].山东体育科技,2014,36(5):14-17.
[7] 朱玛.利益平衡视角下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法律保护[J].河北法学,2015,33(2):166-174.
[8] 张厚福.论运动竞赛表演的知识产权保护[J].体育科学,2001,11(2):18-33.
[9] 凌宗亮.体育赛事转播权法律保护的类型化及其路径——兼谈《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第114条的修改[J].法治研究,2016,10(3):27-35.
[10] 彭静林.体育赛事转播权研究[D].沈阳:辽宁大学,2014.
[11] 侯海燕.体育赛事转播权法律问题研究[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5,32(1):22-26.
[12] 张玉超.体育赛事转播权法律性质及权利归属[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3,47(11):40-46.
[13] 刘珂.“信任”理念的嬗变——休谟、马克思、吉登斯的信任谱系[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7(3):39-45.
(编辑 任丹)
Further Talk about the "Dichotomy" of Defining Legal Attributes of Sports Broadcasting Rights——Discussing with Doctor FENG Chun
OUYANG Aihui
The definition of legal nature of sports broadcast rights has always been controversial. To research this question from the angle of multiple attributes may have some innovation, but also have some defects. And there is a misreading of the traditional dichotomy which defines the legal nature of sports broadcast rights. Compared with current domestic and foreign mainstream point of view, the traditional dichotomy is more reasonable. This paper conducts limited amendment according to traditional dichotomy's limitations. In broadcast connotation, the right belongs to the right of access to the field and belongs to the right of 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 in the literal sense.
sportsbroadcastrights;dichotomy;intangiblepropertyrights;broadcastingorganizationrights;rightofaccesstothefield
G80-05 Document code:A Article ID:1001-9154(2017)04-0066-06
欧阳爱辉,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经济法学,E-mail:basten2018@tom.com。
南华大学 经济与法学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Economics and Law School,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Hengyang Hunan 421001
2017-03-10
2017-05-09
G80-05
A
1001-9154(2017)04-006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