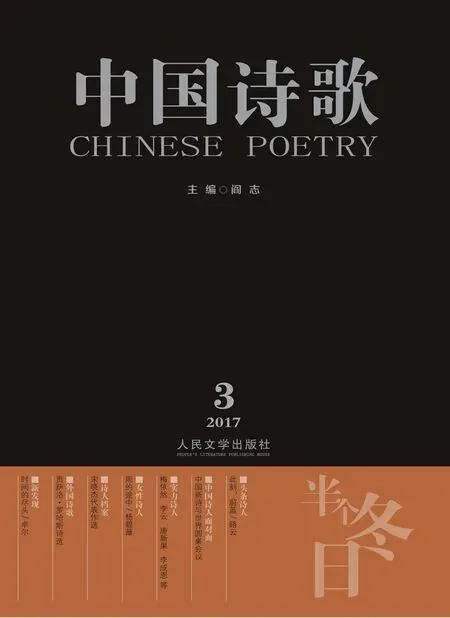诗学观点
诗学观点
□甘小盼/辑
●张大为认为,诗歌与哲学是人类心智的两个极端,诗与哲学的论争,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诗歌哲学本身的一种深刻的文化责任,因此,“诗”“思”并举才是文化和文明应有的格局。而今天的诗歌给人的直观感受,是其自身存在的一种文化失重的感觉,从而也只能在这个“美丽”的文化世界中,处于一种失衡的滑动状态。因而当代诗歌需要的,是以开放而健全的圆融心智,在“诗”与“思”的平衡中,以深刻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来理解自身的文化本质,以深刻加入外部世界秩序的方式来回归自身的文化存在。心智的回环、零度和曲折,或许正是诗歌自身的文化存在“形式”和文化实体诞生的地方。
(《通向诗歌的“文化心智”》,《文学自由谈》,2016年第5期)
●欧阳江河认为,从人类文明的角度来讲,诗歌在美学意义上、伦理和精神性的立场上起到了净化、升华的作用。我们这个时代都不处理崇高。但诗歌还是要处理崇高,并且诗歌意义上的崇高包含了日常性。把日常性包含进来以后,还有一个真实性的问题。一旦包含了日常性和真实性以后,写诗就不是表演,不能一写诗,我就是美的、正确的、正义的。写诗要保持一股狠劲儿,要触及真实,触及现实,触及物象。
(《诗歌要保持一股狠劲儿》,《天涯》,2016年第6期)
●罗小凤认为,新世纪以来,诗与现实的关系发生巨大变化。事实上,诗人从未脱离“现实”,只是“现实”的外延和内涵不断发生迁移和变化。“现实”无法重返,只能调整,即找寻、调整自己在社会中的生存位置。无论哪个年代,任何作品中的“现实”都是现实本体的镜像。真正的现实不随任何外在因素发生变化,但诗中的“现实”却会因诗人的原因而发生变化。关键在于通过对现实镜像的呈现,而呈现人性、灵魂与终极意义的东西。诗人所能做的,只是发明现实、再塑现实。即通过个体经验呈现对公共现实问题的思考,以及如何用语言再塑造诗人所理解的“现实”样貌。
(《现实的发明与再塑造——论新媒体语境下诗与现实的关系》,《诗刊》,2016年10月上半月刊)
●赵亚东认为,在诗歌创作方面,首先要随着对社会形态、对人性认识的加深,个人的诗歌创作逐渐从个人世界向整个社会和人类的整体情绪介入,不断提升自己对身边事物感同身受的能力和自觉性。另一方面,诗歌创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写作前,诗人要做好情绪酝酿和精神准备,甚至对形式感的不断确认,一定要外在的形式和内心的律动充分结合后才下笔。不仅如此,还要注重创作过程中对节奏感的反复揣摩,一定要做到情感与形式的统一,同时避免词语的大众化。诗人的创作来源是个人对生活、对社会的不断思考和感受,诗人必须始终把温暖、光芒、爱,以及感恩和绝望中的憧憬表达出来。
(《赵亚东:在“水深火热中返璞归真”》,《北方文学》,2016年第12期)
●柳冬妩认为,一种深入个体当下生存状态的个人写作语言,与具体的历史语境紧密相关。诗人要恢复诗歌原有的初始性、独特性和纯粹性,并把这种新鲜的感觉直接带入行文之中,使新时代的诗歌包含我们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信息,给古老的汉语诗歌写作带来生气,使写作再度成为可能。诗歌需要的不仅是才气、熟练地调词遣句的能力、对现代诗歌的修养,而更需要一种原初的、在生活刺激下不断磨擦出诗性火花的能力。离开了深厚的生命体验,离开了对于人,以及人所生存的世界之洞察,就不会产生诗的语言,也就不会产生诗的意象。优秀的诗歌就是那些以意象向我们指示着生存无限可能性的诗歌。
(《一种生存的证明》,《作品》,2016年第12期)
●王雪认为,文人创作有些时候是因为“负债”而创作。诗债由单纯的欠他人之诗歌演变为一种创作观念,虽然没有完整的理论表述,但是大量的诗歌创作都与之相关,其对诗歌创作的影响理应受到重视。不同类型的诗债在一定程度上都敦促诗人积极作诗,诗人们在诗债的鞭策下主动作诗还债,这不仅能够提高诗人的写作技艺,也使得其创作量大大提升。但是,任何一种创作观念的影响都是双面的,以诗偿债有时也会造成苦吟之风,而且对于那些致力于毕生作诗偿债的诗人来说,这种宿命观往往会导致他们作诗过于率意而忽视情韵,而不经深思熟虑而信口作诗,必然会出现许多平庸甚至粗俗之作。
(《诗债论》,《中国韵文学刊》,2016年第4期)
●山鸿认为,由于大众趣味的变化,现代汉语诗歌已经找到了发展的方向。需要警惕和提醒的是:个别诗人在现代诗写作实践过程中的不良倾向,对传统的轻易否定和对当下生活的简单摹写都是及其恶俗的。诗歌之美,在于安静而致命的一击,语言的所指精确、能指有力,所指和能指之间有一片开阔地,大开大阖之间,彰显一个诗人的存在。因而当代诗歌所面临的最大机会,是结合当下社会生活所带给我们的心理体验对古代诗歌传统的现代化。
(《现代诗写作实践中的机会和底线》,《当代文坛》,2016年第6期)
●谭毅认为,在诗歌技艺方面,诗人需要能觉察出现实的许多层面和潜能,以及各种可能性的方向和结构,不同方向的力量在这种结构里角逐,修改这些结构。从不同的阶层、地域、人种的生活方式到语言的修辞层面,都需要繁复的生态,并且能够相互切入。作品中的逻辑不应该只有一种、一类、一层。如果只有一层,也许这个作品会更方便于处理它所包裹的现实,但不够立体。依靠线性逻辑是处理不好现实的,我们要从现实中提取主义和观念,构成我们自身的模型。它所呈现的逻辑应该是环状的,或者立体的;由此形成的诗,就整个作品而言,应该是“混而不乱”的。
(《跨越、迁移与综合,或诗的潜能》,《滇池》,2016年第11期)
●李浩认为,对诗歌而言,任何一首优秀的诗歌,其诗性和诗意都是充盈的,必须获得充分保留,而增加叙事性则必然会对诗性构成减损,它们之间的“危险平衡”需要得到反复调适。叙事成分的增加,会增加诗歌的黏稠度,会下沉,这就要求诗人们必须在诗句中经营好凿空和留白。诗歌重情绪,往往截取时间片段,着力于一点一隅,而叙事性的融入则会不经意拉伸它的时间性,至少是数个片段的串联——其中的得失利弊也需要权衡。
(《诗与叙事:片面的随想》,《广西文学》,2016年第11期)
●王士强认为,对于诗歌而言,独特的“发现”是前提性的,现实生活是规定性的、惟一的,而诗歌则可以超越现实,探寻更具可能性的生活样态。诗歌所展现的是一种别样的、异质性的生活,是对于现实生活的补充、超越与提升。诗人是敏感的,具有很强的发现能力的人,他需要对现实生活做出敏锐的体察,并对另外的、可能的生活做出真切的想象,如此方可能发现生活内在的诗意并将之传达出来,引发读者的共鸣。诗人应该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应该对于生活有自己独到的发现甚至发明,说出人人心中有而笔下无的东西。
(《诗歌与发现》,《清明》,2016年第6期)
●汤富华认为,翻译作为语言的属性,却超越了语言的功能,翻译不仅是不同语言的桥梁,也是人类意义的调和剂。翻译的出现,使得操不同语言的人们得以思想互文,人们通过语言进入了他族的心灵。两种不同的语言自然代表着两种完全不等同的诗学观念,个体对诗的感觉也迥然不同。诗歌必须是艺术品,读者可能解释不清,但他们的鉴赏心理非常明白。翻译带来文化异质,在翻译的招牌下,新的文体、新的文字以及新的诗感逐渐成熟,全新的审美形态也悄然形成。以此,语言的语感问题通过翻译的滤光镜而逐渐显出本色。这不仅仅是语言层面,诗学层面,更是社会环境以及意识形态的问题。
(《语感的向度——以“五四诗歌翻译”为例》,《湘潭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杨剑龙认为,在诗歌创作中,诗人首先要有敏感之心,对于世事的发生、对于环境的变化,都有所感应有所反响,这就成为诗歌创作的缘起和动力。文学应该是真善美的艺术,任何虚情假意必定为读者所唾弃,诗歌创作更是如此。诗人应有真挚之情,无论是热爱、歌颂,还是愤懑、讽刺,都应该出自内心的真情。诗人不仅需要激情,还必须要有正义之感,褒奖正气、贬斥歪风,这是诗人的正义之识。在具体的创作中,尤其是传统诗歌的创作中,还必须注意到“意象”与“意境”的结合。
(《我的诗歌创作与我的诗歌观》,《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9期)
●杨志学认为,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诗歌回暖升温。这虽然是好事,但也有一些需要诗人和诗歌界警觉和注意的事情。一是戒“躁”趋“静”。当下诗歌很活跃、很热闹,也很混乱无序,诗人必须做到静心凝神,方有可能写出境界悠远、感染力强的好作品。二是编辑要做好“把关人”角色,最大程度地发现和推出好诗,最大程度地减少关系稿和平庸之作。三是批评家应增强责任意识,重建批评秩序和诗歌标准。四是从传播角度思考,该如何有效抗拒网络化对优秀诗歌的覆盖和淹没问题。五是对五花八门的诗歌活动、诗歌评奖的管理和规范。
(《当下诗歌回暖与升温》,《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11月10日)
●丘树宏认为,中国的当代新诗,首先要守住和弘扬自身的诗歌传统,包括其中的内容和形式。首先诗歌应该是真善美的,这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共同的价值指向,这样诗歌才能给人以真正的意义,诗歌给予人们的必须是正能量。在格式方面,诗歌有和其他文学体裁不同的特色,在格式方面也应该有所规范。当代中国诗歌应该同时具备两个元素。一个首先是中华传统,中国诗歌传统的优秀的独特元素应该保留,这才是中国的。而另一方面,它又不是封闭不变的,特别是在开放的时代,它要走向社会和市场、走向全人类,这样的话,它同时也应该吸收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其他语言的诗歌优秀的东西。
(《诗歌要有明朗的方向和理想——再议鲍勃·迪伦获诺贝尔文学奖》,《南方日报》,2016年11月11日)
●罗振亚认为,在诗歌的竞技场上,最有说服力的永远是文本。新世纪的诗歌形象重构与真正的繁荣期尚有一段距离。这种形象重构基本上出离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个人化写作”的审美与思想境域,它虽然存在一些必须消除的偏失,但也提供了一些艺术趣向和情感新质,只要诗人们能够在时尚和市场逼迫面前拒绝媚俗,继续关怀生命、生存的处境和灵魂的质量,在及物的基础上注意提升抽象生活的技术、思维层次,注意张扬艺术个性,强化哲学意识,协调好当下现实与古典诗学、西方文化资源的关系,避免在题材乃至手法上的盲从现象,让写作慢下来,在优雅的心态中宁静致远,新世纪诗歌就会无愧于时代与读者的期待。
(《新世纪诗歌难以迅速出离低谷》,《辽宁日报》,2016年11月14日)
●吴投文认为,情感表达在诗歌写作中居于核心的位置,诗歌的修辞和形式要素都是情感的载体。一首诗的成功某种程度上就在于恰当的情感表达,而恰当的情感表达又是修辞和形式要素在整体上的协调统一。诗歌的修辞和形式技巧是诗歌的本体性元素,诗歌的主题内涵只有通过恰当的修辞和形式技巧表现出来,才能使诗歌获得稳定可靠的意义视域。诗歌写作固然是随物赋形,形随物移,但物与形的关系也是相互包容的。就此看来,诗歌的修辞和形式技巧内在于诗歌本体,而诗歌本体尽管是一个混沌的形体,却又是修辞和形式技巧的内在转化,因此,在诗歌写作中,对修辞和形式技巧的探索应该是诗人的本能和责任。
(《生命存在的诗性哲学表达》,新诗-龚学明新浪微博,2016年12月27日)
●黄自华认为,一首诗歌能够感染读者,往往在于它营造出来的意境。好的意境是作者在诗歌中表现出来的一种深层次的悟性。情景交融、寓情于景、借景抒情、寓理于境、借境达理的诗歌无疑是好诗歌。好诗歌都应意境优美、深远,让人读后会有一种身临其境、回味无穷的感觉,并且能够引发读者对人生、人性的严肃思考,获得深刻的启示。诗人只有具备足够的内心感知力,才能够与强大的现实撞击,激荡,才能够与庞然大物相撞,并且撞击出其内部的诗性,创作出真正能够打动读者的好诗。
(《从庸常的物质世界里,抽离出精神和境界——评谷未黄诗集〈与蚂蚁谈心〉》,谷未黄微信公众平台,2017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