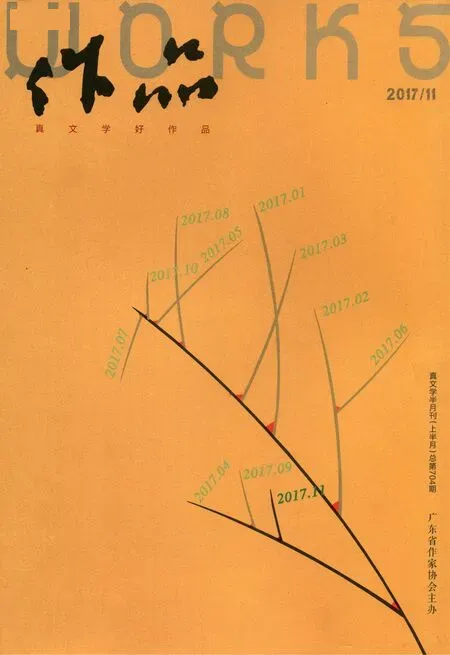有风吹过
文/李克柔
有风吹过
文/李克柔
李克柔女,2000年出生。北京市某中学高中在读。短篇小说《青春痘》发表于《青年文学》,并被《长江文艺好小说》转载。
祝悉觉得自己大概是魔怔了。
她盯着孔楼。孔楼两片薄薄的嘴唇一开一合,他讲的东西祝悉一个字都听不进去。妈妈在厨房里张罗着晚饭,隔着门也能听到噼里啪啦翻炒的声音。傍晚七点,天还亮着。卧室里只开着一盏台灯,有些东西在亮处雀跃,有些则隐到了黑暗里,张着眼睛四下窥望。
祝悉觉得自己就是那双窥望孔楼的眼睛。
孔楼是祝悉的家教老师,教数学的,二十一二岁的样子。到底是二十一还是二十二?祝悉总会追问他。孔楼笑,秘密。孔楼有一颗虎牙,小小的尖尖的,钻石一样,笑起来会一闪一闪,简直称得上是晃眼了。黑色的书桌上放着一个黑白格子的马克杯,里面是西瓜汁,红艳艳的,与周围显得格格不入。不对,岂止周围,是与整间屋子都格格不入。祝悉还记得孔楼第一次进自己房间的时候就瞪大了眼。祝悉啊,你这房间也太——嗯,太酷了吧。祝悉酷爱黑白色,书桌、书柜、地板,清一色的黑色,甚至床单被罩枕头都是黑白格子的。孔楼嘴里啧啧有声,祝悉翻了个白眼。
祝悉这次数学考得不错,妈妈高兴得不行,连连要求孔楼留在家吃晚饭。晚餐有酸菜鱼、四喜丸子、紫米粥。鱼是阿拉斯加鳕鱼,生活在深海,肉质洁白细嫩,和着酸汤一炖,简直能让人多吃一碗米饭。哪怕在夏天这样燥热的季节,一餐下肚,酣畅淋漓。孔楼的吃相很斯文,睫毛长而密,垂下来,在脸上打出小的阴影。祝悉坐在对面,和妈妈聊着学校的事,有一搭没一搭的。我们那个新来的教导主任,哇,简直了。一天天那架子摆的,恨不能往脑门上贴“校长”俩字儿了。关键是他还没头发。孔楼没忍住,嗤的一声笑了出来。抬手掩了掩嘴,眼睛弯成一道桥,几乎有水波在流动了。祝悉愣了愣,低下了头。
班主任又留堂了。从教学楼里出来时天色已经擦黑。足球队的男生还在操场上训练。有球向祝悉飞来,笔直地,坚定地,险些砸到她。满头是汗的男生跑来捡球,匆匆说了句对不起。祝悉看着他小麦色的胳膊,突然想到孔楼。孔楼很白,白到让女生嫉妒。公正地说,他并不属于好看的一类。但是孔楼胜在皮肤白,而且身上有一种气质,很干净,泉水一样通透,清澈,凉凉的。他有点近视,但是坚持不戴眼镜,眼睛总是有点微微眯起来,看起来像在笑,细看又不是。祝悉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孔楼时,差点儿要以为他是语文老师了。你好,我是孔楼,孔子的孔,任他明月下西楼的楼。孔楼说,眼里带着狡黠。祝悉搜肠刮肚想着诗词,大脑却一片空白。祝福的祝,熟悉的悉。她脸有点红。
太阳已经落下去了,道路上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各色店牌的灯光闪着,赤橙黄绿,光斑旖旎,城市把他们尽数衔在口中。书包带在衣服上勒出了细细一片汗。六月天气总是恼人。奶茶店前排起了长队,有人捧着冰饮从祝悉面前走过。凝着水珠的奶茶杯好像一碰就会融化似的。祝悉舔舔嘴唇,蹲下身挽裤腿。耳机里传来嘟的一声。短信。来自祝非。祝悉一滞,迅速关掉了手机屏幕。
挤上地铁,祝悉的头突然就疼了起来,像是有人拿了钢棍在脑子里翻搅,带着十足的恶意。“祝非”两个字像是水蛭。尖利的牙刺进皮里,钩进肉里,吸她的血,一点一点地,毫不留情地。有个男人在她身边打电话,嗓门大得不像话,简直是故意的了。祝悉闻到他嘴里酸腐的臭味,像下水道的死鱼,胃里一阵翻滚。祝悉捂住了鼻子。
回到家,餐桌上已经摆好了饭菜。妈妈穿着粉底碎花家居服,身材有些臃肿。头发随意盘在头上,用了彩色的皮筋。颊边垂下的几缕发丝腻腻的。祝悉踌躇片刻,走上前抱住妈妈。诶,怎么了这是?一身汗,热烘烘的,起开起开。妈妈笑骂,换衣服吃饭啦,今儿晚上有香菇鸡翅。祝悉没说话。你这孩子,聋了?妈妈拍了她一下。妈,祝非给我发短信了。妈妈一怔,你爸他说什么了?我没看。祝悉说,我不想看。抽油烟机轰隆隆的,可劲儿响着。料理台上的瓶瓶罐罐兀自争吵着,有黑色的泪从瓶身流下来,弄污了白色台面。三脚架上几只土豆凑在一起窃窃私语,架在碗上的筷子刚打了鸡蛋,蛋液拉出细长的黄丝,晃悠悠的,摇摇欲坠了。油烟在空气里升腾,它们黏稠而闷热,糊了祝悉一头一脸。你都十七了,怎么还跟个小孩儿似的,妈妈一边解围裙一边说。
忙完所有作业,已经是深夜了。祝悉摘下耳机,耳朵疼得厉害。短信图标右上角那个鲜红的数字1依旧待在那儿,像锋利的纸张割破手指,又气又疼。祝悉咬牙切齿,点开了短信。小悉,功课忙不忙?周末出来吃个饭吧。祝悉飞快打下两个字,没空。锁屏,把手机扔到床上。不出一分钟,叮咚一声。祝悉拧着眉,心脏在胸膛里咚咚跳着,剧烈,不安。爸爸想看看你。韩阿姨从比利时给你带了不少巧克力回来。祝悉的手有点抖,打了几个字又删掉了。再打,再删。反复两三次,终是没有回复。祝悉打开微信,孔楼换头像了,换成了一只咧着嘴笑的柴犬。祝悉笑,发了一条微信过去,小柴犬?不像你的风格啊恐龙。孔楼,恐龙。祝悉喜欢这么逗他玩。去去去,没大没小,叫老师。祝悉发了个白眼过去。你怎么还不睡?明天还上学呢。孔楼问。祝悉的嘴不受控制地咧成弧度,这就睡啦,晚安晚安。没等孔楼回复就丢开手机,跑去洗澡。墙上有一只黑色的钟表,一点点走着,嗒嗒,嗒嗒,一丝不苟地,把时间一点点吞进肚子里。手机的提示灯幽幽亮起来,像一只绿色的眼睛。祝悉回到房间,打开手机。一条微信,一条短信。孔楼说,晚安。祝非问,小悉?祝悉错了错牙。我知道了。她回复。
祝悉今年十七。爸妈离婚的时候,她十五。她记得那时刚刚经历完中考一模。拿着前十名的成绩欢天喜地回到家,看到妈妈坐在沙发上,脸上是无尽的疲惫。祝非在阳台上抽烟。祝悉没敢说话,偷偷回了自己的房间。祝悉的房间是茉莉花白色的,有一点浅的鹅黄装饰。祝悉的床上摆满毛绒玩具,大的,小的,粉的,暖棕的,有熊,有狗。祝悉本来想抱抱它们,可她面对一群动物突然就不知所措了。妈妈推门进来,小悉,妈妈跟你说点事。祝悉很警觉,你俩吵架了?妈妈点头。很严重?她看到妈妈的喉咙上下滚动了一下,点头。有什么东西在祝悉心中呼之欲出了,她拼命咽了口唾沫。屋里的空气安静极了,死一样的安静。只听到秒针嗒嗒的脚步,一脚一脚踩在心尖上。妈妈的嘴一开一合,在说着些什么。祝悉看着妈妈蜡黄的脸,一口整齐的牙也被年岁催成了歪扭的样子。祝悉捂住耳朵,她不想听到妈妈说的话。她甚至觉得,这些话只要不被她听到,就不会发生。指针行走的声音越来越大,歇歇停停,越来越快,到最后几乎是在没命狂奔了。嗒嗒的针脚踩在祝悉的心尖上,血一点点冒出来,几乎要染脏浅色的地板。祝悉颤抖着嘴唇,你们是要,分开吗?妈妈的泪一下子落了下来。
镜子前,祝悉穿了黑色的棉麻七分袖,白色短裤,帆布鞋。脚踝白皙小巧,系着细的红绳。她故意没有绑头发,而是让一头长发披散着。祝悉的发质很好,黑,浓密,带着一点微微的自然卷。镜子里的女孩儿和平时判若两人,但一张脸还是稚气未脱的样子。她想了想,拿起一支口红。很正的红色,女王的裙摆一样,带着一股子傲气和蔑视。祝悉尝试着将它画在嘴上,但红色总会溢出唇线。一次,一次,又一次。她的手有些抖了。
祝非订的是一家川菜馆。服务员穿着黑色的丝质衣裤,上面印着暗绿银灰的花色,长发盘在脑后,一丝不苟。走过红漆的长廊,两边的墙上雕着花纹,是金色的。地毯很软,图案繁乱。祝悉站在包间前。抬头是三个墨黑大字,合欢阁。手心微微出汗,她抿了抿嘴上的口红,推开门。小悉?我们小悉来了。穿着湖蓝长裙的女人上前,亲昵地拉住祝悉的手。祝悉笑了笑,韩阿姨好。我们小悉真是,越来越漂亮了啊。你爸爸天天念叨你,知道你现在高中功课忙,不敢让你分心。祝悉看向祝非,祝非坐在那里,衬衫笔挺,金丝眼镜,一派儒雅。他有些局促,小悉啊。你——祝悉打断他。我妈今儿不怎么舒服,所以没来。祝非点头,你妈妈她跟我说了。你这?小孩子打扮这么成熟干什么。嗨呀,人家小悉也不小了,你别总这么管着她。对了,一会儿记得拿上阿姨给你带的巧克力。祝悉低头,谢谢阿姨。你这孩子,跟我客气什么,韩笑着,露出雪白的牙,伸出涂着蔻丹的手,为祝悉拭去嘴边多余的口红。
祝悉?祝悉!题还没做完呢,你怎么又发呆!祝悉啊的一声。孔楼一脸无奈地看着她。受什么刺激了这是?祝悉不吭声,垂下眼皮。孔楼觉得有点不对劲。两人都不说话。恐龙,我今儿中午,去见祝非了,还有他女朋友。孔楼一愣。我见过那个女人三次了,每次的感觉都是,她真的好漂亮啊,比妈妈漂亮好多。一顿饭下来,我觉得自己像个外人一样。祝悉的声音有点哽咽。恐龙,在他和我妈离婚之前,我问过他,为什么一定要离婚呢?为什么非要在我中考之前告诉我呢?就不能再等一等吗?就不能再等一等吗?你知道他说什么吗恐龙?他说他和妈妈真的再也无法忍受彼此了,他不能因为我而牺牲自己追求幸福的机会。他说对不起小悉,我觉得你已经足够承受这一切了,希望你能理解爸爸妈妈。祝悉趴在桌子上,身体剧烈颤抖着。他还说,爸爸已经有了新的幸福,希望你能祝福爸爸。祝福?祝福个屁!就凭他说出这些话,我一辈子也不会原谅他。祝悉说着说着,突然咧了咧嘴,像是在笑,恐龙,我真的——好心疼自己,也好心疼妈妈。孔楼叹了口气,把手放祝悉头发上,一下下抚着。一室黑白,钟表嗒嗒走着,按着预定的轨迹,不偏不倚。走过的地方像带着水迹,亮晶晶的,只一瞬就蒸发不见了。祝悉抬起头,直直看向孔楼的眼睛。那是一双少女的眼睛,带着六月的稚拙和潮气,湿漉漉的,脆弱,孤单,美丽,像折翼的蝶,像绿树间的烟云,像汁水最丰沛的一枚荔枝。祝悉看着孔楼的瞳孔,里面有自己的脸。有些什么东西裂开了,哔哔剥剥,一片片脱落下来,露出里面鲜红的芯子。小悉?妈妈喊,来开下门,你和孔老师都吃点水果。
有一面巨大的镜子,大到仿佛含括了天地。祝悉站在镜子前。周围是一片白色,她穿着华丽的裙,唇上是暗色的口红。有风吹来,裙子突然一点点裂开了。它们一点点脱落,一片片脱落。缓缓地,笑得恶毒,把少女牛奶一样洁白的鲜嫩的身体暴露给镜子。祝悉慌得弯下腰去。她想找些什么来遮住自己,可是周围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把尖刀。祝悉拿起刀。她的口红融化了,滴在地上,暗红色的,黏稠,芬芳。它们蠕动着不规则的身躯,爬到祝悉的足上、光滑的小腿上,亲吻着,狂欢着。祝悉尖叫起来。
猛地睁开眼,天还没亮。祝悉的头很疼,眼睛酸涩不已。心脏在胸膛里咚咚跳着,很剧烈。窗外有一辆车,逃命似的,在凌晨三点的马路上疾驶而过。祝悉打开灯,从黑色的床头柜里拽出一本相册。粉色的硬壳。女子微胖,男子挺拔,女孩俏丽。一家三口,笑容如出一辙。妈妈不爱打扮自己,一身横条纹的短袖被丈夫女儿的西装和裙子衬着,显得格外可笑。祝悉闭上眼,她想起韩,长裙,盘发。饭桌上,韩阿姨给祝非倒酒。红酒,酒花儿滚入杯中,女人的真丝睡裙一样,称得上千娇百媚了。韩的腕子上有一只白玉镯子,水头极好。不小心碰到杯壁,嘤咛一声,脆生生的,几乎能滴出水来。韩举起酒杯示意,祝非亦举杯。祝悉在一旁看着,两人之间的默契简直像尖锐的玻璃,冲着祝悉的眼球,狠狠刺进去,再连根拔出来,带着血,带着肉,带着神经。祝悉记得几年前,餐桌上,祝非总会劝妈妈一起喝点红酒。妈妈总是皱眉拒绝。祝悉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低下头。指甲嵌进肉里,很疼。
祝非每个月都会来看祝悉,拎着吃的喝的和一堆衣服鞋子。每当这种时候,祝悉就躲在黑色的卧室里不出来,戴上耳机听摇滚。听着听着,往往会调小音量,竖起耳朵留意外面的动静。甚至直接扯下耳机,侧着脸贴在门上。小悉的成绩。小悉最近的心情。小悉还和往常一样挑食吗。小悉。小悉。小悉。祝非问个不停,妈妈也耐心答着。祝悉在屋里听着,抿着嘴。半晌,冷笑,装什么装!
楼下的超市关门了。妈妈去旁边的生鲜市场买了一条鱼,拎回家的时候还没有死透,仍在袋子里徒劳挣扎着,带着一身的血沫子。祝悉正在埋头刷题,妈妈推门进来,张着一双满是血水的手。血腥味和鱼腥味一下子就在空气中弥散开了。小悉,咱们今天吃豆瓣鱼还是水煮鱼?祝悉忍不住屏了气,都成,看你吧妈。妈妈笑,还跟我这儿谦让起来了,一滴血水就在说话间慢悠悠落到祝悉的卷子上。祝悉惊呼一声,匆忙找餐巾纸。边找嘴里边埋怨,妈,这可是我的作业。妈妈嗤笑一声。祝悉擦干净血水,又找来玫瑰喷雾,在屋子里不停喷啊喷,试图把难闻的腥味儿遮住。你这么事儿不几的样子,可真像你爸。
祝悉会对孔楼说一些鸡毛蒜皮,旁边蛋糕店新出的抹茶蛋糕啦,自己新买的一双小白鞋啦,头绳上的一粒珠子掉了啦。她还告诉他,从爸妈离婚以后,她就逼着妈妈把自己的房间全换成黑色的,对爸爸的称呼也变成了全名,祝非。祝非。祝非。说到这里的时候,她会从孔楼眼里看到一种情绪。是怜悯吧,也不全是。也许是心疼吧?想到这里,祝悉甚至会窃喜。祝悉的枕头旁有一只粉色的兔子,是孔楼送给她的礼物,儿童节礼物。恐龙,你真把我当小孩儿啊你?收到礼物时,祝悉笑得前仰后合。孔楼也笑。女孩子的房间,还是得有点粉色。
好不容易挨到放学,祝悉揉了揉涨疼的太阳穴,慢吞吞地收拾一桌子书和卷子。有人惊呼,黑板上没留语文作业。课代表刚要起身去问,就被一堆同学摁住了。祝悉哈哈笑着,和好友一路小跑出了校门。祝悉几乎一眼就认出了祝非的车,她有些迟疑。车窗摇了下来,小悉,爸爸送你回去?祝悉看着面前这个男人。他简直像几天前饭桌上一样面目可憎。祝悉没有说话,一双眼直直地看到祝非眼睛里。她突然发现,这个男人被路灯一照,突然就苍老了很多,眼角的皱纹从眼镜周围爬出来,像丑陋的触角。大概像是妖怪在黑夜里都会现出原形?祝悉恶毒地想。旁边有一对父女经过,女儿不过三四岁的样子,连衣裙,小凉鞋,软软糯糯的,白雪团子一样。牵着爸爸的手,一蹦一跳,爸爸,爸爸爸爸。声音甜得腻人。一笑,露出可爱的豁儿牙。祝悉突然就想到了以前,每次过马路的时候,她总是用小手紧紧攥着祝非的一根食指。祝非在她身侧,山一样,仿佛能挡住往来的车流。她爱吃鱼,祝非总是把鱼肚子和鱼眼睑处最嫩的一块肉择到祝悉碗里。每当这时妈妈总会埋怨祝非太宠女儿了,祝非只是笑,不说话。手机一震,语文老师通过微信群布置了作业。祝悉抬头看着这个男人小心翼翼的笑容,心里突然就疼了一下。
祝非是个很精明的人。妈妈经常这么说,你别看你爸平时一副没心眼的样子,其实啊,他心里那小算盘,噼里啪啦,响着呢。祝非每天下班都爱跟妈妈和祝悉说很多话,这次的投标啦,新的项目啦,策划方案啦。祝非眉飞色舞的,有时那股子欢喜劲儿,简直要从眼角眉梢溢出来了。妈妈呢,也听不懂这些生意场上的事儿,淡淡应几句,两人便再没了话。祝悉记得妈妈告诉过她,祝非其实是个很爱抽烟的人。但是妈妈这个人呢,受得了厨房的油烟,受得了冬天的雾霾,但偏偏半点烟味儿都忍不了。为此,妈妈没少和他吵架。祝非也慢慢改了这个习惯,只是偶尔心情极度糟糕的时候,才会站在阳台上抽一根烟。祝悉永远记得祝非吸烟时的样子,潇洒,惬意,像在享受玉露琼浆。烟雾笼了他的脸。祝悉觉得这时的祝非特别陌生,又或者,这才是祝非真实的样子吗?祝悉打了个寒噤。祝悉想到自己第一次见到韩。韩挽着祝非的胳膊。祝非在笑,是祝悉从未见过的笑。祝悉想到了以前学过的一篇课文,高山流水,俞伯牙和钟子期。那妈妈是什么呢?祝悉越想头越疼。她打量着韩。韩穿着黑色的针织开衫,里面是米色的吊带,掐腰七分裤,阔口,脖子上一条项链细细的,坠着一粒水晶。她知道韩也在打量着她。三个人之间的气氛有些凝固。韩笑了,温温柔柔地,我们小悉啊,这长大了不定好看成什么样呢。祝悉扯了扯嘴角。她觉得口干舌燥,只想快点逃离这两个人。祝悉不知道自己是走了几米,还是已经走过了一个路口。她忍不住回头。祝非在吸烟。韩伸手接过他手中的烟,叼在自己嘴上,一吸,一吐。两人的姿态,甚至吐出的烟雾,都如出一辙。有什么东西掉在地上摔碎了,清脆,决绝,豁朗朗的,被太阳光一照,简直刺眼了。胸口有东西在翻涌,一直涌到喉咙,涌到鼻腔。祝悉仰起头。
已经过了零点了。手机的提示灯亮着。是同年级男生的告白。祝悉只觉得心烦意乱,不去理会。过了一会儿,她想到了什么似的,把聊天记录发给了孔楼。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半个小时过去了。孔楼没有回复。枕头旁的粉兔子咧着大嘴在笑,祝悉只觉得烦躁,恨恨打了它一下。等着等着,祝悉睡着了。迷迷糊糊地,她梦见孔楼回复了。祝悉猛地张开眼,抓起床头的手机。什么也没有,通知栏一片干净。屏幕刺眼的白光亮着亮着就熄灭了。书柜顶有一盆绿萝,长得很好,枝叶繁茂。它大概是有了心事,头越垂越低,越垂越低,终是贴上了书柜的边缘,融进了浓稠的夜里。
放学时,祝非再一次等在校门口,手里拎着很多东西。祝悉走上前去,看着他。祝非说了很多话,关心的,询问近况的。祝悉一一回答。祝非从兜里拿出一个小盒子,打开,是一条银手链,缀着小的藤叶和紫水晶。快到你生日了,爸爸也不会挑礼物。这是你韩阿姨挑的,说你皮肤白,戴上肯定好看。祝非说这话的时候在笑,眼角的皱纹都温柔起来。爸爸觉得也特别称你,就买了。祝悉咬着下唇,咬到发白,才平平静静说出一句话,祝非,你以为你是谁?祝非愣住了。盒盖不知道被谁合上了,啪的一声。惊雷一样,仿佛下一秒就会有雹子砸下来。祝非想说什么,但是忍住了。祝悉看着这个男人,突然就有些后悔。小悉。他叹了口气,你已经两年没叫我爸爸了。
孔楼来的时候,祝悉和往常一样坐在书桌前。长发披散在黑色短袖上,像是刚洗过一样,湿漉漉的,看不出长度。讲课的时候,祝悉一个字也听不进去。她盯着孔楼的手。这双手可真好看,连指尖都泛着浅粉色。她一点点把身子靠近孔楼。她一点点挪动着。也许挪了几毫米,也许挪了几厘米,到底是多少呢,祝悉不知道。她只知道孔楼的呼吸有些乱了。少女的幽香,带着未散的水汽,带着夏天的甜燥。祝悉想象着它们一点点钻进他的鼻子,顺着神经的纹路,她甚至希望它们能够挠他,啃咬他,最好是侵蚀他。祝悉的手臂,藕一样,嫩生生的。祝悉的颈子,祝悉的头发,祝悉的眼睛里有软雾淌出来。她看到孔楼的喉咙滚动了一下。窗外太阳很大,把世界照成刺眼的白色。屋里安静极了。粉色的兔子坐在床头,张着大嘴看着这两个可怜的人,简直笑开了花。
祝悉记不清妈妈是什么时候进来的了,记不清妈妈有没有打自己。也记不清自己最终有没有吻上孔楼的脸颊。
孔楼再没来过。
祝悉的手机相册里只有一张照片,是孔楼站在黑色的房间里,抱着粉色的兔子,眯着眼,一颗小虎牙亮晶晶的。
卧铺。夜晚。火车上一个人都没有。被子枕头全都乱糟糟的,祝悉在狭小的过道里不停走着,时不时有东西从天花板上滴下来。是一种液体,黏腻,温热,从脖子流到后背,温度迟迟不散。祝悉抹了一把脖颈,她看不清手上的颜色。前面有光,有个男人站在那里,背对着她,抱着一只粉色的兔子。祝悉狂奔过去,一个名字在她嘴里,在她的舌头上,在她的齿缝之间。她含着这个名字,几乎要嘶吼出来了。祝悉踩到一个东西,软软的。她看到另一个祝悉瘫倒在血泊里,眼里满是惊恐。她大惊。男人转过身来,是一张兔子的脸,怀里抱着的是孔楼的头。
有露水从草叶上滑落,凉沁沁的。它想与大地接一个吻。
祝悉走在马路上,心里空空的。有老人从旁边蹒跚经过,一个中年女子搀扶着他。两人的眉眼像极了,如出一辙。做女儿的在小声唠叨着什么,老人只是笑呵呵地听着,不说话。他们慢慢走在路上,头顶是艳阳高照。就这么一直走啊走着,走过云影,走过蝉鸣,走过透明的热浪,路变得没有尽头了。祝悉盯着他们,眼睛突然就湿润了。
阳光剪了些树影泼在地上,一荡一荡的,路面就这么变成了江河湖海。
有云影跌进水中,溅起一片迷人的涟漪。
祝悉觉得自己大概是魔怔了。
她拨出一个号码。电话接通了,对方的声音很惊喜。
小悉?
爸。她叫道。
(责编:周朝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