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丧
李传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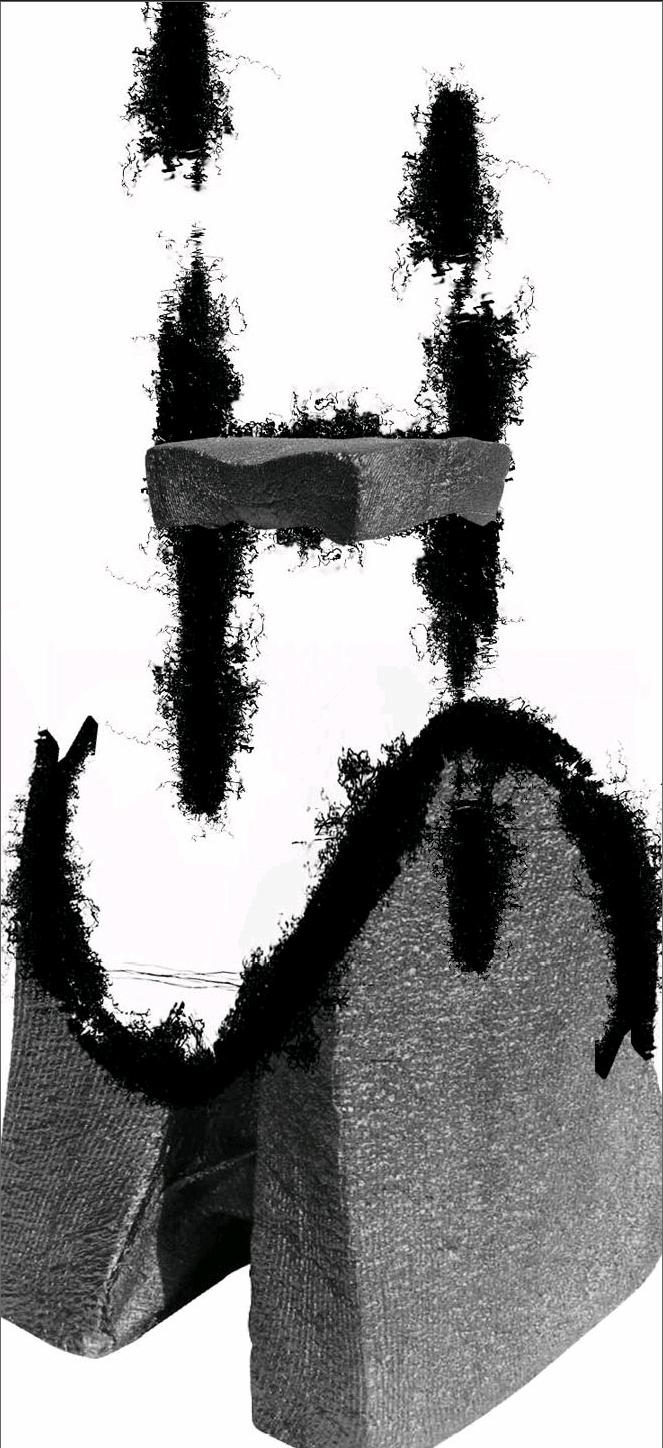
山坡上,有几只鸟儿在打架,它们用尖尖的嘴、用利爪,俯冲撕扯,高声咒骂,各不相让。喜鹊叽叽喳喳吵翻了天,有些虚张声势,而两只乌鸦可能是未婚先孕,迫不及待,就闷声不响,埋头苦干。
平叔已经看了一个时辰,起因是喜鹊先在这棵高大的树顶上做了半个窝,今天突然来了两只乌鸦,也想在这棵树上做窝,这黑鸟恃强凌弱,不讲先来后到的规矩。平叔就给他们解交:“不要争啦,这树大得很啦,各做各的窝呀。”看它们不听,又说:“旁边那棵树还好些,是我解放前栽的,算老干部了。”過一会儿,就自言自语:“日怪!这村里人一家一家都往山下搬了,你们倒好,一个个跑回来了?”他叹了一口气,再说:“唉!争啦斗哇,何苦呢?养儿有什么用啊?你看看我,养了两个儿,就不晓得跑回来……”说到这里,老人的鼻子里就来了稀水,眼前也就模糊了。
一只老旧的吊脚楼,偎在高山一隅,就像秋天的枯树上被喜鹊遗弃的一只鸟窝,孤独而无奈。原先,平叔还有几户邻居,近几年,陆陆续续都搬到镇上去了,有的还进了城。那被遗弃的老房子,有的要垮了,有的被野猪占了,就只剩下平叔这一只房子还能冒出些淡淡炊烟,这空巢里也只剩下一只老鸟,每天伴着这山这房这树这太阳,一个能说说话儿的活人也没有。
当村支书一行人爬上山来时,平叔正在一个黑乎乎的香钵前烧香,他在跟白虎神倾诉。他说:“白虎神啦,我求求您保佑我的两个儿子,保佑我俩儿子都平安。儿呀,我是个没有本事的爹,我笨!我无能!如果我有本事让你们吃饱饭,你们肯定不会跑到外面不回来的!”他唠唠絮絮跟白虎神诉苦的时候,听到有些动静,一扭头见几个干部走进了家门,吓了一跳。平叔愣了一阵,急忙把白虎神扔在一边,来接待客人。
平叔的远祖是梯玛,曾经跟随土司王田世爵去东南沿海打过倭寇,梯玛神功代代相传,平叔家中还保留着敬神的习惯。过早衰老的平叔一手拿了个缺腿的板凳叫支书坐,自己顺势就坐在门坎上。
平叔抽着土烟,不敢主动对生人说话,只对村支书说:“你爹娘真是好有福气哟,生了你这么个好姑娘,在外头过着好日子,还晓得跑回来看爹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段时间老爱做梦,在梦里,我梦到两个儿子都回来看我了,还带了好多糖果子回来给我吃。我只有一只鸡,没粮食喂,又舍不得杀,想等我的儿子回来了好杀给他们吃。”
村支书年轻,就安慰平叔,说哥哥们在外头工作,可能请不动假,等赚够了钱就会回来的。说到了钱,村支书带来的那客人就递给平叔一个红包。平叔没有推辞,他怕一推辞就收回去了。他当着客人就把红包打开了,二百块钱,平叔太需要钱了,村支书跟着也给了平叔二百块钱。平叔一下子得了这么多钱,显然很高兴,他手颤动着把钱往胸口窝里藏,藏好了钱又开始倾诉,可能是太孤独,养成了一个人自说自话的习惯,忽然想起了自己的一生,忍不住泪流满面:“我这腿没瘸的时候,还能上山种地,这几年不行了。有时候给人家算命的时候,也有人开玩笑问我自己是什么命,我就和人家说,我的命根本不要算,生下来就注定我是个苦命人!从记事起,我记得的第一件事就是没饭吃。要不是解放,我家地都没得一垅,因为家里穷,没有女人愿意嫁给我,我光棍一条,直到四十岁的时候,才找到一个寡妇,结婚不到半年,我的老伴就怀胎了!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我的老伴就给我生了一个长把儿的。”说到老伴,平叔脸上现出了难看的笑容。
村支书就给来客介绍,平叔的两个儿子都大了,那大儿子是老伴带来的。现在,两个儿子都跑出去了,寨子里的人都说那两个儿子不是东西。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哪里有儿子因为嫌弃家穷就跑的?妈一死,大儿子就先跑了,也不愿意和爹联系了,他看不起这个爹,怨爹。平叔就和小儿子在地里种点苞谷和红苕谋生活。由于他这个地方是高山,缺水,多年使用化肥,把地都种死了,离了化肥草都不长。平叔没有什么钱来买化肥,别人家的庄稼长得青乌乌,他的黄皮寡瘦,现在靠种庄稼只能是饿不死人,农闲的时候他就挖点山药材,捡菌子卖,捡板栗卖,赚点油盐钱,腿瘸了之后,就麻烦了。
当平叔欠身接过客人递过来的香烟抽了几口,才真正挣脱苦难的缠绵,终于听明白面前站着的客人是县里来的扶贫干部。突然来了县官,他不知道是激动还是害怕,有点像饥饿的孩子终于见到了娘,突然大声哭叫起来,双手在身上拍打:“这日子没盼头了哇,一眼看到底了,这房子要垮了,儿子也不回来,腿瘸了也没钱医,我这日子没盼头了,我这辈子没盼头了哇。”大家全没料到平叔会来这一手,都有些不知所措。客人倒不急,又递给他一支烟,点了火,问:“老人家,今年多大年纪呀?”“甲申的。”客人对甲子计年不熟,就看着村支书。村支书其实也不熟,只说:“今年六十八。”
岁月风霜,平叔牙掉了,头发白了,皱纹满面,看起来有七八十岁了。他平日只能跟树说话,跟石头说话,跟天上飞过的鸟儿说话,找虫子说话,跟神仙说话。所以,当他自言自语时还流畅,一旦面对生人,说话反而结巴了。
来的扶贫工作队员是个博士,不知道他博在哪方面,他拿了个照相机对着平叔咔咔地照,平叔就把动作收敛了些。等平叔完全平静下来,博士就和他聊天,问他现在身体怎么样,说这山上风景美,空气好。倒是陪同的村干部有人沉不住气了,嘀咕道:“他狗日的两个儿子都在外面赚钱,不肯养活爹,把责任抛给村里,抛给政府!”村支书也说这是个难题,他一不是军烈属,二不是孤老,三不是残疾人,不属于民政优抚对象。博士就问,他的腿都瘸了,还不算残疾人?有人说,他没办残疾征。博士说,没办证也是残疾人啦。有人答,上面要证。博士问,知不知道他儿子的电话?有人说,三天一换,两天一变,知道也打不通。
平叔不管这些,只要有人听,恨不能把平日积攒的话都说出来:“现在的国家对我真是好,比爹好比儿子好,知道我的穷日子过不下去了,国家白白给我送钱用,我儿子都没有这样孝敬过!如果不是国家帮我,我肯定就饿死了。”村支书见博士是个好性子,胆子就大了起来,她插话:“依我说,就应该追究他儿子的法律责任。否则,大家都这样,都把娘老子丢给政府,那还养儿干什么?”有人说:“子不教,父之过,他自讨的。”有人说:“他不耕不读,无以为家。”博士听了这话,就对大家说:“我看,一切的根源还是因为贫困,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还是发展生产,只有发展生产,才能让农民真正脱贫致富。”
一行人陪在平叔身边,腿都站酸了,有人就给村支书使眼色,村支书就对平叔说:“平叔,县里领导是专门来白虎寨了解情况的,他还要去看看别处,下一次再来听你说话好不好哇?”博士摆摆手,说:“再听听,这都是老人家的心里话,平日没人听。”平叔已经沉浸在他的世界里:“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挨到过年,活到七十岁。我也不知道我的儿子到底在哪里,小儿子去年倒是回来过一次,还带了个女娃,只住了一晚上,那个女娃子坚决要走,从此再没回来过。如果我的儿子能听到我说这些,我想对他说:“儿啊,你们也都是几十岁的人了,也不知道给我生了孙子没有?我希望你们能回来再看我一眼,我这个当爹的也是快死的人了。儿啊,你们能听到我说的话,就带上你们的媳妇回来看看我,在我咽气后你们能把我抬出这个家门和你妈埋在一起,我这一辈子也算是有个结束了……”
平叔的讲述仿佛创造了一种氛围,让听众进入了剧情,离开平叔家,过了山岗,走了很远,大家的心情还很沉重。博士感慨尤其多,他说:“我们上上下下都在昏天黑地地忙啊,开会呀,没完没了地发文件,填表,我们忙的这些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说完这话,博士沉思了一阵,对村支书说:“一个老人住在这孤山野岭,不可能脱贫的,可以考虑搬迁到中心村去。”
正在大家为平叔的事伤脑筋时,平叔的小儿子突然回来了。平叔的小儿子有大名,叫田国民,从小就长得白白净净,机灵可爱,跟他哥哥一样,本是一块读书的好料,只可惜投胎投错了地方,生下地不满半岁,娘就死了。大儿子等把妈埋了,就责怪是后爹没及時送医抢救才弄丢了妈的命,任平叔如何解释,他都不依,并且愤然离家,放假也不回家。小儿子又太小,平叔没有能力来抚养这个嗷嗷待哺的婴儿,一个大男人抱了去山前山后讨奶,讨不到奶就把洋芋果煮了压成泥,用指头往他嘴里塞。
一天,山里来了一对城里夫妇,买了衣服奶粉,要接娃娃去享福。也是出鬼,这奶娃子见了这对夫妇就没命地哭,平叔说,怕是这娃儿没有享福的命。从此,平叔屎一把,尿一把,一棵草儿一滴露水,田国民居然长大了。平叔没有办法因材施教,更别说什么培优,只能进行放养。五六岁时,该学着干些活儿了。平叔是白虎寨里的老把式,想把一身种地的本事传给小儿子,让他先学放牛,结果连人带牛丢了几天才找回来;平叔带他去地里给苞谷扯草,他把苞谷苗给扯了;再大些,让他去学锄地,他两腿并站着,舍不得下腰,他锄过的地,太阳一晒,苗先死了。平叔大骂一阵,说:“我看你狗日的往后吃什么哟!”
小儿子不会种田,也不想种田,读书也不成,不久,乡下的学校撤并,好老师都跑进城了,平叔没有能力送两个儿子进城读书,大儿子初中刚毕业,就出门打工去了,田国民小学没毕业也外出闯荡江湖。在都市里学得的知识比在学校里多得多。他大开眼界,发现很多东西的地区差价很大。他不再给老板打工,他要给自己打工,他收香菇,收山野菜,收板栗,这些山货土产在山里不值钱,一运进大城市就值大钱。他一收好几车,有赔有赚。过去把这叫投机倒把,现在却叫市场营销,田国民搞市场营销,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城乡经济。
两个儿子不在身边。平叔一人种地一人吃,很舒服了几年。他就把所有的积蓄用来给自己做了一副寿材。寿材就是棺材,简称之为“木”,村里人请木匠打棺材叫“合木”,这“木”底子用的柏树,墙子用的是红心杉,红漆响堂,外表刷黑漆,前后刷了三遍,用了十三斤生漆。儿子不回来,就给来世修一个好房子吧。
“木”终于“合”好了,平叔突然想试睡一下,听说睡了木,腰不痛的。木匠三脚两手就把那黑棺的盖揭了,平叔吃力地爬进棺材,然后慢慢放下身子,把自己仰躺在那长方形的红木盒子里。木匠问:“伙计,感觉怎么样?”“好,可以。”木匠哐一下把那棺材盖子盖了。平叔睡在棺材里,眼前一片漆黑,思想就开了小差。老伴当年没有这样躺在棺材里就被埋了。你不怪我吧?在那边还好吧?还是一个人?没有找个“情况”?夜晚有人陪你说话儿吗……等木匠把恶作剧唱完,把平叔弄出来,他已经分不清阴阳了。
安闲的日子没过几年,平叔就遇到了麻烦。先是上山去弄柴,一脚踩了别人放的野猪夹子,把腿给弄断了。他找人弄些草药敷了一阵,风湿又发了,从此成了瘸子。地是种不了了,平叔就东挪西借度日。他早就想续根弦,或是找个“情况”,也好有个人洗衣做饭,可是,村里的年轻女人都进了城,年纪大的有儿有孙,不肯离家。现在,谁还肯来一辈子侍候瘸了腿的平叔。平叔想喊一个儿子回来,这才想起这两个东西已经好几年没和家里联系过。去村里问,也没人知道他们的行踪和地址。
田国民这次回山里来算得上是衣锦还乡,虽然还是个光杆司令,但已经不是村里那个追狗撵鸡的小痞子了,他上身穿着花格子衬衫,下身是女式九分裤,手里拿着“大苹果”,说起话来夹着一些半调子广东腔。老村长覃建国大发感慨,说,你看,年轻人出去闯闯也好。谁说不会种田就没饭吃,现在是不种田的比种田的吃得还油,穿得还光。
听说田国民回来了,讨债的人接二连三就上了门。来要的多半是他爹的陈年旧账,这小子倒也不耍赖皮,只要身上能搜出钱来,他就还,但有一点,他死活只认还一半。问他为什么只还一半?他说,我这是依法办事,钱是爹借的,爹是兄弟俩的,债当然要二一添作五,一人还一半,另一半该我哥来还。他哥多年前出去了,开始还打个电话,后来就断了,有人说他在一个有钱人家上了门,那家人不认这门穷亲,有人说他是在搞传销,是死是活不知道,反正一直没回过村。债主一想,这欠账本已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现在能得到一半,总比一分钱没得到要好,债主也就认了。
小儿子回来了,平叔每天给白虎神装香磕头也就懒散了,他的肚子不再天天挨饿了,嘴里也不再流清水了,他找小儿子说话,狗东西爱答不答。他给小儿子献殷勤,小儿子竟然说他讨厌。你狗日的回来跟不回来不都一样!他就开始谋划另一件事,他最害怕的事就是怕死在屋里没人管,被蛆虫吃。儿子回来了,照说该了却了这桩心事,但知子莫如父,他料定这小儿子还会再跑掉,所以,他就想抓紧时间把自己的后事安排好。最近,村里有人回来给老爹修墓立碑,大五厢,黑色大理石的碑面子,气派得很。那样的气派平叔自知享受不到,对门的鲍玉富年纪轻轻就给自己打了一通生祭碑,碑立着,只把死期空着,把墓穴敞起。平叔去看过,不大不小,很是羡慕。
一年前,平叔就按照神仙的指点,撑着个小板凳在山湾里为自己物色到了一处吉穴。就在那有鸟窝的大树边,那块地大约有三分地,是洪家让的,平叔用一块五分熟地和他换了。谁知道没换多久,洪家一家子就搬进城去了,这让平叔愤愤不平好久。
选好了吉穴,平叔就在吉穴周围栽了几棵青叶子树。天晴的时候,他爬上山去,在那块地上仰天躺一会儿,他要体会一下死之后住在那吉穴里的感觉。有时候,他会一直躺到太阳落,星星起。这里地势比较高,满天的星星又大又亮,小儿子当年要他给摘星星,没想到这里是可以伸手去摘的。从这里能看到大树上的鸟窝,乌鸦和喜鹊打过仗之后各占一棵树,各做了一个窝,最近大约在抱蛋,不再吵闹。从这里还能看到公路上跑的汽车,能看到山下村委会的蓝球场,能看到新修的卫生室,能看到村长卖酒的小商店,能听到狗叫。听说村里还要安路灯,晚上走路不用打火把了。难怪一家一家都跑下去了,都去“城镇化”了。平叔感到无助,越发放心不下死后的日子,在那边不知搞不搞城镇化?搞不搞火化?他怕烧,死了还烧掉,那不痛吗?
他要田国民赶快拿钱出来给他打墓碑。田国民说,死了再说。平叔说,死了就来不及了。田国民说,这事还得跟哥商量。哥杳无音信,等于不商量,平叔就寻死觅活。皮扯不下来,平叔就想得到村支书的支持,平叔讨好似的对村长说:“还是你们共产党聪明,只让生一个娃,我要是早知道是这样的结果,我也去入了党,只生一个。”村支书却说:“生一个少了,现在让生两个。你老有两个,不多不少,是模范哩。”平叔心中就一阵悸动,为生这个老二,害得我那可怜的老伴也死了!跟大儿子也生分了,把我一个人甩在阳世上这么多年,像一只落单的老乌鸦。
小儿子不肯给老子打墓碑,支书也没得法。金钱世界,没钱,你就没有发言权。正在这时候,村里又开始评“低保”,很多人说这次给平叔一份,也有人反对,说他有两个儿子,凭什么给?低保是给最困难的人以生活的最低保障,每月55块钱。平叔知道,从盘古开天到如今,从皇帝到总统,再到主席,只兴收皇粮国税,偶然发点救济粮,但从来没给老百姓发过“低保”,还月月给发,发工资似的。平叔把这钱拿在手中看了很久,不知这钱用不用得长。
买一包盐,只要几元钱,油一壶,十几元,最便宜的米买一袋,辣椒,自己有。拿了几个月“低保”,生活有了保障,平叔就底气十足了。他对小儿子说:“我现在有中国的低保工资了。”他不说国家的,他爱说中国的,中国的!更精彩的是后一句:“老子不怕你跑了!”他说这话时,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惬意,有一种挑衅味儿。没想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小儿子淡淡然说:“那你就去找中国跟你打墓碑,你不要找我缠了。”平叔想打小儿子一个耳光,等他把手挥到半路,就被那狗东西给接住了。说说不赢,打打不赢,他想了想,就拉了小儿子来找村支书断案。
平叔坐下去容易,站起来很吃力,他大声说:“支书,我小儿子歪纠,你给我评评理。”这小儿子比村支书小不了多少,他把染成了金黄色的头发朝后一扬,笑了笑,算是打过招呼。村支书听了投诉,就劝平叔,说:“这好日子才开头,要好好活着,不要去想死的事,死还早着哩。我们正准备在中心村给你修新屋、洋房子,到时候搬下山来住,又热闹又方便!”
平叔听说要给自己在山下修新屋,还是洋房子,不免心中一动,就说:“叫化子也不想死哩,但我穷怕了哇,我苦怕了哇,现在不说定,他们真的就不管我了哇,死在堂屋里都没得人埋呀。”
博士了解平叔的心事,说他是被生活压垮了的老人,一时半会无法重新树立起信心和勇气。最好的办法,就是顺从他的心意,来慢慢抚平心底的创伤。村支书听他说得有些理,就同意。但是,田国民还是强调爹不是他一个人的,他哥得承担一半,哥不回来,这事谈不拢火。村支书说:“那你哥就负责打棺材的钱,你负责打碑造墓。”田国民眼珠转了转,说:“那要是我搞了他又不搞呢?要搞得同时搞。”遇到了忤逆子横绊筋,村支书也把他没得法。
夜鸦在这个山头叫几声,又跳到那个山头叫几声,灰鸮利箭一般刺穿晨雾,把啸声拉得老长老长。平叔睡不着觉,又无法和这些猛禽说话。慢慢的,平叔感到,原先只以为没饭吃是世界上最难受的事,现在突然感受到还有比没饭吃更让人难受的事。村子突然消失了,没人和你说话了,好多天见不到一个人影。除了天上的鸟儿,地上的虫子,见不到一个活物。他就想到了从前的狗、猫、鸡、牛、猪。要是老伴在世,这些家里都有。如果家里都有,那儿子还会跑吗?
县里的钱拨下来了,村支书对田国民说:“给你家修新屋,房子由公家修,地基归你们自己打,搞牢实些。”小儿子说:“你们要修你们修,我不搞。”村支书说:“打地基预算有一万块钱,你打就把这钱让你赚。”小儿子还是不搞。村支书就生气了:“这里是你的根基,不只是为了你爹,你这个混蛋!”
田国民去县城转了一圈回来,忽然满脸堆上笑容对爹说:“爹呀,我们来整一次酒吧。”平叔显然对整酒很有兴趣,就问:“你又没接媳妇,有什么酒好整?”“你就说你满了八十岁,我们整寿酒。”“屁,你咒我?我还只七十不到,怎么就八十岁了?”“那就整个跳丧酒,跳活丧。你自己看着整,你百年之后我们就照着办,哪些地方要改进,你当场说,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照你的办!”
听说平叔要整跳丧酒,跳活丧,稀奇!村里老人都说田国民成了大孝子哩。老支书覃建国却说,这小子怕是想借整酒收人情钱哩,这么多年,他们家只有送情的份,只出不进,自己没整过一次酒,也是该整整。
对跳活丧最踊跃的竟然是扶贫队的博士,博士是从大城市下来支农的知识分子,博士写论文时知道武陵山中有“跳活丧”的习俗,却從没见识过,现在让他给碰上了机会,岂肯轻易放过?他去见了平叔,又和田国民谈了很久。他说:“你家多年没办过大事,我支持!我要请人来摄像。”田国民说:“那不行,要是在电视上一放,还说我搞封建迷信,要罚款哩。”博士说:“这你放心,上面要是有人来问,你就说是我让搞的,我这是在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田国民说:“你又不是县长,谁怕你?”博士说:“县长我认识,我有办法说服他。我还要把‘满堂音剧团请来唱戏。”田国民说:“那请不起的,几千块钱搞一场。”博士大包大揽,说:“田国民你就只当好大孝子,剧团算我请的,我送一台戏给你老爹祝寿如何?”这事当然划算,只有傻瓜才不搞。
博士果然有办法,他把剧团请来了,把道士也请来了。剧团是全县有名的“满堂音”小剧团。这个剧团有些历史,很受群众欢迎,得过文化部的“乌兰牧骑”奖,有一个名人给他们题过词:“一支轻骑走四寨,满堂好音动八方。”“满堂音”一来,充气的红彩门一搭,果然惊动了四面八方。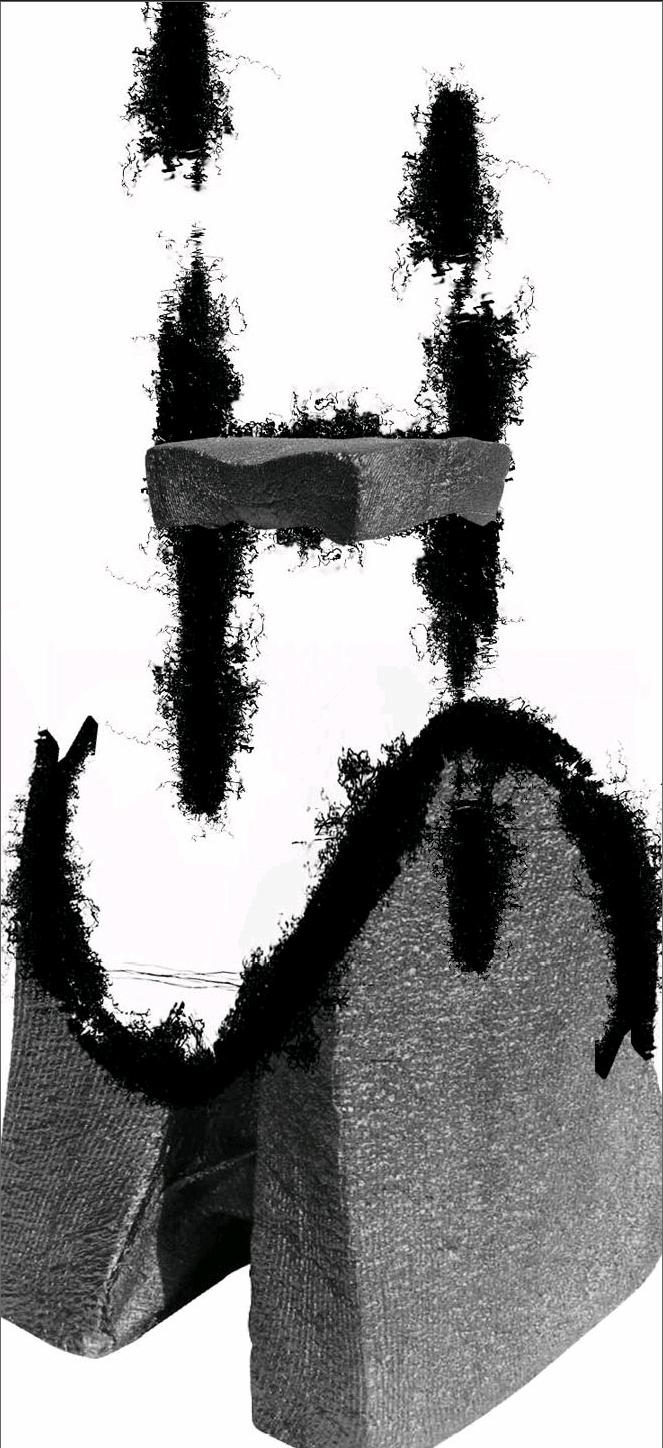
夜色中,山间出现无数火把,电筒,星星点点,慢慢汇成长龙,弯弯曲曲向平叔家住的山上拥来。其中很多人是原先的邻居,他们听到消息,说还住在山上的平叔要跳活丧,心中都突然冒出一种情怀,动了乡愁,恰好时近清明,便想借此回来祭祭祖,既是一种牵挂,也是一种告别。
这个村没通电,有人抬来了柴油发电机,大电灯泡一安,照亮了半边天,那些蚊子、飞虫都朝灯光里扑,前仆后继,视死如归。那机器里的锣鼓喇叭惊天动地,回声阵阵,大树上的喜鹊乌鸦都噤了声。只有猴子在山尖上时不时吼几声。首先是老支书家的那条狗带头冲上山来,各家的狗都跟着跑来助阵,围着喇叭狂吠。接着就是一群留守的孩子,追着狗而来。
田国民请金幺爹当“都管”,都管就在厢房设了桌子,放下一包烟,请人坐在那里收钱记账。平叔家中早有一本账,某年某月谁家接媳妇,送了50元钱,谁家生了儿子,送了20个鸡蛋,谁家死了老人,上了100元情。小儿子让爹把账本拿出来看了一遍。这一次,很多人是来还旧情的,关系深的,你送去100,还回来就200,关系一般的,送去是50,还来还是50。像平叔这种家庭,能把送出去的再收回来就很不错了。新账得记清楚,以后得还。
白虎寨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在家门口看到“人大戏”了。老人们对平叔的“活丧”最为关心,孩子们则对看戏更感兴趣,管他唱歌、跳舞、柳子戏、傩愿戏、皮影戏还是猴把戏,锣鼓一响,脚板子就发痒。
平叔的房子在这山里算是有些年代了,是栗树做柱杉木装壁盖着布瓦的吊脚楼,年久失修,就像一个久病的老人,但还顽强地站立着,像一只老熊舍不得离开最后的一片林子。帮忙的人从屋后竹园里砍了几根高而粗的金竹杆竖在门前,做成灵幡,这法事做几天就要竖几根灵幡。灵堂就设在堂屋里,旧屋一丈二的开间,不大,放下棺木之后就很挤,道士们已经在灵堂里挂起了花花绿绿的神像,写了表,画了符,去房屋各处贴了。
大大一个“奠”字,黑墨还在流,这字是博士写的,有些书法的功力,有学生把“奠”字大声认成“莫”,“莫”就贴在黑棺头正中,把阴阳两个世界隔开来。晨雾迟迟不肯散去,这气氛就很有些天上人间的味道了。
“亡人”未亡,平叔兴致很高,他想找一件新的衣服穿穿,找了一阵没找到,脚上的破鞋沾满了泥,博士急忙把自己的新球鞋给他穿上,又在那黑棺头之前放了一把靠椅,让平叔坐上去。平叔卷了一支大喇叭筒叶子烟拿在手上,偶尔吸一口,吐一下口水,脸上笑得双眼都眯缝了。他摆着样子让博士给他照相。一只孤独的岩鹰在高空盘旋,盘旋,对山间的热闹不以为然,偶尔发出一两声凄凉的啸叫,但电器发出的声响盖过了一切。平叔在品味着自己的节日。
打一通闹台锣鼓,恭请各路神仙下界。神仙界说不定也在整顿作风,一接到邀请,不再讨价还价。各路神灵到了就升帐视事。平叔看着几个年轻的道士跟着老道士念经。这些年轻的道士大都是乡村辍学者,有的小学毕业,有的是初中生,根本就不懂什么佛教道教,他们连伙居道人都算不上,跟了师傅当孝子,做法事,装模作样念经,跟外出打工一样。他们画的符有谁认得呢?他们念的经文有谁听得懂呢?或者说有谁需要认得?有谁真想听懂呢?他们知道哀家要的也就是一种形式,一种气氛,你总不能让哀家冷冷清清吧,默哀三分钟又不习惯,也不能让孝子去长哭三天三夜声嘶力竭吧。从这一点来说,乡村的民俗其形式就远比内容重要。
田国民今天收拾得比他爹还整齐。他忙进忙出,见了生意人就拍肩膀,见了长辈就递烟。说媒的人都在他身上多看了几眼,人人夸他是个大孝子。父子俩多年来所受的冷眼、多少的自卑,都被道士们的仙乐给融化了,或多或少的懊恼、歉疚,都被一阵阵鞭炮炸得粉碎。平叔心中还生出一些父子间的依恋之情。
来了不少人,田国民多年不走亲威,很多认不得了。凡是有人来吊孝,孝子应当上前跪谢的,田国民做出很忙的样子,来去匆匆,加之今日的“丧事”有很大演习的成份,所以,孝子跪谢的事也就免了。客人们给“亡人”磕头也就是对平叔问一声好,有些敷衍了事。要是真办丧事,上了礼的,便会有人送上孝布,近亲后辈就赶快把孝布带在头上。打过招呼,然后吃茶抽烟,找地方去坐,和熟人打招呼。有几处牌桌上已经围满了人,哗啦啦洗麻将,不准赌博,大家就打小麻将,一块钱一盘;打扑克的在吆喝着赶猪,打双升,也打点小钱,都说不带点彩玩得没滋味。流水席在不断地开,来的人都自己去找地方坐席,喝酒自己去塑料壶里倒,跟喝水一样。
从前,办红白喜事,最难的就是办席,杀猪、剁柴、推磨、借桌椅、打豆腐、请厨师,要很多人帮忙,如今这些东西都能去镇上买到,镇上还有了红白喜事服务队,厨师桌椅酒菜一应俱全,主家只认掏钱就行。从前,都穷,能吃,三碗饭,还见肉就抢,满桌饭菜吃得精光。如今大鱼大肉,一席开过,盛下一半,平叔看了心中绞痛。
到处在喧哗。平时没地方说的话,现在有了倾诉的对象,东山的土地南山的菩萨,大家尽情地说个没完。特别是从村子里搬走的人家,这次回来,就特别兴奋,到处看,见了乡亲特别亲热。博士也精神亢奋,他对眼前的一切如获至宝,扛着摄像机到处拍。见有人拍照,道士们就格外卖力,把锣鼓敲得有板有眼,把经文念得抑扬顿挫。博士拍了道场,厨房也拍,厕所也拍,牌桌也拍;狗要拍,老人要拍,美女更要拍,被拍的人就羞涩躲闪,好奇的孩子追着看热闹。有的老人不让拍,怕把魂给摄了,听说拍一次要少一截阳寿,这好日子才开个头,谁肯折寿?
从前,白虎寨办丧事,孝子最少得哭三天三夜,喉咙嘶哑了,眼睛红腫了,根本就哭不出来了,亲戚就来陪着哭,也是时断时续,哭到最后,气氛就不很热烈了。如今,居然出现了代人哭丧,你给他钱,他上山来帮你当孝子,哭爹哭娘,哭诉二十四孝,哭得哀天哀地。他们往机器里塞进一张片子,只卡拉一下,就OK,大喇叭里就冲出来惊天动地的哭丧歌。现代化的机器终于把孝子们从艰难的长哭中解放出来了。听说山下有一户人家,为一笔财产闹得生冤死仇,三个儿子弄得爹妈像讨饭的。前不久,妈死了,村里人没几个愿意拢堆来帮忙,三个不肖子就想在乡亲们面前显摆一下,一人请了一班哭丧的,三个班子打擂台,对着搞,硬是把全村的鸡呀狗哇猪牛羊都吓得全跑到山上躲起来了,剩下的一个老爹也经不住闹腾,心脏病发作死了。
用塑料皮做成的彩色拱门,粉红色,用鼓风机一吹,就像那叫驴子胯下的槌子,一挺就竖起来了,高如门楼。这样的彩门竖了好几个,本来应该是黑色或是白色,人家只有红色,是专门办喜事的,平叔这活丧也可以叫白喜事,田国民也就同意了。能唱歌的机器真是受欢迎,不但死人欢迎,活人也欢迎,而且很快得到了普及,不但普及,还推而广之。生了孩子、结婚、整寿酒、上学、参军、升官、彩票中了奖,猪仔下得多,凡有喜事都用这机器,把那个什么“我们走在大路上”、什么“百鸟朝凤”、什么“干一杯”的,还有什么“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什么“冬天里的一把火”,再放邓丽君,放李玉刚,一个一个唱得落花流水。
今天办的是活丧,“亡人”平叔就活生生笑眯眯坐在那里,慈祥而宽容。有几只蚊子落在平叔手上,平叔很温和地看了看,没动,也没去拍它们,还说:“吃吧,吃吧,我老了,没血哩。”平叔很受用,坐了一阵,相也照了,烟也抽了,口水也吐了一地,就听戏文。他从小爱看皮影戏,现在不容易看到了。他曾经有过雄心壮志,要赚很多钱,要修很大的房子,要给两个儿子娶媳妇,生一桌孙子,每次整酒都要请大戏。谁知道,老伴产后病死了。村里没有卫生室,也没有公路,就这样眼睁睁看着心爱的人死去。
这边的衰乐还在唱,那边戏台子上的歌声还在飞扬,村支书来问平叔:“你满意不?”“满意满意。”“那还想不想死?”“这次死过了我就再多活几年。”“好哇!镇上的新房子快修好了,你就要到镇上去享福了哇。”“好,好。”平叔其实不想离开老屋场,这里留下了太多的东西,一时半会割舍不掉。
人山,人海,赶集,放炮,神仙唱歌。突然,一阵大风吹过,把一根灵幡吹断了。掌坛道士一惊,道士们全都跪倒在神像前念经。都管金幺爹急忙叫人去把灵幡竖起来,不让声张。场坝子里有一棵迎春树,树叶子都还没长齐,鲜艳的花朵却开得十分灿烂,这是白虎寨初春的第一树迎春花。
吃罢饭,大家就把灵堂屋前的场子清开,人群都围到花树下来,这棵迎春树已经在这里生长了几百年,它见惯了人间的哀愁和欢乐。听说要跳丧了,剧团也停了家伙,演员们都跳下了台子围到花树下来,他们很少看到过跳丧。
博士此前几天几夜没睡觉,精神好着呢,他翻看《太平广记》,找到了有关“五溪蛮,父母死,于村外阁其尸,三年而葬,打鼓踏歌,亲属饮宴舞戏……”他又核查唐人樊绰的《蛮书》:“巴人祭其祖,击鼓而祭,白虎之后也。”见了这些记载,他确信这种跳丧的风俗历史是十分久远的,只是这跳活丧是何时兴起来,不得而知。
博士问金幺爹:“下面还有些什么内容?”金幺爹故弄玄虚:“多着哩,好看的还在后头。”
博士就对都管大声说:“你们只管原汁原味地搞哇!”金幺爹就对着平叔高喊一嗓子:“老伙计,我们今朝来好好地陪你玩一天。”
几支牛角同时吹响了,鼓点咚咚,鞭炮轰炸,大家齐声喊:“撒忧儿嗬!撒忧儿嗬!”一时间,山鸣谷应。平叔的腿脚不方便,无法挤到花树下去,他仿佛觉得自己已经从阴间走了一遭,已经变成了游魂,飘荡到阳世来了,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哪家办喜事?又是哪一个老朋友走了。
歌师一面击鼓,一面就起了板:
“呜呼哀哉呜呼哀 ,
連喊三声呜呼哀 ,
人死如同一捆柴,
倒在地上不起来,
哭的没得唱的好,
跳脚摆手玩起来!”
悠扬而又深沉的古歌声中,一帮人迫不及待进了场,张二叔、王二叔是一定要上场的,都无队长也上了场,他们做出各种造型:猛虎下山,燕儿扑水,牛擦痒,狗连裆,鹞子翻身,他们玩出各种花样。有的年轻人在专注地看老人跳丧,有的年轻人眉来眼去,在人群里找自已的相好。金小雨挤在人丛中,他故意挤在秋月身后,悄悄用手指去戳她,秋月回头一看是小雨,也就站着不动,让他戳,小雨见秋月不动,就有些放肆地往她身上挤,恨不能把身体的一部分挤进她身子里去。闻着秋月的头发香味,小雨绷紧了四肢,感到特别地受用。
平叔年轻时就爱跳丧舞,现在看着听着,手脚就有些痒,筋就抽动起来,身上突然就有了力量,那瘸了多年的腿就像通了电似的。他猛地一跃而起,踉跄了几步,就朝花树下冲过去,居然加入了跳丧的队伍。
大家看到瘸子平叔突然站了起来,而且进入了跳丧的人群,开始是惊愕,继而一片喝彩。平叔按捺不住激动,满脸通红,神助似的,恣意而跳,嘴里还大声地呼喊着:“撒忧儿嗬!撒忧儿嗬!”天地仿佛也在一起跳动,要让他把多年没跳动的舞步都挥霍一空。几个老人兴致极高,都围过来,和着平叔的舞步跳动:猛虎下山、犍牛拉犁、怀抱子、播五谷。是如此地生动,是如此地古朴,是如此地忘情。跳着跳着,就发现平叔有了些踉跄,有些妙曼,大家以为他在跳醉舞,就更加喝彩。平叔眼花缭乱,他在人群中看见了老伴的身影,还是那么温顺,那么漂亮,朝他回眸一笑,他像吃了好酒,特别地兴奋,心跳加快。突然降临的太多笑脸太多欢乐把他弄得有点像高压的气球,但这气球被放置太久,老化了,就像被扎了一个小小的洞,什么地方在咝咝地放着气。突然,平叔双手向上,跃了一步,再努力跃一步,一下子就扑到地上去了。
村支书发现平叔倒在了地上,立刻扑过来,她毕竟还年轻,又是个女孩子,看到平叔暴睁着眼,手就不免一阵颤抖。几个老伙计手脚迟缓,也都扑过来。平叔是对活丧感到满意呢还是对眼前的场面感到满意呢,是被死亡迫近的信息击中了呢,还是对神灵表达一种臣服呢?平叔是一个正在与死神过招的老农民,他走过了生命的沼泽,透支了体力,来到了新房子的大门口,却没有了力量跨进门去。
平叔这个样子,把博士吓了个半死,这事是他张罗的,没想到会出这样的意外,在学术专业面前,他游刃有余,在突然事故面前,他不知道如何是好,先自吓哭了起来。倒是都管金幺爹冷静,他走过来把平叔翻过身子,用手指去试了试鼻息,又翻了翻眼,他在平叔的脸上拍了一巴掌,说:“老家伙是真死了。”小儿子田国民大喊了几声爹,哇地一声嚎哭起来。随着田国民的一声哀嚎,整个场子上立刻僵住,一片死寂。
金幺爹是人上人,当了一辈子知事客和都管,很见过些场合,他站在那里,联想到那经幡的突然倒地,他猛抽了三支烟,先对田国民说:“你爹这是走的顺头路,你不要怪别人。”田国民点头。金幺爹要个回扣:“说话算数?”田国民点头。金幺爹就对博士说:“别哭了,你不是说这是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吗?你不是想照相吗?前面搞的那都是假的,下面才是搞真的。我们‘就汤下面!”金幺爹又对女支书说:“这是平叔的福分,场子都支开了,不可能再搞第二场了。”支书问:“哪怎么办?”金幺爹力挽狂澜,大喊一声:“道士接着念经,戏给我照演,大家接着跳丧!接着跳!再跳两盘哒就开席,搞酒喝!”
都管发了话,寨子又一次喧闹起来。黑棺头上的奠字墨迹已干,牢牢地贴在了上面。此前,平叔还心满意足地坐在这里让人给他照相,眨眼间,他就永远躺在这“木”里头一动不动了。
平叔的暴亡给白虎寨带来的似乎不是悲哀,而是无尽的欢乐。住在这里的最后一个老人死去了,喧闹的村寨在夜的深处尽情地宣泄着不快,被冷落的白虎寨终于找到了一种释放怨气的方法,大家尽情地喊叫着,跳动着,扭转着身子,用脚死命地蹬踏着大地,像踩踏着仇人的尸首,也分不清天上地下,人间梦境。大家奇怪着,平叔临死居然不瘸了,这是道士的法力?还是回光返照?从默默无闻一生,到轰轰烈烈离去,就只眨巴了一下眼,这让活着的老伙计们浮想联翩。
不知谁忘情高唱一声:“亡人死了好有福,睡了一副好棺木。”
有人就和:“撒忧儿嗬!”
又有人唱:“在生种哒千斗田,死哒不带一粒谷。”
众人和:“撒忧儿嗬!”
有人唱:“养儿防老狗扯蛋啦!”
有人接腔:“国强民富才有福哇。”
有人接着高唱一声:“你真是一个好社员,一世的英名留在后。”
众人齐和一句:“撒忧儿嗬!”
村支書想起了和平叔才说不久的话:“你满意不?”“满意满意。”“那还想不想死?”“这次死过了我就再多活几年。”“好哇!镇上的新房子快修好了,你就要到镇上去享福了哇。”“好,好。”
平叔一个人走在通往另一个世界的路上,寒风刺骨,云遮雾绕,飘忽不定,他时不时回过头来张望。
撒忧儿嗬!撒忧儿嗬!难道真的能把一切忧愁都撒掉吗?这些梯玛唱过的古歌,忽高忽低,亦长亦短,在这深山野岭,唱到情浓之处,没有了悲伤,没有了怨恨,只有对逝去的怀念和温馨的送别。
平叔死了,大儿子还是没有回来。等了三天,田国民就把爹埋了。村人都骂大儿子不是个东西。
小儿子抱了灵牌跪在坟前,大树上的几只喜鹊听见田国民说:“爹呀,您可别怪我。”
责任编辑 何子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