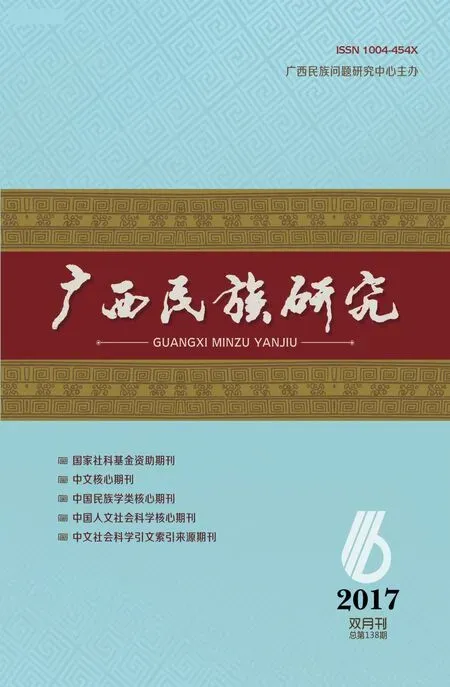主体间性视域下的民族志书写*
黄治国 李银兵
主体间性视域下的民族志书写*
黄治国 李银兵
科学民族志不断暴露出来的缺陷和后现代民族志在方法和视角等方面的种种实验,为我们开启了一扇理解和探讨民族志书写的新门。主体间性视域下的民族志书写,基于对主体性写作传统的批判与超越,重在把实在主体转向关系主体,进而去探讨不同主体间如何达成共识和互识等相关问题,最终实现理顺不同主体间关系的目的。而厘清民族志书写中的多重主体及其关系,不仅能使民族志书写的真实性和人文性得到强化,也昭示了公共人类学成为可能。这些都是当代民族志书写的本质诉求和发展需要,定能推动民族志书写的新一轮革新。
主体性;主体间性;民族志;公共人类学
人类学是以研究人及其文化为主的学科,田野调查和民族志作为推动其学科发展的“两翼”,一直以来不断受到人类学者的重视,并产生了众多的理论成果。但随着《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天真的人类学家》《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等一系列民族志作品的出版,人类学界长期存在的各种争议和丑闻被揭露无遗,进而导致“在人类学内部,民族志田野工作和写作已经成为当代理论探讨和革新中最活跃的竞技舞台。民族志的注意力在于描述,而就其更广阔的政治的、历史的和哲学的意蕴而言,民族志的写作就更富于敏感性,因为它将人类学置于当代各种话语(discourses)中有关表述社会现实的问题争论的漩涡中心”[1]8。接踵而来的人类学理论反思和范式革新,则进一步表征了“表述危机”在民族志书写中的严重性。“缺陷和不足常常标志着知识的魅力,它们象征着一种重新系统地阐述老问题和提出新课题的努力。”[1]10在西方,象征人类学、结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派、反思人类学、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民族志文本和理论范式层出不穷;在中国,诸多学者也从理论和操作层面对于民族志书写进行了反思与建构,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了民族志书写的“中国忧思”。但令人遗憾的是,诸多的民族志作品更多地关注民族志书写的形式和内容,而较少关注民族志书写主体这个中心,这极不符合民族志书写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和现代社会的要求,因为“现代性的特征正是在于:人作为主体既是他所建构和控制的世界的基础,又是这些世界的中心”[2]31。正如保罗·拉比诺所说的那样,“对民族志写作中的表征危机的元反思(metareflections)表明了人类学关注的重心已从对它与异文化之间的关系,开始转向对我们文化中的表征传统和元表征的元传统(metatraditions of metarepresentation)的一般性关系关注。人类学与它的‘他者’之间宏观和微观的权力话语关系终于开始面对质询。”[3]304因此,“当所有的民族学家都理解在他们的资讯人和他们之间正在发生某种相似的东西的时候,民族志将取得一个巨大的进步。”[4]158基于此,本文以现代社会广泛流行的主体间性理论为分析视角,力图从民族志书写中不同主体间关系入手,分析实在主体向关系主体转换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关注关系主体中主体间的共识和互识达致的方法和策略,建构主体间性视域下的公共人类学,最终为民族志书写的真实性和人文性及未来发展提供一条有效的路径,以就教于大家。
一、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民族志书写的时代诉求
一般而言,民族志发展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业余民族志、科学民族志及后现代反思民族志。业余民族志写作的理由和阅读的动力主要来自“新奇”,它是业余写作者信手拈来、自由放任的产物;科学民族志则以客观而成立,力图达到文本是体现“科学”的工具的目的;反思民族志认为知识界勇敢地承认民族志研究的现状与理想之间的差距,并做出反思性和真诚的承诺,因而守护住了职业“真诚”的底线。[3]译序15这都说明,“我们不是从参与观察或(适合于阐释的)文化文本开始的,而是从写作、从制作文本开始的。写作不再是边缘或神秘的一维,而是作为人类学家在田野之中及之后工作的核心出现。”[3]30但在写作和制作文本中,民族志作者“一言堂”发声的中心地位始终没有改变。仅在反思民族志中,由于“多声部”发声的出现,民族志作者的书写权威才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但这种挑战,都是广泛建立在民族志作者主导性基础上的产物。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在统一秩序下来探讨地方性意义,其结构和逻辑其实丝毫未受触动,一个已经定型的体系依然强加到了土著人身上,民族志作品的主调与色泽仍然是西方主义的。”[5]
主体性民族志书写弊端及其危害催生主体间性民族志书写的产生。主体性民族志书写弊端的彰显,在现时代的人类学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场著名的争论上:弗里曼和米德关于太平洋群岛上萨摩亚少女有无青春期问题之争、奥贝塞克里和萨林斯关于夏威夷岛屿上库克船长被杀的相关描述和阐释的真实性之争、斯图尔对孟朱关于种族屠杀和人权灾难描述的真实性的揭露以及蒂尔尼在《挨尔多拉多的黑暗》中,针对沙尼翁对雅诺玛玛族开展生物医学研究工程的目的及给当地人带去伤害的事实,进行无情批判和曝光。虽然引发这些争论的原因很多,但正如有的学者认为不外乎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民族志研究的职业道德、科学权威背后的意识形态广泛存在以及多元主义应该得以倡导。[6]不可否认的是,主体性民族志书写作者“一言堂”的书写方式,定是引发这些问题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正如作家罗兰·巴尔特说:“作家并未被赋予在一种非时间性的文学形式储存库中去进行寻选择的自由。一位作家的各种可能的写作是在历史和传统的压力下被确立的。”[7]204但实际情形则是,民族志作者往往把自己的“权宜书写”说成是“权威书写”,进而给读者带去一些误导。正如有的学者这样评价格尔茨描述的巴厘斗鸡游戏:“尽管格尔茨用现象学——解释学作为伪装,但其实在‘深度游戏’中并不存在从当地人视界(native’s point of view)出发的对当地人的理解。有的只是对建构出来的(constructed)当地人的建构出来的视角的建构出来的理解。”[3]107那么,这种过分强调民族志作者在书写中的作用和地位、把他者视为单纯的书写客体的做法,究竟会给民族志书写带去什么影响?总的来说,就是引发出人类学界“表述危机”的出现。具体而言,这种危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民族志真实性受到普遍怀疑;其次,民族志价值性受到下降;第三,民族志书写的客位方法受到批评;第四,民族志作者的职业道德和意识观念等受到批判。因此,要消除主体性民族志书写的弊端及其带来的危害,则需要我们对民族志作者与文化主体间的关系进行重新审视。这样,主体间性理论在民族志书写中就应运而生。主体性民族志书写弊端及其危害是主体间性民族志书写产生的客观条件和现实基础。
实验民族志的种种实验为主体间性民族志产生奠定实践基础。正如克利福德所说:“在传统民族志中,通过给一个声音以压倒性的权威功能,而把其他人当作可以引用或转写其言语的信息来源,‘被访人’,复调性受到限制和整编。一旦承认对话论和复调是文本生产的模式,单声部的权威就受到质疑,这种权威也被揭示为一门主张再现文化的科学的特性。”[3]44随之而来的实验民族志,充分体现了多重主体叙事的功能,给我们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民族志作品。虽然从总体上来说,在民族志书写中,作者的主体性地位还存在,但是多声部发声毕竟意味着一种新的书写方式的开始。心理动力学民族志、新现实主义民族志及现代主义民族志成为这种书写方式的代表。比如,新现实主义民族志的代表作《尼莎:一个昆丹妇女的生活与言语》,运用人类学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对话,去反映不同人对同一文化的反应和看法。而在现代主义民族志的代表作《摩洛哥对话》中,作者德耶尔把在田野对话中所获得的资料进行编辑和修饰,形成了以对话录为主的民族志作品。对话(discourse)的方法在民族志作品中得以很好地呈现,对话成为时下民族志书写的一种时兴的隐喻。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终究掌握笔杆子的人是民族志作者,因而这种对话在结构上就不对等,对话也就不是真实的,或者说这种对话绝不是处于平等地位的人们之间的对话。殊不知,在实验民族志的很多“对话性文本”作品中,主要通过对话、话语、合作文本及超现实主义这四种修辞方法,则为我们呈现出了另外一番景象。[1]103比如,在文森特·克拉潘扎诺《图哈米:一个摩洛哥人的图像》中,充分运用超现实主义修辞方法,通过对资料的高度剪辑,把文本作为神话描述出来,让读者、作者和文化主体一起去解读文化主体的心灵、情感等相关问题,以此来唤起人们对于他者的心灵世界进行关注。“实验潮流对民族志实践的探究和质疑,只能被视为是健康的。实验潮流应该被当作过程来理解,因为它展示了人类学的变迁。”[1]227总之,虽然实验民族志在总体上还属于主体性民族志书写,并且在处理民族志作者和文化主体关系上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主体间地位不平等导致作者中心论危险、主体间对话引发相对主义的产生、对话缺乏坚实的物质基础而衍生主观主义危险等。但不可否认的是,恰恰就是实验民族志作品中的这些尝试,比如,对话、沟通、多元书写等,为后来的主体间性民族志书写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主体间性理论的不断成熟为主体间性民族志书写奠定理论基础。近代哲学在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和培根“四假相”的引导下,从传统的形而上学本质论开始转向认识论,确立了以主体为主、主客二分的对象性思维方式。其中的主体性为主的认识论方法,后经康德“人为自己立法”和费希特的自我哲学得到了不断发展。到20世纪初,由于语言哲学的兴起,主体性哲学从此开始由盛到衰,慢慢地被以胡塞尔为代表的现象学派所取代。有学者这样总结现象学派兴起的原因:“从认识机制上看,作为本原和基础的个体主体性的出现是其构成有意义论题的前提;从自身逻辑上讲,其萌芽于近代主体性哲学的深刻危机中;从思维方式上看,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转换与思维方式的现代转型密切相关;从社会历史背景来说,其凸显的是当时社会发展困境的一种折射和反映。”[8]此后,主体间性正式产生并经历先验性主体间性、存在论主体间性、阐释学主体间性、批判理论主体间性等几个发展阶段,其理论在发展中得到了不断成熟。本部分笔者主要以现象学社会学奠基人之一许茨所主张的观点为例去分析主体间性理论。许茨的主体间性理论是对胡塞尔主体间性理论的继承与超越,其把主体间性理论从胡塞尔的先验层面转向了经验层面。正如他所说:“为了与我的同伴沟通我的理论思维,我必须放弃这种纯粹的理论态度,我必须回到这个生活世界及其自然态度上去。”[9]337“因为我们作为其他人之中的一群人生活在其中,通过共同影响和工作与他们联结在一起,理解他们并且被他们所理解。”[9]231许茨断言:“人认为他的同伴的身体实在,他们的意识生活的实存,进行相互沟通的可能性以及社会组织和文化的历史给定性都是理所当然的,这就像他认为他生在其中的这个自然世界是理所当然的那样。”[9]410其后,舒茨通过“我们关系”“视角呼唤”“接近呈现”“他人自我”等理想化模式把主体间性关系的思考推向操作层面,并引发了学界对主体间性的进一步思考。后来的哈贝马斯就把主体间性放在对社会历史的思考中,提出了其富有历史和现实感的交往沟通理论来,特别是强调了集体或群体的重要性,这是难能可贵的。比如,他说:“‘自我’是在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中凸显出来的,这个词的核心意义是主体间性,即与他人的社会关联。唯有在这种关联中,单独的人才能成为与众不同的个体而存在。离开了社会群体,所谓自我和主体都无从谈起。”[10]53“我无论是在肉体之中,还是作为肉体,一直都是在一个主体间所共有的世界里,集体共同居住的生活世界就像文本和语境一样相互渗透,相互重叠,直到相互构成网络。”[11]59随着主体间性理论的不断成熟,其本质特征逐渐彰显出来:“‘主体间性’的基本内涵是指在交往过程中所实现的人与人之间的统一性的关系。它也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即主体间的共识问题和主体间的互识问题。”[12]其主要通过交互联系性、独立平等性及可沟通性等特征来展现。因此,主体间性理论的不断成熟为主体间性民族志书写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总之,在对科学民族志书写的弊端及其危害的批判与反思中,在实验民族志书写的尝试和引导下以及主体间性理论的不断成熟中,主体间性民族志书写慢慢浮出了水面,并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民族志书写潮流。客观条件、实践基础和理论基础,多维视角的“力的共同体”促使了主体间性民族志的产生。主体间性民族志书写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因而是必然的。
二、从实在主体到关系主体:主体间性下的民族志书写
恩格斯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13]277王铭铭也说:“自己想做的是一种‘关系的民族志’,而不是整体的民族志和后现代民族志。我认为,要造就一种真正现实的人类学,我们的民族志研究要更注重对关系的研究,这个意义上的‘关系’绝非本土民俗中的‘关系’,而是一种结合了主位观和客位观、民族志与民族学方法的论述。‘关系’可以从内外关系、上下关系、左右关系及前后关系去看。”[14]279-280透过现象看本质。在不同主体间关系的分析中,我们慢慢找到了主体间性民族志书写的特点和优点来。诚然,主体间性理论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过于理想主义、有导向形式主义之嫌、缺乏客观根基等,但瑕不掩瑜,把其运用到民族志书写中,不仅会使民族志主体从实在主体到关系主体的转换,而且还会加强民族志书写的真实性和人文性。那么,主体间性下的民族志书写,具备什么样的理论特征和实践本色?
首先,不同主体在民族志书写场中是一种共在、共享及共感的关系存在。“共在”说明在民族志写作中,民族志作者和文化主体不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间的平等关系,文化成为链接他们关系的不证自明的先在条件。也可以说,对于文化的求解把民族志作者和文化主体先在的、平等的统帅在一起。“共享”是指民族志作者和文化主体都有互相影响的作用,他们之间可以用共通的经验方式来经验文化这个共同的世界。这就为作者和文化主体去认识、理解及互识文化提供了一种可能。“共感”说明尽管我们每个人在时空上有着自身的独特性,也有着对文化不同的感受和认识,但是我们之间不同的感受和认识却可以通过角色互动等方式来形成对于文化的共同感受。以上共在、共感、共享关系的建构为作者和文化主体之间建立平等关系和协作关系提供了保障,这就为摒弃以往民族志作者把文化主体有意或无意忽视、歧视的做法,提供了批判和认识前提。随之而来的是在主体间性民族志书写中,我们再也不会看到像马林诺夫斯基用诬蔑性的语言咒骂当地土著的生活“好像狗的生活一样无聊”[15]158-159之类的话语。
其次,不同主体在民族志书写场中要能做到交互理解。在民族志书写中,作者如何理解文化主体、文化主体如何理解作者,这是他们达到沟通和理解的基础。在西方,许茨运用了诸如“接近呈现”(appresentation)、视角互易性(reciprocity of perspectives)、“面对面关系”(face-to-face relationship)、“我们关系”(we-relationship)、“变形自我”(the alter ego) 等理想类型和方式去“说明参加互动的个人都失去了各自的经验结构的独一无二性,从而获得了普遍性与无人称性即社会性的特征”[12],他们之间能实现理解和沟通。在中国,朱炳祥教授运用“互镜”模式去说明主体间沟通的认识论基础,虽然其认为的主体主要是指民族志作者,但在其分析不同“主体”和“客体”关系时,则是间接运用了和主体间性同样的认识思路和分析办法。他从中国传统文化视角入手把民族志作者分为三个主体,即知性主体、观念主体和写作主体。他进而指出应该放弃科学主义的实证主义的“镜式”传统,进而选择通过“互镜”的民族志形式——在“主体”与“客体”相互映照的多重影像中,达成主体“认识自己”的目的。[5]虽然其互镜模式中的“客体”包括文化主体,但更多的则是指向田野中的一切事项,因而正如他自己认为的那样,主体民族志下的认识仅仅具有相对的意义与价值。[5]笔者认为其主张的主体民族志有倒向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危险,其主体民族志范式存在的一个最大不足在于忽视了文化主体的重要作用,而更多的是对民族志作者这个主体进行多次解构和建构而已。一般而言,文化不外乎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种,物质文化是客观的文化,精神文化是主体内在的精神结构和心灵图式。民族志书写主要是发挥文化描述和文化批评的功能,也就是说民族志书写的主要目的是求真和至善。求真和至善是处于对立统一中的一对矛盾,在其中,求真是第一位的。民族志理应是民族志作者和文化主体一起对特定文化的翻译过程,物质文化自身不会发声,因而作为主体的民族志作者和文化主体之间达到互信、互通就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笔者认为在主体间性下的民族志书写中,要真正做到对文化客观真实的把握,应该加强对于民族志作者和不同主体间关系的反思,把朱炳祥教授主张的互镜模式和现象学社会学主张的交互沟通与对话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最终实现不同主体间的互融和互信。
再次,不同主体达致共识和互识是主体间性民族志书写的重要条件。正如王铭铭教授认为的那样,民族志书写就是民族志作者对文化的翻译过程,“民族志作者把自己研究的最终成果称为‘翻译的作品’,为的是强调这个文本背后还有‘作者’,还有‘事实’,而他们自己只不过是某些文化意义的传递者,是‘造化’文化理解桥梁的工程师。”[16]189因此,为了避免对于文化翻译的“诱”和“讹”结合所造成的文化误解,我们应该吸引更多的主体进入民族志书写。这种情形在中西方后现代民族志文本中,都已得到体现。比如,在西方,“对话性文本”就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代表。但马尔库斯和费切尔认为对话性文本需要面对“两种危险”和“一种批评”:“一种危险是现代主义的探究可能不知不觉地陷入田野经验的公开表白和忏悔之中;另一种危险是,它可能不知不觉地陷入衰弱的虚无主义之中,使得我们不可能从民族志经验概括和归纳出任何东西。最近的一种批评已经提出,既然民族志作者终究是掌握笔杆子的人,那么现代主义实验所表述的就不是真实的对话。”[1]102-103在中国,为了更好地阐释其主体民族志主张,朱炳祥教授进行了一个“微型民族志”的个案书写。在行文中,他提出了包括作者、文化主体和评论者的“三重主体”说。但正如在文中处于评论者身份的“第三主体”刘海涛指出的那样,主体民族志微型实验中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有无必要、有无可能让“第一主体”的自由讲述更进一步;主体民族志是消除“表述危机”的一种解题思路,但有可能并不是唯一路径;忽视了田野观察的重要意义;研究队伍亟须培养问题。[17]纵观中西方以主体为主的民族志书写现状,都存在着未把不同主体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描述整体的缺陷。主体间性民族志提倡在不同主体平等、沟通的基础上,必须要加强不同主体之间的对话和沟通,最终使不同主体对特定文化达致共识和互识,这是主体间性书写的重要条件。因为只有在不同主体之间达到互识的基础上,他们之间才能达成共识。也只有这样,在互识和共识下写成的民族志文本,才会是真实可靠的。当然,对于如何达到主体间的共识和互识,本文第一部分论述中有所涉及,以下主要强调科学实践在主体间性民族志书写中的重要作用。
最后,实践是推动主体间性民族志书写发展的不竭动力。为了消除“对话性文本”主观反思下无理论根据和归宿的不足、主体民族志主体间的松散关系,笔者提出主体间性民族志书写。但主体间性民族志还存在一些不足,比如,主体认识还停留在经验层面,带有先验哲学色彩,没有从实践层面对其本质加以深化;主体关系更多的建立在沟通和认识层面,没有很强的客体支撑;主体对文化的共识和互识都是建立在理想类型上,形式主义过强,操作主义较弱。针对这种情形,应该把主体间性民族志书写建立在科学实践的基础上,这样才能为其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实践之所以能成为主体间性民族志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归根到底是由实践的本性和人类学特点决定的。科学实践是物质性活动,具有为主体间性关系梳理奠定坚实的客观基础的作用;科学实践除了具有客观物质性、主观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三大特征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则是直接现实性,其可以对民族志书写进行客观、及时的经验。因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检验真理本身具有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两面,这就能很好说明主体间性民族志的发展现状和未来前景。人类学就是理论的实践。[18]24-25理论的实践和实践的理论交织在一起的民族志文本,可以很好地展示人类学这门兼具理论和实践于一体的学科的独特魅力。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19]500因此,主体间性民族志书写应该把科学实践观作为自己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借助多重主体的互相协作,进一步把民族志书写推向前进。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践成为推动主体间性民族志不断发展的动力。
三、从“表述危机”到公共人类学:主体间性民族志的公共情怀
对于当前出现的民族志书写危机,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这种认识情势直接引发出了人类学界不断反思、批判与建构热潮。但在这些研究热潮中,我们还没看到一种范式或者一个主题能很好地表征人类学和民族志书写的灵魂和实质。“因为时代要求一门学科在它的新的和修正后的研究领域设定议题,这既不是20年前的结构主义、认知人类学、马克思主义或者象征/阐释主义的路径,也不是更早期的关于亲属制度、宗教 、仪式和信仰的经典主题的讨论。”[3]9因此,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主体间性民族志书写,它的提出绝不是用一个具体范式取代另一个范式,而是在对以往所有民族志书写范式和具体实践进行抽象和概括下的产物。它的产生不仅能起到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表述危机”的作用,又能提出一种新的民族志书写方法,还能起到提高民族志理论高度和人类学学科地位的作用。
首先,在消除“表述危机”中提升民族志的表述功能和批判能力。虽然当前人类学界出现的“表述危机”在形式上表现多样,但其实质上还是指在文化描述和文化批评上出现的危机,即是民族志在达致求真至善实践上出现的危机。因此,“只有通过提高传统人类学的异文化的描述功能,我们才能提高人类学的本文化批评功能。”[1]21而以往人类学界出现的批判、反思与建构,都是“关于一个复杂的、有问题的、局部的民族志的图景,难道不可以导向写作和阅读的更精妙更具体的方式、导向互动和历史性的文化新概念,而不是对民族志的放弃?”[3]55民族志书写归根到底还是一个写作实践,写作主体和写作内容在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去看,民族志写作也就是“写什么”及“如何写”的问题,而主体间性民族志书写在这两个方面都体现出了超越其他民族志书写方式的特点和优点。因为主体间性民族志书写通过主体间性取代主客二分法、交互关系取代主从关系、关系主体取代实在主体等方式,很好地理顺了主体间的关系,彰显了不同主体间的平等和协作关系,实现了主体间的“和而不同”。同时,对主体间不同关系的梳理很好地实现了把本体论和辩证法有机结合的目的。科学实践的引入,则更加加深了主体间性民族志书写的内涵和外延。辩证法与实践观的有机结合,能很好地解决写作者的伦理问题和保证写作内容的真实性,进而达到保障文本的本真性和价值性的目的,这是民族志书写的科学性和伦理学要求。而对于写作中的具体技巧来说,则可以显得更为自由和灵活。
其次,在主体间性民族志书写中去建构和发展公共人类学。主体间性理论体现出的特征,充分说明了在人类的公共生活空间中存在一个“公共生活领域”,这个领域体现差异性、共时性、民主性和开放性等特点,因而利用主体间性去看待和认识这个公共生活领域,揭示了现代社会生活的公共本质、表达了多元共生的整体理念、体现了消解中心的平等原则。[20]这和当前人类学界的发展趋势和理念不谋而合。“人类学从来都有公共关怀,正是学科内在的文化批评的维度构成了推动它研究其他社会的根本动力。近几十年来出现了应用的或实践的人类学(applied or practicing anthropology) (尽管用它自己的话说还处于学科中的二等公民的地位)。但是,对公共导向的、公民的人类学的期望日益高涨并在目前成为主流。”[3]14主体间性与人类学最新发展趋势相结合,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民族志书写应该在主体间性理论指引下,更多的介入和书写诸如环境、灾害、疾病、毒品、饥荒、权利等公众事物中去,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民族志个案作品。“公共人类学是‘为公众思考’的人类学,应带着强烈的公共关怀意识,站在民众的立场服务于社会公众,为社会大众的福祉进行呼吁和辩护。”[21]总之,主体间性理论的理念、实践及视野范围都与当前人类学提供的公共人类学相匹配,因而其定能在公共人类学的建构中占据不可缺少的地位。当前,中国社会公共人类学的指向和归宿都在人民大众身上,因而主体间性民族志的书写更应该去关注人们大众的喜怒哀乐,进而为建构起一门“迈向人民的人类学”或者“为人民服务的人类学”[22]371-372做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贡献。
最后,主体间性民族志书写彰显出了强大的公共情怀。主体间性民族志的提出,不仅为解决当前民族志书写的“公共危机”服务,也不止为公共人类学的建构做铺垫,其更大的意义在于其主张的主体视角具有的人文关怀。在人的不断“异化”“物化”的今天,人的对象化与人的社会化之间矛盾重重,这就直接导致人类在追求自由和幸福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主体间性民族志书写的提出,在人类终极关怀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其对主体的重视和高扬充分体现了现代社会现代性的要求;尊重和理解不仅符合中国传统“和合学”的传统精神,也符合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念;其对作者和文化主体的真正理解,超越了现实一般认识,达到了一种生存意义上的领悟;通过共识和互识,进而促进公共社会领域的和谐的理念能为解决现时代矛盾所用和建构未来社会所需。正如朱炳祥教授所说:“探索民族志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自明性基础,这种探索将人类学还原为真正‘研究人类的学问’,将民族志还原为真正的‘人类志’。”[23]克利福德和马尔库斯也说:“对公共人类学的期待暗示出,这门学科将在它的研究努力中更关注它的责任、它的伦理和它对各种他者的义务,而不是关注将它作为一门学科进行推动的行会似封闭的,对辩论、模式和理论传统的痴迷。”[3]14因此,人类学和民族志只有面向人类的终极关怀,才能获得学科不断发展的动力的源泉。今天,主体间性民族志书写已经介入“公共”之事,关注“公众”之心,抒写“公共”情怀,产生“公众”效应。假以时日,其定将促使人类学成为一门专门研究公众、服务公众的真正的“公共”人类学。同时,虽然主体间性在解决人类生存问题上具有的特点和优点,已使其逐渐成为当代社会新的思维方法和认识模式。但直到今天,在理论和民族志实践上,其巨大的理论和实践威力却还未完全彰显。当然,我们坚信,只要自然的恶化、人类本质的异化、文化的不断消逝以及人类生存危机等矛盾和问题没有完全解决,那么,主体间性理论及主体间性民族志书写定会有广阔的实践空间。
总之,本文立足于把西方现象学社会学理论中的“主体间性”理论和民族志书写有机结合起来,凸显了主体间性民族志书写在弥补主体性民族志书写弊端及当前人类学界“表述危机”上的超越性和优越性,彰显出主体间性民族志书写的理论素养和实践向度,看到了主体间性民族志书写具有的人文关怀和公共情怀,这一切都为人类学成为真正的“公共”人类学奠定了坚持的基础。“人类学这个曾主要是以其消遣性,好奇性,或其道德延展性,还有为殖民当局的需要,行动管理的便利而为人们阅读的学科,现在竟变成了一个思索论辩的主要场地。”[24]英文版序言3因此,当务之急是加强对人类学理论的不断反思、强化学科对人的尊重和理解,就显得如此重要。主体间性民族志的提出,不是要打破和消解人类学和民族志书写上的常规模式,而是为我们对于文化、对于他者提供了一个新的思维方法和视角。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中这样说道:“未开化人的具体性思维与开化人的抽象性思维不是分属‘原始’与‘现代’或‘初级’与‘高级’这两种等级不同的思维方式,而是人类历史上始终存在的两种互相平行发展、各司不同文化职能、互相补充互相渗透的思维方式。”[25]中文者序5本文的写作初衷和最后归宿也许就在这里:文化需要保护,他者需要理解和尊重,尊重他者就是尊重自己。
[1][美]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E·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M].王铭铭,蓝达居,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2]高宣扬.当代社会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M].高丙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4][美]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M].高丙中,康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5]朱炳祥.反思与重构:论“主体民族志”[J].民族研究,2011(3).
[6]沈洪成.民族志的三重性:科学、反思与行动[J].青海民族研究,2011(1).
[7]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A].后现代主义的突破——外国后现代主义理论[M].李幼蒸,译.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
[8]高鸿.现代西方哲学主体间性理论及其困境[J].教学与研究,2006(12).
[9][德]许茨.社会实在问题[M].霍桂恒,索昕,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10][德]尤尔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M].郭官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1][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M].曹卫东,付德根,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1.
[12]何林.许茨的主体间性理论初探[J].求是学刊,2005(3).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4]王铭铭.人类学讲义稿[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
[15]Bronislow Malinowski.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M].(New York:Harcourt Brace&World)1967.
[16]王铭铭.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7]朱炳祥,刘海涛.“三重叙事”的“主体民族志”微型实验[J].民族研究,2015(1).
[18][美]麦克尔·赫兹菲尔德.什么是人类常识——社会和文化领域中的人类学理论实践[M].刘珩,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1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0]周菲.“主体间性”理论视域中的公共生活[J].河北学刊,2006(5).
[21]陈兴贵.理解公共人类学学科内涵的四个维度[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6).
[22]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八卷(1957-1980)[J].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23]朱炳祥.再论“主体民族志”民族志范式的转换及其“自明性基础”的探求[J].民族研究,2013(3).
[24][美]克利福德·格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C].王海龙,张家煊,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25][法]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M].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THE ETHNOGRAPHIC WRITING I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SUBJECTIVITY
Huang Zhiguo,Li Yinbing
The emergent weakness of scientific ethnography and various empirical trials of postmodern ethnography with various methods and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have opened a new door for us to understand ethnographic writing.Based on the criticism and transcendence of traditional subjectivity writing,the inter-subjectivity ethnographic writing places emphasis on the transference from specific subject to relation subject,and further explores such issues as how to achieve consensus and mutual recognition between different subjects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relationship among different subjects ultimately.Thus,not only can clarification the multiple subjects and their relations in ethnography strengthen the authenticity and humanity of ethnographic writing,but it also predict a possibility of public anthropology,which is the essential appealing and need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ic writing,giving rise to a new round of innovation in ethnography.
subjectivity;inter-subjectivity;ethnography;public anthropology
罗柳宁﹞
【作 者】黄治国,历史学博士,信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信阳,464000;李银兵,法学博士,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贵阳,550001
C952【文献识别码】
1004-454X(2017)06-0054-008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清代绥远城将军与北部边疆治理研究”(14CZS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