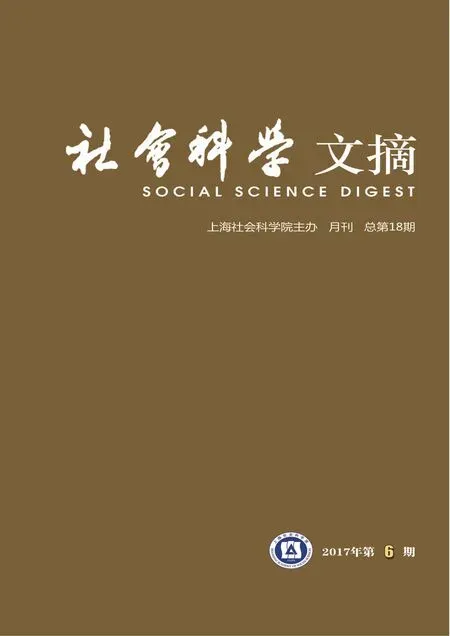论《开往中国的慢船》中作为“符号”的中国与美国形象
文/张小玲
论《开往中国的慢船》中作为“符号”的中国与美国形象
文/张小玲
村上春树的《开往中国的慢船》如题目所标示的,“中国”这一符号是文中的重要因素,小说就是以回想“我”与3位中国人的交往为主要线索而展开。所以,多有研究者对这部作品的中国人形象加以评论。但笔者通过对这部作品前后3个版本的对比以及与《作为记号的美国》一文的互文性比较发现,这部作品里隐藏的美国文化符号和中国符号同等重要。本文联系《作为记号的美国》等村上初期的散文评论,对《开往中国的慢船》里“中国”与“美国”的他者意义作一比较研究,以此探究村上初期文学里“中国”与“美国”这两种文化符号的内涵。
隐藏的“美国”文化符号
《开往中国的慢船》这一短篇小说就内容来说,随着版本的不同,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1980年4月在文艺杂志《海》上的初出版本,接着1983年5月村上春树加上了《穷婶母的故事》《纽约煤炭的悲剧》等其他6篇短篇小说,由中央公论社出版发行了同名的单行本。这一版的内容已经和《海》的版本有很多不同。1990年由讲谈社出版的《村上春树全作品1979~1989》的第三辑中收录了《开往中国的慢船》,这个版本和单行本相比,又发生了明显改变。中国大陆的林少华译本基本和最后一版一致,而台湾的赖明珠译本依照的是单行本。
虽然《开往中国的慢船》版本之间差别很大,但是,在所有版本的开头部分,都以小号字体标示的4句歌词作为引言。这首歌曲是1948年由美国作曲家Frank Loesser(1910~1969)创作,英文曲名为:"On a slow boat to China"。文本的整个故事很像是叙述者听了这首歌曲,无意之间受到了触动,由歌词中的“中国”二字联想到自己和中国人交往的往事。这种由歌曲而感的文本的起因,显示了“中国”这个文化符号的地位具有可置换性,并非我们所想象的那么重要。而如果细读过文本,了解了全文的回想性叙述模式,以及具体的回想内容,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在全文中的位置也的确局限在一种文化“符号”的层面,和现实中的“中国”并没有多么紧密的关联。
在第一部分中,叙述者苦苦回想自己第一次遇见中国人究竟是1959年还是1960年,却不得而知,最后,找到的脑海中的线索却是“对了,那是约翰逊和帕特森争夺重量级拳击桂冠那年。记得从电视上看过两人的较量”。这段话里的“记得从电视上看过两人的较量”一句,在《海》的初版和单行本中没有,在全集中加上了。帕特森指的是Floyd Patterson(1935~2006),是美国的著名拳击选手,21岁时就成为拳击史上最年轻的世界重量级拳王。约翰逊即Ingemar Johansson(1932~2009),是瑞典的著名拳击选手,曾在赫尔辛基奥运会上获得重量级拳击银牌,转为职业拳手后5年便获得了欧洲冠军。约翰逊曾在1959年的世界重量级拳王向帕特森挑战,并出人意料地打败对手,将世界重量级王冠捧回欧洲。《开往中国的慢船》文本中指的就是这场比赛,而且从全集版中我们可以得知,这场比赛在日本是被转播过的。也就是说,和上文提到的美国歌曲一样,叙述者对于“中国”的记忆依然是通过追溯与“美国”有关的文化事件的线索而得以重现的。
在文本的第4部分,描述了28岁时我和高中的中国同学偶遇的情景。在叙述相遇的具体情节之前,有一段叙述者自身对这次相遇的评论。在初版和单行本中保留了这一段,但在全集版中被删除了。事实上这段描述非常耐人寻味。除了这段话里可能招致误解的政治性因素(比如提及战犯山下大将)以外,也许作者更多地是从整个文本的内容加以考虑而删除的:这个文本说的是与“中国”有关的记忆,而这段冗长的日本士兵和美国士兵的描写,似乎有些偏题。但是笔者认为,恰恰是这样貌似跑题的描述反映出前文所提及的这个文本的重要特征:《开往中国的慢船》里其实“美国”是个隐蔽却重要的文化符号,“中国”和“美国”两者具有密不可分的关联。
同样的,文本的第五部分的结尾,初版和单行本版一致,但全集版中作了较大的修改。将两个版本进行对比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在前一段里除“中国”以外,还出现了纽约、圣彼得堡、列宁格勒等其他的地名,其中纽约出现了两次。也就是说,在原文本中传达出这样一种信息:“中国”和“纽约”等地点所代表的意义是一样的,即都不是“为我而存在的地方”,是“我”以外的符号化的“他者”。之所以在全集版中删除了这些地方,笔者认为原因也应该是:这些其他地名的出现似乎妨碍了文本里凸显“中国”这个主要因素。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尽管版本不同,但是在《开往中国的慢船》中,表面上“中国”是主要论述元素,事实上“美国”这另一个“他者”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删节的前两版倒是更能体现作者的本意。那么,这个现象产生的原因何在呢?这个问题和《开往中国的慢船》整个文本反映的中心内容有不可分割的关联。
作为“他者”的“中国”与“美国”
在《开往中国的慢船》第一部分,叙述了“我”努力追寻记忆中和中国人第一次相遇的时间,但是在赶到图书馆以便搜集线索的时候,“我”却对这种追寻行为本身产生了虚无感,于是又毫无所获地离开了图书馆,并且这样陈述道:“整个小学时代(战后民主主义那滑稽而悲哀的6年中的每一个晨昏)我所能确切记起的不外乎两件事,一件事关于中国人的,另一件是某年夏天一个下午进行的棒球比赛。”这句“战后民主主义那滑稽而悲哀的6年”凝练地暗示出了这个文本中体现的“我”的美国观。村上春树出生于1949年,1955年至1961年在关西的西宫市一所小学度过6年时光,这个时期也正是日本在美国的民主理念指导下而实施“战后民主主义”的阶段,而文本中的“我”认为这是“滑稽而悲哀的”。从文中特别描述的棒球比赛的插曲我们就可一窥这种感情的具体内涵。而在很多历史资料中,我们都可看到当时美国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和前来拜访的昭和天皇的一张合影,照片上的麦克阿瑟高大魁梧,还两手叉腰,而一旁的昭和天皇身材矮小,表情卑微。这张具有象征意义的照片中表现的氛围和村上这部文本中所提及的“滑稽和悲哀”的感情是相通的。
在这样的情绪之下,“我”记住的另一件小学的往事,就是在一所中国人小学中遇到的监考的中国老师——“我”遇见的第一个中国人。他教育日本小学生不要在课桌上乱写乱画,并要求孩子们大声回答“明白”,而且要“抬起头,挺起胸”“怀有自豪感”。这种“抬头、挺胸、怀有自豪感”的情绪,20年后的“我”依然清晰地记得。这种情绪和前文所提及的战后民主主义给“我”留下的“滑稽和悲哀”的情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且,这两种情绪都是经过20年时间冲刷仍然留在心底的深刻回忆。不过,一个是针对占领国的“美国”,一个是针对曾经被日本侵略过的“中国”。
从历史上来说,近代以前日本一直要面对如何处理与文化母国“中国”的关系,而近代以来,无论是“脱亚入欧”,还是“和魂洋才”,都是日本在“东方”与“西方”之间艰难寻找着自己的文化身份的表现。20世纪日本发动的对中国及东南亚各国的大规模侵略战争,也正是在这种寻找道路上所犯下的严重错误。但是到了战后,在面对占领国“美国”广泛而深入的文化影响的时候,如同作品主人公“我”一样,又重新回到反省与“中国”的密切关系的思考中的日本人也不在少数。从时间上来说,“我”的大学时代是60年代,毕业以后是70年代,这个时期“美国”文化已经不再停留在表面的战胜国所代表的先进文化层面,而是渗入了社会的各个方面。松本建一曾指出过,中国和美国本来就像是盾的两面,都被认为是日本的“他者”,这其实是近代日本为了不被“脱亚入欧”的近代化道路所彻底同化而采取的策略。但是,从明治维新开始不过百年,“对于我们来说,美国已经不是‘他者’。经过了‘被占领的日本’这个过程后,已经呈现出了‘美国化的日本’的面貌”。前文第一部分列举的《开往中国的慢船》中所隐藏的众多美国文化因素可以让我们洞察这一点。理解了这样的文化背景,再来看村上这篇文本中所描绘的“中国”,我们恐怕才能深刻理解为什么文本中的“我”只记得小学时代的两件事情——一件关于“美国”,一件关于“中国”。
但是,是不是通过重新树立“中国”这个他者,“我”(所代表的日本人)就能够正确地认识和确定“自我”呢?文中种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大学打工时代遇见的中国女大学生虽然和“我”有着充满温情的交往,然而这种相互的安慰因为“我”无心的过失无疾而终。文中的第四部分,“我”在毕业之后遇见了推销百科全书的高中时代的一位中国同学,两人淡淡交谈之后分手。而这位中国人在日本的生活来源建立在中国人圈内的商业交易之上。这个事实验证了前一部分女大学生的话:“这也不是我应该在的地方。”
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这个“他者”并没有让“我”找到主体应有的位置,“我”倒是通过和“中国人”的交往,意识到自己其实和他们一样,在这个“被美国化的日本”无处立足。相对于很多身处众多美国文化因素而不自知的日本人来说,文本的作者能够意识到“美国”的他者性,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我”面对战后民主主义所产生的“滑稽而悲哀”的情绪,正是对“美国”这个他者的反拨。也正因为这种反拨,“我”开始追寻与另一个他者“中国”的相互关系,如同近代日本这个民族国家所做过的那样。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开往中国的慢船》这个文本具有很大的文化象征意义,这其实是日本近代史的一个隐喻。如同日本近代史上所发生过的悲剧一样,无论是面对“中国”还是“美国”,“我”最终都没能通过“他者”树立合适的“自我”。因为这个“他者”是被强烈“符号化”的。
符号化的“他者”与边缘性的“自我”
社会学的意义上“自我”这一概念是通过“他者”才得以实现意义界定的。如果没有处理好“他者”,那么这个“自我”也就值得推敲了。1983年4月号的《群像》杂志曾经发表过以“美国”为题的专刊,村上的题目是《作为记号的美国》。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这个文本,就会发现:村上对“美国”的认知和《开往中国的慢船》里对“中国”的认知简直如出一辙——一种强烈的符号化存在。
作者在文中提到对于“作为实体的美国完全没有兴趣。换言之我不想同时间地认知作为共同空间的美利坚合众国。我感兴趣的是,我自己的时间性中的认知的美国,或者是想象的美国”。这个“美国”是通过“小小的玻璃窗”——即摇滚乐、小说、电影等文化媒介——窥探到的纯粹的情报的集合。这些媒介是否能够真实地反映“美国”尚是疑问,不过,“这些情报归根到底只不过是记号而已”,先将得到的情报分成琐碎的记号,再重新构建,一步步集合成大的情报,“这就是对我而言的美国”。而在《开往中国的慢船》中,“中国”也是“我”从《史记》《中国的红星》中读到的情报的集合,所以是“是唯我一人能懂的中国,是只向我一人发出呼唤的中国。那是另一个中国,不同于地球仪上黄色的中国。那是一个假设、一个暂定”。“中国”或者“美国”,都是“我”通过媒介得到“符码”,然后重新建构的符号。
那么,究竟为什么在“我的认知”中需要“美国”(或者“中国”)这个文化符号呢?《作为记号的美国》中这样说道:“对于我来说,也许可以说,美国也就是为了回避同心圆的护身符。所谓同心圆,就是以我为中心的,我→家庭→共同体(学校·职场)→国家,这样的具有精神连续性的同心圆。我一直在努力地试图在某个地方切断这种精神连续性,却无法切断。所以,我将在这个同心圆之外的、与这个同心圆中心不同的‘美国’这个圆带到了自己的生活中。”因为有“美国”这个他者,“以这点作为目标将自己相对化就成为可能”。通过上文对《开往中国的慢船》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我”在文本的开头似乎要通过追溯和“中国人”的交往,寻找某种历史、某种自我定位,但很快就对这种追溯本身产生怀疑。而且,通过自己与3位中国人交往的回忆,“我”不仅没有找到“自我”,反而发出了和中国人一样的“这也不是我的场所”的感叹。《开往中国的慢船》这一文本以貌似历史的追溯开篇,却以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收尾。也就是说“中国”这个“他者”,事实上也成为了“我”切断和共同体的精神连续性的工具。从这一意义上说,《开往中国的慢船》和《作为记号的美国》虽然一为小说,一为散文,却具有强烈的内在联系。《开往中国的慢船》似乎可以看作《作为记号的美国》的姐妹篇——《作为记号的中国》。
的确,《开往中国的慢船》这一文本,可以说是描述了一个“个体”追寻民族、国家层面的“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未果,从而切断和共同体的“精神连续性”的过程。“我”发现了“日本”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在面对“中国”“美国”这两个他者时,只是表面的文化符号的接受,所以无法确立真正的独立的“文化身份”。由此,“我”对在“日本”这个共同体中寻找“自我”失去兴趣,从而深刻意识到“我”这个个体的边缘性。这里就涉及到村上研究中一个经常被谈论的话题:“疏离”(detachment)与“介入”(commitment)。在《村上春树去见河合隼雄》一书中,村上曾自述,自己通过1991年到1994年在美国的4年生活,考虑问题的视角发生了的变化,即由以往的“疏离”姿态向“介入”转换。也就是说,包括《开往中国的慢船》在内的村上初期作品是在所谓“超然”的姿态下完成的。如此,我们也能理解文中明显的个人主义色彩的由来。但通过对《开往中国的慢船》以及村上其他初期散文的细读,我们可发现:所谓“疏离”,是在意识到“共同体”意识形态强大之后,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之后不得不采取的姿态,而不是与生俱来的漠不关心。
小结
总之,《开往中国的慢船》虽以“中国”为题,却反映了一位“日本人”在面对“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他者”时的彷徨与思考。这种思考姿态本身是日本近代道路发展的一个缩影,具有文化象征意义。但是,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对待“他者”,却是日本在近代一直未能处理好的一个问题。《开往中国的慢船》和《作为记号的美国》中都反映出将“他者”“符号化”的认知模式。而不能正确地认识“他者”,也就是无法正确地建构“自我”。在透彻认识到日本在近代“文化身份”建构道路上的失败以后,“我”采取的应对方式是将自己边缘化,切断和“共同体”的精神联系。不过村上春树这种思考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显示了对历史及意识形态的某种关注,他自己所认为的从“疏离”到“介入”的转变是有必然性的。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摘自《中国比较文学》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