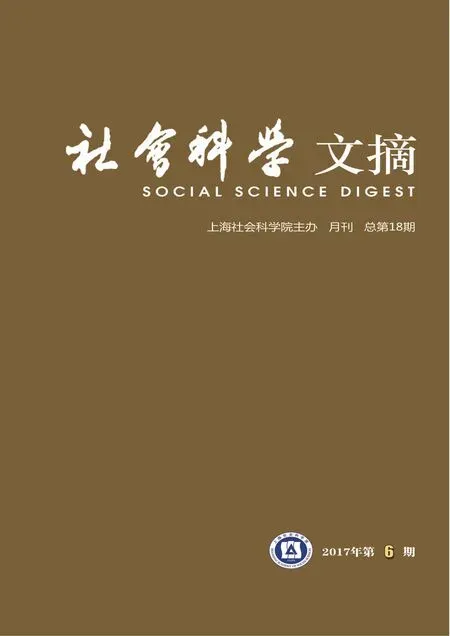论《江南三部曲》的“乌托邦”反思
文/姬志海
论《江南三部曲》的“乌托邦”反思
文/姬志海
时至今日,潜藏在《江南三部曲》三个小说文本内部的本质联系并没有得到切中肯綮的剖析与解读。论者以为,《人面桃花》中的那个由张季元们前赴、陆秀米们后继但建设无果的“现代性启蒙乌托邦”在各种乌/恶托邦居于统摄全局的核心地位。四代乌托邦/恶托邦故事,正是在与这一“乌托邦”的对照联系中才被激活自身存在的全部意义。它是其他三者共同指向的联系枢纽和辐射中心,其所寄寓的理想瞩望至今仍然是一个未竟的事业。
《江南三部曲》的反乌托邦主题考辩
在《人面桃花》发表后,格非曾说道:“我所关注的正是这些东西——佛教称之为‘彼岸’、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的完全平等自由的乌托邦,《人面桃花》中讲到的桃花源也是这么一个存在于想象之中的所在。”此后,不管有意无意,批评界关于《人面桃花》(连带“三部曲”后续的《山河入梦》《春尽江南》)的评论重心,很多一部分都集中在对其乌托邦/反乌托邦言说的解读上。
“乌托邦”一词,随着英国政治家和小说家托马斯·莫尔爵士于1516年发表用拉丁语创作的小说《乌托邦》而遐迩闻名,流传开来。“乌托邦”(Utopia)这个词包括两个希腊语的词根,即,“没有”(ou)和“地方”“处所”(topos),在拉丁文中意思是“不存在的地方”。同时,因为谐音的缘故,这个词就兼有“理想”“美好”和“虚幻”“缥缈”等附加涵义。
其实,在这个词的诞生之先,乌托邦思想就已源远流长。关于乌托邦的思想起源和最早的系统阐述,学界普遍认为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也有人将之追溯到更早的希伯来先知。后来,许多国家和民族中更是都出现过有关乌托邦的论述,涉及宗教、哲学、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科技等各个领域。作为文学的乌托邦作品是“关于一种完美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空想描述,它表达了人们对美好世界的梦想。乌托邦……是对能够保证每个人都过上值得一过的生活,并摆脱了匮乏和痛苦的理想社会的重建”。
就这种小说类型的写作范式而言,是远在托马斯·莫尔的第一部近代乌托邦小说中就奠定了的。后来的乌托邦小说创作者,无不沿袭着莫尔的创作心路,即不断地在追求“进步”的诱使下,创设和构想着新的理想社会的完美运行模式,并据此构想了许多关乎人类未来发展前景的设计方案。作为“经典乌托邦小说”殊异面目出现的“反乌托邦小说”事实上不过是前者在现当代的发展余绪和新变而已。无论是在经典乌托邦小说,还是在对前者进行救弊补缺、反思扬弃的“反乌托邦小说”里,乌托邦这一概念在学界是有其约定俗成的确定性内涵的,即它的基本着眼点在于建立一个稳定、统一的理想社会——凸出的是人的集体存在的社会构想模式。
当然,作为格非创作成熟期的巅峰作品,《江南三部曲》理所当然地包容着多方面可供发掘的复杂内蕴,但不可否认,对“乌托邦”的企盼、反思和袪魅是这诸多复杂内蕴中的基本主题之一。倘以西方小说范畴中的“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为参照坐标,结合特殊的汉民族文化传统和中国百年历史实际进程中现代化乌托邦情结的曲折沧桑,就不难发现,贯穿三部曲的主题红线是格非对乌托邦的不断建构、反思、解构和袪魅。其中的乌托邦包括:《人面桃花》《山河入梦》中分别以花家舍、普济和梅城等为“载体”的“前现代古典乌托邦”、启蒙色彩颇浓的“现代性启蒙乌托邦”“反现代‘共产主义’乌托邦”,以及《春尽江南》中以荒诞和悖谬的方式兑现了的、颇具后现代色彩的“伪现代乌托邦”。在这种主要以反思和抗辩的“反乌托邦”视界的观照下,格非在深刻内省的基础上,声讨和诘问这种种沾染着中国文化历史境遇特殊色调的乌托邦神话所折射出来的严重弊害和社会恐怖图景,消解和反叛其所各自宣称代表的终极“真理”“正义”“自由”“善良”“幸福”等,质疑、批判和颠覆其“企图一劳永逸地永久性解决全部社会矛盾”的许诺。
概而观之,格非在《江南三部曲》中关于“乌托邦”的反思,基本上是以否定性极强的反乌托邦形式呈现的。他对各种许诺给人们带来终极解放的乌托邦都持有很大的戒心和质疑,认为其可能事与愿违地产生更大的集权、专制、奴役、剥削和压迫等。
四代“乌托邦世界”的追求与反思
具体而微,格非在《江南三部曲》里,统共写了四代乌托邦/恶托邦故事。
表面看来,仕途蹭蹬、罢官回籍的陆侃企图“将整个村子用一条没有间断的风雨长廊连起来”的乌托邦追求,似乎缘起于一幅“桃花源”图,而实际上作者在文本中着意映射的是在前现代中国社会绵延已久的“大同情结”。这种情结是社会矛盾普遍化、尖锐化、深刻化的结果;是政治黑暗、人欲肆虐、灾难四伏、人类群体存在环境恶化时,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中国古代的往圣先贤对深重灾难普遍表现出的“救世”愿望的缩影;是由孔子和墨翟理想世界中的尧舜时代、道家理想世界中的黄帝时代、许行理想世界中的神农时代,共同杂糅叠加而成的陶潜的世外桃源。格非有意地将陆侃的这种人人看来无异于疯狂的追求和抱负通过其女儿秀米之眼,在秀米惨遭蹂躏的土匪窝花家舍那里化为“现实”。花家舍的“总设计师”是同样饱读诗书、立志独与天地之大美相往来的王观澄,和同气相求的陆侃一样,他立志使其辗转寻访到的祥和、僻静的花家舍在自己手里实现“大同世界化”,“要花家舍人人衣食丰足,谦让有礼,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成为天台桃源”。然而这种理想最终在一场火并中毁于一旦,花家舍成了血腥之地。这验证了貌似保守昏聩的丁树则的那句“桃源胜景,天上或有,人间所无”的谶言。
与对陆、王的前现代古典理想乌托邦的单纯批判视角不同,对于张季元、陆秀米二人醉心其中的、彰显着浓厚启蒙色彩的现代文明式乌托邦,格非显然在质疑其非理性的同时,给予了其较多有保留的肯定。在感情和精神上双重背负着张季元遗志的秀米,自日本接受了现代西方思想浸润后重回家乡,领导成立了普济地方自治会,在一间寺庙里设立了育婴堂、书籍室、疗病所、养老院和普济学堂,以知行合一、积极介入的入世情怀,从启蒙新民和革命救国两个向度,祈求能在普济一带乃至整个中国建立理性、科学、民主和人道主义的人间天堂。为此她宁可放弃基本的亲情伦理(这间接造成了母亲的过早离世和儿子的不幸罹难),而最终只是落得个身陷囹圄、家破人亡的悲惨结局。革命失败后秀米的闭门禁语,拒绝小驴子的来访。这暗示了在时代多种残酷力量和内部变节行为的各种因素的联合压迫、绞杀和掣肘之下,在风刀霜剑中苦苦摇曳支撑着的乌托邦暗火最终只能走向彻底寂灭的归宿。区别于《江南三部曲》中其他类型的“乌托邦/恶托邦世界”,唯有这一注定在中国几千年来长期积聚的历史惰性和文化矢量的双重吊诡下似乎永远也无法实现的现代性启蒙乌托邦,才真正居于其他三种乌托邦/恶托邦类型逻辑内聚力指向的中心,意义非凡。
《山河入梦》的故事把《人面桃花》的历史语境从清末民初拉近到新中国建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干天斗地的“大跃进”精神的催生下,陆秀米之子谭功达终于未能走出母亲精神基因暗中昭示的乌托邦幻想的宿命式老路,无可逃遁地一头扎进新一轮天下大同、山河都入梦中的桃源幻景中。在自己雄心勃勃的梅城规划成为泡影之后,他却在郭从年领导和主宰着的花家舍人民公社里,和自己苦苦寻绎的理想国猝然相遇。但是,直到得知姚佩佩的来信早已被当局监视和掌控,他才对自己苦苦执着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的荒谬性算是有了彻底反省,才看清了貌似道不拾遗、秩序井然的花家舍人民公社绝非什么乌托邦理想天堂!
与《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两部反乌托邦小说不同,格非在《春尽江南》中的反乌托邦故事不再是对消失远遁于某个特定时空的“过去时”陈述,而是将小说的取景框直接对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直至21世纪以来的世态众生。较之前两部小说中三个乌托邦建构各自浓淡不匀的历史“漫漶”色彩,格非明显地在《春尽江南》里植入很多真实的时代符码。可以说,以现实日常生活为依托,直接描摹百年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几代人为之上下求索奋斗的“现代化”诉求——这一集体乌托邦理想——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启的新一轮时代转型中,以悖论方式兑现后的全部荒诞和困境,正是《春尽江南》这部反乌托邦小说的最大主题。在格非看来,这种终于摆脱了前现代农业文明的现代化乌托邦理想带来的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不仅没有“毕其功于一役”,完成百年中国乌托邦进程终点的历史夙愿,而且还导致了诸如精英精神的沦陷、道德人性的丧失、生态环境的污染、个人主体性的异化乃至整个民族文化身份的迷失等更加恶劣的负面恶果。现今的中国现实本身已经发展到令人震惊的荒诞程度。王德威曾颇有见地地指出,《春尽江南》这部小说似乎因为单一刻板的现实主义手法而略显辞气浮露。但也许在格非看来恰恰相反,他的《春尽江南》这部反乌托邦小说根本不再需要什么特别的先锋小说艺术手法的发明创造(相对而言,《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两部都还有共同的“逃亡”和“宿命”的神秘主义色彩),只需要对这个处处流溢着丑陋和罪恶的现实本身进行稍事剪裁、略微浓缩的写实性勾勒即可。正基于此,格非才以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塑造“典型环境”“典型人物”的主要结构技法,将他对当下社会的痼疾、当代人精神困局的思考,在《春尽江南》中,通过诗人谭端午的忧时伤世、颓废放逐和律师庞家玉不断追赶时代节拍、最终幻灭的人生轨迹,盘根错节的其他故事人物升降沉浮不同运命的各色表演,一一挥洒投映在时代转型期千秋盛世虚幻外衣的掩盖下的、由种种丑陋和罪恶交相辉映共同织就的世纪末的斑驳图卷中。
《江南三部曲》的逻辑内聚性
论者以为:《人面桃花》中的“现代性启蒙乌托邦”在上述的各种乌/恶托邦中居于统摄全局的核心地位。
首先,陆、王心仪的前现代古典桃花源式乌托邦和张季元、陆秀米努力建设的颇具启蒙色彩的现代文明乌托邦,实际上象征着格非对于古典中国在现代化嬗变过程中的分娩阵痛!正如陈独秀在其《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振聋发聩地指出的那样:“儒者三纲之说, 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共贯同条, 莫可偏废。三纲之根本义, 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 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之制度者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与阶级制度极端相反。此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也……”由此来看,《人面桃花》中的两种乌托邦分明就是中西伦理政治分别在封建礼教三纲和启蒙自由平等两种截然不同的本原下(这二者之价值冲突不可调和)各自设计的乌托邦规划蓝图而已。王观澄践行的一厢情愿的古典浪漫主义桃花源式乌托邦方案失效的原因恰恰在于其内部现代性因素的匮乏,这种乌托邦载体的放大版,充其量也就是类似“太平天国”天朝迷梦那样的在历史上循环不止却又始终因为诞生不了现代性的生产关系而终究停滞不前的历代农民起义。
其次,在晚清之际由张季元们前赴、陆秀米们后继的彰显着科学、民主、自由、幸福启蒙色彩的现代性乌托邦版本,虽然难免有矫枉过正的非理性弱点,但是这种方案毕竟是传统中国由封闭的老大帝国向世界现代文明的一次悲壮尝试。这种乌托邦的多舛运命,早已由中国近现代启蒙和救亡的两大时代主题力量悬殊的博弈所预设和谱就:由于封建主义加上危亡局势,陆秀米们经营的现代性文明乌托邦不可能得到稳步发展的空间,在各种反动势力的反复碾压和掣肘下,最后只能夭折飘零。这就预示着:由于启蒙理想被挤压,老大帝国几千年的封建余毒并没有随着共和国的建立而得到“彻底之解决”。共和国前三十年在郭从年们假共产主义的旗号下,打倒所谓资本主义的同时,走向比之更加野蛮落后的封闭保守、高度集权、以平均主义为核心特征、缺乏民主意识的反现代乌托邦。
郭从年们致力建构的“反现代‘共产主义’乌托邦”与张、陆向往的“现代性启蒙乌托邦”之间的承续与变异逻辑说明:本来应该在现代性启蒙和民主革命充分展开后,才可能得以完全清洗的封建主义余毒,但是在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中,这个过程由于太过短暂即告夭折。在这样的情况下,“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种种设想就很有可能使“封建主义”借尸还魂。
复次,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过了一个多世纪艰难曲折的现代化进程,终于从呼唤现代化的思想憧憬全面进入到接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现代化乌托邦理想的实践操作阶段。但是,在西方由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两个引擎开启的世界“现代性”潮流被引进以后,基于历史的重负、现实的国情等复杂因素的制约,“去政治化”的中国并没有得到一劳永逸的疗愈。在貌似千秋盛世的虚幻外衣的掩盖下,格非看到了这一乌托邦寓言在现实中国真正得以以其反面的“恶托邦”形式兑现以后更加荒诞和悖论的一面。“市场化”所带来的也不仅仅是文化的商品化,还有权力与资本在各个领域的合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格非在《春尽江南》中承续了前两部小说中的反乌托邦主题的基本文意和主题内蕴,自觉对照与张、陆理想中的“现代性启蒙乌托邦”,将这种“恶托邦”的全部荒诞与困境视觉化为一幅世纪末的浮世绘。
比及王观澄建构的“前现代古典乌托邦”和郭从年建构的“反现代共产主义乌托邦”,《春尽江南》中的这幅“恶托邦”无意流溢出更多的后现代主义的狂欢化色彩。在端午夫妇犒劳“国舅”一行的答谢晚宴上,我们看到:资本家在读马克思,黑社会老大感慨中国没有法律,被酒色掏空的投机文人在呼吁重建社会道德。这群本属于巴赫金狂欢理论中的“小丑”角色,现在却俨然被“加冕”成为社会正义的引领者。在堪称“温柔富贵乡、人间销金窟”的花家舍旅游胜地举行的诗歌学术研讨会上,我们更是看到高贵纯洁的诗歌和污浊不堪的会所沆瀣一气、革命追缅的情怀和妓女文化的情趣携手共舞——什么高贵与卑贱、什么庄重与调侃、什么伟大与渺小、什么意义和荒诞,都已再难分清彼此之间的绝对界限,所有的一切不过是洋溢着后现代狂欢色彩的大杂烩而已!这是一个一切高度都被铲平的社会,这是一个一切深度都被填埋的当代。随着生活、生命中应有高度和深度的被解构,包括牺牲、献身这样往昔充满神圣光辉的意象也被完全袪魅,变得荒唐可笑。正如格非借助故事叙述人端午在一首诗歌中对“牺牲”的解读中诠释的那样:“牺牲,本来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或者说,是文明的一部分……而在今天,牺牲者将注定要湮没无闻。没有纪念、没有追悼、没有缅怀、没有身份、没有目的和意义!”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摘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