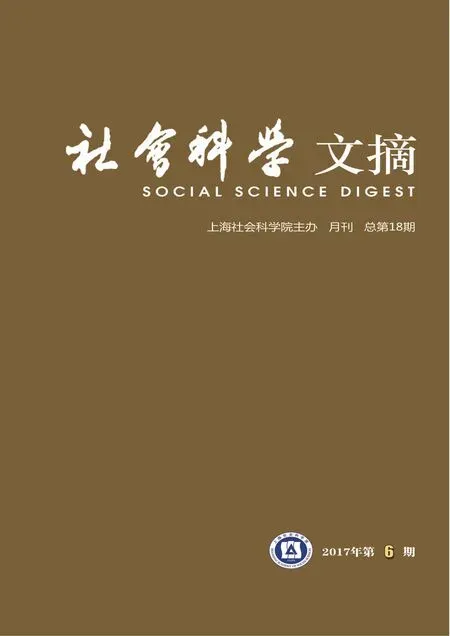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生性与新传统
文/刘占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生性与新传统
文/刘占虎
人类社会总是在不断的演进中实现其质性发展的,而“发展”作为对事物内在规定的批判扬弃,必然蕴含着独有的内生逻辑。在社会主义500年的时代节点上,“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成为中国道路自觉、理论自觉、话语自觉的重要课题。作为在“中国道路”上不断创造“中国奇迹”的“中国人”,最有理由以“中国话语”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生逻辑,让世界听知“中国话语”而得知其实质内涵和世界意义。
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全新的事业
马克思主义以更为彻底的方式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科学社会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未来方向,然而,这一“宏大叙事”的理论品格无以给不断发展的实践提供事无巨细的“调味单”。恩格斯对此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让科学理论照亮现实,一方面需要理论本身的科学性以及理解它的科学方法,一方面还需要人们自觉构建贯通“理论科学=实践有效”的具体实践机制。让社会主义成为“科学”,也就意味着要求人们以科学的方法研究它、实践它、发展它。
1516年,空想社会主义诞生后,社会主义从“科学化”到“实践化”,经历了理论变革的“艰难”和实践变革的“曲折”。前者主要体现为如何整体理解和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和时代精神,在文本解读和学理致思中减少认知分歧;后者主要体现为在“世界历史”尚未形成的时代境遇下建设理想社会主义而存在的地域性差异和阶段性困境。总体来看,这些探索尚未结束,也不能因为没有完美答案而终结。习近平指出:“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此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样也充满了艰难与曲折。邓小平在探索中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开拓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邓小平没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过明确的定义,而更多地是以“否定性”的话语来表达它应有的实践内涵。首先,就其否定性的内容而言,主要有三:一是不是资本主义,二是不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三是不完全是经典作家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从“不是”、“不完全是”到“是”的话语转变,是一个全新的理论命题和实践课题。中国改革开放的艰难探索正是在回答这一问题。其次,就否定性思维的方法论意义而言,它“为解决社会主义的本质与中国特殊国情的矛盾,提供了一个有待于实践充实、而不是预先给出定义的叙事框架。”这一“叙事框架”不仅为不断“解放思想”提供了思想空间,也为做到“实事求是”拓展了实践空间。
社会主义事业没有被终结,也不会被终结。实践中的挫折,只不过是以辩证否定的方式调试着科学社会主义的出场方式,因而可以作为推动其不断前进的历史基石。理论上的曲解,只不过是人类不断走进历史来把握现实和未来的思想调试,因而可以在变革的时代实践中得到合理的澄清。社会主义是一项全新的事业,需要科学理论与创新实践的双向构建来彰显其科学性和生命力。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三种存在样态
社会主义“在中国”,表达的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场域的存在状态。它既可以表达“在中国”的空间性分布和时间性延续,也可以表达与中国实践、文化传统的结合方式,还可以表达与中国实际深度融合后的发展成果。
关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存在样态,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种:
其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合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结合”,首先是与中国共产党的“结合”。在党领导中国民主革命中,逐步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化命题”,其中“结合”的内容包括“中国实践”和“中国文化”。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完成后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与经济社会文化不发达的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形成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毛泽东思想”。在改革开放中探索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发展着的中国实践“相结合”,内容包括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国文化传统、时代发展特征等。“结合说”既表达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机制,即“化什么”和“如何化”,也表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形态,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其二,社会主义价值自觉的“出场说”。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是因为它的科学性——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更在于它的价值性——契合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然而,社会主义“在中国”不等于社会主义的“中国化”,有了“中国化”的过程,也不意味着一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然结果。这就存在一个“在场”与“出场”的辩证关系问题。科学社会主义“在场”,既可以是作为理论思潮的“在场”,也可以是作为指导思想的“在场”,还可以是人类存在所必需的“乌托邦精神”和价值符号的“在场”。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之必然和应然的“存在”,体现为探索和建构美好社会制度的在场性。社会主义价值自觉,就是将这一价值定位落实到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上来,作为在中国的时代“出场”。“出场说”既表达着社会主义作为科学和价值的历史合理性,也表明了从“科学”向“实践”跃升中的规律约束和条件制约。
其三,创新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说”。马克思主义是开放和发展的科学,科学社会主义同样以“发展性”作为其先进性的实践品格。比较而言,“结合说”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在中国场域的“发展”,“出场说”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从“科学”到“实践”的“发展”。这两个维度的“发展”都源于时代创新实践,表现为理论出场的话语革新,沉淀为中国社会的整体进步。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层面看,既需要整体理解科学社会主义,并根据时代场域进行“原生态话语”的本土转化,形成指导中国实践的科学理论,也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来解答“倒逼理论”的时代问题,形成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这一意义上的“发展”,在“结合说”的维度上体现为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的双重变革,在“出场说”的维度上体现为社会主义价值在中国场域的意义彰显。由此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可以更好地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时空交融”的生成逻辑和未来图景。
以“世界历史”视角分析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存在样态,就能清晰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的简单相加,而是将“中国特色”作为具有内在规定性的“修饰语”和“定位词”,阐释着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特定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场的内生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存在样态,但不是一般的“在场”,而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内生形态,表征着社会主义真精神在当代中国的时代“出场”。它已经具有了新的内在规定性,因而是一种新事物。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内生形态。坚持马克思主义,重在坚持和运用其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建设社会主义,重在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和核心精神。具体来看,一是价值指向,即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在发展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以人文本”的科学发展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努力实现建设美好社会制度与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的一致性。二是阶级属性,即发展社会主义旨在为广大劳动者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创造人民群众的福祉。三是批判本性,即社会主义批判和吸收以往社会形态所有积极成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意味着既不走“邪路”也不走“老路”,但不回避学习和吸收其他社会制度形态中的有益成分,也不回避反思和吸取既有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四是世界场域,即社会主义是以“世界历史”的形成为前提的。中国改革开放实践,既是中国“世界化”的过程,也是世界“中国化”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在双向融合中充实了新的实践内涵,彰显着世界意义。五是规律约束,即遵循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时空约束条件。新形势下,依然明确“三个没有变”,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就是要把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约束条件动态地结合起来。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解决当代中国发展问题和实现中国人民福祉的中国理论。长期以来,人们将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视野”与评价它的“标准”混淆起来,从而产生了“见仁见智”的分歧。一是与经典社会主义的比较视野来看,认为它提出了经典理论中所没有的理论命题和实践课题,进而将中国语境下的“发展”理解为基于中国立场的“修正”。二是与“苏联模式”的比较视野看,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曾经参照“苏联模式”,而随着苏东剧变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它也面临着“有”与“无”、“是”与“非”的合法性问题。三是与资本主义的比较视野看,认为它吸收了资本主义的部分要素,进而“调侃”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其中消解了社会主义作为高级社会制度形态所具有的批判性,也“颠倒”了发展逻辑上的“本”与“末”,陷入了以“要素”判定“本质”的虚无主义。这些理解“视野”,尽管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他者镜鉴,但不可以直接作为衡量和判断标准。衡量和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是看是否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逻辑和核心精神,二是看是否有效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和实现中国人民福祉。这二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规定性,形成以“事物本身”(实“事”)来理解事物(求“是”)的内生逻辑。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价值自觉和社会主义精神时代出场的中国个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不是仅仅因为中国人民看到其价值性,更是因为在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激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时代价值,实现其在中国场域的价值出场和意义生成。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诸多社会发展方案的曲折探索和反复比较中选择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曲折和挫折,从经验和教训中凝练着社会主义真精神,在改革开放实践中赋予其以新的时代精神和中国内涵。在改革发展中,立足于历史条件的“中国性”,着眼于时代条件的“世界性”,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制度。中国人民在不断解答中国发展问题中探索并形成社会主义价值出场的中国方案。
当代中国发展问题具有“古今中外”的高度聚合的时空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解答时代的普遍性问题而向世界贡献着中国智慧,因为根植于中国大地而蕴含着中国精神,因为秉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蕴含着社会主义精神。
作为新传统的新内涵和新话语
长久以来,人们习惯于以“传统—现代”二元对立思维看待人类社会的发展,进而以价值层面的“好”与“坏”来标签化。这种简单对待历史的方式,粗暴地阉割了“传统”生成的历史经脉,阻滞了“文化”传承中的文明积淀。如何看待“传统”延续与“历史”发展的在内机理,也就成为如何安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中国新传统的时代课题。
其一,传统是代代相传中经过实践浇灌和历史萃取的实质性内容。界定传统的标准是“人类行为、思想和想象的产物,并且被代代相传”。也就是说,传统是作为“代代相传的事物”在历史的矫枉过正中萃取出来的具有实质性内容的文化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悬置在空中的理论命题,而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因而“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社会主义“在”中国,不仅因为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而作为“中国传统”的一部分,而且因为与中国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而形成经过实践浇灌和历史萃取的实质性内容,即所谓中国的新传统。
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基于“内生性”的品格而成为“时尚”。历史的发展、传统的沉淀,是一个动态的承续过程。一方面,不能单纯地以时间序列上的先后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传统与文化在内涵指认上是中性的,因而需要在认知思维上自觉修正以“新”本身作为“好”的标准取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另一方面,明确并非所有“过去的东西”都能成为传统。作为“代代相传的事物”是否能保持延传中的同一性和持续性,是其能否通达传统实质的内在维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史”尽管是短暂的,但因为其特有的内在规定性而作为中国的新传统。它不是因为作为一般的“时尚”而倍受人们关注,而是因为基于“中国逻辑”的内生性而具有不断朝向未来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开启着建构人类美好制度的新方案。
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为要“实质性内容”而需要“新话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曾作为一个有待实践充实的“话语”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在近40年的创造性实践中具有了新的内在规定性,因而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有机性在中国的生动呈现。这种内在规定性作为中国之“特色”本身就是社会主义价值自觉的中国个案,体现了对社会主义话语影响力的中国符号建构。当代中国的理论自觉和话语自觉,就有必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中国时代实践中形成的新传统,置于“西方传统”与“传统中国”的双重话语体系之间,重新审视其历史方位和内生逻辑,以新话语来阐释其时代内涵,为构建人类美好制度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在中国”尽管是在“外源或外诱现代化”的条件下开启的自主创新之路,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中西古今”高度聚合的时代场域中已经形成了特有的中国逻辑和中国内涵。基于此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孕育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生性和新传统。以学理自觉明确这一点,不仅可以在中国道路自信之理论建构上摆脱“他者化思维”,而且有益于保持理论上的清醒来夯实中国制度自信的思想基础。
(作者系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摘自《科学社会主义》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