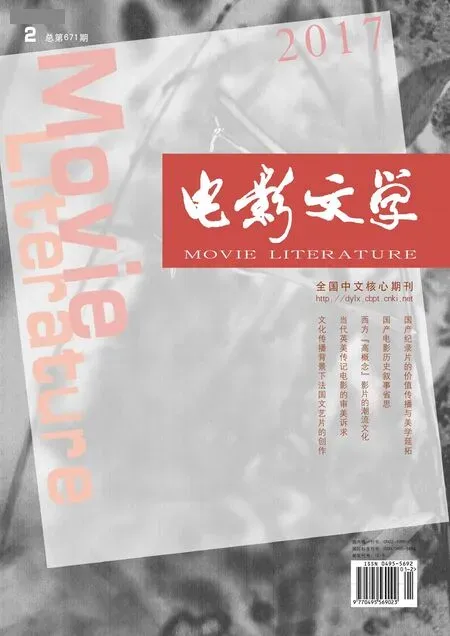间谍电影的“父—子”叙事演变分析
李玲玲
(百色学院文传学院,广西 百色 533000)
在各种电影类型中,间谍片与政治形势最为息息相关,甚至有论称“间谍片几乎是世界电影史上唯一具有清晰的政治史纪年的类型”[1]。几乎所有间谍片的叙事根基都是建立在“一道极度鲜明、不容混淆的敌我阵线”[1],间谍片与世界政治局势的密切关系,让间谍片的叙事也紧紧依赖于世界政治局势的变化。只有世界上依旧存在这一道严格鲜明的敌我对立,间谍片中特工英雄深入虎穴惩恶扬善的叙事模式才得以成立。正因为如此,在冷战结束之后,电影学者们纷纷认为间谍片这一类型也将伴随敌我阵线的消解而行将就木。我们也确实看到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作为间谍片标识的“007系列”迎来了低谷。然而,间谍片在低沉几年之后却再次死灰复燃,以《碟中谍》《谍影重重》及复活的“007系列”为例,间谍片再次进入观众视野。间谍片的死灰复燃,与间谍片的内部调整不无关系。复活归来的间谍片虽然沿用了传统间谍片特工深入虎穴摸清敌情步步为营的叙事迷局,但其背后的精神内涵早已截然不同。在后冷战时代间谍片进行的各种类型调整的尝试中,以《碟中谍》系列、《谍影重重》系列及“007系列”的新作《007:大破天幕杀机》为代表,间谍片呈现出的“父—子”叙事改变尤其值得注意。
一、从“父令子行”到“弑父”
与其他电影类型不同,间谍电影受制于现实政治的因素,电影中的主角间谍特工常常是依附于间谍组织的,电影往往是间谍组织派出一个任务,特工去执行这个任务。个人—组织是间谍片特别的人物关系结构。而间谍电影由于常常设置主人公“父亲”的缺席,如邦德就是一个孤儿,于是我们常常看到,特工与其上级领导者之间形成了微妙的关系。在“007系列”中,透过种种细节,可知邦德是被上级M招到特工组织的,而且也正是M一手训练培养了詹姆斯·邦德。影片有意将M设置为年长于邦德,同时也是唯一一个能制服有些许叛逆的邦德、让其乖乖听话的人。父亲的缺席,年长的男性对其人生的介入,这明显暗示,年长的男性M其实在邦德电影里,就是父亲身份的代表。于是,在冷战时期的间谍电影里,其实暗藏着几层叙事:第一层叙事是在敌我之间展开的,以“007系列”为例,通常是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冲突构成了影片最重要的叙事元素;第二层叙事是主人公的爱情叙事,这个与论题关系不大,暂表不论;第三层叙事就是主人公与组织的合作或者“父令子行”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冷战间谍片时期,主人公与苏联之间的矛盾越明显,那么主人公对组织/上级的忠诚就越得到肯定。第一层叙事潜在地强化了第三层叙事。然而,冷战结束,间谍片的叙事模式出现了极大的改变,其中最大的改变即第一层叙事与第三层叙事的关系变了,苏联这个敌对势力已不复存在,间谍片要获得发展,必须重新寻找敌人,而后冷战时代创作的间谍电影,不约而同地将在冷战时代曾经忠诚的组织/上级作为敌人,从而影片只剩下两层叙事:一是敌我矛盾——我和组织/上司的矛盾;二是爱情叙事。冷战时期间谍电影的“父令子行”模式,变成了“弑父”。
首先打破冷战间谍片的“父—子”叙事模式的电影是《碟中谍1》,这部于1996年上映的影片,极大胆地抛弃了冷战间谍片将苏俄间谍作为反派人物的常见设定,而将主人公伊森的上司——美国间谍组织头目吉姆设置为反派人物。饶有意味的是,吉姆与伊森的关系并不寻常,这个引领伊森成为特工并塑造了他作为特工的价值观的人,对伊森来说不是简单的上司,更是导师,是伊森心灵上的“父”的形象。影片开始,“父”被杀害,为“父”报仇成为引领伊森展开戏剧行动的原因,随着追踪真相的深入,伊森才发现原来仇人正是“父”,于是,冷战间谍片常见的“父令子行”的叙事模式,在这部影片中被替换为“父子冲突”,并在影片高潮,通过“弑父”这一行为解决了“父子”冲突。《碟中谍1》之后,“弑父”叙事便常常在间谍片中上演,其中《谍影重重》系列便将“弑父”叙事发挥到极致。这个系列影片一开始,主人公伯恩便失去了记忆,随着各种针对他的暗杀纷沓至来,他走上了探寻逃命与追踪真相的道路。随着追问的深入,伯恩发现自己原来是一名冷酷的杀手(特工),如今他不但脱离于组织之外,而且追杀他的正是其上司——曾经训练他并塑造他的人,他的“父”。“父子”冲突再次出现,并且电影高潮处,伯恩与伊森一样,做出了“弑父”的举动。《谍影重重》系列之后,再次出现“弑父”叙事的间谍片是《007:大破天幕杀机》。这部电影虽然不同于上述两部影片围绕与上司/导师的纠纷展开,但是影片有意将反派席尔瓦设置为另一个邦德。影片开场有意设置两人相同的特工经验、相同的特工身份背景及对M的感情,影片还特意设置两人多场交心对话戏份,强化两人一体两面的关系。正因这种一体两面的关系,所以当席尔瓦将矛头指向M时,他同时也是邦德的替身。M虽然是女性,但是结合系列影片设定(系列影片中M首先是作为男性形象出现的,尽管之后M由女演员饰演,但是其人物性格身份设定都未变)及M与邦德的关系,M代表的依旧是“父”。影片的高潮依旧发生在“父”的死亡时刻,尽管邦德没有直接杀死M,但邦德的复像席尔瓦替他完成了“弑父”的任务。
二、“弑父”叙事的深层原因
为何冷战结束后,“弑父”叙事会替代原有的“父令子行”的模式陡然出现?
“弑父”是文学批评中常见的概念,从《俄狄浦斯王》到《圣经·旧约》以降,父子冲突主题便是常见的结构母题。有论者认为,“弑父”并不简单指对“父亲”形象的谋杀,“父”与其说是父亲形象,不如说是父亲形象背后所指代的父权秩序。“弑父”本质是“对某种父权式专断和僵化的秩序法则产生出感情上的离合性(与亲合性相对)、心理上的本能抗拒以及由内在恐惧所衍发的文化防卫机制,从而以逼视的姿态表现出对其决绝意识和审丑化处置”[2],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由于“父”所指的具体秩序不同,从而在“弑父”叙事上呈现不同的主题倾向。文学界对“弑父”叙事的认识,也可以用在对间谍电影“弑父”的理解上。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几部“弑父”间谍片,其“父亲”形象有着明显的相似性。《007:大破天幕杀机》中,M被设置为不为情感所动、冷酷无比的上司。影片开始时,她为了完成任务,不惜下令让狙击手朝邦德开枪。而随着影片的推进,反派人物邦德的复像——席尔瓦之所以要“弑父”,也正是憎恨于M在国家意志面前毫不犹豫地选择牺牲特工们的生命。国家意志大于个人生命,是M作为“父”的重要特征。在《碟中谍1》中,上司吉姆同样出现了与M一样的特质,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自己的价值倾向。在影片的高潮,吉姆与伊森对决,吉姆坦承自己之所以叛变是因为害怕冷战的结束让自己不再有价值,从而变得一无是处,把个人价值完全依附于国家间谍事业,与M并无二致。《谍影重重》中伯恩的对手及上司,更是M与吉姆的另一个极端化的分身。他制订的“绊脚石”计划,把活生生的人塑造成超级杀手,这些超级杀手没有自我,只有上级传达下来的国家意志,他们的人生只依附于国家需要。在这里,国家意志已经完全碾压个人价值,成为绝对化的真理。而这些影片中的“弑父”行为,其实都是对“父”所代表的国家意志倾轧个人价值取向的清算,对把个人国家机器化的行为的反思。而个人意志完全服从于国家意志,这正是冷战间谍片的内在价值。如冷战阶段的“007系列”,无论是007还是反派人物,都被设置成国家机器的一员,他们都依附于政府机构,其行动都依附于国家意志展开,电影的戏剧矛盾也是基于两个人物所代表的国家意志的冲突建构起来的。政治身份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切。这些影片为了强化邦德作为国家机器的身份,还有意淡化他个人化、人性化的一面。影片看似将邦德设定为风趣幽默、风流倜傥、英勇无畏、魅力非凡的人物,但其实这种设定恰好与影片中的苏俄间谍形成鲜明反差,这些电影里出现的苏俄间谍作为邦德的对立面,无一不是冷酷刻板、嗜血无情甚至变态扭曲的。邦德风趣幽默的特质在这里并不是作为个人化的特质存在的,而是作为意识形态表达,与苏联形成反差,满足西方社会对二元对立的冷战阵营的想象。与此同时,邦德还总是无亲无故,来去自如,他不会陷入任何伦理困境之中,包括两性关系——尽管邦德时常陷入两性关系中,但爱情伦理在他身上毫无作用,他可以前一秒与这个女人发生关系,而下一秒马上与另一个女孩往来(后冷战时代间谍片的特工在这方面与邦德大相径庭,他们不但陷入恋情甚至结婚成家,伦理困境成为他们作为特工无法回避的问题。这种设定正是让特工也呈现人性化的一面,从而反思冷战间谍片中特工国家机器化的价值倾向)。爱情伦理乃至所有伦理的缺席,让邦德成为无畏的武器,完全服从于国家意志的代表M。而M其实就是《碟中谍1》《谍影重重》及《007:大破天幕杀机》冷酷的“父”的形象的滥觞。
从这个角度看,后冷战时期间谍片出现的“弑父”叙事,其实正是对间谍片的冷战遗产进行清理,“弑父”即是对冷战价值体系的抛弃的体现。
三、“弑父”与身份危机
与“弑父”的叙事母题相应,这些影片不约而同地运用“寻找自我”的叙事外观。《007:大破天幕杀机》中,一直无亲无故、风流洒脱的邦德竟然罕见地回顾起了自己的童年,回顾起自己走上特工之路的历程,而且更是将决战之地选择在自己的故土,其“寻找自我”重新出发的意味不言自明。有学者认为,寻找身份,其实是“人们的社会文化关系处于分化重组、再构造、再确认的状态,个体不得不在阶层、种族和社会体制的文化之间进行各自身份的选择……我(们)是谁?不再只是哲学意义的抽象问题,而成为社会文化关系中如何定位主流与边缘、多数与少数、群体与个人关系的现实问题”[3]。在间谍片中,与“弑父”同时出现的身份危机,就是原有的社会价值结构崩塌之后,面对新的社会主人公不断审视自我的表现。“寻找自我”一方面意味着对自己原有的身份进行重审,另一方面是重构新的价值体系。“寻找自我”的前提是“自我”的迷失。这一点在《碟中谍1》中表现为伊森受人迫害,他的身份受到质疑,他必须自证清白。在《谍影重重》中,“寻找自我”则直接表现为追问“我是谁”。然而,由于主人公都是无辜者,那么“自我”的迷失则意味着现实世界中是非标准已然崩塌颠倒。
这些影片与冷战间谍片不同,主人公面对的强敌不再是苏联,而是来自本国政府机构组织的其他特工,善恶对立也不再如冷战间谍片那样鲜明,而是混沌不清的。主人公们“追寻自我”实质是要在是非模糊的后冷战时代恢复行之有效的价值体系。不过,当发现幕后真凶是“父”时,试图恢复价值体系的目的被替换为摧毁旧有价值体系。《碟中谍1》便是沿着这一模式发展的。影片的高潮,伊森杀掉了吉姆,他不但找回了自己的身份,而且这个身份已经与之前吉姆赋予他的身份不再相同,他寻回的是摒弃吉姆冷战价值体系后的新的自我。“寻找自我”的叙事外观是基于“弑父”而出现的。面对“弑父”后的价值崩塌,主人公们必须寻找新的价值归所。而摆脱冷战个人国家机器化的价值取向,回归人本精神,是后冷战时代间谍片“弑父”叙事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