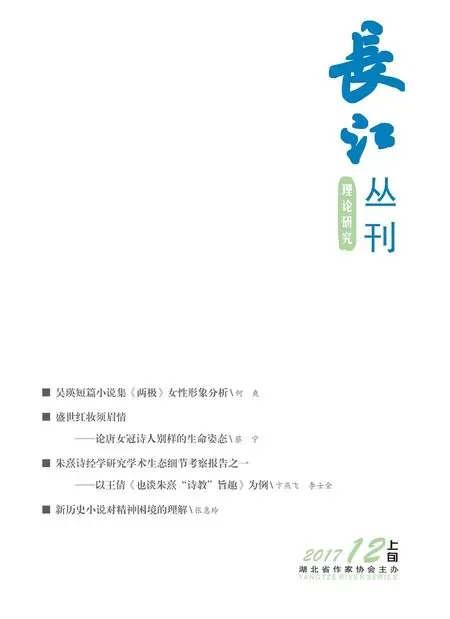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缘起
刘海花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缘起
刘海花
土地是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保障,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的土地制度历经了数次的改革与演变,党和国家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后,最终确立了以“包产到户”为中心思想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本文通过查阅文献、论文著作等资料就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如何确立及成功实施的原因两方面做了简要的概述。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确立 原因
新中国成立以后,土地问题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首要任务,根据实际情况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带领下,经过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及人民公社三个主要阶段的改革,促使我国土地制度虽然历经坎坷但是最终顺利过渡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自此之后,农民获得了土地的经营权,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为此后我国各项事业的长足发展做出了的贡献。
一、新中国历次土地体制改革及其弊端
(一)土地改革时期(1949—1953)
经过四年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取得最终胜利,但胜利的景象之下掩盖的是国民党匆忙出逃后留下的一片狼藉,针对此种情景中共中央迅速作出反应,1950年6月30日召开中共七届三中全会,颁布了全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较之以往的任何一次都多有进步之处。这期间,广大人民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广泛开展农业生产运动,消灭封建地主所有制,使农民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愿望,农业生产量大大超越解放前。其后农村由于政策实施不当出现了一些问题,首先是“两极分化”现象层出不穷,据当时对东北地区18个村进行调查,富农占农村户数的1.8%,人口的2.6%,土地的3.9%,耕畜的6%,车辆的7.7%,[1]这就表明贫富差距逐渐扩大,不利于农村的综合平稳发展;其次,农业生产力水平依旧低下,虽然土改后农业生产快速增长,粮食增产,然而由于缺乏现代化生产工具和足够的财政资金支持,生产时常中断,生产力水平始终停滞不前,阻碍了国家综合能力的提升。
(二)农业合作化运动(1953—1958)
土革后建立起农民占有小块土地的个体经济模式,而针对土改后农村改革再将何去何从的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了农业互助组织。1949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为1132亿公斤,棉花总产量为890万担,而到1954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1695亿公斤,棉花总产量达到2130万担。[2]随着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其局限性也日渐突显出来:由于合作社的初期成功,大大助长了党内的急躁冒进主义,致使各地开始盲目扩大发展指标,在农村经济体制上留下了后遗症。
(三)人民公社化时期(1958—1978)
1958年我国正式迈入人民公社时期,这一阶段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产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人民公社是指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位,它是党的整风运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的产物。
人民公社最大的特点是“一大二公”,“一大”,是指公社规模大。当时毛泽东为《大社的优越性》一文写了这样的一段话:“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当然有很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3]因此,各地涌现很多千户社、万户社;“二公”,是指公社公有化程度高,土地的使用权完全掌握在人民公社手中。
人民公社建立初期各地争先恐后,纷纷建立人民公社,截止1958年全国农村普遍实现人民公社化。这一制度在农村历经20多个春秋,但在这20年中,农业总产值平均递增只有2.6%,粮食产量为2.3%,棉花为1.4%,猪牛羊肉为3.9%。[4]这一阶段也是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发展最缓慢的20年,农民生活水平很低,贫困人口与日俱增。
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缘起
1956年秋,在高级社刚刚普及不久,在其第一个生产周期浙江省永嘉县就出现了类似包产到户的现象;后来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又出现了两次同样的现象,但这在当时“左”的指导思想蔓延和人民公社盛行时期是不能被容忍的,于是屡次遭到扼杀。直到1977年11月,在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带领下,安徽省首先突破限制,将农活责任到个人,由此包干到户、到组等做法逐步出现并实施。1978年底,小岗生产队20户农民秘密开会商议,拟定承诺书并按下手印,第一次正式实现了分田到户,与此同时,四川、广东、甘肃等一些省区也相继出现这种现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正式确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一)内因
1、人民公社体制自身的弊端
人民公社体制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自身的缺陷是先天性的,因而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公社体制的强制性
其强制性主要是无论经济生活还是日常生活对于入社农民来说基本没有人身自由,而发展到后期国家规定一旦入社便不可以再退社。一方面在经济生活中,公社实行党委领导制,以党代政,以政代社,强制农民怎样生产,生产什么,什么时候生产等。当时,湖北省沔阳县农民贴出的大字报,就是对此的不满写照:“天下雪,地下秧,谷芽落地一扫光。”“干部强迫命令大,整好熟田不插秧,一切停止把湖下,误了一年好庄稼”。[5]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公社对于入社成员实行军事化管理,社员不仅没有星期天,而且农民想要在业余时间进行各种副业生产都会受到限制。早在1962年7月,邓小平在《怎样恢复生产》一文中就认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最为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一种生产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6]
(2)“一大二公”的平均主义泛滥
人民公社时期,在分配方式上采取“工分制”作为计量标准,由于这种分配制度只重视工作时间,完全忽略了实际劳作态度和工作质量。[7]刘少奇在1957年也曾多次提到:“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大量的表现在分配问题上”。[8]公社时期按工分来分配的报酬制度,其实这是一种严重的平均主义,结果导致干好干坏一个样,老实人吃亏,耍赖皮的人则占了大便宜,长此以往,许多人都不愿意积极干活,很多农村出现了粮食烂透了,烂地里了都没有人愿意收,农民对于自己以后的生活失去了信心对于公社也失去了信心。
由此,可以看出人民公社的做法是不合乎实际的,脱离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应有的轨道,从根本上就没有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
2、政策颁布利于农民切身利益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个人与集体利益分配相对清晰,调动了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农业生产经营本身与生产者的产品分配挂钩,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发展多种经营,生产力获得大大解放,农业产量迅速增加。1988年与1978年相比,平均每一农村劳动力创造的农村社会总产值增长1.8倍,平均每年增长10.9%;每一农业劳动力创造的农业总产值增长65.1%,平均每年增长5.1%;生产的粮食增长16.3%,平均每年增长1.5%。这10年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大于从1949年到2975年的29年。[9]同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促使劳动力的使用和分配更为合理,把大批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乡镇企业促使劳动力资源得到更为合理的配置。
(二)外因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亲情观念早已渗透人心,亲情可以激发成员对家庭的忠诚,愿意放弃部分经济利益而为家庭做贡献。这既是私心的作用也是潜在的情感(亲情)在起作用,劳动者更顾小家却不顾大家(生产队)是自私的表现,然而劳动者更顾小家却是出于对亲人的爱。[10]很多农民认为在生产队中工作,是为集体而劳动的,并且劳动的多少与自己没有直接关系,所以每次分配都要斗争一番,来努力争取自己的利益扩大化。而如果就一个家庭而言,父母之间、兄弟姐妹之间都是血浓于水的,每个人都不会为了利益而可以损坏亲情,相反个人可以适当的牺牲自己的利益来帮助自己的亲人。
家庭和生产队这两个集体对于农民来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在生产队中一味按照平均制分配,不管其他因素,那么意味着它始终无法开出一个令农民满意的条件来促使他们积极努力工作;在家庭中,情感很难用一个标准来衡量其价值,当生产队中发生利益纠缠时,人人都可能出现偷懒、怠工等现象,而当这种“不公平”被家人所接受时,他们就会竭尽所能,为了家庭的共同利益而努力,相对应的农业生产力明显上升,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
“太上以德扶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左公·僖公二十四年》)也就是说,虽然对于治理国家或管理集体来说,基本家庭观念的亲情之间不如以德治民有效,但利用家庭观念来处理某些事情也不失为一种有效措施。[11]一个人他生活的空间可以很大,但最基本最牢固的应该是家庭,只有将家庭关系处理妥当,才能生活的更加和谐与美好,才能在此基础上既解决自己的温饱又满足国家生产的需求。
三、结语
综上所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举,自实行后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的成果也是有目共睹的,不仅改善了旧农村的落后面貌,而且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以家庭为基本生产经营单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有小农经济的某些特点,但它既能与小生产相适应,又不排斥社会化、规模化、产业化生产,能够与现代大市场相适应.现在我国农民群众的生活质量越来越好,生活幸福指数也越来越高,而现阶段小康社会的逐步完善也充分证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我国农村的实施是成功的,不仅给我国农业找到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而且对世界各国都有借鉴意义。
[1]张神根.中国农村建设60年[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
[2]陈吉元.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M]大同:山西经济出版社,1972:125.
[3]毛泽东选集[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57~258.
[4]农业部计划司.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26,47,146,256.
[5][6][8]林志友.人民公社体制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比较研究[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
[7]白杨.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变迁[D].沈阳:辽宁大学,2007.
[9]傅晓.新时期我国农业政策的走向[J].安徽农业科学,2007(3).
[10][11]邓曦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成功的文化因素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9(7).
西北民族大学)
刘海花(1992-),女,汉族,甘肃武威人,历史学硕士,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