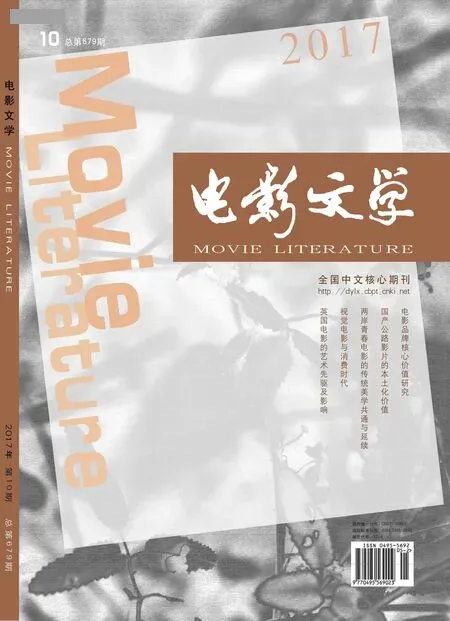影片《英国病人》的多主题研究
舒 瑜
(西京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3)
一、从小说到电影
早在电影艺术发展的初级阶段,从文学作品中汲养就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随着电影艺术的不断发展,将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更是十分常见。文学作品丰富的内涵为改编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同时,将著名的文学作品搬上银幕也迎合了阅读者和观影者的审美期待。虽然将文学作品搬上银幕大受欢迎,但事实上,真正成功的改编并不多见。由于小说、戏剧与电影属于不同的艺术形式,它们讲述故事、塑造人物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所以在改编的过程中对于创制者来说是否忠于原著就成为一个困难的抉择。对此在业界有两种呼声,一是倡导在改编过程中将文学作品原原本本地搬上银幕;另一种说法则是鼓励电影创制者在改编过程中的再创造。[1]事实上,将文学作品中的故事和人物原原本本地搬上银幕反而很难原汁原味地呈现原著,在时长的限制下,电影创制者在改编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应该学会取舍、适度“背叛”,从而将原著中的核心故事生动地呈现在银幕之上,而导演安东尼·明格拉和制片人索尔·杂恩慈就是美国好莱坞将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优秀代表。
1996年,初出茅庐的美国导演安东尼·明格拉将迈克尔·翁达杰于1992年所著的小说《英国病人》成功搬上银幕,这一勇敢的举动奠定了安东尼在好莱坞的地位。之所以称安东尼对《英国病人》的改编是勇敢的举动,其原因在于迈克尔所著的这部小说拥有着丰富的主题和复杂的人物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并不适宜改编成电影,改编的难度巨大。在改编的过程中,曾经拥有着丰富改编经历的制作人索尔·杂恩慈为影片《英国病人》的成功改编也贡献了巨大的智慧。在二人多次的修改、编写后,一部源于小说又高于小说的影视作品诞生了,凭借着巧妙的改编和优良的制作,影片《英国病人》不仅获得了许多观影者的热切推崇,而且包揽近十项奥斯卡金像奖及世界范围内的重量级奖项。
影片《英国病人》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讲述了男主人公阿尔玛西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生活、情感经历。在一次沙漠探险的过程中,阿尔玛西与杰夫里及其妻子凯瑟琳偶然相遇,这次偶然的相遇彻底改变了男主人公的命运。在探寻沙漠绿洲的过程中,阿尔玛西与有夫之妇凯瑟琳相恋,得知真相的杰夫里十分愤怒,决定驾驶飞机与阿尔玛西同归于尽,正是这次危险驾驶夺去了杰夫里的生命。为了尽快医治在撞击中受伤的凯瑟琳,阿尔玛西用沙漠的路线图与德军交易并换取了一架飞机,但死神却再次降临,飞机失事使阿尔玛西的大脑受到重创、面目完全烧毁。失去记忆的阿尔玛西住进了盟军的医院,在医院中阿尔玛西被称为“英国病人”,同时,医院中的阿尔玛西备受盟军情报员的怀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他离开了人世。在医院期间,影片还穿插呈现了医院护士汉娜与印度士兵基普的情感故事。正如上文所述,《英国病人》包含了多重主题,在改编成电影的过程中,导演选择性地突出了阿尔玛西的生命故事,使整部影片在保存多主题面貌的同时,更具有统一性和协调性。本文将在概述《英国病人》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过程基础上,立足影片中的战争故事、两性故事和民族故事,对该片中的反战主题、爱情主题及身份主题进行研究,以期从主题研究层面较为完整地呈现美国当代电影发展历程中这一优秀的改编之作。
二、影片《英国病人》中的战争故事与反战主题
影片《英国病人》中的男主人公阿尔玛西本是匈牙利的贵族,在富足的生活中,阿尔玛西钟情于探索远古的历史,这也是他只身前往沙漠探索绿洲的原因。这位富有诗意的历史研究者本应该沉溺在自己的梦想与追求之中,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却烧毁了他的梦想,使他在几经波折后不仅痛失爱人、朋友,还终生活在自责悔恨的泥淖中,忧郁而终。影片《英国病人》中的战争故事和反战主题并没有采用宏大叙事模式,而是将叙事的焦点集中在男主人公阿尔玛西的生命轨迹之上,通过描述战争对阿尔玛西命运的改写呈现出令人动容的反战思想和深入人心的反战主题。
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以同盟国和轴心国为对垒双方的二战战火燃及五个大洲。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实施扩张侵略的罪恶行为,但被迫应战的同盟国也不可否认地成为战争的参与者。影片《英国病人》就是立足战争对人类生命的毁灭和对个体命运的改变来表达反战思想的。无论是邪恶挑战的一方,还是正义应战的一方,都会在战争中对个体带来灾难,而这就是战争的固有属性。《英国病人》的男主人公阿尔玛西在沙漠探险中爱上了凯瑟琳,凯瑟琳丈夫的报复行为使凯瑟琳生命垂危。为了拯救挚爱之人的生命,阿尔玛西找到了同盟国的英国军队寻求帮助。在战争年代,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变得珍贵而难得,阿尔玛西独特的姓名和对沙漠执着的热爱引起了英国军人的怀疑,英国军人判定阿尔玛西很可能是德军的间谍。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英国军队将阿尔玛西拒之门外。无奈之下,阿尔玛西将珍贵的沙漠地图作为筹码与德国军队进行了罪恶的交换,换取了能够飞离沙漠的飞机,为救治凯瑟琳争取到了宝贵的机会。这次交换不仅使阿尔玛西的挚友即地图的绘制者含恨自尽,还间接伤害了成千上万同盟国无辜者的生命,同时这次罪恶的交换也彻底改变了男主人公阿尔玛西的一生。
在影片《英国病人》中,我们能够看到叙事者是以一种冷静客观的姿态讲述阿尔玛西与德国军队之间的交换,并没有表露出对于阿尔玛西罪恶行为的不齿。[2]事实上,在这种极端困境之中,阿尔玛西别无选择,深陷沙漠的他已经竭尽全力地与英国军队协商,在万般无奈之下才选择了出卖重要的地图来换取带领凯瑟琳离开的飞机。对于阿尔玛西而言,这一抉择无疑是痛苦的,战争将阿尔玛西推到了陌生群体和挚爱个体之间的利益选择前。可以说,无论阿尔玛西如何选择,他的余生都将活在痛苦之中,而这就是战争强大而深远的破坏力量。随着影片故事的推进,我们不难发现阿尔玛西的余生都活在无法逃离的自责与悔恨之中,成为一位永生难以痊愈的“英国病人”,而这也是影片《英国病人》反战主题的精华所在。在阿尔玛西的命运悲歌之外,影片还通过汉娜、基普等主要配角形象的人生命运呈现了反战主题,汉娜和基普原本生活在战争之外,但战争巨大的影响力也波及了他们的生活并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汉娜原本生活在加拿大,在其家人和亲人死于战争之后,形单影只的汉娜以医护人员的身份来到了战场,在绝望之中留守在阿尔玛西身边照料这位同样绝望而痛苦的战争受害者。而基普原本可以在家乡成为一名医生安然度日,战争爆发后,基普以印度锡克兵团军人的身份来到了异乡战场。虽然基普与汉娜相恋,但最终两人却在战争的影响下分道扬镳。
三、影片《英国病人》中的两性故事与爱情主题
影片《英国病人》中的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爱情故事是一段婚外恋。男主人公阿尔玛西和女主人公凯瑟琳在沙漠相遇,此时的凯瑟琳已经拥有了一位非常爱她的丈夫杰夫里,而这次偶然相遇也使三人陷入了情感的旋涡中。从表面上看,影片中的凯瑟琳是一位传统的女性形象,她言说着自己对于自然和丈夫的热爱。但事实上,凯瑟琳的内心却无法在这段平实的婚姻中得到满足,企图寻找灵魂之爱的力量也推动着凯瑟琳逃离道德和婚姻的束缚走向阿尔玛西的怀抱。而发现妻子与阿尔玛西在公寓中共度良宵的杰夫里无法抑制对阿尔玛西的愤怒,决定与阿尔玛西同归于尽,在开飞机撞向阿尔玛西的过程中丧命,而在飞机即将冲向地面的瞬间,杰夫里用他最后的时间表达了对凯瑟琳的真挚爱意。如果说凯瑟琳与杰夫里的婚姻代表着主人公打破道德限制的成功,那么阿尔玛西与凯瑟琳的恋情就代表着主人公大胆追爱的失败。在这段三角恋关系中,阿尔玛西一直处在道德与情感的矛盾之中,无论是在凯瑟琳丈夫杰夫里在世时,还是在杰夫里过世后,阿尔玛西都挣扎在这一矛盾之中。在杰夫里制造的撞机事故中,凯瑟琳身负重伤,为了给凯瑟琳提供及时的治疗,阿尔玛西向德国军队出卖了情报,终身背负着道义上的谴责。不仅如此,阿尔玛西在道德与情感之间挣扎过后,并没有如愿以偿地抱得美人归,在驾驶其用沙漠地图换来的飞机时,二人再次遭遇袭击,凯瑟琳也香消玉殒,这使阿尔玛西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英国病人”。影片《英国病人》在叙事的过程中并没有表现出对阿尔玛西和凯瑟琳的谴责,反而流露出了些许同情,呈现出了在两性关系中个体面临着道德与情感之间的矛盾和挣扎,为观影者留下了更多自由解读的空间。
在影片《英国病人》中,除了阿尔玛西、凯瑟琳、杰夫里之间的悲剧三角恋情之外,汉娜与基普之间的爱情悲剧也得以呈现。汉娜在失去挚爱后几乎丧失了生存的希望,在濒临绝望的心境下,汉娜才选择照料“英国病人”阿尔玛西并遇到了“重生”的希望——基普。当拥有着古铜色皮肤的拆弹军人基普出现后,汉娜被基普的异域风情所吸引,二人在一起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但细观影片不难发现,汉娜经常无意识地按照白人主流文化价值观念来改变、影响基普,而基普虽然乐于接受这种改变,却无法真正变成汉娜所希望的样子,这也为二人的分离埋下了伏笔。战争结束后,来自加拿大的汉娜和来自印度的基普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二人的分道扬镳不仅是因为国籍的差异,也在于他们背后迥然不同的文化差异与融合的失败。
四、影片《英国病人》中的民族故事与身份主题
影片《英国病人》中的阿尔玛西在失去凯瑟琳的同时也失去了记忆,从而获得了一个十分模糊的身份——“英国病人”,而这种模糊的身份或许正是主人公一直以来所追寻的。在沙漠中走投无路之际,阿尔玛西首先想到的是向英国军队求助,但特殊的名字使他并没有在英国军队处得到身份的认同,这直接导致了阿尔玛西与德国军队交换地图,间接地帮助了敌人,而这一举动所带来的愧疚使阿尔玛西的自我身份更加模糊。虽然他拥有正常的思考能力和识记能力,但却始终想不起自己的名字。从心理层面而言,阿尔玛西刻意地遗忘掉了自己的身份。影片中反复出现的意象物是一部宣扬民族融合、文化平等的著作,即希罗多德的《历史》,阿尔玛西一直将这部书带在身边、反复阅读。影片通过意象物《历史》为绝望中刻意模糊身份的阿尔玛西提供了精神支柱,同时也表达了民族融合和文化平等的希望。[3]
与阿尔玛西刻意遗忘身份不同的是影片《英国病人》中的基普,基普一直在寻找自己的身份。基普出生并成长在印度这个殖民国度,基普自幼以来所接受的教育熏陶及文化熏染都指向了与自己身份不符的白人文化,这使基普对自己原生民族所赋予的身份缺乏认同,渴望在白人文化圈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也是基普选择远离家乡、征战异国的重要内在驱动力之一。[4]但在白人世界中,基普逐渐意识到自己对原生民族的热爱,尤其是在他的战友身亡后,基普内心升腾起强烈的对本民族身份的认同感,在这种文化夹缝中的生存状态也得到了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