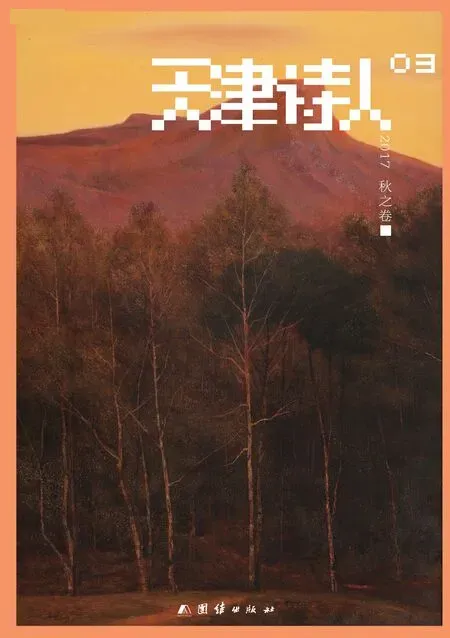写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几句话(外一篇)
金汝平
不必挂在嘴上,不必印在名片上,但你要记住:你是一个诗人,并以此为骄傲。内心没有骄傲的人,根本无力创造,一切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创造者,内心都是骄傲的。
人生苦短,写诗是快乐的。只有写诗的人才能隐秘地享受。
当你丧失了青春,才会明白青春是何等珍贵。青春赐予你勇敢,无畏,狂热的激情,青春赐予你叛逆,反抗,战斗的欲望及蔑视一切权威一切秩序的力量。只有一个伟大的青春期,转瞬即逝,然后是衰退,枯竭,平庸,妥协,是生命力不可抑制的萎缩,理想之鸟坠落进现实的污浊里。
如果在青春期写不出好诗,你不要期望中年或老年写出好诗。
如果在青春期不是诗人,更不必梦想中年或老年成为“大师”。
青春期,你必须迈出那成为诗人重要的一步。如果这第一步不能迈出,诗的远征则永不能开始。
你要握紧手中的笔。你要洞察自己动荡的心。
喧嚣的市场的叫卖声中你要关紧你的窗,同时打开你精神上的众妙之门。
向高手挑战,不必和低手过招。某些胜利以及它带来的荣耀是廉价的,廉价的荣耀并非我们真正渴求的荣耀。
兄弟,我深知你内心的深处渴求着什么,那也是我所渴求的。而我常常听见一个声音这样古老而悠远,“跨过时代的破旧小径,穿过死亡的门户,到我这儿来吧,因为好梦凋谢,希望落空,采集来的当年的果实也腐烂了,我倒是永恒的真实,在你从此岸到彼岸的航程中,必将一而再、再而三地遇到我[印度泰戈尔]。
你可以放弃诗。这并非错误,更非罪过。但不必以生存的压力物质的压力为借口。没有一个时代,诗人活得如鱼得水。痛苦出诗人,痛苦也出勇士;叛逆者,凶手,刺客,恐怖主义者,痛苦也出疯子,精神病人,出虐待狂与被虐狂,出麻木的人,白痴,出政治家、恶棍,出那些能够超越痛苦的人,痛苦也出和尚、尼姑、隐士,出智者。痛苦又何尝不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和痛苦做殊死的抗争,最终,诗人仍在痛苦中。“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被时代践踏被时代伤害被时代凌辱甚至被时代无情毁灭的诗人还少吗?他们留下诗歌。——这活过、爱过、梦想过、抗争过的见证。但也不要问:“这到底有什么用?”
虚无主义,乃一切精神价值与意义的可怕敌人。对诗人亦如此。当虚无主义剥夺了你对诗歌的热爱对诗歌的信念,你的创造力必荡然无存,你成为虚无主义的牺牲品。
写诗,也不过是我们与虚无肉搏的一种方式,它支撑着我们出生入死,哪怕最终仍归于虚无。
你必须寻找自己的同志。那些不是你同志的人,也并非你的敌人。作为诗人,敌人就是那些阻碍、控制、抹杀你的创造力的东西。在与它的斗争中,我祝愿你获取一些小小胜利。里尔克说过:“有何胜利可言,挺住就意味着一切。”
我们只是比你先行一步。先行一步就跨入中年,先行一步就逼近死亡。
现在,我们被称为“中年诗人”。
而我要反驳叶芝著名的见解:“那随时间而来的智慧”,不,除了智慧,随时间而来的还有愚蠢,还有僵化,还有保守,还有停滞不前,还有对传统文化的屈从,还有写作无形的陷阱。
中年为诗人写作带来了雄厚、博大精深、包罗万象的可能,同时我看见它布下更多阴森森的危机。随着生命的衰退,我们尖锐的批判性被削弱,创造的锋芒在减少。
某种意义上,危机是难以克服的,难以战胜的,否则就不是危机。
纵观中外诗歌史,那在中年以后的越写越好的确是寥寥无几。
多少杰出的诗人,青春期就把一生的杰作写尽了,写完了。
更多残忍的事实是:
激情之火熄灭了,诗也不复耀眼。
“红旗还能打多久?”中年诗人们的写作还能继续多久?
而未来的国度,未来的春天,呼唤着属于自己的诗人,只有那些最纯洁最敏锐的耳朵才能听见。它呼唤着你们,也选择着你们:你们中间有谁能够被幸运地选择?
人生苦短,写诗是幸福的。写出杰出诗歌的诗人,更是幸福的。哪怕这隐秘的幸福,他人仍难以分享。
最后,我要说出我年轻时候说过的一句话,那像是祝愿,更像是预言:“让我们的诗成为世界的垃圾堆上盛开的鲜花。”
两种不同的诗歌史
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诗歌史。
最客观最全面的是学者们白头到老呕心沥血写下的诗歌史,最乏味最枯燥最四平八稳也最匮乏真知灼见的也是这种诗歌史,哪怕它们被选为文科大学生研究生的“教科书”,或者“必读书”“参考书”。
通过按部就班的学习与考试,应该说,这类“教科书”相当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于是,一整套固定化模式化标准化的文学理念作为答案源源不断地灌输给一代代文学青年,而他们也具备了朝他人炫耀的指手划脚的权利:“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诗佛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然而,伟大的文学从不会轻而易举地水落石出,尘埃落定,它们仍然隐藏在时间的亘古黑暗中等待着重新发现的一缕澄明之光。那被忽视的,也未必没有宝贵的价值,那被高高举起的、也有可能再度沦落在遗忘之中。更为重要的是,那些被称为“伟大诗人”的诗人,他为什么伟大,哪些方面伟大,伟大对后者又有什么启发,提供了什么可资借鉴的艺术经验,什么压抑什么消极的作用,仍需要不断地、持久地、多角度多侧面地重新评价,把古往今来极度驳杂繁复极度混乱不堪的文学现象作简单化的处理,标签化的处理,并试图构造一种相当稳定的文学秩序,它带来的文学知识只是死的文学知识。
还有另一种诗歌史。那是诗人自己内心里的诗歌史,诗人眼中的诗歌史。
和学者们相比,诗人的审美选择带有个体性、异质性和随意性。由于神秘的偶然的机遇,诗人遇见的第一本诗集或者第一个诗人,肯定会对他的一生产生明显或隐秘的影响。十八岁读泰戈尔和三十岁读泰戈尔,不可同日而语。早年读坏诗,那是极其可怕的营养不良,定会带来写作上的面黄肌瘦。而当他有眼光有胸怀有见解之后,他的阅读同样带有不可避免的倾向性。为内心深处创造的强力所驱迫,他更多选择那些能够在当代特殊语境中能够刺激他的创造力的东西。纯粹的欣赏当在他的注意之外。并不是一个文学史中占据显赫位置的诗人就会让他俯首,不,或许一个身边兄弟的一首诗作,倒叫他一定程度上发现了自己,打开了自己。而这个诗人兄弟和他一样是才华横溢却又默默无名的,这样的事实在古今中外比比皆是:如马拉美启发了瓦雷里,布勒东启发了勒内·夏尔,庞德启发了艾略特,而在中国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地下诗界,食指影响了北岛,根子影响了多多,多多又启迪了一大批更年轻的诗人。对于阅读,诗人表现出很大的片面的兴趣。正如卡内蒂所言:“没有混乱的阅读,诗人不会诞生”,又有哪一个诗人,是按照文学史的指引亦步亦趋地读书呢?可能有,但太少太少。
我们感到了诗人的率性,诗人的意气,诗人的随心所欲,诗人的刁钻古怪。平衡地冷静地对待经典作家和他的天性是格格不入的,摆在书架上的书,有些永远摆着形同虚设,有的则是在茶余饭后随手翻开又随手合上,或者抛进楼下绿色的垃圾箱!一起扔进来的还有废纸、桔子皮、空酒瓶和烂了一半的红苹果,让那些拾破烂的人们收罗起它们凯旋而归吧,人生阅历,童年的回忆,痛楚的苦难的生命体验,审美观的不同,工作环境的区别,甚至胖与瘦的差异,都会不同程度地支配着他阅读的取舍,他对诗人的选择。他会对一个诗人爱得如痴如醉无以复加:“天才,天才,绝对是横空出世的天才!牛逼,牛逼,光芒四射的牛逼!”,也会对另一个同样杰出但他不感兴趣的诗人熟视无睹,还会对另一些诗人深恶痛绝白眼一翻看不见黑眼珠:“这是什么烂诗,烂得和这个不要脸的黑暗世界一样烂,烂得臭气冲天”。我想,当马雅可夫斯基以未来主义者的名义高亢地宣布狂野地宣布:“把普希金托尔斯泰从现代的轮船上扔下去”的时候,肯定会有许多诗人咬牙切齿恨不得把马雅可夫斯基扔进大海溺死,也肯定有和他心心相印的年轻诗人手舞足蹈蹦蹦跳跳。审美上的标新立异,让诗人团结又分裂,分裂又团结,团结又分裂再不断地分裂下去。我们应该对此理解并付以淡淡一笑。有些诗人一辈子只能喝酒不能谈诗,有些诗人喝酒谈诗但谈得面红耳赤摔破酒杯扬长而去,诗人与诗人虽然置身于诗人的阵营中,其实差异大于一个诗人与一个普通他者的距离!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猫找猫,狗找狗,两个黄鹂鸣翠柳鸟儿问答,伟大浩瀚的自然界也是如此呀!因此,一个诗人,在茫茫世间踽踽独行,他的影子是飘忽的是孤单的,任人践踏,但在他脆弱的内心深处,他总是苦苦寻找他的精神之父,寻找精神上亲密无间的弟兄。只有如此,他的写作才会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拥有了坚定的无形之力。最终,诗歌不会抛弃他,他已把自我联结到和历史文化有关的广阔博大的精神谱系之中。
这就是诗人自己的诗歌史。
有时,这诗歌史可能会零散地、碎片地呈现在诗人笔下,更多的时候,这诗歌史已深深地刻骨地书写进诗人的血液和呼吸中。并直接决定着写作的成败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