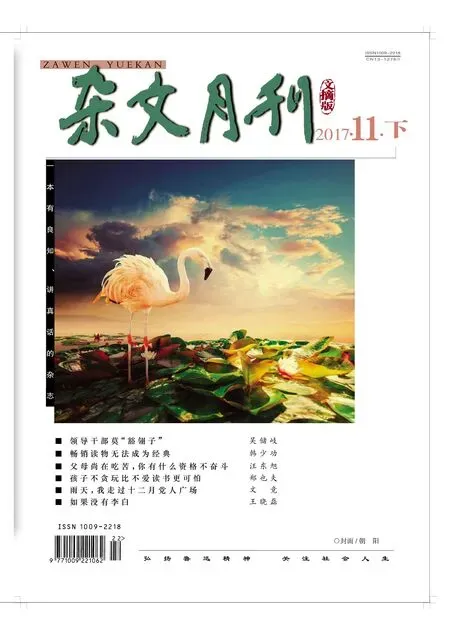托尔斯泰的忏悔
□狄青
1852年7月,彼得堡《现代人》杂志收到一篇来稿,作者是一名在高加索山区驻防的炮兵下士,署名“耳·恩”,小说题目叫《童年》。杂志主编涅克拉索夫觉得这是位天才,把作品拿给屠格涅夫看,屠格涅夫说:“给他写信,告诉他我欢迎他,向他致敬并祝贺他。”涅克拉索夫回信给小说作者,希望他继续写作,同时商量小说发表时可否用真名,对方回信同意——于是,一个叫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作家从此声名鹊起。
许多年后,屠格涅夫在临终前,给托尔斯泰写去一封信,诚恳希望托尔斯泰回到文学,不要辜负自己的才华。而这时候,托尔斯泰正每天穿着长褂和他自己亲手缝制的布鞋,行走在底层农夫之间。事实上,在完成了《安娜·卡列尼娜》后,他的文学创作便停止了。而他给世人的解释是一篇《忏悔录》。这是一篇忏悔自己同时也在剖析他人的文字,与卢梭、奥古斯丁《忏悔录》中叙述的内容迥然不同,托尔斯泰要探讨的问题其实只有一个:人生的意义何在?我们为什么而活?
说实话,初读《忏悔录》,我就被震惊了,因为托尔斯泰完全颠覆了我们对传统意义上“作家”的认知,那就是,作家不能只是一个写作者,还要懂得忏悔、接受心灵的拷问,继而才有可能超拔。忏悔不易,救赎更难,一个人要拉他人出沼泽,自己却站在泥塘里,谁救赎谁?身为贵族的托尔斯泰产生了放弃所有财产的想法,但遭到妻子强烈反对,这成为他们夫妻关系恶化的重要因素。结果是:托尔斯泰放弃个人财产,转到夫人索尼娅名下。我们不能责怪索尼娅,她为托尔斯泰生了十三个孩子,单一部《安娜·卡列尼娜》她就抄了七遍。她只是一个希望过安稳生活的女人,她崇拜但不理解托尔斯泰。
从《忏悔录》里我感到,对托尔斯泰来说,思考生命的价值和信仰的意义,是他的天生责任和义务。所以,他开始俯下身子去倾听那些沉默的大多数。从那些隐忍的底层人群中,他看到了信仰对于生命的意义,看到了信仰与浮华生活之间隐秘的对峙关系。
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托尔斯泰从很早就开始审视自己了。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能读到这种痛苦求索的痕迹,皮埃尔、列文、聂赫留朵夫,也包括安娜,他们之所以成为经典形象,不是因为他们有过人的英雄壮举,而是因为他们背后有一个伟大的思想者。
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说,托尔斯泰的呐喊是与众不同的,他拥有一切,却不能忍受自己的特权地位。人们追逐荣誉、钱财、显赫的地位和家庭幸福,并把这一切看成是生活目标。而托尔斯泰拥有这一切,却竭力放弃这一切,他希望平民化并且和劳动人民融为一体,是源于一个思想者、一个作家的创造精神。
事实上,在俄罗斯,作家对自我的忏悔促使他们的笔触突破表层,向社会纵深方向挺进,向人的灵魂深处迈进。就如鲁迅所言,这种“对人的心灵进行拷问,在洁白的心灵下面,拷问出心灵的污秽,而又在心灵的污秽中拷问出那心灵的真正的洁白”。
放下文学创作的托尔斯泰,却为教育普通民众写了《民众教育论》,为儿童写了《启蒙读本》《与儿童谈道德》,为农民写了《荒年补救方法》《拯救饥民》等。他以这种方式,凸显一个作家的价值与担当。
有多少人可以认识到自己身上挥之难去的恶念?认识到生命中已经腐烂的那些部分?认识到生之中即隐藏了死亡呢?因而,得以鼓足勇气,真正的否定自我,重新来超越自我?
这些年,我听到最多的话,就是一个作家一定要把故事编好,将作品写好,而思考嘛,想多了不仅无益,有时候甚至会阻碍一个作家的发展。是啊,“速食化”“数字化”叠加,我们要的是脑洞大开的想象力,要的是只争朝夕出东西,思考也好,思想也罢,那是思想家的事情,不是作家的事情。而个别文学创作越来越像大工业生产,谁在上游工作,谁盯下游工序,都已安排好。我们还需要忏悔什么?那不是没事找事嘛!这一切,托尔斯泰一定想象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