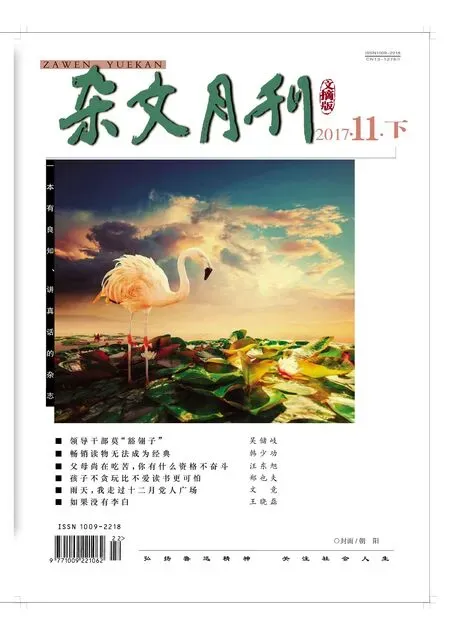畅销读物无法成为经典
□ 韩少功
文学经典是一个弹性概念,通常是指那些影响长存的作品,在文学史上具有典范、指标、基石的意义。其实,这些作品大多留有知识精英的物权印痕,切合历史上中(产)等阶级的总体心理需求——因为只有读书人才可能掌控评说、课堂、图书馆、文学史,以及向公众传导文学信号的职能。经过一段不太长的岁月,迷信与公文不知何处去,很多文学作品却依赖众多读书人的齐心合力,仍能顽强地保值增值,一次次重返书架。
读书人五花八门,并非统一的整体。有的白皮肤,有的黑皮肤;有的信基督,有的归佛门;有的敢担当,有的颇颓废;有的傍权贵,有的走江湖……于是产生不同的文学标尺,也是常情。但不管他们之间差别多大,既然都读书,既然都在书里泡,就如同一群棋友对棋艺还是会形成大致相近的规则。这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其“经典性”也许跨不出政治红区的边界;《阿凡提的故事》的“经典性”不一定能在基督教地区有效;但《罗密欧与朱丽叶》《西厢记》《红楼梦》之类就不一样了。这些读书人共有的美人梦、精英闷骚、愤世纠结,能引起更广泛和更持久的共鸣,成为兴奋的更大公约数。
这印证了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说法:凡经典都是建构之物,有一个经典化的过程,常常取决于什么人、为了什么、凭借什么来上下其手。
在这里,较小的公约数常常离不开政治、宗教、经济等方面的特定推力;而较大的公约数则有赖于知识界更为广泛的通则和共鸣。
不过,这并非事实的全部。地摊上那些花哨的畅销读物能不能成为经典?那么多涉性、涉金、涉官、涉暴的文字,明明挠到了很多人的痒痒肉,不胫而走,呼风唤雨,为什么就很难碰上什么“经典化”的好运气?甚至捞不到一个较小公约数?可见,建构并非无条件的,无法由知识话语权一类来随心所欲。在罗兰·巴特笔下,葡萄酒是法兰西人建构出来的一种文化图腾,不一定天经地义。这也许没错。但法兰西人再任性,再有能耐,也没法把阴沟水建构成什么至尊国宝。这里的区别在于:与阴沟水不同,葡萄酒具备了基础条件,具备了候补图腾的可能性,在营养、口感、气味、色泽等方面显示出无可替代的价值优势。这就是后现代主义者不应忘记的另一半真相:思想与艺术终究是硬道理。
天不变道亦不变,道不变文亦不变。只要人还没有变成机器人,只要这个最大的“天(自然)”还没变,那么某种普遍的人性之道,或说人类较为广泛和持久的价值共约,就会构成经典化的隐秘门槛,把泡沫逐渐淘汰。托尔斯泰作为一个“思想大户”(切入宗教、道德、政治的时代焦点),乔伊斯作为一个“艺术大户”(竟然发现、开发、释放出意识流这等奇物),就这样跨入了门槛。还有一些“资源大户”,比如《西游记》(佛教文化资源)、《聊斋志异》(道教文化资源)、《三国演义》(王侯文化资源)、《水浒传》(江湖文化资源)等,也是各得先机,各成气象,成为不易绕过去的大块头——至少在中国是如此。相比之下,大仲马、张恨水一类超级写手,再热闹也还是偏轻偏小,在大指标上不给力,最可能就被建构者们的目光跳过去。
不难看出,经典化是一个动态过程,却是一种有限界的分布函数。换句话说,“建构”是文化权重者们做的加法;而淘汰和遗忘则取决于天下人心,是更多人在更久岁月里操作的减法,一种力度更大的减法。
前者有偶然性;后者有必然性。
换句话说,前者是运之所成,靠机缘;后者则是命之所限,靠实力和品质。在这个意义上,大部分文学史其实皆可半信半疑,因为任何一个文学作品,都是在这种加法与减法的双向对冲之下,进入一种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无限漂泊,需等待下一本甚至N本文学史的再度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