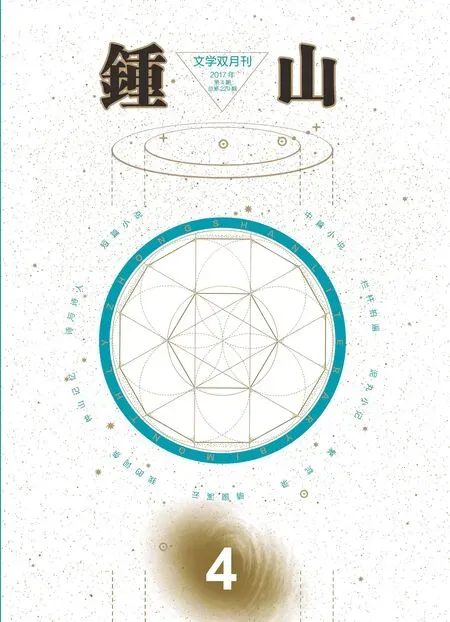胡适的驻美大使当得怎么样
王彬彬
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的全面侵华开始,中国的全面抗战也开始。8月间,蒋介石希望胡适偕同钱端升、张忠绂,以半官方身份赴欧美,以演说、发表文章等方式揭露日军在中国的暴行、 争取欧美国家政府和民众对中国的同情和道义上的支持。胡适一开始是不愿意的,在国难当头时离开,他觉得不光彩,但终被说服。9月9日,胡适等人在南京上船往武汉,船到武汉后换乘飞机到香港,又从香港飞往美国。胡适于1937年9月26日抵达旧金山。1938年7月26日,从美国到了欧洲。9月17日,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特命全权大使”。10月3日,胡适从欧洲回到美国纽约。10月5日,胡适赴华盛顿就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
1941年12月8日(美国东部时间为7日),驻美大使胡适正在使馆内吃午饭时,接到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电话。罗斯福说:“方才接到报告,日本海空军已在猛烈袭击珍珠港! ”对于身心疲惫的胡适,对于处于深重苦难中的中国,这真是天大的喜讯。这意味着美日之间战争的开始,意味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意味着中国的对日抗战在切实的意义上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既然美国参战了,日本的失败便是无可置疑的,而且时间不会太久。此前,胡适一直以“苦撑待变”自勉,也以此勉励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人。苦撑了几年,这“变”终于来了。胡适当驻美大使,本来就是客串,从这一刻起,胡适便觉得自己作为中国驻美大使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应该尽快辞去这个外交官的职务,回到本来的生活中。
但胡适真正辞去此职,则要到1942年秋。1942年8月15日,胡适接到重庆发来的准其辞职的电报,当晚11 时,胡适复电曰:“蒙中枢垂念衰病,解除职务,十分感激。”9月6日,中央通讯社正式发布了胡适辞驻美大使职的消息:“我国驻美大使胡适,近来因患心脏衰弱,不胜繁剧,迭向中枢表示去志。兹闻中央已准其所请,拟另畀工作。其驻美大使继任人选,已内定由魏道明氏担任。”“中央社”的消息,强调了是先有胡适的一再请辞,后有中枢的免职决定。9月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国务会议正式决议,准驻美大使胡适辞职,以魏道明继任。9月18日,胡适离开华盛顿,卜居纽约。
日本全面侵华后,与美、英等国的矛盾也渐斩尖锐,而美、英等国对华援助的态度也渐渐积极。国民政府竭力争取美、 英等国物质上和道义上的援助,而废除不平等条约,则是争取美、英等国援助的重要内容。如果在中国人民正在艰难地抗击日本侵略者时,美、英等国宣布废除此前与中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那对中国的抗战当然是巨大的支持。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就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努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既然中国的抗战成了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中国战场的地位也就大大上升。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苏、荷等26 个国家在华盛顿签订《对法西斯轴心国共同行动宣言》(即《二十六国公约》,后又称《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宣言》宣布,各签字国政府赞同罗斯福、 丘吉尔于1941年8月14日签订的《大西洋宪章》。《宣言》更规定:各签字国必须使用全部军事和经济力量,共同对抗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侵略; 各国保证不单独与敌国缔结军事协定或和约。在这次共同行动中,中国是领衔者。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使得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时机真正成熟。
1943年1月11日,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与美国国务卿赫尔代表两国政府在华盛顿签署了《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简称“中美新约”。同一天,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与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在重庆签署了《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简称“中英新约”。“中美新约”和“中英新约”的签订,宣告了中美、中英之间此前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废除。
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国民政府解除胡适驻美大使职务,有什么逻辑关系呢?
2013年7月,台湾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了《郝柏村解读蒋公八年抗战日记(1937—1945)》,厚厚的两大册,共一千四百多页。郝柏村抗战时期是国军军官,参与了抗战全过程,赴台后曾任“总统府侍卫长”,长期在蒋介石身边服务,由他来解读蒋介石抗战时期的日记,自然是很合适的。由于某种技术性困难,郝柏村解读蒋介石日记时,未能附上日记原文,不过,从郝氏的解读中,完全能够知晓日记原意。蒋介石每个星期日,会在日记中写下“上星期反省录”。1942年10月18日,是星期日,蒋介石照例写了对上星期言行的反省。对这一天的“星期反省”,郝柏村做了这样的解读:
胡适在著名文人中,算是支持蒋公的,以其在中美的声望,任为驻美大使四年,但无工作绩效可言,仅个人得名誉博士十余项。他不是职业外交官,不敢说话,恐获罪于美国,但外界犹以为美倭破裂交战,是胡的功劳。其实当时对美外交,系由宋子文奔走,故决定撤换胡适,否则现在取消了不平等条约,外界必认其功劳更大,政府要撤换他更难了。蒋公感叹文人名流,其为国不过如此,其实用胡,乃代表中美立国共同理想象征,非依其外交实务。
晚年的郝柏村显然对胡适并无好感,在解读中也可能多少夹带了自己的看法。但郝氏基本是在转述蒋介石的看法和感叹,则是毋庸置疑的。抗战爆发后,蒋介石选择胡适任驻美大使,并非因为胡适是外交长才,乃是因为胡适在美国的巨大声望,这一点,是一开始便为天下人明了的。但天下人不知道的,是蒋介石在这一天的日记中透露的这两种信息:(一)蒋介石对胡适在驻美大使任内的表现,是很不满的,对其业绩评价甚低,甚至认为”无工作绩效可言”;(二)蒋介石之所以在1942年秋下定解除胡适大使职务的决心,是因为不愿意由胡适代表中国政府在废除中美之间不平等条约的“中美新约”上签字。代表中国政府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新约”上签字,这当然是极其荣耀的事情。如果胡适依然是驻美大使,这份荣耀便当然地属于他。而蒋介石则不愿意让胡适享有这份荣耀,于是在“中美新约”签字前,解除胡适的驻美大使职务。
胡适生前不知道蒋介石内心对他的真实看法和态度竟然是这样,如果知道,也许会伤感不已,也可能会令他更深刻地思考民国时期文人与政府、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
但胡适的驻美大使到底当得如何,也不能完全由蒋介石、郝柏村一流人说了算。
二 我所见过的所有胡适传记、年谱,不管是海外、境外还是大陆出版,都对胡适使美期间的外交劳绩,有高度评价,当然,不包括大陆特殊时期的出版物。
胡适这样的学者,办理具体事务的能力当然不会很强。但蒋介石选中胡适为抗战时期的驻美大使,看重的本来就不是他的事务性能力。胡适对美国很了解,胡适在美国的朝野都有良好声誉,作为中国的“形象大使”,胡适是极其合适的。在那个特殊时期,有胡适代表中国活跃在美国的朝野,能够赢得美国从官方到民间对中国的好感,而这对美国最终大力援助中国、与中国并肩抗击日本,意义决非很小。用今天的时髦话说,胡适体现的是一种“软实力”。这样说,并非意味着胡适使美期间具体事务上无可称道,而是强调:蒋介石所期望于胡适的,胡适尽心尽力地做到了。如果蒋介石真的认为胡适使美期间“无工作绩效可言”,那是蒋介石忘了任命胡适当驻美大使的“初心”了。
在众多谈论胡适使美功绩的文字中,傅安明的《略谈胡适使美的成就》 一文具有特别的权威性,因为作者在1936 至1949年间,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馆秘书。作为胡适的部属,他目睹和参与了胡适当驻美大使的全过程。
傅安明的文章首先介绍了《纽约时报》闻知胡适将卸大使任而于1942年9月3日发表的评论。《纽约时报》的评论对中国政府解除胡适大使职务表示了惊讶,文章说:“重庆政府遍寻中国全境可能再也找不到比胡适更为合适的人物。他1938年来美国上任,美国朋友对他期望至高,而他的实际表现,又远超过大家对他的期望。他在美国读书、旅行、演讲,对美国文化之熟悉,犹如对其本国文化之了解。他所到之处,都能为自由中国赢得支持。如果对于他的去职深感遗憾,尚不足以表达我们的心意。”于此可见,胡适使美四年,是怎样赢得美国舆论界的尊敬与重视。
傅安明文章从“演说造势”、“外交胜利”、“善交美国政要”等方面介绍了胡适的使美成就。
胡适擅长演讲。使美期间,胡适频频在美国各地演讲。所有的演讲都围绕一个中心,即揭露日本在中国的暴行,分析战争局势,强调日本必败而中国必胜,当然还要呼吁美国朝野对抗战中的中国给予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应该说,胡适演讲的成效是巨大的,大到引起了日本的恐慌。傅安明文章说,《纽约时报》1940年10月31日引述了日本最具影响力的英文报纸《日本时报》的一篇专电,专电声言,在美国的大选年,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在美国巡回演讲,激发美国民众的仇日情绪,引导美国进入战争危境。专电特别强调,美国总统已经保证置美国于战争之外,而胡适竟公然不断呼吁美国参与战争,这是极其危险的,专电说,如果是英国驻美大使这样做,一定会引起美国内政利益集团的抗议,而胡适的言行,竟然没有受到任何非议,只能说明是受到了美国政府的幕后支持。专电最后要求美国国会的相关机构对于中国驻美大使胡适意欲祸害美国的行为予以关注。日本的报纸发表这样的专电,实际是在对美国政府放任胡适的演讲表示抗议。而这也从反面说明胡适的演讲是有明显作用的。
郝柏村解读蒋介石日记时,指责胡适不务正业,“仅个人得名誉博士十余项”。其实,胡适使美期间,所得各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有几十个。然而,一个外国使节,接受驻在国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决不能说是与大使职责无关。胡适使美期间,美国各大学争相授予其名誉博士学位,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美国各大学对胡适的认可。而对中国驻美大使的认可,就是对中国的认可。那时的中国,多么需要国际社会的认可,多么需要美国朝野的认可。
美国各大学之所以争相送上博士帽,又与胡适以演讲征服了各大学有关。
傅安明以胡适成功阻止美国对日妥协并最终促使日美开战为例,说明胡适的“外交胜利”。此事胡颂平编著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叙之甚详。日本全面侵华后,美国对日本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封锁,其中包括重要战略物资的禁运。1939年7月26日,美国政府更是宣布废止《美日商约》。1941年7月25日,罗斯福命令冻结日本在美国的全部资金。美国的经济制裁对日本形成巨大的压力。1941年11月21日,日本方面向美国国务卿赫尔提出了“临时妥协方案”,日本将越南南部驻军减少至二万五千人,美国则有限度地恢复美日通商,特别是要让日本获得石油供应,同时要求美国停止对中国的一切道义和物质上的援助。为缓和美日紧张关系,美国政府一开始有意接受日本的条件。果如此,则对中国极其不利。胡适第一时间将此情况报告了蒋介石,并立即向赫尔表示了严重抗议,蒋介石闻讯十分惶恐,复电胡适说:
此次美日谈话,如果在中国侵略之日军撤退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以前,而美国对日经济封锁政策无论任何一点之放松或改变,则中国抗战必立见崩溃。以后即使美国对华有任何之援助皆属虚妄,中国亦不能再望及友邦之援助,从此国际信义与人类道义皆不可复问矣。请以此意代告赫尔国务卿,切不可对经济封锁有丝毫之放松。中(正)亦万不信美国政府至今对日尚有如此之想像也。
从蒋介石的复电,可知此事对中国的关系何其重大。这也等于给胡适下了死命令,一定要阻止美国对日妥协,哪怕是一丁点的和临时的妥协,都对中国是致命的打击。胡适于是见赫尔,见罗斯福,反复强调美国对日妥协之不可。当时日本方面代表官方在美国从事外交活动的是野村和来栖两个使者。赫尔曾同时召见胡适、宋子文、野村和来栖,胡适与日本使者自然进行面对面的辩论。中日两国使者几番较量的结果,是美国方面认可中国的意见,放弃对日妥协,日本败下阵来。12月1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对英美作战,数日后,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据《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12月8日(美国东部时间为7日),罗斯福召见胡适。罗斯福与胡适有很亲密的友谊,所以不拘形迹。罗斯福对胡适总是直呼其名,不用敬语。一见面,罗斯福便说:“胡适! 那两个家伙(引按:英文原文是‘The two guys’,指野村和来栖)方才离开这里,我把不能妥协的话,坚定的告诉他们了,你可以即刻电告蒋委员长,可是从此太平洋上随时有发生战争的可能,可能发生在菲律宾及关岛等处。”罗斯福预料到拒绝对日妥协,必定让日本恼羞成怒、狗急跳墙,只不过没想到日本先在珍珠港发疯。
胡适离开白宫不久,就接到了罗斯福的电话,得知了日本偷袭珍珠港之事。
三 使得美日关系破裂、 把美国拉入抗击日本的战争中,无疑是抗日期间中国最大的外交成就,不平等条约的废止还在其次。而这项成就,是胡适在驻美大使任上取得的。郝柏村解读蒋介石日记时,把胡适在此事上的功劳一笔抹杀,认为完全归功于宋子文,实在是很荒谬的。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引述了王世杰、罗家伦等人对此事的看法。也曾当过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王世杰认为,促成美国拒绝日本要求、从而导致日本偷袭珍珠港,是胡适使美期间的“历史性成就”之一。王世杰说:“在日本与美国交涉期间,胡适博士曾将我国政府的主张和希望剀切诚恳的向美国政府披陈。除此以外,他并未作任何特殊的活动,或运用任何外交手腕去影响美国政府;可是当时的罗斯福总统和赫尔国务卿对于这位‘书生大使’和他的慷慨陈辞,是很重视的,他的披陈是有重大的影响力的。”王世杰进而感慨:“在现代的外交工作上,使节的人格与信望究竟重于使节的外交技能。”罗家伦也说,促成美日破裂、日军偷袭珍珠港,与抗战成败有着重大关系,而“这项决策虽是由于当时蒋委员长的明智和坚定,但是执行的大使在其驻在国的声誉、人望,及其和当局的友谊与互信不能说不是其中重要的因素。”王世杰、罗家伦都强调了胡适的声誉、人望在对美外交中的不可取代的作用。胡适本不是职业外交家。那一套职业性的外交技能当然非其所长。但是,胡适有一般职业外交家所没有的声誉、人望,有一般职业外交家所没有的坦荡、诚实。而在罗斯福这样伟大的政治家面前,胡适的声誉、人望,胡适的坦荡、诚实,远胜于那种职业性的外交技巧。
傅安明在以此为例说明胡适的“外交胜利”时,引述了美国学者比尔德(Charles A. Beard)的观点。比尔德是极端的孤立主义者,对于美国因珍珠港事件而卷入战争十分不满,所著《President Roosevelt and the Coming of the WAR,1941》对此有尖锐批评,书中强调:“美日最后交涉的失败,实由于胡适的影响。”
傅安明还从胡适与罗斯福私谊的角度阐述了胡适使美的成就。使美期间,胡适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建立了十分亲密的私人关系,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在那时,能与罗斯福建立那样亲密关系的中国人,除胡适外,还能找到何人?而在那个时候,作为中国的驻美大使,与罗斯福这样的美国总统建立亲密的关系,对于中美关系、对于中国的抗战,又何等重要! 这期间,美国政府克服重重障碍,借款给中国,拒绝与日妥协,以各种方式支持中国的抗战,谁能说与罗斯福喜爱、欣赏、信赖胡适这个驻美大使没有关系?
但蒋介石的确对胡适不太满意,最有力的证据便是任命胡适为驻美大使后,又命宋子文以其私人代表的身份赴美,与美国政府打交道。胡适是在1938年9月被任命为驻美大使的,宋子文则是1940年6月赴美。宋子文赴美后,中国的驻美大使实际上就有两位。胡适被称作“书生大使”,而宋子文由于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又是作为蒋的私人代表出现,便被称作“太上大使”。胡适本来就看不起宋子文这种绣花枕头。宋子文赴美后,对胡适颇多责难,二人关系就自然不会融洽了。胡适这一时期的日记、书信,多次透露了与宋子文的矛盾。1940年7月12日,胡适在日记里记述了宋子文对其到处讲演的指责。宋子文对胡适说:“你莫怪我直言。国内很多人说你演说太多,太不管事了。你还是多管正事吧。”对此,傅安明在《略谈胡适使美的成就》中予以了驳斥:“其实,胡的部属多人帮他管理‘正事’,只有两事部属帮不上忙,必须他亲自出马,一项是广交朋友,以及与总统、部长、议员及名流显要的接触。另一项就是发表演说。因为他有中国大使职位与国际名流声望的双重身份,由于这双重身份,他与美国显要接触及在美公开发言,都能发挥高度效力! ”
指责胡适讲演太多,固然荒谬,但宋子文表达的可能真不只是一己看法,“国内很多人说你演说太多”,应该并非虚言。
宋子文以蒋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赴美后,便急于立功,急于显示自己比胡适能干。对于宋子文这种心态,王松在《宋子文大传》中有所分析。1940年11月29日,日本正式承认汪伪政权的前夕,美国决定将拖延了许久的一亿元对华借款立即兑现,以示对重庆国民政府的支持。对于蒋介石和重庆国民政府,这当然是重大喜讯,也是驻美使节的大功一件。但宋子文却想独享此功。胡适是中华民国政府官方派遣的驻美大使,当然应该由胡适代表中国在借款的有关文件上签字。但其时胡适人在纽约。在华盛顿的宋子文得知借款即将发放,立即命人打电话给胡适,让胡适在纽约等他,不要回华盛顿,他有要事须赶往纽约与胡适商谈。没能联系上胡适,宋子文又给胡适下榻的旅馆打电话,又请李国钦等人转告胡适,务必留在纽约等他。“宋子文的做法显然是不想让胡适分享借款成功的功劳。”后来,当胡适看穿宋子文的“巧计”后,禁不住嘲讽道:“真是‘公忠体国’的大政治家的行为。”
宋子文如此小肚鸡肠,胡适与他共事之艰难,就可想而知。胡适的生日是12月17日。1940年12月17日,是胡适五十岁生日,这天的日记里,胡适写道:
做事的困难,一面是大减少了,因为局势变得于我们有利了;一面也可以说是增加了,因为来了一群“太上大使”。但是我既为一个主张发下愿心而来,只好忍受这种闲气。我的主张仍旧不变,简单说来,仍是“为国家做点面子” 一句话。叫人少讨厌我们,少轻视我们——叫人家多了解我们。
这番话,有些沉痛,有些悲壮,也有些自负。所谓“为国家做点面子”,就是当好中国的“形象大使”之意。作为中国的大使,美国朝野和国际社会,对胡适的看法,某种意义上就是对中国的看法;对胡适的好感,某种意义上就是对中国的好感。然而,因为来了宋子文这“太上大使”,“书生大使”胡适要扮演好“形象大使”的角色,难度就更大了。
四 不过,宋子文拼命与胡适争功、抢功,未必完全是个人私欲和野心驱使,也可能有蒋介石以某种方式的授意。蒋介石1940年6月派遣宋子文赴美,与胡适共同从事对美外交,这时候宋子文的身份是蒋介石私人代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干脆以宋子文取代郭泰祺任中华民国外交部长,但仍留在美国工作。这里的原因应该是很复杂的。对胡适的工作力度不满意,无疑是原因之一,但这应该不是主要原因,更不是全部原因。抗战期间,美国的援助,对于中国之重要,是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的。负责对美外交和争取美援的工作,是特别重要的工作,这方面的成就、功绩,也是最受人重视、尊崇的。这期间如果在对美外交、争取美援方面取得重大成就、建立卓越功绩,那就是辉煌的政治资本,那就在日后国内的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正因为如此,驻美大使,是一个极受人瞩目的职位。可以说,胡适从就任此职的第一天起,就受到国内许多人的关注、挑剔,受到许多人的艳羡、忌妒。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王世杰,1940年8月8日给胡适写了一封回信,信中先说:“七月二十二日来信,已于前日收到,鲠生信亦收到。关于外电所传召兄返国事,日前弟曾致兄一电,想已递到,兄函已分送布雷、詠霓看过,并已送请介公阅过。介公阅后,嘱弟否认外电所传。弟当告以此事已过去多日,不必再发否认消息,不过外交部对于此类消息,此后以即刻纠正为是,介公深以为然。布雷兄已将此意告亮畴,彼谓今后当照办。此事只好就此结束。”所谓“召兄返国”,就是中国政府免去胡适驻美大使职务,召其回国。这是外电的报道。胡适就此事致信国内王世杰等人,究问为何有此传闻。王世杰将此事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命令宣传部长王世杰辟谣。这虽然是谣传,但却未必事出无因。因为这时候,蒋介石的确在考虑撤换胡适。郝柏村在解读蒋介石1940年11月13日日记时,写道:
胡适之使美,因其非职业外交官,且以学者大师性格,蒋公并不满意其工作,诸如美援的争取贷款要求,或许学者性格,不习于向他人低声下气,故实际对美工作,均由宋子文以私人代表身份办理。而蒋公对大师级的大使,亦不愿稍显责难之意,故调换驻美大使,为考虑已久之事。
这番话中其他的意思下面再说。这里只指出,蒋介石早已在考虑撤换胡适了。外电之所以有召胡适回国的报道,应该是蒋介石在某种场合透露了撤换胡适的想法。甚至是蒋介石有意将此消息透露出去,让外电先报道此事,试探一下国际国内和胡适本人的反应。毕竟,撤换胡适这样的驻美大使,并非随意之举,蒋介石必须反复斟酌、权衡。
王世杰1940年8月8日给胡适的回信,在解释了对外电谣传的处理后,接着写道:
兄一生是一个友多而敌亦不少的人。兄的敌人,有的是与兄见解不合的,这可以说是公敌。有的只是自己不行,受过兄的批评指斥,怀恨不已。这种小人也颇不少。兄的友人可以说都是本于公心公谊而乐为兄助的;也许有些是“知己”,却没有一个人是“感恩”。这是兄的长处,任何人所不及的。兄自抵华盛顿使署以后,所谓进退问题,便几无日不在传说着。有的传说,出于“公敌”;有的传说,也是完全无根。同时与这些公敌或小人对抗的,也不少。譬如最近返国的陈光甫,就是一个。我不相信兄是头等外交人才;我也不相信,美国外交政策是容易被他国外交官转移的。但是我深信,美国外交政策凡可以设法转移的,让兄去做,较任何人为有效。这不是我向兄说恭维话,这是极老实话……
从王世杰的信中可知,自胡适就任驻美大使始,国内就对此事议论不断。有人是出于公心而怀疑胡适的外交能力,有人则出于私怨而妒忌胡适的被如此重用。王世杰则坚定地认为,胡适是最合适的使美人选。美国的外交政策如果能够因为中国使节的工作而变得有利于中国,那么,最适合扮演这个角色的中国人,就是胡适。
蒋介石未必不明白这一点,不然就不会派遣胡适使美。胡适之后,再派宋子文赴美,也不必然意味着蒋介石对胡适的不满。对美外交,是极其重大的事情。中日两国,在华盛顿进行着激烈的外交战。日本方面就有野村和来栖两名大使级人员在美工作,中国也派两名大使级人员,完全不希奇。但蒋介石又的确对胡适的工作绩效不很满意。前引郝柏村对蒋介石1940年11月13日日记的解读,告诉我们蒋介石主要是嫌胡适争取美国借款的力度不够,其原因,蒋介石认为是胡适以学者大师之尊,不肯对美国政要低声下气。换个别人,蒋石介可以训斥,可以把自己的不满尽情发泄。但对方是胡适,蒋介石即便内心有再大的怨气,也只能忍着。在政府体制内,胡适是蒋介石的部属。但胡适更是“学者大师”和国际名流,蒋介石不能“稍显责难之意”,只能总是客客气气地下命令。这一定令蒋介石很郁闷、很窝火。
至于蒋介石认为胡适工作不力,恐怕更多的还是一种主观的感受,而非客观公正的评价。中国急需美国援助,蒋介石对美国借款的期待,真如大旱之望云霓。旱得冒烟了,旱得着火了,情急之下,再派宋子文赴美,希望有更厚黑的云霓飘过来。
但蒋介石早就考虑撤换胡适,却另有更重要的原因。这就是,胡适人在美国,担负的是对美外交使命,却要隔着太平洋干涉国内的政事,这才是更令蒋介石恼怒的事情。
五 郝柏村在解读蒋介石1939年9月3日日记(“上星期反省录”)时,写道:
令胡适赴美办外交,胡竟与蒋辩难内政诸问题,一个自由主义的学者,与以国家民族利益而牺牲个人自由格格不入,可想而知。故蒋公叹中国首领之苦,异于先进国家。
胡适以驻美大使身份而与蒋介石辩难内政诸问题,这才是令蒋最终决心撤换胡适的最根本原因。胡适本来身份是“自由主义的学者”。从郝柏村的语气里,可以看出他对胡适这类“自由主义的学者”是何等厌恶、鄙夷。郝柏村是如此,蒋介石当然不会不如此。此前,作为一个自由主义学者,胡适屡屡批评“党国”的大政方针,也与蒋介石的“党国”发生过尖锐冲突。蒋介石内心深处,对胡适这类人是厌恶、鄙夷的。作为“党国”之体制外的知识分子,胡适批评党和政府,虽然逆耳,但蒋介石还可忍受。当胡适被任命为中华民国驻美大使时,就成了党国体制内的一名官员,就成了蒋介石的部属,再要思出其位、干预国内政事,那就是蒋介石无法忍受的了。在蒋介石看来,胡适的身份是驻美大使,本职是对美外交,与自己谈“正事”时,只应谈中美关系,此外都是胡适不应闻问的。而胡适呢,当了几十年自由主义学者,批评了几十年国内政治,决不会因为一纸驻美大使的任命,便脱胎换骨的。胡适仍然在原有的言行轨道上惯性滑行,仍然远隔重洋与蒋介石辩难内政诸问题,怎不令蒋介石觉得胡适太不“懂事”? 驻美大使的官阶虽然不算很高,但在当时是极其重要的使命。能否争取到必要的美援,关乎对日抗战能否坚持、重庆政府能否存续的大问题。如果争取到了可观的美援,那就是头等功臣。而蒋介石又是很不情愿让胡适来当这样一个头等功臣的。蒋介石本来内心里对胡适是嫌恶、鄙夷的。只是因为在中国亟需美国援助时,胡适最适合作为中国的“形象大使”与美国交涉。孰料胡适虽然进入了体制、虽然到了万里之外的美国,虽然本分是外交,却仍然恶习不改、故伎重演! 那些年,蒋介石最关心的,是来自美国的消息。可以想象一下:当蒋介石在清晨、在深夜,接到胡适从美国发来的电报,急切地想要知道美国对华态度的新变化,而胡适却是在与其探讨国内问题,蒋介石的失望和哀痛有何等深重,蒋介石的怒火又是何等炽烈。这样的时候,蒋介石一定会想:必须撤换胡适,否则,如果对美外交取得重大胜利,那胡适便是国家的大功臣,到了那个时候,无论他留在体制内还是退回体制外,都是无法应付的。
所以,撤换胡适的想法,应该在胡适上任不久就在蒋介石心中产生了。只不过,撤换胡适,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并不能贸然行事。既然不能撤换,那就再派一人赴美,既分胡适之劳,更分胡适之功。于是有宋子文以私人代表赴美之事发生。前面说过,日本也有两名大使级人物在美国活动,中国再派一人,本不奇怪。但加派一人,本意应该是令其协助胡适、令其与胡适携手并肩、共同作战。但派宋子文赴美,则说明蒋介石的“本意”并非如此。因为,胡适本不喜欢宋子文,二人气味不投,这一点,蒋介石是深知的。明知胡、宋二人不可能有良好的合作,却偏是派宋子文赴美与胡适合作,这岂不耐人寻味?
胡适使美期间,一般是通过陈布雷与蒋介石联系,给蒋介石的报告和建议都通过陈布雷转达。1939年11月27日,胡适致电陈布雷,请陈向蒋转达对行政院人事变动的看法。这期间,胡适在美听说“宋子文先生将任要职”,或许取代孔祥熙任财政部长,胡适认为此举不妥,于是通过陈布雷向蒋介石表达反对意见。胡适强调,孔祥熙作为财政部长,在协助、配合使美人员向美借款方面,措施有力,而宋子文如果代孔长财部,则在向美借款上“恐不能如向来之顺利”。胡适指出,宋子文“个性太强”,难以与人合作,在美国政要那里,宋子文也“印象颇不佳”。胡适对陈布雷说,这种种情形,“因国内恐无人为介公详说,故弟不敢避嫌疑,乞吾兄密陈,供介公考虑。”陈布雷当然会立即向蒋介石转达,而蒋介石也一定会十分反感。在蒋介石看来,这就是在干涉国内政事,这就是作为外交官的胡适在思出其位、 不守规矩。但蒋介石也同时知道,胡适是颇不欣赏宋子文的,是觉得宋子文难以与人共事的。而明知胡适与宋子文水火不相容,蒋介石却在数月后偏派宋子文赴美与胡适共同从事对美外交,只能理解为蒋的本意就不是让宋子文去协助、配合胡适,而是让宋子文去覆盖、取代胡适。
胡适是被正式任命的驻美大使,而宋子文只是蒋介石的私人代表。按理,宋子文应该充分尊重胡适,在处理对美外交事务时,胡适理所当然起主导作用,但到了美国后的宋子文,根本不把胡适放在眼里。1941年4月15日,罗斯福约见胡适、宋子文,在座有美国财政部部长、次长以及其他人员多人,而宋子文高谈阔论、滔滔不绝,全无胡适说话的份。当天日记中,胡适记道:“全是子文一人谈话。”胡适虽没有过多地表示不满,但特意记述全是宋子文一人谈话,却分明流露了内心的压抑,流露了难言的委屈、哀愁与凄凉。宋子文之所以敢于如此不在乎胡适,恐怕不能仅用其是“国舅”来解释。宋子文赴美前,蒋介石肯定会与其谈话,面授机宜。如果蒋介石谆谆告诫宋子文,赴美后一定要与胡适搞好关系,一定要充分尊重作为”国家代表”出使美国的胡适,那宋子文应该不至于在胡适面前如此放肆。或许我们不能认为,蒋介石明确授意宋子文赴美后处处与胡适为难,但我们却可以相信,蒋介石并没有嘱咐宋子文要与胡适友好相处。而只要蒋介石没有嘱咐要与胡适友好相处,宋子文便可以不与胡适友好相处。宋子文并非愚钝之徒。蒋介石派自己赴美,并非是要自己协助、配合胡适,而是要自己实际上覆盖、取代胡适,这一点,他是心领神会的。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在蒋介石看来,胡适就变得可有可无,或者说,变成完全多余了。1941年12月23日,重庆国民政府任命宋子文为外交部长,仍在美国工作。此举令胡适与宋子文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此前,宋子文的身份是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而胡适是被正式任命的驻美大使。尽管宋子文实际上并不把胡适放在眼里,但在名分上,胡适毕竟居于宋子文之上。而现在,宋子文成了外交部长。外交部长是驻外使节的顶头上司。宋子文一夜之间成了胡适的顶头上司,却又仍然留在胡适身边领导胡适,这就让胡适非常尴尬了。
前面说过,1942年1月1日,《二十六国公约》在华盛顿签订。而蒋介石就是要赶在这个历史性的文件诞生前任命宋子文为外交部长。郝柏村在解读蒋介石1942年1月1日日记时,写道:“宋子文此际接替郭泰祺为外交部长,但仍在美工作,驻美大使则为胡适,故在重庆乃由蒋公暂兼代外交部长。昨日日记,中美英俄四国(后及二十六国)宣言,如由胡适签字,则宋子文亦应以外交部长身份,参与仪式”。原来,蒋介石匆匆任命宋子文为外交部长,就是为了让宋子文参与签订《二十六国公约》这历史性的事件。而之所以要让宋子文与胡适共同参与签字仪式,固然有刻意让宋子文获得光环、荣耀的成份,但更主要的,恐怕还在于不愿意让胡适独自享有这份光环和荣耀。换句话说,是不愿意让胡适这“自由主义的代表”获取更多的政治资本、具有更大的政治力量。
六 现在我们明白了,蒋介石是分两步走,才把胡适从驻美大使的职位上挪开。第一步,是在《二十六国公约》签订前,任命宋子文为外交部长,参与“公约”的签字仪式,同时也架空胡适作为驻美大使的权位;第二步,是在分别与美英签订“中美新约”“中英新约”前,撤换胡适,根本不让胡适有参与取消不平等条约这极为辉煌的历史时刻的机会。
宋子文被任命为外交部长而仍旧留在美国,胡适的驻美大使就彻底地有名无实了。宋子文实际上以外交部长的身份扮演起驻美大使的角色,对胡适这个名分上的驻美大使,连起码的礼仪也不讲了。1942年5月17日,胡适给翁文灏和王世杰写了一封信,其中说:“某公在此,似无诤臣气度,只能奉承旨意,不敢驳回一字。我则半年来绝不参与机要,从不看出一个电报,从不听见一句大计,故无可进言,所以我不能不希望两兄了。”所谓“某公”就是宋子文。这里的意思说得明白,自从宋子文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后,胡适就完全出局了。半年来没有看一个电报,没有听一句大计,这不是他自己不要看、 不要听,而是宋子文根本不拿给他看、不说给他听。所有的电报都不给名分上仍是驻美大使的胡适看,哪怕是蒋介直接发给胡适的电报,宋子文也不容胡适闻问;所有的事情都不与名分上仍是驻美大使的胡适商量,宋子文独自就处理了。宋子文之所以敢于如此,是因为他知道,这正是蒋介石希望他采取的态度。而胡适是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是对“机要”“大计”有自己的看法的,但因为别人根本不理睬他,也就没有“进言”的可能,所以只好寄希望于翁文灏、王世杰,希望他们能对蒋介石有所诤谏。在信中,胡适又说:“去年十二月八日我从国会回家,即决定辞职了。但不久即有复初之事,我若求去,人必以为我‘不合作’,对内对外均费解释。故我忍耐至今,我想寻一个相当机会,决心求去。我在此毫无用处,若不走,真成‘恋栈’了。两兄知我最深,故敢相告,不必为他人道也。”郭泰祺字复初。胡适说,珍珠港事件一爆发,他就知道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就有了辞职的打算。而这时,重庆国民政府任命宋子文取代郭泰祺任外交部长,胡适担心自己如果辞职,会被国内国外认为是不愿与宋子文合作,所以就暂时隐忍了。
到了1942年的9月8日,胡适的驻美大使职务终于被免。
但蒋介石真的认为宋子文在美国干得很好吗?也未必。郝柏村解读蒋介石1942年9月13日的“上星期反省录”时,写道:
美国外交对我冷淡轻视,如为人的问题,则调回宋子文,当不难恢复原状。
这句话实在意味深长。这里被蒋介石反省的“上星期”,就是重庆国民政府宣布免去胡适驻美大使后的一星期。这意味着,美国方面获悉中国政府免去胡适驻美大使的职务后,是很不高兴的。所谓“对我冷淡”,当然是美国政要对在美国的宋子文很冷淡。而美国的这种反应,自然也是宋子文向蒋介石报告的。美国的态度当然十分重要。蒋介石在得知消息后,甚至有了“调回宋子文”以求“恢复原状”的打算。这里的“原状”是什么“状”呢?就是宋子文以蒋介石私人代表赴美前的状态。
如此说来,以罗斯福为首的美国政要,的确不怎么喜欢宋子文而更喜欢胡适。而蒋介石始而以宋子文架空胡适,继而干脆撤换胡适、让胡适彻底离开对美外交的岗位,真是一个错误。
1937年9月,胡适受命以半官方身份赴欧美时,随行者有钱端升和张忠绂。张忠绂后来在回忆录《迷惘集》中说:“二十世纪的外交家应当是一位诚恳可亲,广交游,平易近人,能获驻在国一般人民爱戴的真君子。适之正是这种人物。他曾一度赢得‘一个伟大的民主人’(A Great Democrat)的雅号。抗战期间,由他先之以半官式,继之以正式大使的身分,驻在美国,这对于国民政府甚为有利。独惜在美国战争爆发后,他被撤换,外交部长亦由宋子文继任。战后美国舆论对国民政府由同情转为敌视,其原因虽多,但与重要官吏人选,似亦不无关系。”张忠绂的意思是说,如果胡适的驻美大使一直当下来,战后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态度就不至于“由同情转为敌视”,而如果美国没有抛弃国民政府,或许历史的发展演变就会有所不同。
蒋介石或许是最早意识到这一点者之一。1947年12月,当美国政府对蒋介石政权日益不满时,当美国越来越明显地流露出欲抛弃蒋介石政权的意向时,蒋介石又想请出胡适去当驻美大使。胡适12月14日、16日、17日和29日的日记都记述了此事。这一回,胡适以几种理由拒绝了。我想,还有一种理由胡适没有说,那就是上一回的大使,当得人太累而心太凉了。
蒋介石再度请胡适使美,充分证明胡适上一回把驻美大使当得很好,否则,蒋介石怎么会在危急关头又请这个他内心深处颇为不喜的“自由主义的学者”再作冯妇呢?
2017年5月21日深夜急就
注释:
(1)(4)(9)(10)(11)(12)(19)(22)(24)见《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五册,第1748 页,第1783—1784 页,第1744—1745 页,第1748页,第1747 页,第1748 页,第1688—1689 页,第1777 页,第1784 页。
(2)(3)见《胡适年谱》,曹伯言、季维龙编著,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598 页,第598 页。
(5)(7)参见李新总编之《中华民国史》第十卷(1941—1945),石源华、金光耀、石建国著,中华书局2011年7月版,第414 页,第423—428页。
(6)见李新总编之《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九卷(1940—1942),中华书局2011年7月版,第6697 页。
(8)(21)(23)见《郝柏村解读蒋公八年抗战日记》(下),第992 页,第873 页,第977 页。
(13)(14)所引傅安明语见其《略谈胡适使美的成就》,载《胡适研究丛刊》第二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15)(20)见《宋子文大传》,王松著,团结出版社2011年9月版,第161 页,第162 页。
(16)(18)见《郝柏村解读蒋公八年抗战日记》(上)。第639 页,第429 页。
(17)王世杰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第471—472页。
(25)见傅安明《略谈胡适使美的成就》,载《胡适研究丛刊》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