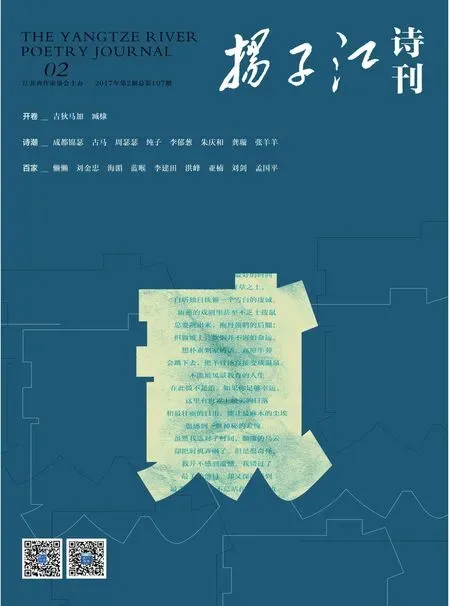对称与对刺,兼及“必然性”诗学
——读祁十木和耿玉妍的诗
景立鹏
对称与对刺,兼及“必然性”诗学——读祁十木和耿玉妍的诗
景立鹏
1
肯尼斯·勃克在分析济慈的一首诗时说道,“一首诗是一个行动,是制造它的诗人的象征行动——这种行动的本质在于,它通过作为一个结构或客体而存在下去,我们作为读者可以让它重演”。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诗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寻找一种象征行动与内在经验的美学对称。而祁十木的创作恰恰反映了这一点。从他的诗中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一种动作的流动感,如“你抬起手,指着发光的第一片叶子/数着冬天和春天,哦,还有夏和秋”“他坐在狭窄的房间中央,面朝铁门,想象/开门的人……要把手伸入左侧口袋,轻轻拿出火柴/点燃叼了五分钟的烟”“我趴在窗口,看两只猫打架”等。与这种流动感与动作性对称的,其实就是内在的精神动作,它暗示着体验、想象、意识的多重扭结的组织过程。行动的过程,即是经验与认知通过隐喻获得形式化的澄明的过程。例如《凌晨,灯下读马骅》。“你用整整一夜磨一个词”的过程其实也是诗人在词语中阅读和追问的过程。“碎石飞溅/像从前的生活。肮脏”不仅是对马骅的生存状态的指认,也暗示诗人对生活的某种认知。由此可知,“你抬起手,指着发光的第一片叶子/数着冬天和春天,哦,还有夏和秋”就不仅仅是诗人的对话者“你”的动作,而是暗含了“我”的某种精神动作。正因为这种行动上的对称关系的存在,在结尾诗人才说“用一页泛黄的纸/我就能缅怀我自己”,最终亮出自己的底牌。
同时,这种对称关系不仅体现在一种修辞行动的辗转腾挪上,还体现为一种结构性的对称。祁十木的诗表面上看依然采用的是口语化的叙事,但是其叙事内容往往具有形而上的抽象性,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由动作结构组织起来的意识框架,因此,具有很强的暗示性和隐喻性。比如《烬》一诗,从整体结构来看是“他想象……”(“他坐在狭窄的房间中央,面朝铁门,想象/开门的人”“他往前迈一步,门自动打开”)的结构,与之平行的是“吸烟”(“要把手伸入左侧口袋,轻轻拿出火柴/点燃叼了五分钟的烟”“一丝火星掉落。他的黑裤子/被燃烧出洞,露出的膝盖,在缓慢流血”“那人不说话,极速抽光最后的五支烟”)的过程,而最底层的则是一个“回忆/时间”(“那些故事一并涌上来,他已不再年轻”“光阴,被他吐在日光灯下,抬头的瞬间,逐渐飘散”“放不开的往事,究竟意味着什么”“他能说出故事吗?用最沉重的词”)的结构。透过这三重结构的协奏可以窥见诗人关于生命/时间的一种悲剧性的沉吟与深思。虽然“他”无所指,但皆有所指,虽然“他”始终保持沉默,但是似乎又什么都说出了,从而抵达了诗人经验的澄明之境。这一点《情人》呈现得更是含蓄动人。由两只打架的猫,到“催生一场暴雨”,进而引申出夏季雨夜的阅读,再穿越到百年前一个老诗人的爱情故事,最后又回到“两只猫踩着湿漉漉的砖瓦/轻盈地往另一个房顶迈开步子”。而这层叠、圆融的结构性象征行动背后却是与此对称的经验的底牌:“他们可以沉溺于这一夜的阴雨/可以偏居于彼此的灵魂”。而《蜂巢》则把这一点做到了极致,只不过他把“蜂巢”的精密结构运用到对一代人的生存命运的反思上来了。表面上描述蜜蜂和蜂巢的关系,实际上隐喻了个人与历史的关系问题。这种隐喻性使得对称的经验在陌生化的语境中获得精确的形式感和丰富的内在意蕴,正如哈罗德·布鲁姆所言,“诗本质上是比喻性的语言,集中凝练故其形式兼具表现力和启示性。比喻是对字面意义的一种偏离,而一首伟大的诗的形式自身就可以是一种修辞(转换)或比喻。”而想象、经验、情感则构成了这种“比喻”“必然性”的美学对称。
2
如果说,祁十木的诗歌寻求的是一种话语形式与诗意经验之间的“必然性”的美学对称的话,那么耿玉妍的诗则表现出与经验与话语的对刺。这主要体现在她诗歌中强烈的追问、质疑与反思姿态(如“既然大地已经离开了冬天/美离开了死亡,为什么我还会梦见你?”“我们山长水阔。我该用什么神态见你?/见一见你?”等)。具体到诗作中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对话性的对刺方式。例如《夜读荷尔德林》一诗。“我”始终是在寻找一个对话者,“阅读你那些/美丽而无用的分行”,翻译的障碍使这种对话的努力成为徒劳,而荷尔德林那“无用的分行”对于存在的迷雾而言同样是徒劳。两种徒劳通过不可对话的“对话”“加速沉沦”。这是通过一种对话的徒劳来暗示一种存在的孤独与无力感。对话的不可能性更加证明了对话的必要性,是一种否定之否定造成的对经验的更深入地对刺。又如《夜读穆旦并想起战争》一诗,通过对穆旦诗中战争书写的反思指出:“你迷恋的苦难是一场乌托邦/苦难中的诗意也是。//而战争的结尾总是/被拉伸的生存,和被实体化的虚无。”以对话性语境切入对战争的思考,显得更加深沉、含蓄。而《1967,周作人致鲁迅》一诗在这一点上更加明显。诗人借周作人的口吻来向鲁迅倾诉个人遭际。整体历史情境的诗意化用使得对历史的反思更加具体、尖锐而含蓄。这种借历史酒杯,浇诗人心中块垒的方式正是其对刺方式的变通方式。
另一种对刺方式则是个人独白性质的反思。比如“我那些不被听见的情感/在内心左右撞击,回声轰鸣/它是一头被困的野兽/汹涌,但找不到出口”(《致Murphy》)“月色如水/我拿什么度过/这冷峻的时光?”(《夜晚跑步即景》)但有时这种个人独白性的对刺需要外在机缘的触发,例如在《听雨》中,诗人感觉到“钟声停摆,花朵绽放/雨从高空落下来/人世如荒原般漫无边际”;在《听Day Dream tears》时,她又会发现“在生活背面,永远生长着/音乐,挤开另一个空间/被黑夜编码,淌过/热烈的血液,燎伤骨骼/飘浮起我/没有重量的灵魂/世界也变得轻飘飘”。
而有时这种与现实对刺的方式又是通过幻觉或者一种意识流的形式展现的。这也许反映出作为女诗人,耿玉妍话语方式和想象力中更具个人特色的部分。例如《意识流》中,从荷尔德林的形而上色彩,到月色的惝恍迷离,再到夜色中酒和尼古丁的迷醉,使“我只能坐下织一场苦涩的梦,泡一杯/去年的兰花”。在这生存的旷野中,诗人沦为一只被历史豢养的“硕鼠”。但是在意识和历史的裹挟中,诗人最后仍然保持徒劳的清醒:“让我在你的隔壁安眠吧/把脚抵着你的脚,驱散大地深处的忧郁。”而这种欲求最终仍然只是一种徒劳,但是正是这种意识的徒劳,更加深了与生存体验对刺的力度。无论何种表现形式都足以看出诗人在自我世界中对外在世界的内在悲剧性的体认与质疑。耿玉妍的诗的显著特色是注重内在生命的体验,同时用一种个人化的幽闭语式刺穿现实、历史的老茧。这种对内在性与外在性的调和与熔炼,不管是个人语调上的还是精神立场上的自觉已经逐渐构成一批优秀的80、90后诗人的显著特征。
3
总体而言,祁十木和耿玉妍的创作分别从“对称”和“对刺”两个向度上实践了两种介入现实的路径,而且都是在一种非常个人化的话语策略中展开的。从个体诗学层面来看,这也体现出诗歌写作的某种“必然性”特质。布鲁姆认为,“‘必然性’,即不可避免的语言表达是伟大的诗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特征。”这种“必然性”在我看来可以引申为对一种表达形式的唯一性和有效性的确认。它通过诗人个性化的表达方式获得唯一性的有效表达,那么这首诗势必会成为一首优秀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