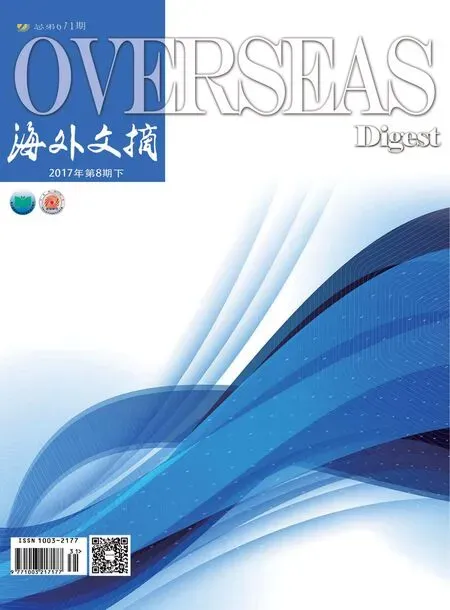后真相时代:道德悖论与动态路径探究
钟思雨
(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24)
2016年Oxford Dictionaries将后真相(Post-truth)定义为‘relating to or denoting circumstances in which objective facts are less influential in shaping public opinion than appeals to emotion and personal belief.’其意思就是说,我们自认为自己进入了后真相时代,了解到了后真相政治,但是实际上这样的时代与真相,更多反应的是群体或者个体当前的情绪诉求,而不是斥诸于事实本身,即就是凭借个人偏好与理解程度解构事实,进而建构自己头脑中的事实。后真相这一概念在2016年的重新提出也呼应着英国脱欧(Brexit)与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总统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尤其是针对当时白宫新闻秘书肖恩·斯派塞(Sean Spicer)对特朗普就职演说时的评论,美国总统顾问凯莉安·康威使用“alternative facts”即双向思维来进行辩护。其结果就是,将后真相这一词又推到了风口浪尖,乔治·奥威尔的1984也重新回到了大家的视野,引发了群众对于真相与谎言界限的担忧。2017年,安德拉梅默克尔继续第四次连任德国总理,但是却隐藏着隐患--权力的消逝与民粹势力的回暖。德国新选项党Alternative fü r Deutschland(AfD)的地位上升并且获得13%的选票,这意味着继60年后民族主义政党将第一次进入德国政府Bundestag,民粹主义与后真相时代的交汇变得越发复杂。
而相比之下,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又一次通过丝绸之路政策迎来经济与外交的快速发展时期。在2017年10月18日召开的19大,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中国引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转折点,这都预示着中国将继续拥抱改革的崭新面貌,人民朝着中国梦的蓝图更加迈进。但是,深处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也身受其影响,人民周围也充斥着各种反转新闻与冗余信息,后真相时代的威力是否会慢慢逼近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因此,首先,从认知上明确真相的含义与重要性,进而找到后真相时代的根源,了解到一定程度上后真相时代与民粹主义的关系。其次,针对世界上的质疑,将再次回到人民视野的且依然具有参考意义的1984与中国现阶段进行对比分析。最终,立足自身,找到规避后真相时代的途径,通过后真相这根线去解读中国目前群体事件的根结所在。
1 真相的属性与困境
在讨论后真相时代背后的原因之前,后真相与假新闻的区别是需要先去理清的,进而了解假新闻是如何在后真相时代膨胀发展起来的。首先,真相是脆弱且重要的。在现代区别于后现代,真相是现代的,意思是真相是立足于现代的事实与承接的历史的,是具有真实性与连续性其真相的可能性是不会被质疑与拷问的。而在后现代时期,由于立足点转变为了后事实,其真相与事实存在着被消除,排斥,甚至遗忘的风险。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后现代时代就是后真相时代。从哲学的角度,真相在后现代被看作是更为具体的形式,也就是说,真相仅仅是顺应着“disquotational device”,即真相只有放置于确切的时间,具体的语境,解读于特定的语言才具有意义。在这一意义上来讲,后现代,也就是后真相,其关键作用的便是其碎片化的真相与概念的特殊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假新闻是碎片化信息中的一种。其次,网络作为第四权力,消极意义上也被视为传播无知的工具,给每个人创造了人人都是专家的幻想。而对于作为后真相时代一部分的假新闻,是欺骗性媒体产品的快速识别符号,但是却往往不可避免地存在且继续衍生。正如詹姆斯·波尔(James Ball)提出的,在现实的背景下,传统媒体通常一方面从假新闻中获取推动力与利润而另一方面又在与其做斗争。实际上这就是道德规范的两难困境,在利益获得方面,被市场经济驱动的媒体,需要依靠吸引受众的眼球获取收益,而以消费者与专家角度看待媒体新闻的受众,又是凭借着自身的喜好与视觉满足非理性的重复着自身的信息偏好。而在新闻自由与正义道德规范下,新闻工作者又在力求寻求真实与真实背后的意义,其结果却可能因为残酷真相而不被受众承认与接受,在这个意义下,实则并没有真相可言,而只是偏好不同,并且这样的偏好还不能够以不同的立场定义,因为大多数的立场与质疑新闻都是相通的。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2016年曾有做过关于假新闻的研究调查,研究表明假新闻项目获得了870万的点击关注,而真新闻却获得了730万的关注。然而,假新闻超过真新闻的背后是一种叫做‘appeal-to-authority’的心理博弈,意思就是使得接收者认为自己是这个主题的权威。因此,在真相错综复杂,网络推波助澜,新闻工作者陷入两难中的无能为力的背景下,我们发现很难划一条分割线区分坏新闻与假新闻,而假新闻也很难成“pantomime villain”童话里的反面角色,真相背后支撑的信任感却在不断消减。
逃避真相具有反现代的特征。抗争现存的趋势与存在的证据,甚至是试图消除过去与未来,当时与当地,本民族与其他民族,他者与自我联系的记忆与记录,其结果导致在于我们无法再与过去对话,甚至无法理解濒临灭种的语言,民族的话语。乔治·奥威尔的1984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去深刻反思的原因,不仅在于小说揭示了隐藏在背后的真相的重要性,而且在于教给我们去认知欺骗的视角。欺骗总是作为一块屏障将人民与现实隔开,以至于人民无法去反思自己生存的现状。与之相反,真相却具备着超越世俗主义与人类话语的力量,能够协助建立真实与美好事物之间的联系。但是如今,真相更多的是小说,正如尼采所提出的“truth are illusions about which one has forgotten that this is what they are;metaphors which are worn out and without sensuous power;coins which have lost their pictures and now matter only as metal,no longer as coins.”正如我们所能感受到的,真理已经变成一种现在如此贬值的硬币,以至于人们都不愿意捡起它。
信仰缺失不仅是心理层面的问题,而且也是政治意义层面的问题,涉及政治稳定与政治合法性的问题。信任感的流失削弱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并且危害着政治社会稳定。政治稳定,正如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提出的,并非政治体系处于静止状态,而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相对的持续性和政治体系的一些比较基本和主要的成分,如基本的政治价值、文化和政治的基本组织结构,不发生变化。”真相具有跨越性的特征,作为人类理解语言与理解整体的核心概念,但后真相时代存在的问题就是,用碎片化的信息割裂这样的互动,使其检索与真相获得功能的失真。米歇尔福柯提出,说真相的任务是一个无止尽的劳动,尊重其本身的复杂性是任何权力都不能否定的义务,否则便会加强沉默的奴隶性。真相的存在,增强着差异性互动的可能性,促进整体和谐氛围的形成。然而,后真相时代的否认真相减少了沟通与交流所能够仰仗的共同话题与普遍性共识,其结果就是,我们找不到一个公共空间参与和交流我们不一样的话题与观点,唯一存在的便是重复的爱好与情绪诉求。人们住在唯我主义的容器里,忽视我们生活在社会共同体的事实,唯一能够感受到的就是,通过社交媒体放大性的报道而产生的悲痛与慰藉感,抑或者是被煽动分子所撩起针对异国,异民族,异地区,差异社会阶层等的愤世嫉俗感。
2 后真相时代背后的原因
真相或者说真理的贬值,迫使我们不禁地发问这背后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深知,后真相时代不是一个静止不动的现状,而是一个多因子促成的动态过程。同时,也就暗示着这样动态过程的因子会在不同阶段发生新生,演变与消失的环节。
首先,从近些年的黑天鹅事件分析,由极左极右翼势力领导的极化主义与民粹主义成为一个重要的推动因子。这个文化现象在美国是比较明显的,根源包括着新保守势力的价值观,反移民情绪和白人至上主义的融合,正如美国杂志作者劳拉·杜卡(Lauren Duca)在Teen Vogue中所发表的言论,“Trump won the Presidency by gas light.His rise to power has awakened a force of bigotry by condoning and encouraging hatred,but also by normalizing deception.”但是这不是一个唯一或者说全新的现象,民粹主义是经历了不同时期与不同国家的发展演化的。事实上,19世纪中期的纳粹主义,便是民粹主义的体现,标志着欧洲历史上从现代到后现代转变的政治危机。而这个现象产生的原因,部分是与逐渐消逝的信任感与孤独感的上升造成。弗洛姆(Erich Fromm)在其《逃避自由》中提出,德国人民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深深感受到孤独感与追求自由两种矛盾心理,他们不愿意承担自身选择的风险,最终选择逃避自由,将自身自由权利赋予纳粹,陷入到谎言重复千遍的真相环境中。Emst Nolte提出,“Facism is resistance to transcendence.”一方面,纳粹主义不是与过去的断裂,而是仅仅从过去的历史中生长出来的,就像是浪漫主义具有连续性的特征,从18世纪20年代的拜伦浪漫主义发展为20世纪60年代的享乐主义。另一方面,纳粹主义是“techno-bureaucratic”的现象是一种超越了过去的发展。极权主义创造了新机器—集中营像奥斯维辛Auschwiz,这一机器由单个的人组成,并且他们试图去完成技术工作,即民族意志。因此,民粹主义的发展也是即连续性的发展,又在新时期迸发出新的态势。
其次,社交媒体的出现便是为新时期民粹主义的新态势供应着新工具。用户层面来说,社交媒体就像是过滤器一样,基于每个用户的点击记录推算出用户的喜好,人们沉浸在营造的舒适与充满鼓舞的信息编织的拟态环境中。而从信息把关人的角度来说,浩如烟海的信息也增加着把关人去追溯信息来源与检验信息真假的工作负担。部分政治家针对受众对传统倒三角叙事方式厌倦的心理,主动利用社交媒体或者大众媒体进行一次虚假或荒谬演讲或者是讲一个严肃的政治笑话。这样的虚假信息,不仅打破了传统的规则—讲笑话前说出妙处看节目和比赛时知道结果,而且利用了意想不到与不协调的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深谙其道,通过幽默与接地气的重复‘big lies’,在推特上掀起了一阵狂欢。2012年,为了争取共和党候选人的提名,博关注度,持续质疑奥巴马的出生证明,而后又矢口否认其言行。在与克林顿希拉里的总统竞选中,发布一些色情信息或者是发表污蔑女性的言辞,以达到侮辱对手与获得关注度的目的。基于自身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标签,特朗普发布关于移民与遣民的错误声明。针对他的政治修辞,The New York Times(2016)公开声明,特朗普的举动与策略将使得媒体越发狼狈,变得越发不值得信赖。因此,我们需要反思“stone slackers”一词,并且追问是否虚假信息的内容与形式会助长群众对政治嗤之以鼻的态度,进而对政治产生冷漠或者蔑视情绪。
再者,由经济危机与质疑的科学创造的环境下,信仰缺失与将谎话处于不断地恶性循环之中。安科纳(D’Ancona)曾从经济信号中追溯信仰缺失的原因,强调说2008年的经济危机被视为是一个关键的信号,预示着官方公共言论威信度的下降。而科学本身被视为是一个自我修正的过程,其不确定性几乎总是存在的。一定程度上,科学的任务就是在消除不确定性,比如说通过科技革新来消除时间与空间的距离,减少发布模糊信息与数据的次数。从某种意义上,科学与真相都具备着跨越性的特征,并且互为联系促进。但是,在后真相时代,不确定性却隐形地被共识文化取代了。詹姆斯·凯(James J.Kay)把后科学的科学描述为一个过程,一个认识到知识与理解之间存在差距,而且这些差距无法通过革命性的科学解决。他认为(革命之间)人们不一定要试图解决或排除世界的矛盾的观点,不管他们是否以科学为基础,而是将多个观点纳入同一个问题解决过程。因此,对政策过程的科学投入的质量需要一个扩大的同伴共同体,由所有在这个问题上对话相关的人组成。以气候变化这一议题为例,关于气候变化中最具争议的便是北极熊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海面上升,栖息地减少导致濒危灭绝的论述。但是实际上,2007年与2017年的北极熊数量进行比较,却显示着北极熊的数量在不断地上升,而这一现象也被克罗克福德(Crockford)称为情绪化的传播。
3 区分1984与中国
明确了后真相时代讨论的紧迫性与重要性之后,如何定位目前中国所处的阶段是一个亟需澄清的问题。尤其在西方媒体与电影解读政治形象时,美国2016年电影《降临》更是在剧中,将中国的最有力领袖称为将军,隐形地将中国塑造为已经崛起且与美国为之抗衡的军事力量。奥威尔的1984原型取自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即当时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将1984中的重要信条进行分析解剖,是中国与老大哥“big brother”划清关系与回应质疑的有力方式。
首先,“战争就是和平”。作为老大哥政党的第一个标语,表明了三个大洋国之间的根本目标,在于用尽机器生产的多余产品,以防止整体的生活水平提升。正如书中主人公威尔森在日记中记录到,人民生活在这样虚构的持续战争中,每天都会因为政府组织的仇恨活动而变得极度狂热。但是涉及到中国对于战争的态度,在经历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将和平与发展作为其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的基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我们应该提升自身的软实力,将中国新的面貌呈现给世界。同样,承接这古代人智慧与现代人期许的一带一路计划,也是呼吁着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步骤,作为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桥梁。
其次,“自由就是奴隶”。联系着第一个标语,目的在于减少财富增长以达到稳定其等级社会。为了保持社会稳定,政府使用双向思维去合法化其政治行为,正如奥威尔描述的,任何事情都可能是真实的,所有的事情都在脑海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真正发生的事情,但所谓的自然规律是无稽之谈。但在中国却存在着渠道,使得人民能够评判政府行为并且通过互动反馈去改进政治事务。虽然,受到官僚作风的影响与经济寻租的推动,部分行政官员无法找准自身的定位,政府内部的确存在着腐败现象。但是,因为社会媒体与政府政策的有力互动使得政治制度更加透明化,权力放置于阳光下。而以往一直以官本位自居的行政官员,也转向民本位的思想,开设微信公众号与官方微博,积极主动地将信息公开且回应人民的意见。正如格兰斯(Grans)提出的,国家的民主可能直接或者间接地属于人民,但是只有人民被告知的时候民主过程才是有意义的。以雷洋案为例,一名受过良好教育的环保主义者雷洋,在北京一家按摩院外被便衣拘留后死亡,而本案最大的关注点就在于官方给出的死因说辞即心脏病死亡与其家人从雷洋身上淤青推断产生了出入。作为回应,人民日报表示赢得公众对此案的信任将是一场艰苦的战斗,这也便是我们接下来需要继续思考的问题,如何更好利用社会媒体中呈现的公众舆论将其作为折射社会问题的体温计,而规避社交媒体碎片信息与失真信息带来的信任缺失。
再者,“无知就是力量”。如果说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中,生活在新世界的人们不愿意去思考与反思带来烦恼的事实与真相,选择用玛咖来催眠自身,这是一种主动的催眠。那么,在1984下的人们,由于来自监视器与新话字典的行为与言辞压迫,而惧怕形成区别于正统思想的异端思想,这是一种被动的放弃。“The essential structure of society has never altered,that is,there have been three kinds of people in the world,the High,the Middle.And the Low…Of the three groups,only the Low are never even temporarily successful in achieving their aims…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Low,no historic change has ever meant much more than a change in the name of their masters.”而这就预示着一个三角形状的社会结构,最顶端是最有力量且永远监视着中下层的老大哥,就像是环形监狱中心瞭望者一般。紧接着是内部政党承担着国家大脑的作用,但只是百分之几的人处于这个位置,而中层下面便是占据着百分之八十五的大众。处于三角层层监视下,产生任何与所谓正统不符合的言论与行为都是不可能的,而且会变成异端进行批判,折磨,最终教化,也就是最后主人公终于发自内心的相信二加二等于五的思维模式。区别于此,中国的社会结构更为趋向橄榄球状,且结构具有动态性与流动性,为进入中间阶层与上层创造了条件。大众媒体的到来给中国网民尤其是年轻人带来了“狂欢”时代,如自发研制“习大大表情包”,关于名人的卡通漫画,抑或者是弹幕党的狂欢,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样的狂欢又是带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最开始狂欢的来源是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psychoanalytic framework”,即精神分析框架,其中将这样幽默诙谐的方式作为表达压力与情绪的发声器。作为社会期许,社会规则或者社会力量结构的逃离与接受,用幽默的方式去使得政府或权威变得不具备压迫性与易于亲近。但是,批判地来看待,在社交媒体的运用上还是有一段路需要走,这样选择幽默方式去娱乐自己实际上是一种对于生活与现实的无奈,造成“自己是专家”假象与“去权威”的方式实际上也是一种消极的社会信号。
虽然将1984与中国现阶段进行了区别,明白了社交媒体在中国发展中所形成的特殊含义,还是需要继续去探讨将引起后真相时代带来的因子,是否也会产生同样的反应,中国可以通过什么方式去减少或者说规避后真相时代到来的脚步与伴随的危害。
4 如何避免后真相时代的消极影响
如何避免后真相时代的消极影响,简单来说,就是如何有力规避引发后真相时代的因子,或者是探测出这些因素的积极方面转为发展的动力。正如,在探讨1984内容与现阶段中国发展对比时,虽然社交媒体加速信息的碎片化,与增加的错误新闻的发布量,但是也同时给了每个网民发声的机会。
因此,在社交媒体方面,中国网络空间加入缓冲器即形成有制度化的规则与政策成为了趋势。面对2016年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的数据显示,虽然中国有7亿的网民,但是其新闻自由度是排世界第176名,跟随其后是叙利亚,土库曼斯坦,北朝鲜,厄立特里亚等国家。面对这样的争议,亟需澄清的是管制背后的逻辑,能够加快去了解动态过程与找到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立足点。中国媒体上迅速崛起的学术研究集中在公共媒体上,对媒体控制的政治逻辑产生了两个密切相关的核心观点:一是审查更容易影响导致集体行动的内容。二是不会引发集体行动的关键报告可能会被鼓舞,以缓解信息短缺的状况。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审查与规制的初衷,不仅仅是在于传播信息给大众,而且是达到公民教育的作用。一方面,国有媒体或者说官方媒体有助于中国的官方纸质媒体的经济来源不是来于大财团或者经济组织,而是与国家政府紧密发展起来的。基于此,在中国社交媒体中虚假新闻的两难困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同时也减少了由于利益导向而取悦民众所带来的恶俗文化等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内部媒体一定程度上作为外交事务的感应剂。国内政策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外交事务的制度。马修·约翰逊(Matthew D.Johnson)也指出中国从重大社会运动如Arab Spring等汲取了教训,通过一个复杂的赞助制度来支持独立的纪录片制作者,这种制度保持了外国军队的独立性,并且通过对可允许范围的限制性与模糊性。因此,中国管制逻辑不只是指的国内公共信息,而也是一种信息安全环境下的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更多情况下,这不是一个策略问题,而是一个意识形态领域安全问题。
虽然国家已经形成了解决后真相时代因子的逻辑与成熟方式,但是还是需要借鉴国外事件,反思存在的不足之处。在后真理时代,重新审视真理的概念或理论,“证据”的说明是不够的,对道德的承诺在于我们致力于与他人持续的接触,并保持和发展与他人的关系,和更广泛的世界一样。从网络管制的角度,需要去反思由国家建构起来的“safety belt”,怎样去处理延伸的安全带与个人自由言论的关系。与此同时,媒体公司担任支持力量,将其嵌入到国家基础设施中,然后将审查实践外包给公司和用户。结合这种无形的援助之手,宣布用户连接到新兴的电子政务系统可能会限制人们的参与与互动。
但是,塞缪尔·亨廷顿在分析“民主化的第三次浪潮”时明确地指出,“halfway house does not stand,”这意味着部分自由化是不可持续的。部分政治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把双刃剑:它可以刺激民主转型,并促进政治适应性和复原力,同时也可能会因为社会动员程度过高而影响了社会稳定。其次,基于公众与民粹主义现象,一方面,需要去反思公众对后真相事件的态度与使用的方法,进而去探讨还原检索的可能性。因为真相或真理的复杂性与过于专业化使得人们很难掌握事实的全貌,进而无法还原信息与历史本身。同时,加上新媒体总是采取cherrypick的方式产生一些片面的信息,更为加速了这样碎片化的情景。而如何去改进这样的现状,个人观点是,我们需要去避免过于关注或依赖新媒体,而是应该试图去创造一个空间或场所能够将碎片化的信息粘粘起来。安德森(Anderson)曾经提出一个Google Scholar的项目叫做Newshouse,引进hypertext即超文本的概念,旨在“建立网络”,使读者能够轻松访问其他页面上的相关信息。且在添加或删除链接时,将文章或链接在知识树中的位置纳入考虑的范围。信息与新闻阅读的内部链接可以增加凝聚力和实用性,使读者可以通过方便地访问其他文章来加深对主题的理解。这样超文本的概念与思维是值得每一个受众去借鉴的。另一方面,需要对道德与真理做出贡献与承诺。如马尔帕斯·杰夫(Malpas Jeff)提出的对道德的承诺在于我们致力于不断与他人接触,保持和发展与他人以及更广泛的世界的关系。维持这些关系需要我们关注我们之间的差异和共同点,因此伦理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在可能最初似乎是道德差异的问题上进行谈判。不仅准备接受认知失调困境——真理从属于社交媒体,并且为情感诉求与非理性的个人信仰忽视。而且也需要有接受不完美政府形象的勇气,且协同制定可操作的策略,促进国家与社会的发展进步。
[1]Ball James,Post-Truth:How Bullshit Conquered the World.London:Biteback,2017.
[2]Levinson Paul,Fake News in Real Context.New York:Connected Editions,2017.
[3]“On Truth and Lie in an Extra-Moral Sence,”in The Portable Nietzsche,trans.and ed.
[4]Michel Foucault,“The Concern for Truth.”in Foucault Live (New York:Semiotext(e) Foreign Agents Series,1989) 308.
[5]Gross,Michael.2017."The dangers of a post-truth world"in Current Biology 27(1).
[6]See Ernst Nolte,Three Faces of Fascism:Action Francais,Italian Fascism,National socialism,trans.Leila Vennewitz(New York:Mentor Books,1969)529&537ff.
[7]See Georges Gurvitch,The Social Framework of Knowledge,trans.Margaret A.Thompson and Kenneth A.Thompson (Oxford:Basil Blackwell,1971)207-12.
[8]D’Ancona Matthew,Post Truth:The New War on Truth and How to Fight Back.London:Ebury,2017.
[9]Davies,G.L.(1966).The concept of denudation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27(2),278-284.
[10]Dr Susan Crockford.(2017).Polar bear scare unmasked:The saga of a toppled global warming icon [video].Retrieved
[11]George Orwell (Eric Blair),1984,Chapter 2,page129.
[12]Gary King,Jennifer Pan,and Margaret E.Roberts,“How Censorship in China Allows Government Criticism but Silences Collective Expression,”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7,no.2 (May 2013):326-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