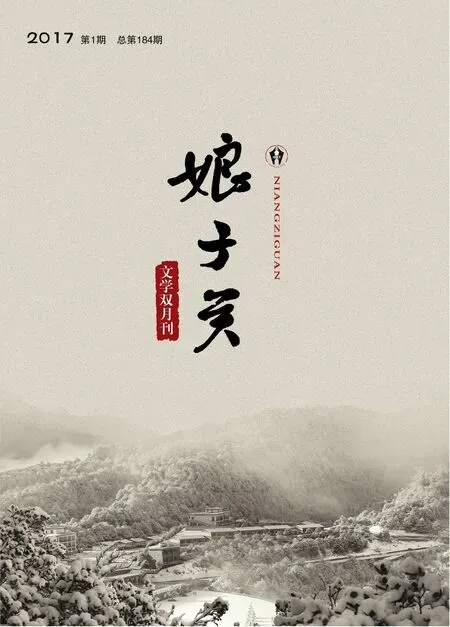侯伯良与小大王
●侯讵敏
侯伯良与小大王
●侯讵敏
在盂县众多的民间传说中,侯伯良与小大王的故事无疑是比较独特的一个。
侯伯良,元末明初人,苌池侯姓第五世先祖。按《侯氏家谱》所述:侯氏在本地属“高门巨族,历代世家”。侯伯良为人“秉性耿直,勤劳良善,扶弱济困,惜老怜贫”,是当地有名的大善人。
小大王即藏山大王,据史书载,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宋高宗赵构下诏,封河东神祖赵文子为“藏山大王”。文子是赵武的谥号,赵武便是历史上有名的赵氏孤儿。小大王显然是人们对藏山大王的昵称。
藏山原名盂山,位于盂县城北近四十里处,因程婴藏匿赵氏孤儿于此十五年而得名。藏山有座古庙叫作藏山神庙,又叫藏山神祠。藏山神庙由来已久,庙里最早供奉的是程婴和赵武,神台上单祀程婴,赵武持程婴之拐杖立于神台下面。许多年以后,祭祀的格局有所改变,先是改赵武侍立为陪坐,后又变成赵武居神台之中而坐,程婴、公孙杵臼列于赵武左右。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程婴和赵孤便幻化成了当地专属的保护神。“我盂之境环处皆山也,土地硗瘠,士庶繁多,既无川泽以出鱼、盐之利,又无商贾以通有无之市,人人无不资力穑以为事。向若一岁之内颇值灾旱,饥寒之患不旋踵而至,由是赖我公(程婴)之丰功厚德,居山之灵。风行草动,状带威神,为云为雨,往祷者无不应,一方之人到今受赐无得而称焉。至四方之人,但往求者亦应之。又以见俱蒙覆露也。”(金大定十二年,公元1172年碑碣《神泉里藏山神庙记》)“其灵通远迩,其享无贵贱老幼、水旱疾疫,恳祷者即获休应,其庇庥不啻一方,或宰是邑者调宰他所,遇酷旱相像虔祈,无不云兴雨作,故庙祀之处者多盂之编民。”(大元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碑碣《重修神泉里藏山神庙记》)不过,刚开始,小大王还只是一个配角,“庙之侑坐赵孤者,灵更明矣,有人窃负而往者,亦能救旱意,其襦中之风不坠焉。”(金大定十二年,公元1172年碑碣《神泉里藏山神庙记》)
有一年,苌池周边逢大旱,从开春至六月没下过一场透雨,万般无奈,四乡百姓不得不组织起来到藏山神庙去祈雨。鉴于侯伯良在当地的声望,他被众人推举为祈雨的最高指挥者——水官。
作为“水官”,在祈雨期间,侯伯良每天一日三餐只能以小米米汤充饥。侯伯良带领求雨的人马从苌池到藏山一天徒步往返四十多里山路,每人每天要在大太阳底下轮班跪香两三个时辰。这还不算,为了表示虔诚,求雨的队伍早出晚归前,还要抬着神主牌位举着香烛赤脚光膀子在村街上游行一圈儿,到了庙上,也要以这种状态在庙前庙后、大殿配殿继续绕行数圈儿,谓之“转香”。
如此这般,半个月过去了,看看老天,却仍然没有丝毫要降雨的迹象。年轻气盛的侯伯良终于被激怒了,他从地上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尘土,用手点指着手持拐杖站在神台下边的赵武调侃道:“你是藏山小大王,我是苌池侯伯良,就算你三年不下雨,我地底下还存着万石米哩。”说完,冲那些还在跪香的人一挥手说:“算了,甭跪咧,都起来回吧,咱求人家,人家不搭理咱,有甚办法?大不了是个没饭吃,人家不管我管。”
处在侯伯良那个时代,一个人也许敢于公开斥责朝廷,甚至造皇帝的反,但很少听说有人胆敢当面指责神仙的。所以即便是侯伯良这样不计后果的狂人,也不敢对端坐神台之中的程婴有所不恭,而是选择了向随侍身份的小大王开炮。
参加祈雨的老老少少,这些天哪个没有脱掉一层皮,只是敢怒不敢言罢了,一听侯伯良这声指令,不亚于见到大赦的圣旨,立马就有多人响应。剩下几个胆小的,既怕得罪神灵,又怕开罪众人,踌躇了好半天,结末还是选择了一起离开。
就在回来的路上,大家碰到一个卖猪的,挑着七八个猪崽子。估摸是因天大旱,人心惶惶,小猪无人问津,这人跑了好几天都没做成一笔买卖,扔了舍不得,养又养不起,正在那里愁得要死要活的。侯伯良见这人可怜,二话不说便买下了这担小猪。
说来也怪,就在当晚,一声炸雷过后,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平地起水尺数。侯伯良临时放在院里的小猪不知什么时候已把墙根拱出了一道道深沟,雨水顺势冲垮了侯伯良的院子,并冲毁了他的地下大粮库,所有的粮食一粒没剩。据说苌池现在的陆西口麻河(大土坑)就是侯伯良当年的粮窖遗址,那条被称为官道沟的大土沟也正是当年那场大水留下的痕迹。侯伯良跟小大王赌气,结果遭了水灾报应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在盂县传开了。小大王的神通、灵验在侯伯良身上得到了最大的印证,人们对小大王的崇拜可谓与日俱增。随着小大王的神像越来越多地被人们请来请去,慢慢地,只知求大王不知求他神的心态在信徒中已逐渐养成,小大王的神位在藏山最终取代了程婴的主导地位。而侯伯良也因此成了盂县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传奇人物之一。
有人可能会说,小大王坐藏山主位是正统观念使然,更何况“若不复知有文子,又岂复知有二公?”(明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碑和碣《祀藏山大王说》)一件顺乎天理,合乎民意的事,于侯伯良何干?的确,尊卑有序,长幼有别,儒家思想文化的作用岂可小觑。好在笔者的记述只限于民间传说,不足以成为任何学术研究的借鉴资料。
当然,记录民间传说也应本着搜“旧”如“旧”,尊重“历史”的态度,不能随意篡改。盂县有个文化工作者叫闫钟瑞的先生,曾整理过不少民间传说,其中有一篇题目是《小大王赌赢侯伯良》,发表在韩万德先生主编的《藏山文化通览》上,后又被收录到由崔亮云、杨玉牛二位先生主编的《盂县古话》里,文章跟笔者讲的是同一件事。不过在闫先生的文章里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时间上的错误,一个是逻辑上的错误。
关于侯伯良生活在“清朝嘉庆年间”一说,可能是闫先生的杜撰,也可能是笔误。藏山现存的大明嘉靖四年《崇增藏山神祠之记》碑文中,苌池纠首侯文整、侯文会、侯文贤、侯文忠正是侯伯良孙子的孙子。
至于侯伯良“独霸一方,横行乡里,无恶不作。”一说更是无稽之谈。试想:如果侯伯良担心藏山大王“萌发善心,降下雨来,”破坏了他放高利贷的“美梦”,他应该虔心许愿,向小大王求恳,而不会去“一不烧香,二不叩头,用水烟袋点着正殿里大王的鼻子,”大声呵斥,以激怒小大王。从侯伯良的四句打油诗“你是藏山的小大王,我是苌池的侯伯良,你打三年不下雨,我地下藏有万石粮!”中也不难看出,侯伯良的意思分明是说我不怕你不下雨,而不是我希望你不下雨。所以说闫先生的文章在逻辑上根本站不住脚。
著名作家张石山有言:“搜集整理民间诸如古话、笑话、民谚、童谣等口头文学段子,最好按照原样整理。最要不得自作多情、妄加改动。那样的话,非但无功,简直就是有罪。”在此,仅借此言与读者诸君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