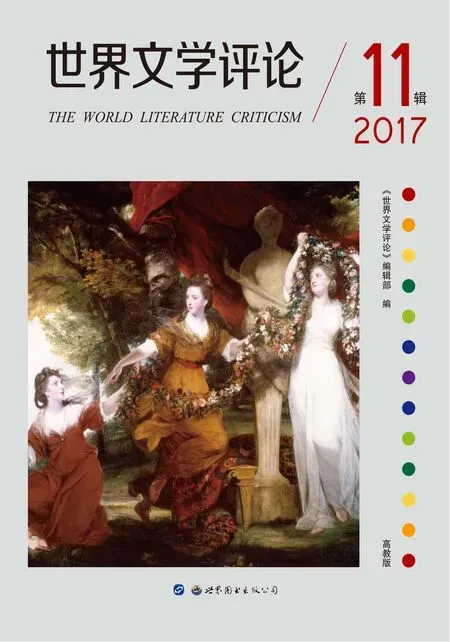晚清英国漫游者对中国社会空间的凝视
洪思慧
晚清英国漫游者对中国社会空间的凝视
洪思慧
晚清时代,英国来华漫游者书写了大量的游记之作。通览此类作品,可以看出晚清七十余年间英国访华游记文学创作从表面记录向深入表述的发展轨迹。这种转化的基本条件,来自漫游者们努力拓展对中国社会空间地域的凝视范围,不断扩大对中国社会空间形象的认知对象。英国漫游者空间视域拓展与转换的内在动因,在于他们急需寻找商业化殖民空间的集体意图和期望描绘差异化他者的个人表现心理。在摆脱了凝视空间受限时的同质化与表面化书写后,许多访华游记作品表现出多面性与差异性的凝视观感,从而实现了对中国社会空间形象的新发现与新认识。
英国漫游者 中国社会空间 凝视拓展
Author: Hong Sihui
is from the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imagolog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晚清之时,英国来华漫游者日渐增多。虽然他们的个人情况与文化背景各不相同,对中国社会空间观察的视角、焦点也各有差别,但以约翰·厄里“游客凝视”的观点来看,其共同身份都是“异域漫游者”,都在用启蒙运动之后西方人注重实证的凝视方法来认识异邦世界。这些访客热衷于用文字记录所见所闻,创作出数量可观的游记文学作品,描绘了彼时形形色色的中国社会情景。纵览国内译出的此类著作,不难发现自鸦片战争之后70余年间,英国漫游者在华的地理移动范围逐渐延伸,凝视空间的聚焦点在不断扩大,使得他们建构的中国社会空间形象,从早期的同质化和表面化记录走向后期的多面化和差异化描述。漫游者凝视空间拓展转变的动因:一是列强国家竞相争夺中国社会空间的集体利益需求,二是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个人意志发挥的结果。从文学意义上看,漫游者凝视过程深化的结果则是多角度、多视野地展现了晚清中国社会的空间形象,极大地丰富了西方访华游记作品的内容。
一、空间视域禁锢下游记写作的同质化与表面化
晚清的不同时期,在西方漫游者的凝视记录里,对中国社会空间形象的认知存在有较大的区别,总体来说是从单纯的记述向多样的表述转化。两次鸦片战争前后,来华的英国漫游者因为受制于活动地域的管束以及前人作品的影响,不同作者所写的游记文本普遍存在着相同话题与相似评价,雷同的叙述比比皆是,主要表现为描写的同质化和论述的表面化。
(一)社会集体想象物羁绊下的同质化描写
翻阅此时英国漫游者的游记,不难发现作者们对诸如科举考试、宗教信仰、祖宗祭祀、压迫妇女、溺死女婴、女子缠足、民间赌博、吸食鸦片、乞丐流民、官员昏庸、刑法严酷等现象的描述,往往具有千篇一律的笔调和观点。例如,对中国城市空间街道的记述,普遍的结论是街道狭窄、通行不便。英国传教士施美夫眼中的广州印象为:“看到一条接一条难以称之为街道的狭窄的大街小巷。当游人向前走去,他会看到狭窄的街道继续一条接着一条,使他的脑中渐渐留下印象,这就是广州街道的普遍特征。”布莱森夫人笔下的汉口是“街道非常狭窄以至于货车或马车都无法通过。在某些中等的街道上我伸开两臂几乎能摸到两边的东西。汉口最宽的街道也只能并排行走四五个人”。英国传教士麦高温说:“中国的城市给人一种这样的感觉:它刚刚建成,并且因为在建设之前给它留的地方实在是太小,所以不得不委委屈屈地挤成一团。那条主干道,即使要负责的交通是最繁忙的,给它留下的宽度也只有十到十二英尺。但是认真算来,它的实际宽度只有四五英尺,这是由于道路两旁商家们的侵占,他们为了摆放货物,用凳子、桌子占用了一部分。普通街道就更不用说了,还要更窄一些,胡同里的干脆只有三四英尺。”
此外,当时西方大量印行的一些商业性的中国游记作品,对后来者显然具有先入为主的影响。仔细检阅可以发现,有些游记作品或借用他人的观察结论或是相互传抄,往往将己见与他见混为一谈,不少相似的内容多非作者亲见亲闻。如英国驻香港总督布莱克写有《港督话神州》一书,他在该书中就中国妇女缠足一事评论道:“中国女人的缠足,犹如中国人眼中欧洲妇女的束腰,可以说都是一种严重的身体畸变。但前者对身体的伤害要比后者为轻,因为后者不仅使骨骼变得畸形,而且几乎使人的五脏六腑移位。”布莱克此番言论实际上是借鉴他人的说法,因为该书出版于1909年,而有关西方妇女束腰比中国女人缠足危害更甚的言论,在此之前几十年的许多游记作品中已多次出现。类似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使得包括英国游记作品在内的西方游记之作,在对中国社会空间的描述中充斥着不少道听途说(并非作者耳闻目见)之词,杂糅了不少传说和想象(他人论述和有关套话)。当然,这种现象的背后也有书商的推动作用——很多游记出书很快,显然是为了满足大众的好奇心。
造成游记作品论述同质化的原因,主要是漫游者所在国度的社会集体想象物制约了他们的眼界,尤其是那些异国形象的负面套话,为观察者事先勾勒出中国城市形象落后、灰暗的轮廓。中国学者孟华指出:“套话是形象的一个最小单位,它浓缩了一定时间内一个民族对异国的‘总的看法’”,晚清时期的英国来华漫游者,一般都受到了前人所写中国游记中套话的影响,来华后更以相关的套话来对应凝视的现实,最终在自己的记录作品中进一步“证实”有关异域的套话。其次是许多人来华之前阅读了一些前人所写的有关中国的论著,不免会戴上先入为主的有色眼镜,“西方人对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认识往往取决于他们在本国的经验”,当漫游者们面对他者的陌生现象难以深入理解时,很容易产生程式化的倾向,加之鉴别和洞察事物的能力有限,形成认知能力的迟钝和观察结论的偏差,结果往往在自己的游记中继续添加老生常谈和相同的结论。
(二)个人认知能力局限中的表面化论述
游记作品描述表面化的原因,主要是漫游者在华的行动空间范围受限,影响着凝视效果的发挥。1840年之前,清廷在西方殖民强国窥伺中国的背景下,禁止外国人进入中国内地,阻断了漫游者到中国广大城乡空间的观察之路。1842年五口通商之后的一段时期内,禁令在地方各省依然有效。因而这一时期的英国游记文学作品所描述的中国城市空间形象,基本以《南京条约》规定开放的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五个口岸城市以及南京、北京、汉口为主,鲜有深入内地城市游历的记录。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天津条约》,虽然规定外国人可以前往中国内地经商、传教,但实际上欧洲人在华出行有意想不到的种种困难,故当时一些漫游者往往需要乔装打扮,穿着中式服装前往内陆省份探险行走。对此,英国学者约·罗伯茨记述道:“1842年《南京条约》订立之前,外国人在中国活动极受限制,广州是唯一的对外贸易开放口岸,那些到过中国其他地方的西方人是偷偷摸摸进行的。1842年以后,外国人有权从五口出发,作半天旅行,但必须在天黑以前回到五口住地。……19世纪后期,虽然外国人有权利在内地旅行,但他们仍然使用中国服饰,库柏‘头戴发辫,身着马褂’溯长江而上,以避免遇到敌意而发生意外事件。柯乐洪1882年在华南旅行时就是穿着全套中国服装,以避开好奇的中国人。”“十九世纪西方关于中国的大部分记载仅仅涉及到通商口岸和沿海地区。甚至到1871年,库柏仍然这样写到:‘内地那些巨大的省份还很少有人问津,数以百万计的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和状况仅仅被肤浅地观察。’西方人在中国内地旅行时遇到的人们还没有被通商口岸流行的排外情绪影响。这些见闻经常提供极为不同的印象。”
其次,漫游者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程度有限,也极大地限制了他们游记作品的广度和深度。英国探险家丁乐梅根据亲身经历指出,描述中国的文章“它们中的大多数都由知识体系绝不完备的作者们写就”。剑桥大学第二任汉学教授翟理思1902年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演讲时说:“对中国和中国事务的认真关注只是近年来的事情。25年前,在整个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只有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教授。”显然,英国来华漫游者的文化层次参差不齐,特别是一些来去匆匆的游客,他们的记述常常带有片面成分。对此,港督布莱克承认:“对于真实的中国,我们只有肤浅的了解。普通的欧洲人要是万一想到中国,头脑里便会浮现出一个未开化、不诚实、充满尔虞我诈、有过多原罪的国家。”英国探险家威廉·吉尔也说:“‘北京是什么样的?’我知道回到英国后,一定会有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曾经以为自己一定能回答,但我见到的东西越多,这个任务看起来越难完成。”的确,汉文汉语和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对外来者是一道高高的门槛,精通汉语和中文的麦高温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年,他写的《多面中国人》《近代中国人的生活掠影》等著作,今天读来仍然有许多片面和不准确的内容,那些一般普通漫游者所写的游记,只能是走马观花的速写和道听途说的杂录。
二、空间视域拓展后游记创作的多面化与差异化
晚清西方来华漫游者不甘于行动空间受限的状况,他们在多种利益和动机的驱动下,逐渐突破禁令,冒险深入中国内地和边疆进行探险考察,寻找新的未开垦的殖民贸易空间。其中英国漫游者们力求突破凝视中国的地域限制以及自我社会集体想象物的羁绊,努力扩展凝视的空间范围并寻求自我的梦想,为多角度、多方位构建中国社会空间形象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一)多面化观察——中国社会空间的新发现
在对大清帝国腹地进行探索的过程中,漫游者们开创了对中国社会空间从表面化到多面化的凝视拓展。马嘉理是较早穿行云贵地区的英国人,肩负着了解当地状况的侦探任务,一路受到沿途各级官府的保护(实际是监控)。他眼中的贵阳显然与一般同质化的游记不同:“至省城贵阳。我甚爱此地,人群彬彬有礼,毫不生厌。街上熙熙攘攘,却无人尾随或盯视,时有惊异表情,但仅此即止,几番闻其雅言‘有客自远方来’。沿主街行至仆从预定客栈,一路光景如画,无数招牌及印染布匹沿街摆卖,红、蓝、绿各色雨伞闪闪发光,伸出店外,似诱雨来。”英国探险家威廉·吉尔成为第一个到达川西北地区的欧洲人,他为此获得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和巴黎地理学会的金质奖章,他对成都描写是:“城市格局良好,街道笔直,角度相宜,道路铺砌完好细致,其中一条非常漂亮,依着穿城而过的河流而建。……成都的商铺相当不错,能买到各式各样的货物,尤其有个很大的丝绸市场。”还有一路溯长江而上、深入西部地区观光探险的立德夫妇。作为商人兼冒险家,立德于1898年驾驶“利川号”轮船抵达重庆,开创了人类用机械船只上溯长江的最远记录。立德夫人曾深入汉口附近小镇了解情况,她写道:“我曾听过不少中国小镇的故事,所以第一次踏进镇子时,吃了一惊。我常听人说,那儿的景象如何如何可怕,那儿的气味如何如何难闻。但我认为,讲这些故事的人,肯定没去过伦敦东区,也不晓得法国南部和意大利的城市是什么样子。汉口给我的印象十分清洁,尽管街上拥挤不堪,但大多数人都彬彬有礼。”
在众多积极探索中国未知空间的漫游者中,英国记者丁格尔(中文名丁乐梅)克服种种困难,深入西南边疆的探险经历更为奇特,其行为颇具个人主义的典型代表。丁乐梅于1909年徒步在四川、云南边陲省区行走1600多公里,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居住在穷乡僻壤中条件奇差的旅店,不时还需扎起帐篷抑或借宿人家,饱受困苦、病痛、孤独的折磨。丁氏对四川沪州市的评价是:“它是长江上游人口最多、最富裕的城市。它可算是一个非常干净的中国城市了,街道均被精心维护,上面建有备货充足的大型商店,到处都显露出商业繁荣的迹象。”作者游历昆明后感叹这个城市在10-20年里发生了巨大变化,修建了滇越铁路,创立了以云南陆军讲武堂为代表的新式军队,警察在废除旧习俗改进市容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修建了当时全国最好的中西建筑风格监狱,在这个偏远的内陆省份竟然创建了壮观的云南大学和农业学校。
由此看到,与那些中国城市脏乱差、中国人形象雷同化的记载相反,在深入华西地区、西南省份的漫游者笔下,中国社会空间形象发生了改观,呈现出多面化的景观。由于他们几乎都是率先踏足一处未知的地区与城镇,不受集体想象观念的潜在影响,也没有前人的相关游记论述可资参考,因而他们的凝视结果既多姿多彩又较为真切客观。法国学者巴柔指出:“形象就是对一个文化现实的描述,通过这种描述,制造了(或赞同,宣传)这个形象的个人或群体,显示或表达出他们乐于置身其间的那个社会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虚构的空间。”凝视中国社会空间视域的延伸、视角的扩展,使异国形象得以丰富和全面化,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社会集体想象物对真实文化现实进行不自觉虚构与想象的可能。
(二)差异化凝视——中国人文景观的新认识
在对中国内地及边陲探索的过程中,漫游者们还开创了对中国人文社会从同一性走向奇异性的路径。在中国边远地区的旅行非常艰苦,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危险,需要探险家具备足够的勇气。《泰晤士报》中国记者莫理循从四川穿越云南抵达缅甸边境,他说:“我虽然不谙中文,也没有带任何的翻译或者随从,仅仅是单枪匹马,赤手空拳,但却没有任何担心,因为我心中充满对中国人的信任。……跟我的同胞一样,我是带着强烈的种族厌恶来到中国的,但是这种感觉逐渐被强烈的同情和深深的感激所替代。每次当我回顾这次旅行,回顾我走过的许多省市的时候,我就想起中国人的友善、好客,他们充满魅力,让我一路上都心情愉悦。在我看来,至少中国人没有忘记他们的格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漫游者们在深入凝视中国西部和西南地区时,发现了许多新奇的人文景观。英国探险家威廉·吉尔1876年从成都出发,通过藏区东部进入四川西北部岷山地区,成为第一位涉足此地的外国旅行家,他描绘了很多川西汉藏交界区域和云南地区的城镇风光,记录了当时西方人很少了解的藏、纳西等少数民族的生活情景。吉尔非常欣赏贡自卡的自然风光,他说:“我们在竹巴龙附近穿过金沙江,抵达海拔11 675英尺的贡自卡。这村边的景色如果能西移几千英里,简直能让一个瑞士酒店的老板发财。清晨,我登上屋顶,目光在山谷令人忘情的美景中流连。只见山谷四周是草木茂盛的山峰,大片淡黄色的花朵让我不禁想起英国的河岸。……法国传教士已在此购地建房作为夏季住宅。确实没有比这里更令人愉快的地点了。”吉尔对川西汉藏交界区藏族人的描述给当时的西方读者带来新鲜和惊奇,例如他对打箭炉地区藏族人的描述:“打箭炉位于山脚下一小片开阔的山谷之中,三面环绕大山,东面开放,围着破败失修的城墙。喧闹的河水将城市一分为二,河上一座木桥跨越,岸边有很多树木。这里的街道非常狭窄脏乱,店铺很差,各种奇形怪状的‘野蛮人’身处其间:有的身穿粗糙的毛哗叽或棉衣,脚上是高筒皮靴,头发或纠结或长长地绺绺垂肩;有的穿着油腻的皮衣;喇嘛则全身披红,头发剃得很短,手上摇着转经筒,同时低声念颂着‘唵、嘛、呢、叭、咪、吽’。……这里的男女都戴着大量黄金和白银饰品,还有沉重的耳环胸针,上面装饰着大量细碎的绿松石和珊瑚,脖子上还戴着经盒,其中有些是黄金做的,还有些上面有非常精致的银丝装饰,这东西是用来放祈祷文的。有些女人非常漂亮,长得与汉人完全不同。”立德先生则根据自己在长江上游航行的经历,写作了《穿越长江三峡》、《峨眉山等地游记》等游记作品,记载了大量川藏地区民族民俗风情,生动描绘了中国西南城乡的独特图景。
约翰·厄里说:“凝视是通过标志和差异被建构起来的,而旅游就包含着收集标志和寻找差异。”很多事物的标志性符号常常带有表面化的特征,很容易被游客们理解和传播;而差异性的寻找则不能随大流,对它的追求需要潜心关注。在中国内地从事凝视拓展的漫游者们就是在寻找差异化的空间形象,所以他们的游记作品与众不同,展示出了独特的差异之美。特别是这些漫游者对中国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多民族生存现象的关注和记录,成为19世纪中后期中国西南地区民族志的宝贵资料。
三、漫游者空间视域拓展转换的动因与意义
以往,人们在谈论英法等列强势力对晚清中国内地、边疆地区渗透的现象时,多指出其帝国主义的殖民与贸易意图,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在我们细读当时漫游者留下的游记文本资料后,笔者认为英国来华漫游者力图扩展空间视域,造成凝视中国社会空间视角的位移、转换的基本原因,可分为集体行为动因与个人行为动因两类——前者以不同方式与传教、殖民、贸易活动有着密切联系,而后者是与此类行为无关的学者、探险家、旅游者等,因而应该区别对待。
(一)探寻商业化空间的国家殖民意图
英国来华漫游者力图扩展空间视域的首要原因,明显带有加紧对中国的殖民扩张,争夺在华贸易利益的需求,这就成为一种附加在漫游者身上的集体行为动因。19世纪中后期,积极前往四川、云南、贵州、西藏省份探险、考察者首先是英国人,其目的在于连接、打通英国殖民地缅甸和印度与中国的通道,以方便经商贸易。1875年,柏郎上校率领的英国探路队勘测滇缅交通,翻译马嘉理在云南被杀,英政府为此强迫清廷签订《烟台条约》,进一步对列强放开了西南地区,此后众多的西方漫游者纷至沓来。
英国虽然是第一个实现工业革命的国家,但随后美、法、德、俄等国也先后完成工业革命,走上了与英国竞争海外市场的道路。特别是19世纪下半叶第二次技术革命之后,美国、德国等国在工业生产总量上赶上和超过英国,使英国丧失了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此时正当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国的扩张目的指向中国的西北和西南,特别是西南地区对英国的战略地位更加重要。曾任英国皇家炮兵团中尉的探险家托马斯·布莱基斯顿的报告写道:“至于印度与中国东、中部之间的交通路线,从地图上来看,最可行的应该是乘汽船沿布拉马普特拉河上溯至萨地亚或其附近,然后再到扬子江,两者间的陆路直线距离仅220地理英里左右。但我们对其间地区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我要劝告英印政府,不要迟疑,加紧探索。”1861年,布莱基斯顿组建考察队溯长江而上,成为首批不加乔装打扮深入四川腹地游历的欧洲人。他们沿途勘测航道、绘制地图、观测气象、了解风俗民情,引发了英法两国此后30余年探索、争夺中国西南地区的活动。
英国人在西南的探查是要打通与印度、缅甸殖民地的经贸通道,与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地竞争;向西北地区探险则是试图制衡俄国在中亚和中国西域地区的扩张。这种战略图谋在冒险家立德的游记中说得很清楚:“1875年协会没有重大的地理发现。与喀什葛尔的外交联系实际上断绝了,马嘉理被杀后迟迟没采取有效手段,这样一来,两条路线本来很有希望开通,却因此受阻。此事未能解决,并由此导致了不信任,这些不利因素阻碍了进一步探险,以致我们去年对中华帝国边远地区的地理知识毫无增长。”“俄国人在西北再次大举扩张,英国却在西部和西南部毫无动静。浩罕地区剩下部分已被侵占,现在俄国人的统治范围已经与天山接壤,这些高大山脉的腹地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国家之间的通行要道。”对于日不落的大英帝国来说,任何力量都无法阻缓对新殖民地的攫取,英国驻华使团二等秘书密福特对此直言道:“瓜分中国这头巨兽的行动即将开始。……若德国有意占领山东,繁荣其殖民经济,将使山东成为华中地区与俄国之间的缓冲地带。而俄国实际早已占领满洲,并觊觎直隶多年。不管怎样,就算俄国将直隶与北京一同吞并,也没有什么值得特别惋惜的。……若德国反对别国在山东继续扩张的话,我们也没有什么损失。若法国意图更改其大亚洲地区殖民地的边界,我们为何要干涉呢?恢复缅甸殖民地,使长江地区可以自由贸易,对英国来说已经足够了。”从他们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漫游者们转换凝视空间场景、视角现象的背后,闪现着殖民者们寻求更多的权力和利益,在列强诸国中扩展英帝国势力范围和扩大贸易途径的意图。
(二)描绘差异化他者的个人表现需求
约翰·厄里认为,历史上曾有一个从“个体旅行者”到“大众社会游客”的转变过程,19世纪就是单一游客凝视的时代。英国来华漫游者力图扩展空间视域的第二类原因属于个人行为动因,即某些学者、探险家、旅游者等所从事的漫游活动背后,没有政府利益或商业企图。这些人以上述的丁格尔、立德夫妇为代表,他们的主要特点在于以个人意愿为基点,进行漫游视角的转换,实现了从“求同”转向“寻异”的自我发现。约翰·厄里指出:“人们会选择要去凝视的地方,因为他们对强烈的愉悦感有着期待,特别是通过幻想产生期待。人们的这种期待要么是在程度上有些不同,要么就包含着某种与惯常遇到的有所不同的感觉。这种期待是被建构起来的,并且通过各种各样的非旅游的东西加以维持……这些非旅游的东西建构了旅游凝视,并且强化着它。”对于未知空间的凝视包含着凝视者强烈的期待,在迥异的文化背景下,这种期待又被放大了。勇于向闭塞的中西部省份探索的英国人,在凝视中国城市的“看”与“被看”关系中,作为“看”的一方,实际上同时体验了本土与异域在自然风物、社会特征与人文性格等方面的差异,亦是自我认知与发现的过程。
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城市时代三个相互重叠和延续的阶段。那么,与时间相对应的必然是空间领域。可以想见,从工业空间而来的英国漫游者进入到农业空间之中,在对中国社会空间形象视点转换的过程中,他们能够强烈地感受到新鲜、独特的空间位移,实现自然空间与心理空间的置换,从而影响到他们固有的空间意识形态观念,实现了凝视的拓展。丁乐梅对此有独特的体验,他在徒步穿越川滇的行程中,凝视着云贵高原的壮丽山川和秀美城镇,深深被中国所震惊。他赞叹道:“这个国家确实也魅力非凡。……偏远地区最能吸引她的崇拜者:寒冷丛林中,高山峰顶上,远离尘世处,峡谷裂缝间……对我这类人而言,它们是多么美丽啊!相较于人类社会渺小的舒适生活,许多人还是更愿意在万物皆如原初的地方体验神创造的曼妙奇迹。我很高兴我摆脱了西方社会的喧嚣,褪下了人造衣衫以及其他被冠以文明之名的无用装饰,前往只与风起风落为伴的寂静山巅,在遥远角落中自由地行走与呼吸——感谢上帝,世间仍有尚未被侵袭的角落。”从西方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下来到东方贫穷落后的偏僻地域,漫游者会如何感想呢?丁乐梅(他出身于富裕家庭而且在青年时代挥霍无度)在经历了困苦的西南之行后说:“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再尤其是其中较为贫困的阶级,教会了我们如何过一种没有家具、没有多余物品乃至没有最最基本的必需衣物的生活,我不能不被这一优点深深震撼,它是这一伟大国家在挣扎求生的过程中获得的。这种生活方式,大概会在黄种人与白种人的竞争中成为他们的优势,……它也暴露出了我方文明的些许劣势。”
总之,英国漫游者凝视拓展后游记作品的多面化与差异化呈现,一方面是对中国城乡与社会空间的客观聚焦与描绘,另一方面也是为满足漫游者们绘制一幅“差异的他者”图景的心理需求以及殖民贸易的目的。在这幅图景中,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空间形象与英国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空间形象截然不同的巨大差异,满足了长期以来西方对东方的想象,合乎漫游者们对“他者”的心理期望。
注解【Notes】
① “晚清”时段,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定为1800-1911年,本文以多数史学家将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为起点,终至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如此限定,只得将著名的马嘎尔尼使团成员19世纪初期出版的访华作品,以及辛亥革命前后英国漫游者的一些重要游记舍弃,尽管它们有助于从更长的时间范围来说明本文的主旨。
② 约翰·厄里:英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曾任教于兰开斯特大学,1992年提出了“旅游凝视”理论。
③ 滇越铁路是1901-1910年法国人投资修建的从中国云南昆明到法属殖民地越南海防的窄轨铁路,当时被称为与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相媲美的世界第三大工程。
④ 打箭炉,清代及民国时期地名,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府所在地康定市。
In late Qing Dynasty, British travelers came to China and wrote a large number of travel notes which showed the trend of writing from superficial description to comprehensive description. The conversion was on the basis of extend gazing areas and enlarge cognitive objects. The inner reason of conversion was because British travelers eager to fi nd commercial colonization space for collective intention and depict differentiated "otherness" for personal intention. After they escaped from homogeneous and super fi cial writing, many travel notes revealed a multifaceted and difference gazing impressions, thus made foreigners re-discover and reunderstand China social space images.
British travelers China social space gazing extension
洪思慧,武汉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形象学。
作品【Works Cited】
[1][英]John Urry:《游客凝视》,杨慧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8-200页。
[2][英]施美夫:《五口通商城市游记》,温时幸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
[3][英]约·罗伯茨:《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蒋重跃等译,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9页。
[4][英]约翰·麦高温:《多面中国人》,贾宁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174页。
[5][英]亨利·阿瑟·布莱克:《港督话神州》,余静娴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6]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7][英]约·罗伯茨:《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蒋重跃等译,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8页。
[8][英]约·罗伯茨:《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蒋重跃等译,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9页。
[9][英]约·罗伯茨:《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蒋重跃等译,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1页。
[10][英]丁乐梅:《徒步穿越中国》,陈易之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11][英]翟理思:《中国和中国人》,罗丹等译,金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10页。
[12][英]亨利·阿瑟·布莱克:《港督话神州》,余静娴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139页。
[13][英]威廉·吉尔:《金沙江》,曾嵘译,中国地图出版社2013年版,第25页。
[14][英]马嘉理:《马嘉理行纪》,曾嵘译,中国地图出版社2013年版,第109页。
[15][英]威廉·吉尔:《金沙江》,曾嵘译,中国地图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页。
[16][英]阿绮波德·立德:《亲密接触中国——我眼中的中国人》,杨柏译,南京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17][英]丁乐梅:《徒步穿越中国》,陈易之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第47页。
[18]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6页。
[19][澳]莫理循:《1894年,我在中国看见的》,李琴乐译,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20][英]威廉·吉尔:《金沙江》,曾嵘译,中国地图出版社2013年版,第192页。
[21][英]威廉·吉尔:《金沙江》,曾嵘译,中国地图出版社2013年版,第146页。
[22][英]John Urry:《游客凝视》,杨慧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译序第8页。
[23][英]托马斯·布莱基斯顿:《江行五月》,马剑等译,中国地图出版社2013年版,第259页。
[24][英]A·J·立德:《中国五十年见闻录》,桂奋权等译,南京出版社2010年版,第91页。
[25][英]A·J·立德:《中国五十年见闻录》,桂奋权等译,南京出版社2010年版,第93页。
[26][英]密福特:《清末驻京英使信札1865-1866》,温时幸等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30页。
[27][英]John Urry:《游客凝视》,杨慧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2页。
[28][英]John Urry:《游客凝视》,杨慧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29][英]丁乐梅:《徒步穿越中国》,陈易之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第43-44页。
[30][英]丁乐梅:《徒步穿越中国》,陈易之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第67页。
Title:
The British Travelers' Gazing Extension of China Social Space in Late Qing Dynas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