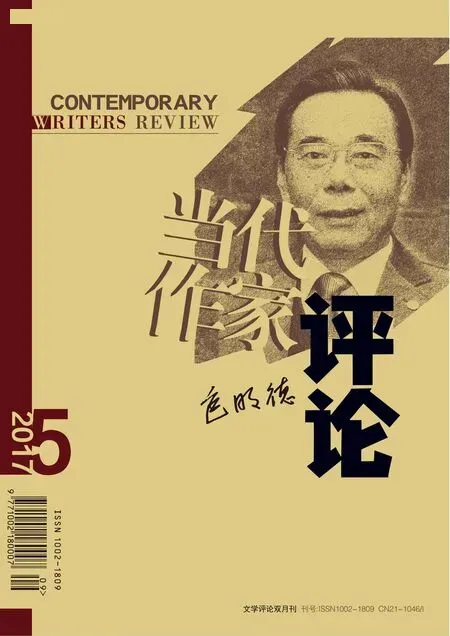“少数民族文学”构造史
李晓峰

少数民族文学
”构造史
李晓峰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虽然一直伴随着各个民族的历史,但直到1949年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立之前,“少数民族文学”并未因其历史的客观存在而生成一种知识,或者作为表述国家文学历史及现象的核心概念被命名和建构。因此,考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构造史,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少数民族文学”的命名及知识等级
1949年9月茅盾撰写的《人民文学》“发刊词”是“第一次文代会”精神在实践层面的具体规划和落实。不仅对新中国文学的性质、新任务、新目标、理论资源、批评范式等做出具体规定。同时在“人民文学”的6项任务和4个要求中,将“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活动”和“国内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列入其中。故此,学者们普遍认为,《人民文学》“发刊词”最早提出了“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这是正确的。因为,尽管1930-1940年代在介绍苏联及其他国家少数民族情况时,就已经出现过“少数民族之经济文化”、“少数民族教育”的概念,如《苏联少数民族地方经济文化的向上》,但并没有出现“少数民族文学”。
但是,《人民文学》“发刊词”在少数民族文学学术史上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命名。“发刊词”第4项任务是: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活动,使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与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形式相结合,各民族间互相交换经验,以促进新中国文学的多方面的发展。
在如何实现这些任务中的第3条“要求给我们专门性的研究或介绍论文”则规定:举类而言,就有中国古代和近代文学,外国文学,中国国内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学,儿童文学等等。对象不论是一派别,一作家,或一作品;民间文学不妨是采辑吴歌或粤讴,儿童文学很可以论述苏联马尔夏克诸家的论理,或博采众言,综合分析而加论断,或述而不作;——总之,都欢迎来罢。
上述“任务”和“要求”,实际上涉及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范式、社会功能、目标任务、学科地位四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使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与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形式相结合”,是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范式的规定。“新民主主义内容”包括文学创作指导思想和作品表现内容两个方面。即,要用“新民主主义”的思想,去反映“新民主主义生活”;“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形式”,指的是各少数民族自己的传统文学形式。也就是说,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基本创作范式,是以新民主主义思想为指导,用少数民族自己的文学形式,去反映少数民族新民主主义生活。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从国家文学的高度,对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做出的统一规范。
从历史发展看,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型为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创作规范转换为各民族文学形式与社会主义内容的结合。而且这一规范与“政治方向的一致性与艺术形式的多样性”的文学总规范相一致,因此成为少数民族文学的核心评论标准。
其次,“各民族间互相交换经验,以促进新中国文学的多方面的发展”,是对少数民族文学功能、目标、任务的规范。强调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学交流与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与新中国文学发展的关系,具有明确的导向性。不但确立了少数民族文学在新中国文学中的地位,而且赋予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更高目标和更重要任务。这些规范,在后来的《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以及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都得到了非常具体的体现。
再次,“发刊词”将“中国国内”“少数民族文学”与 “中国古代和近代文学”“民间文学”“外国文学”“儿童文学”等分支学科并列在一起,在建构了“新中国文学”学科基本体系的同时,也赋予了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平等地位。从中国文学学科史的角度,这是自晚清借鉴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分类原则、标准和体系,设立“中国文学门”后,进行的又一次本土化创造。
复次,“发刊词”还对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层次和知识等级进行了划分。
“中国国内少数民族文学”在“发刊词”中出现一次,“国内各少数民族文学”出现两次,二者无论是学科意义还是知识等级,都不相同。其中,“少数民族文学”作为各民族文学的集合体,成为“新中国文学”下属二级学科;而“各少数民族文学”指的是国内每一个具体民族的文学,如蒙古族文学、藏族文学、朝鲜族文学等。也即是说,“少数民族文学”是高一层级的学科概念;而每一个民族的文学,是“少数民族文学”的次级概念,既我们通常所称的三级学科。这种划分,对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定位、规划、布局以及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及理论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我们知道,现代学科具有多重含义:“其一,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其二,按照学问的性质而划分的门类;其三,学校考试或教学的科目;其四,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发刊词”中的“少数民族文学”至少具备了上述“要义”的三个:1.少数民族文学是“新中国文学”这门科学的分支;2.少数民族文学是关于中国文学这门“学问”中专门研究“少数民族”的文学的具体学术门类;3.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知识体系中次级知识体系。这样,“少数民族文学”在现代学科范畴中就具有了“学科”、“学术”、“知识”三重具着内在联系的属性。
而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基本上沿着上述三个方向发展。如,在学科层面上,“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以独立的学科身份,纳入到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从而在学术队伍、学术研究、人才培养三个方面为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发展奠定了基础。相应的,国民教育体制的学科建制上,“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科之下,又以民族为单位进行了管理体系的建制和专业命名及布局。这就是今天的“蒙古语言文学系”、“维吾尔语言文学系”等。如,中央民族学院自1951年5月开办藏语班,至1950年代末,共开设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90多个民族语文班。这些学员承担了少数民族历史文化情况调查、民间文学收集整理,创制、改进和推行民族文字等多重任务。草创期的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不但云集了国内众多学者,同时也培养了新中国第一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人才,推出了新中国第一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成果;在学术研究层面上,依托学科建制和专业布局,在二级学科层面形成少数民族文学综合研究以及三级学科层面的藏族文学研究、维吾尔族文学研究、哈萨克族文学研究等以族别展开的民族文学研究;在族别文学研究中,又形成了各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古代文学研究、现当代文学研究、文学史研究等不同专业和研究领域,学科体系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在知识层面,国家从“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知识角度,确定了少数民族文学国家知识属性,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学史知识的系统化生产。1958年7月1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座谈会,讨论并决定编写各少数民族文学史。1958年8月15日,中宣部下发《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纪要》。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的意义,正如1960年老舍在《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中所言:“今后编写的包括各民族文学的中国文学史将是多么全面,何等丰富多彩啊!它将的确足以阐明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可见,作为多民族国家知识生产的各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写,从一开始就不是知识分子的个人行为。这也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的重要特征。
所以,如果仅仅认为《人民文学》“发刊词”提出了“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显然是极不全面的。
二、作为“新文学”的“少数民族文学”及其话语规范
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和《人民文学》“发刊词”都指出,“新中国文学”是在“党的领导”和“毛泽东旗帜下”的新文学。对此,1963年《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有更为详细的阐释:“作为这个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的革命的文学事业,它的使命是要在我国建立历史上一种崭新的文学——社会主义文学。这是一种彻底革命的文学,它的产生和发展,一方面要建立自己的崭新的理论,找出自己崭新的道路,在新的理论的指导下,沿着新的道路进行崭新的创造,一方面要与旧的习惯、势力和偏见进行斗争,和一切反动的、落后的思想进行斗争。”“少数民族文学”、“新文学”的性质和地位,也是由 “新中国文学”的性质决定的,因为,少数民族新文学是社会主义新文学的一部分。所以1953年《中国作家协会章程》中明确把“发展各少数民族的文学事业”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任务。1960年老舍在《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中也明确指出:“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每个少数民族的文学事业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祖国整个文学事业的一部分。”1962年《中国当代文学史稿》总结指出:“我国的事业也是各民族的共同事业。各民族的文学艺术都处于平等的地位,同是社会主义文艺不可分割的部分。”
少数民族文学的“新文学”性质,以及在一体化的“祖国整个文学事业”中“不可分割”的地位,意味着少数民族文学必须要遵循一体化的社会主义文学基本规范,即在“崭新的理论”指导下,开辟“崭新的道路”,进行区别于“旧文学”的“崭新的创造”。然而,正如《人民文学》“发刊词”对“少数民族新文学”进行的规范中所暗示的那样,“少数民族新文学”在推动中国文学整体发展之外,还负有自己的特殊使命和责任。这种特殊使命和责任,规范了“少数民族文学”构造方向,决定了少数民族文学的话语范式。
1953年周扬在第二次文代会的报告中,将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作品,称为“标志了国内各少数民族文学的新的发展”。老舍也多次用“新文学的兴起”、“新的文学也生长起来”、 “已经有了新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 “我国各少数民族中都出现了崭新的社会主义文学”来概括少数民族文学。1959年,《文艺报》也称 “许多兄弟民族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新文学”,“我们也把曾经是‘一穷二白’的兄弟民族文学领域改造成万紫千红、争妍斗丽的大花园。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现象”。《中国当代文学史稿》也称少数民族“初步地建立了自己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学。”
那么,受到一致肯定的少数民族“新文学”究竟“新”在哪里?
1952年1月,玛拉沁夫发表的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被评价为“写了新的主题、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先进的力量,用新的伦理和新的道德精神教育人民”的“新型文学”。
这里的五个“新”代表了对少数民族“新文学”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评价标准,但并不是全部。我们注意到,本时期对少数民族“新文学”的“新”,有如下评价标准:“以国内各民族兄弟友爱的精神,创造了少数民族人民中先进分子的形象,真实地描写了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的新旧光景”,“这种新文学一开始就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下,遵循着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进行创作的。许多新起的优秀作者一开始拿笔,就是以社会主义文学的建设者自期的。这些青年花朵是在党的雨露滋养下开花结果的”,“在加强民族团结,在提高人民政治觉悟与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上,在促进各民族文化的繁荣上,这些新文学也都发生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充分地证明了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与文艺政策的正确性”,等等。
这些正面评价标准涉及思想与内容两个方面:一是赞美新生活、展现新面貌、塑造新人物、表现新思想、传达新情感;二是歌颂党的领导和党的领袖、歌颂社会主义给少数民族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宣传党的民族平等政策、歌颂民族团结。
但是,这并不是说少数民族文学只要在思想倾向和作品内容符合这两个规范,就能获得如此评价。如,《人民文学》在发表《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同期,发表了哈萨克族布卡拉的哈译汉诗歌《复仇的姑娘》,以及苗族永英的诗歌《我们是一群苗家》,但这两首属于“少数民族新文学”的诗歌,并未收获一个“新”字,原因何在?《复仇的姑娘》写了一位正要奔赴朝鲜战场的美丽姑娘的身影;《我们是一群苗家》写了苗族对毛主席的感激和对民族大家庭的歌颂。这显然都符合社会主义新文学思想内容的规范。但仔细阅读便会发现,前者“复仇”的原因并未揭示,“身影”不免模糊;后者的感情十分真挚,但直白的歌颂,了无诗意,民族特征更是了无踪迹,在形式上也没有做到“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与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形式相结合”。这与《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完全不同。《科尔沁草原的人们》除思想内容上的五“新”外,还具有浓郁的民族气息,如鲜明的民族性格,独特的草原风光和蒙古族民俗,特别是蒙语和蒙古族民歌的嵌入,使这篇小说将本民族传统文学形式嵌入到小说这种非本民族固有文学形式之中,从而为“新中国文学”增添了特别风景。
这说明,少数民族新文学的评价标准,除了思想内容的“新”外,还有文学之为文学的特定要求和规范。这种规范使“政治倾向的一致性与艺术风格的多样性的统一”变得更为具体。于是,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与中国传统诗学以及各民族艺术形式,便获得了合法性和阐释权力。
然而,周扬、老舍等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正面评价,并不代表此时期少数民族新文学已经完美无缺。正如老舍指出的:“是不是我们对各族人民的新生活已经反映得极为有力了呢?对各民族的阶级斗争已表现得极为深刻了呢?严格地说,还不能够有力,还不能够深刻!而且有些作品无论在思想内容或艺术形式上都还存在着一些缺陷。少数民族作家还应当要求自己层楼更上,更有力、更深刻、更多更好地反映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反映阶级斗争,反映各民族在建设与斗争中的团结与协作!”这说明,在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两个方面,少数民族文学都存在一些问题。《复仇的姑娘》《我们是一群苗家》的问题不在思想内容上,而在艺术形式上。再如,国家为保证少数民族文学发展设置的两条“高压线”——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时有触碰,如《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对维吾尔族穆汉买提翟宜地、孜亚萨买提地方民族主义的批判,对钟敬文大汉族主义的批判。因为,这两种民族主义直接影响到“各民族艺术都处于平等的地位”以及 “各民族间互相交换经验,以促进新中国文学的多方面的发展”的国家规范,也涉及少数民族民间文学遗产“批判继承”和“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原则能否正常执行的问题。
但是,无论是对少数民族新文学的肯定,还是对存在的问题的批评,甚至批判,其目标只有一个,即:少数民族文学,必须要构造成社会主义的少数民族文学。
三、 “兄弟民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交错并置
尽管《人民文学》“发刊词”提出了“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并确立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学科地位,但是,少数民族文学无论作为“新文学”还是新学科,自身发展都需要时间与过程。因此,在1950至1960年间,虽然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思考已经在如何界定少数民族文学的标准上深度展开,如,何其芳认为,“判断作品所属民族一般只能以作者的民族成分为依据……不以作者的民族成分为标准,再另外订立一些标准,恐怕都是不科学的,其结果是许多民族的文学史对于作家和作品的讲述都会发生混乱和重复”。但是,在当时,并没有人对 “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科学性以及使用的规范性进行讨论、规范和统一。相反却出现了“少数民族文学”、“国内各民族文学”、“兄弟民族文学”、“各兄弟民族文学”、“各民族文学”、“各少数民族文学”,甚至“多民族的文学”等在不同语境同时使用,或内涵相同但表述有异,或表述相同但内涵多有差异的“概念混杂”情形。
其中,“少数民族文学”在国家文学话语权力层面,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领域较多使用。如1953《中国作家协会章程》提出的“发展各少数民族的文学事业”、1958年中宣部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的指示以及座谈会、老舍在1960年中国作协第三次理事(扩大)会议所作的《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1961年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的《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编写计划(草案)》,以及中宣部召开的关于各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讨论会的议题中,都使用这一概念。相应的,在周扬、徐平羽、何其芳等具有国家权力话语性质的“讲话”中,也都比较一致和规范地使用“少数民族文学”或“各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个别学者如费孝通1951年的《发展为少数民族服务的文艺》、张寿康的《论研究少数民族文艺的方向》、徐祖文1956年的《发展中的少数民族文学艺术事业》等,也都使用少数民族文艺或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与此同时,“兄弟民族文学”或“兄弟民族文艺”不仅同时使用,而且频次远远超过“少数民族文学”。
如1956年老舍的《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1960年贾芝的《祝贺兄弟民族文学史的诞生》,1957年何许的《“各族通用”——两本兄弟民族情歌集读后》,1959年袁勃的《让兄弟民族文艺更加繁荣——云南兄弟民族文艺简介》,《人民日报》的《兄弟民族的诗风歌雨——舒舍予代表的发言》、郭光的《建国十年来的兄弟民族文学》,昌仪的《兄弟民族文学的巨大成就》《文艺报》的《突飞猛进中的兄弟民族文学》等。特别是在最早的三部中国当代文学史——山东大学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编写组1959年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1949-1959)》、1962年华中师范学院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以下简称《史稿》)、1963年《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中,在具体论述中都使用了“兄弟民族文学”、“各兄弟民族文学”的概念。
这种概念混杂且“少数民族文学”的规范化表述被“兄弟民族”替代的原因有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与新中国成立后在整个国家语境中普遍将汉族之外的少数民族称为“兄弟民族”的国家“流行语”有关。如,仅1951年语言文化方面,见诸报端的就有李志纯的《开展西南兄弟民族的文化教育》、马学良的《帝国主义怎样摧残我兄弟民族的文化》、喻世长的《参加中央西南访问团调查贵州兄弟民族语言的工作报告》、蔡美彪的《内蒙呼伦贝尔地带各兄弟民族语言概况》等。这说明,在将少数民族称为兄弟民族已经成为一种语言习惯的语境中,将少数民族文学称为“兄弟民族文学”或“各兄弟民族文学”是一种特定时代的特定语言习惯。
其次,将少数民族统称为“兄弟民族”也是国家在各民族平等的法律规定基础上,表达认同情感及平等关系情感化的政治话语,其中折射出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也就是说,虽然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整体语境中,将汉族之外的少数民族称为“兄弟”民族,是空前的历史性进步,但“兄弟”这种强调却也指认了各少数民族“非兄弟”的被歧视的历史。因此,在“多民族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兄弟”民族无疑包含着国家对这一历史的理性反思和对少数民族地位和价值的重建。前者已经体现在《宪法》中以民族平等为核心理念的法律规约中,后者则体现在对各少数民族“兄弟”感情的重新建构上。所以,这里的“兄弟”,既非“男子先生为兄,后生为弚”的长幼次序,也非“同姓宗族”之宗族关系,而是在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家庭”这一家国同构传统观念下,对曾为“夷、狄、戎、蛮”等四方之异族的少数民族平等关系重构的情感化修辞。而如果进一步辨析,这种修辞,仍清晰可见大汉族主义以及“中原中心”居高临下的等级观念的投影。如果从多民族国家的成长历史来看,对少数民族的“兄弟”关系的认同建构,也是少数民族对汉族“兄弟”情感的认同建构,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多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基础。
应该指出,从学术规范上说,在少数民族文学概念已经提出的情况下,将情感修辞的“兄弟民族”延伸到少数民族文学范畴,用“兄弟民族文学”置换“少数民族文学”,或者二者混用,既不严谨,也不科学。但是,我们既要体察国家用“兄弟”这一修辞的良苦用心,也要认识这一概念所折射出来的正处于构造之中的少数民族文学的特定时代特征。因此,不能夸大“兄弟民族”的情感修辞功能,也不能不注意“兄弟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同义。
例如,《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在介绍少数民族文学的成绩时,“少数民族文学”、“兄弟文学民族”、“少数民族作家”同时使用,但其内涵却一样。华中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绪论”第六部分题为“多民族的文学”,但在具体论述时却又使用了“兄弟民族文学”一词。这种混杂和交叉的情形,反映了研究者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学科严谨性与表述情感化之间的立足点的漂移。即,一方面意识到自己的话语是文学史的学术话语,另一方面又要刻意表达对少数民族的“兄弟”感情。
但是,从学术观念和学科发展的角度,本时期,在“少数民族文学”、“国内各民族文学”、“兄弟民族文学”、“各兄弟民族文学”交叉混杂的语境中,有一种逐步规范化的走向,即,由情感修辞向规范化的学科和学术话语逐步迈进。如1956年老舍在《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中使用了“兄弟民族文学”一词,而1960年的《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则使用了“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再如,贾芝1960年的《祝贺各兄弟民族文学史的诞生》与1964年的《谈解放后采录少数民族口头文学的工作》,其概念的使用也出现了变化。
但是,不能因此将这种变化简单理解为一种线性的进化过程。从大的语境来说,当各少数民族完成社会形态和社会意识的根本转变,当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认同建构起来,特别是当少数民族的主体地位的稳固和平等身份诉求不再有危机和焦虑,或者说,当“兄弟”关系不再需要特别强调的情况下,“兄弟民族”的情感修辞功能便会衰竭,“少数民族文学”这一国家学术话语的主线就会浮现出来。而当特定社会政治文化语境中需要强调“兄弟”的情感和平等关系时,“兄弟民族文学”仍然会隆重登场。
例如,1959年“建国十周年庆典”语境中,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包括文学)取得的成就以及一体化程度,无疑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成立十周年必须要全面总结的。于是我们发现,正是 “建国十周年庆典”这一特定语境,“兄弟民族”的使用频率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峰值。而 1959年开始组织编写,直到1962年和1963年才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和《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也不约而同使用了 “兄弟民族文学”。因此,认为老舍《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标志着“少数民族文学”完全取代“兄弟民族文学”,是将历史线性化的简单判断。实际上,“兄弟民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交错混杂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末。
1979年,以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程的重新启动为标志,《光明日报》发表《要重视少数民族文学》一文,不仅开启了摆脱极端政治束缚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新纪元,也标志着作为国家知识、学科和学术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不同表述,真正统一到科学、规范的学术话语上来,作为用来指称汉族之外的中国其他民族文学的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才终于完成了核心概念的构造历程并进入到新的发展时期。其重要标志是:1979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的成立;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建立;1983年《民族文学研究》的创刊;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少数民族文学系的成立和获得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硕士学位授权;1983年中央民族学院“藏缅语族”语言文学博士点的诞生。
四、“少数民族文学”构造镜像的“多民族文学”
没有少数民族,就没有多民族国家;没有多民族国家,就没有少数民族。将这一历史逻辑的推演,移置到文学,便生成了具有高度耦合性的没有“多民族文学”就没有“少数民族文学”,或“没有少数民族文学”就“没有多民族文学”。
因此,本时期在诸种混杂交叉的概念中的“多民族文学”的提出及应用,是“多民族国家”内生性的国家知识概念,它成为“少数民族文学”构造过程的镜像或控制耦合(Control Coupling),二者都以“多民族国家”为基点,共同描述了多民族国家的文学结构形态及组成关系,包括整体与局部的关系、部分与部分的关系,并且能指和所指可以互相换位,在场与不在场相互提示和指认。
具体而言,多民族文学是多民族国家中,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学共同构成的整体,强调的是每一个民族文学在国家文学中的主体性和整体性,包括历史上存在过的民族创造的文学。少数民族文学是指多民族文学共同体中,主体民族(汉族)文学之外的其他被命名为少数民族的民族所创造的全部文学。多民族文学,意味着多民族国家全体民族文学同时在场,且地位、身份平等;少数民族文学只在多民族国家文学中作为特定的表述对象时使用,但并不意味着汉族文学不在场。因为,在多民族国家中,如果没有人口“多数”的主体民族,就不会有人口“少数”但同样具有平等的主体地位的非主体民族——少数民族。所以,作为少数民族文学构造镜像的多民族文学,时刻提示着人们对少数民族文学在国家文学中的地位的认识以及少数民族文学的自我定位——少数民族文学是多民族国家中多民族文学中的少数民族文学。这也正是在少数民族文学构造的过程中,当谈到少数民族文学地位和意义时,总会谈及多民族国家和多民族文学的原因。
如,1951年费孝通从多民族国家“大家庭”的角度提出发展少数民族文艺的重要性。同年,张寿康指出:“少数民族的文艺,是中国文艺中不可少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谁要是把少数民族的文艺推在中国文艺的大门之外,那他就是否认祖国伟大现实的人”。“中国文学不仅仅是汉文的文学——这是全中华的文学”。“以汉族为主并不等于没有汉族之外的其他民族,以汉族文学为主流并不等于不要其他民族的文学。”1955年玛拉沁夫在给中国作家协会的信中,对这一问题做了进一步论述。 玛拉沁夫指出:“我国和苏联一样,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我国的文学也应当是、一定是中国各民族的文学”,“我国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国家,作家协会也当然是以汉族作家为主的,然而又因为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所以作家协会也必然是各民族作家的统一组织”。这里的“各民族文学”是包含了汉族文学在内的“各民族文学”——多民族文学。而且,明确指出了“各民族文学”的基础和前提是“多民族国家”。也就是说,费孝通、张寿康和玛拉沁夫都是从“多民族的国家”的角度,注意到了多民族文学。
正因如此,1955年3月,中国作家协会在给玛拉沁夫的“回信”中称“你对我国多民族的文学工作的意见,是正确的”。这里的“多民族的文学”回应的是玛拉沁夫在信中两次提到的“多民族国家”,以及对玛拉沁夫“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文学”的概括。
“多民族文学”也出现在1956年老舍《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中,在批判大汉族主义“对兄弟民族文学工作未能给予应有的注意”时文章指出,“在文艺战线上,多民族的文艺这一概念似乎还未形成”,显然,大汉族主义排斥的是少数民族文学,由此造成了汉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之间的割据,这种割据显然是对多民族文学共同体的分解,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背道而驰。
我们发现,在少数民族文学构造史上,“多民族文学”意识的增强与“少数民族文学”构造的逐渐成熟同步。如1959年邵荃麟在《文学十年历程》中指出:“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许多兄弟民族都有其自己的文化传统,但在过去反动阶级的大汉族主义统治下,各兄弟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是没有平等地位的,因而在文学上也是没有平等地位的。过去一些汉人所著的文学史中就没有兄弟民族文学的篇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彻底废除了我国历史上民族压迫制度,各民族进入了平等、团结合作的新时代,成为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在文学上也第一次出现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与繁荣。”在这里,他的“兄弟民族文学”指的是少数民族文学,而“多民族文学”则与老舍一样,是指包括汉族在内的多民族国家的多民族文学。1961年,何其芳在谈到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意义时也指出:“直到现在为止,所有的中国文学史都实际不过是中国汉语文学史,不过是汉族文学再加上一部分少数民族作家用汉文写出的文学的历史。这就是说,都是名实不完全相符的,都是不能此较完全地反映我国多民族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发展的情况的。”这里,何其芳的“多民族的文学”也是直接对应“多民族国家”的“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所构成的多民族的文学共同体。再如,达翰尔族作家、理论家孟和博彦在《发展多民族的文学 加强民族文学交流》中,也根据内蒙古文学发展现状指出:内蒙古的文学是“蒙古族,包括汉、满、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各个兄弟民族共同发展的多民族的文学”。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诗集《我握着毛主席的手(兄弟民族作家诗歌合集)》“出版说明”开篇即说:“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十年来,各兄弟民族的文学由于民族得到了解放,由于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照耀,都获得了新的生命,在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和繁荣的宏伟局面。”虽然是没有汉族诗歌在场的“兄弟民族”诗歌的合集,但“多民族国家”意识却指认了汉族诗歌的在场。1960年老舍在《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中,也明确地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角度提出了“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学”,他指出:“汉族文学是我们多民族文学的主体”,“群众文学创作(指各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笔者注)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对建设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学,有重大的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史料在使用“多民族的文学”的同时,也使用了“少数民族文学”或“兄弟民族文学”这一概念。而且,“多民族文学”是在“多民族国家”的前提下使用的。这样,不仅区分了“多民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或“兄弟民族文学”的层次,同时也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邵荃麟、孟和博彦等人的“共同发展”的“多民族的文学”,也是《人民文学》“发刊词”中早已确定的“新中国文学”的发展目标——通过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活动,促进新中国文学的发展。这即是说,没有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就谈不上“新中国文学”的发展,这正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直接推动力。因为,共同发展的多民族的文学,也是多民族国家政治、文化乃至国家意识形态整体规划与建构的诉求。从这一意义上说,作为“少数民族文学”构造镜像的 “共同发展”的“多民族的文学”,是这时期中国文学最前沿、最具现代性的文学话语,它实质性地将少数民族文学提升到国家文学的高度,并且揭示了中国文学的多民族属性。
从“少数民族文学”构造的学术史角度,多民族国家——多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兄弟民族文学),这样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三个词组的排列,揭示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中国话语”产生的历史语境和基本内涵。“少数民族文学”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民族文学”的标识性话语,“少数民族文学”构造的完成,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民族文学”“共同发展”时代到来的标志。至于“多民族文学”潜蕴着的巨大的整体性文学观念变革能量,也成为推动少数民族文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一点,已经在60年后(2007年以来)的关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讨论中得到证明。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史(1949-2009)”(项目编号:13amp;ZD121)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少数民族重大理论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50208)阶段成果〕
李晓峰,吉林大学文学院;大连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李桂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