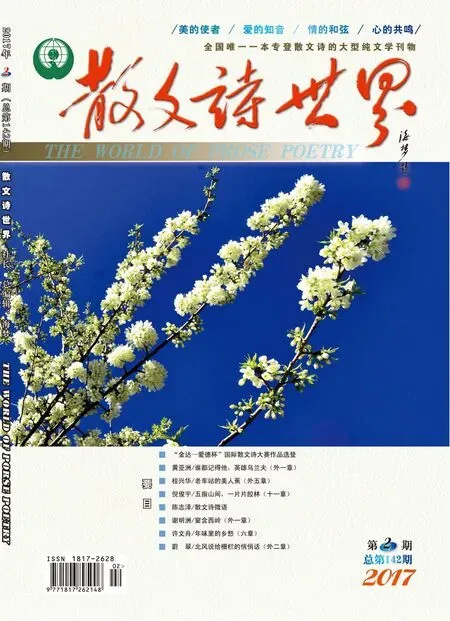辽河口(外二章)
辽宁 文 景
辽河口(外二章)
辽宁 文 景
辽河在这里入海。
魏碑体红得发紫的三个亮眼大字,咔咔咔刻在一块几米高的巨石之上,是名人,还是人名?拔地凛凛威风!
一只海鸥叫响这条拐了三道弯儿的辽河尾部,顺势展翅,猛地,扑向大海,它只管扇动它那银灰色翅膀,没有读到也不会留意那块巨石,以及那块巨石上的响当当署名,或是签名。
辽河口的口,谁能说得清它的界线到底在哪儿?
有谁能准确地画出一条线,说这条线的这一边是辽河,另一边就是大海,这一朵浪花是属于大海,那一朵浪花是属于辽河?——浪花共融共生共荣。这么想来,辽河口也可以叫做河海口。一个混血儿。
混血儿是开放的产物,据说聪明。也可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天才。
走近大海,天下所有的事物都会感到自己的矮小渺小,自惭形秽,
此时,你可以看到,亮亮闪闪的辽河,立马变得谦虚平和起来。
自己奔突1430多公里日思夜想的目标已近在眼前,毫不犹豫,刹那间全都溶了进去,连同刻在巨石上的想要不朽的地标姓名和拔地威风。其前方,远方,你已找不到它的形体,却分明能感受到,它和大海一样无始无终自强不息的灵魂。
重登西炮台
一步一个台阶,累得你呼哧呼哧大口喘气,才能一步步靠近它,登上它。
一面向海。由黏黏的黄土糯米牢牢地团结起来筑成。
墩墩实实的一个大块头,卧在那里,高高的,四周的一切都在它的眼皮底下。
以封闭的土办法,去抵御开放的洋办法。霸气十足。
身上还有一个个洞,那些个洞的眼睛,洞的魂灵,
死死地盯向滩涂大海,一排排青面獠牙的浪涛扑过来,滩涂上鱼鳖虾蟹呜哇乱叫。
一颗颗头颅燃烧,惨叫,血的河,一起喷溅苍天。
一声吆喝,吊桥平稳地落下,荡悠悠桥身洒下一串嬉闹的银铃声。
护城河摇啊摇,摇碎了沿岸的芦花,摇碎了玫瑰,腥味苦味连同自由的鱼儿倏地远去。
旧式兵营里好像有人在上课,人影枪影炮影晃动。
忽地,有一群海鸥惊起,在湿地半空上下盘旋,
一群红领巾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上来,一个个手机频频仰视,拍照。
或许,未来将是用一块小小芯片指挥一场不分国界不分前方后方的铺天盖地的海陆空战争。
金牛山遗址
一个小小的山包,上面不过有一两棵树,几丛野草。
普通得过目即忘。如果放在连绵群山的浪涛里,如一滴水没入了大海。
有仙则名。那仙——
十几万年前就深藏在它的底层,头骨脊椎骨坚硬,牙齿咯嘣咯嘣响,
上世纪八十年代被考古掘出。一群在此逝去的先人有望复苏,重演历史。
非意志的小小山包刹那间名声大震。
我开始想象,在这里十几万年前生活过的人类,
风餐露宿。石刀石斧长矛,打猎采矿。
肯定没有见过别墅,轿车,席梦思,彩电,微波炉,冰箱,洗衣机,手机,地铁,高铁,大炮,飞机,航天器,导弹,宇宙飞船;洗头房,歌舞厅;地球一家人;信息化战争……
肯定没有见过神仙,不曾以至现在也无法见到赫赫功名,煌煌金银……
单纯、干净勤劳的金牛山人——我们的祖先。
我不愿意看到,后人会从灰烬里引出假丑恶的佐证,侃侃清谈,
让早已死去成灰的先人,燃出不伦不类的命题和名声。
我在想,人是自然物质,一定会顺应自己本身的运动规律运动,
运动永恒,人类和自然今后到底会繁衍成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