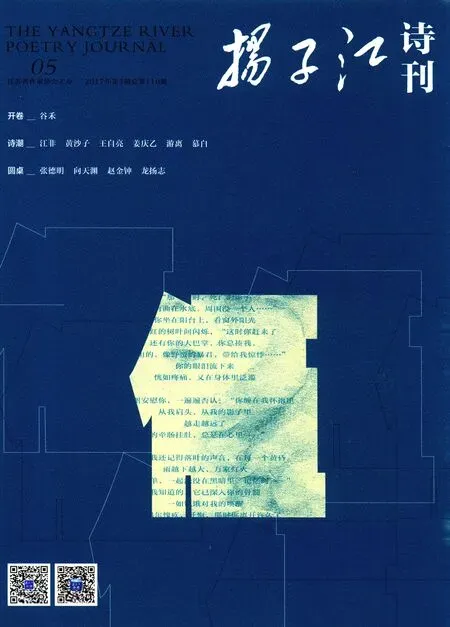黄沙子的诗
黄沙子
黄沙子的诗
黄沙子
饮水注
向茶杯里注入滚烫的水,在黑暗中
你无法准确感知何时该当结束。
即便一生中你曾无数次
将一杯水倒得恰到好处,
谁又能保证这一次仍是如此。
奇迹不可能总是发生。每活过一天
你的技艺就更加纯熟一点,
每活过或卑微、或无所顾忌的一天
就是将死神的外衣脱下一件。
狗也深知这个道理,
只要打开门,它就会咬着绳子,
请求我带它出去溜达一圈,
我们沿着沙湖散步或者奔跑,
那并排行走的两个灵魂
如此相像、高大又孤单。
一生该当如何度过我从未找到答案,
但我知道欢欣有多少
痛苦就与之等同:不会更多
也不会更少。黑暗中我凭借经验
向茶杯里注入滚烫的水,这小小的容器
承接着人类的一切伟大梦想,
即使满溢出来,也终有倒完之时。
渡 船
用作渡船的是一艘水泥做成的船,
它的好处是不必担心腐烂。
乘坐渡船的人其实可以绕远路,
从河流的浅处涉水,
但我们忙着赶往对岸,
忘记了沉重的肉身可能会
加剧水泥的下降速度。
如果一艘船提供的浮力
与它承受的压力不相称会怎样?
易于腐烂的事物可能飞得更高,
正如跑调的嗓音唱出更大声的歌曲。
我们旁若无人地谈起
过去很久的事并且赞美它们,
直到憎恨的光深入骨髓。
谁也不知道一艘船到底要
载走多少人过河才会坍塌,
渡河的人中谁会成为受害者,
成为那最后的一个。
也许一群人走亲戚回来,
会满足深水对于灾难的渴求,
这样一艘水泥的渡船
波涛也只能让它轻微晃动,
在我们到达对岸之前
它已经抵消了一部分向上的力。
有用之物
从一片低洼地里
我们把腐烂的棺木拖出来,
里面还有一些骨殖被泥土和水
侵蚀得几乎无法认清。
但有人记得那是我们的
一个前辈,仔细论起来
其实相隔并不算太远。
坚硬的头盖骨现在只需要
轻轻一捻就变成细末,
因为潮湿它们发出沉闷的呲呲声。
我们起出了所有看起来
是埋下而非本来就在这里的事物,
一连几天田野上到处
都是做着同样事情的人。
越来越多的雨水落在平原,
让原本高昂的地势显得有些低沉,
还算结实的棺木被挖出来后
有很多其他的用途,
比如铺在水井边,河滩上,
让打水的人不至于陷进淤泥中。
祖父六十岁以后再也没有下田耕作,
但他记得哪一块土地里
埋着哪一个人,因而在他的指引下
我们准确地找到很多有用之物。
吞 食
我曾以为人世
仅仅由活着的人构成,但空气中
还有更多死去的和未曾降生的。
我喜欢爬到视野辽阔的砖瓦窑顶远眺,
让视线越过白雪覆盖的稻田和河流的源头,
或是望向近处的炊烟,
依据风吹过的声音来判断
哪些地方仍有活着的人在劳作,
哪些则已被深埋泥土中。
一些鸟雀停歇于没有树叶的枝头,
它们比我更容易感知春天,在春天
我们从一切可以吞食的物质里
采集养分以资度过时日,
包括从别处飞来的鸟
它们的粪便中那些未曾
消化的青草,带着湿气的风。
我知道它们从远处运来了水,
将早已过去的日子又过了一次。
傻 瓜
一场巨大的变故之后我在人群中
感觉自己被遗弃。
大街上黑衣人比白衣人多,
不知道是否因为夏天到了,
法国梧桐停止飘落飞絮。
商场门口渗出的冷气像是穿进
我的肺让我一阵咳嗽,
一个推着婴儿车的女人走过来,
她过于年轻,根本不像母亲。
她毫不费力地推动车子的样子,
像是里面根本没有婴儿。
她微微仰起头,似乎头顶有人在对她说话,
脸上带着掠鸟回巢的笑容,
阳光让她的牙齿温暖,
白色的连衣裙散发出利箭一般的光芒。
她拒绝了我伸出的手,
我觉得自己像个傻瓜一样地哭了。
甲 虫
在红螺寺有人发现
路上的两只漂亮甲虫,
其中一只已经被踩死,
看起来就像落在地面的
陨石的颗粒,带着陌生的光。
活着的那只正在向草丛爬去,
它似乎忘记了自己会飞,也忘记了
给同伴收拾残骸,哪怕是
短暂的凭吊也没有。
我们蹲下来用树枝帮助它前进,
它显得更加慌张,
一个劲地在那里转圈。
我们只好后退,一直退到以为它
不可能看到我们的地方。
它终于停止爬行,站立片刻后
打开翅膀飞走了,我想正是这认真的站立
让它找到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仿佛一个人在经历恐惧、他人的死亡之后
总是会陷入沉思,
但还是会孤身去往远方。
灯火从不曾熄灭
当黄昏用轻薄的纱雾将我们笼罩,
船头就会挂上一盏马灯。
即使随后的满天星光将人世
照得亮如白昼,灯火
也从不曾熄灭。
我也曾试着在陆地上短暂生活,
坐在树旁,身下的泥土坚实,
青草肆无忌惮到处都是,
草丛里的昆虫,空中飞过的盐老鼠,
门窗关上时的吱呀声,
让我无法分辨到底哪一种梦境
更能还原生活本身。湖水无根无依,
一个人的世界无亲无故,
在这里,只有轻轻晃动的树影
和我的影子重叠,
让我得以安然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