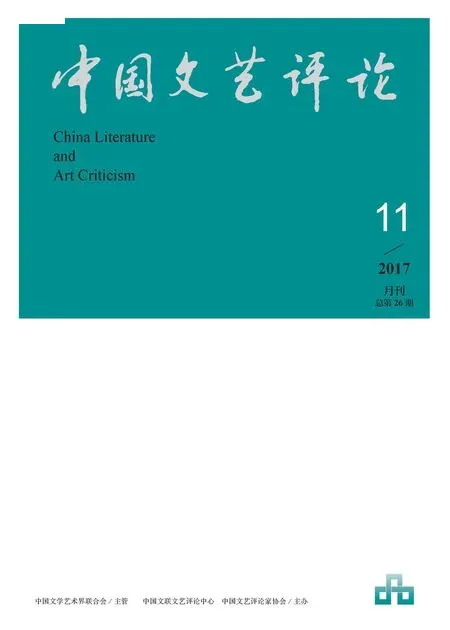香港文学的“在地抒情”传统
蔡益怀
香港文学的“在地抒情”传统
蔡益怀
香港文学的“在地抒情”是以香港的眼光审视香港事象与社会人生,以香港的话语说香港故事的书写特色,充分展示了香港文学的独特风貌。在当代的香港文学作品中,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诗歌,都不乏在地书写、在地抒怀的佳构。通过作品,我们可以看到香港的创作人,有相当自觉的“在地关爱”意识,且形成了从生活出发这种“在地抒情”的传统。
在地抒情 本土 在地关爱 文学
香港文学是一个很难说得清楚的话题,大范围的泛泛而谈,容易失之笼统,没有多大意义。所以,我今天打算把话题收得窄一点,仅从个别方面来说说我所了解或观察到的现象,这就是香港文学的“在地抒情”传统。
这些年来,关于“本土性”“本土化”的讨论,是香港社会乃至香港文学的热点议题。在时下的香港,“本土”几乎成了一种政治正确的代名词,非本土则是非我族类的“他者”“外来者”,必须加以抵制、排斥。“本土”二字蕴涵了本地优先、拒绝国族主义的迷失,当这个概念运用在文学范畴,似乎也超越了文学本身,而染上意识形态的色彩,有唯“我”独尊之势,以至于出现拒绝收编的论调;“本土”似乎也成了文学判断的首要标准,是一面矗立在道德高地的大旗。鉴于本土论述已出现变调,我今天想换一个角度来讨论香港文学,并表达自己的一点不同思考。我认为,我们在讨论文学的本土议题时,有时候其实混淆了“本土”与“在地”的概念,而堕入到一种政治语境中,或者说将一些单纯的文学问题政治化了,以至于忽略了文学本身的讨论。在我看来,我们在文学上要讨论的焦点与其说是“本土”,不如说是“在地”。所以,我今天是从“在地书写”的角度来讨论香港文学的地方特色与人文关怀。
当代著名的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曾提出“恋地情结”(Topophilia:love of place,又译为“在地关爱”)的学说,来说明人对于环境的一种天然的依恋感。在段义孚看来,人对于环境有两种基本的情感,一种是“爱”,一种是“怕”。“恋地情结”让人跟一个地方产生情感联系,如触觉上的快乐以及难以言喻的归属感。这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大致表现为一种“在地抒情”,即对于一个地方的记忆、想象、认同,对故乡、家园的深情回顾与歌咏,强调的是一种“地方感”“地方精神”。从这个维度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香港文学从来不乏在地的书写,而且形成了一种“在地抒情”的传统。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香港新诗中就有不少直接取材于香港都市风景的作品,如李育中的《维多利亚市北角》:“蔚蓝的水 / 比天上的色更深更厚 / 倒像是一幅铺阔的大毛毯 / 那毛毯上绣出鳞鳞纹迹 / 没有船出港 / 那上面遂空着没有花开 / 天呢却留回几朵 / 撕剩了的棉絮 / 好像也旧了不十分白 / 对岸的山秃得怕人 / 这老翁仿佛一出世就没有青发似的 / 峥嵘的北角半山腰的翠青色 / 就比过路的电车不同 / 每个工人驾御的小车 / 小轨道滑走也吃力 / 雄伟的马达吼得不停 / 要辗碎一切似的 / 把煤烟石屑溃散开去 / 十一月的晴空下那么好 / 游泳棚却早已凋残了”,这首诗为后人留下了早期香港一角开发时期的风貌。再如,鸥外鸥的《和平的础石》《狭窄的研究》,陈残云的《海滨散曲十章》,黄雨的《萧顿球场的黄昏》《上海街》等,也都直接书写香港都市风情,发出了那个时代的感叹。
在香港的文学版图上,侣伦、黄谷柳、舒巷城、西西、也斯、李碧华、董启章等,都留下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文字,表现了一种“居于斯爱于斯”的文化情怀,沿续了一种“在地抒情”的传统。比如,舒巷城的名作《鲤鱼门的雾》《太阳下山了》,都是具有相当代表性的作品。《太阳下山了》为读者描绘出西湾河风情,古老街市附近的牛腩粉档、艇仔粥档、咖啡红茶档……月光下,泰南街的夜市,卖武的、讲古的档口……无不历历如绘、撩人神思,无疑都是当年香江风物与市井风情的传神写生。最难得的是,在舒巷城笔下有着一种浓郁的原乡情怀,即对故园的“不了情”,对已逝去的“埠头”的深深怀缅。让我们来看一段文字吧——“这时太阳早已下山了。月亮从鲤鱼门海峡上升起。档口上的火油灯、大光灯和月亮的光溶成一片。不远处,泰南街街尾那根灯下有几个孩子在‘跨背跳’。一个扇着葵扇的妇人坐在矮凳子上跟她的男人吵架。男人站起来,忽然转身走了,很快地就消失在沙地上黑压压的人丛里面。热闹的沙地,由于穿着木屐的孩子们在档口和档口之间穿来插去,时而响起一阵踢跶踢跶的声音。”这就是舒巷城笔下的西湾河风情,作者是带着美好的回忆,以饱含深情的心灵之光透视故土,因而笔下的一景一物都带着情感的氤氲,这不啻是旧时岁月的怀缅曲、咏叹调。可以这样说,舒巷城是上世纪中下叶香港“在地抒情”独树一帜的代表,值得读者与文学研究者重视。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他们所生活的地方就是其创作的应许之地,写作的根只有深植于足下的土地,才可能枝繁叶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香港文学的“在地抒情”更为出彩,如西西的《我城》、李碧华的《胭脂扣》都是出色的代表性作品。《我城》以“童心”看香港,透过阿果、阿发、阿北、麦快乐等人物的眼去审视观照这座“我们的城”,描绘出70年代香港的都市风情,如同时代浮世绘、城市寓言。李碧华的《胭脂扣》讲述一个30年代的塘西名妓到阳间寻找旧情人的故事,作品借主角如花的眼来看80年代的香港,用香港本身的角度“回望”当前、“回望”历史。如花的追寻,正是一次追寻原乡之旅,饱蕴浓厚的香港情怀。日本学者藤井省三对此有精警的评述:“小说以风俗为中心,把30年代的记忆巨细无遗地重现出来……这部小说并非重演‘传统的爱情故事’,香港意识的创造这个‘变奏’方是主题。” 李碧华的《胭脂扣》引发出一股怀旧风潮,一时间“塘西文类”蔚为大观,海辛的《塘西三代名花》、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董启章的《地图集》等,纷纷以港人的本土意识去追缅过去、书写历史,重现香港的历史画卷,重绘历史的“地图”。
当然,香港作家的想象并非只限于历史的重述,文化身份的追寻是回归前后香港文学的另一个母题,可以说,对身份、对故园、对“家乡”(以香港为家)的追寻构成了港式的“寻根文学”。如马国明的《荃湾的童年》,透过荃湾的变迁,透视香港的社会嬗变,并反思不同层面的社会问题,作品中发出了“我在何方”的疑问:“今日德声小学和搪瓷厂都已经在荃湾的地图里消失了,就如中国染厂和曹公潭的清溪一样。荃湾也早已不存在一块小童追逐时,尘土飞扬的空地……当身边周围熟悉的景物都改变了,你不得不问:‘我在何方?’”这正是香港作家地方情怀的一个体现。
事实上,在当代的香港文学作品中,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诗歌,都不乏在地书写、在地抒怀的佳构,比如诗人刘伟成的《上环正街》,对街坊生活作了平民化的书写,整首诗透过个人的观察刻写市民的日常生活景况,并以电车的意象作结,对城市的变化作出引人深思的暗示:“斜度稍缓,尽头是电车的路轨 / 给车轮磨得光亮,叮叮,叮叮的 / 带着整街海味的羶臊 /伸向城市善忘的心脏。”对于日常生活的书写,对生养与成长之地的追怀,突显了香港文学的在地关怀,这在“80后”、“90后”的创作中,也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如年轻诗人余颖盈的《星下的老家》:“深水埗老家的地址 / 在我的手掌心内 / 沿着那一根根脉络 / 又回到旧居来 / 已然摸索不到邻居的味道 / 也遗失了后楼梯的猫毛味 / 童年大方的愤恨啊 / 母亲把我的闪卡全数撕碎 / 母亲说我童年不会违抗 / 她叫我穿什么我都依 / 穿什么都好 / 穿的都是那个年代 / 就喜欢望向远远 / 用那远视的眼 / 那不是工厂的烟囱 / 我说不是 / 那是远方的一列火车的烟囱 /朝我这一方来 / 快要把大陆的姐姐送到我身边来 / 曾经 / 很诚实 / 我告诉小学老师我的家没有冰箱 / 连我的回忆也是盐腌过来的 / 在星星下 /我的确回到老家去 / 但不能再看到那里六楼的故事 / 而那个麻烦的包租公 / 今天可能轮回作小孩上学去了/ 还跟他计较什么 / 今天的黑夜仿佛不那么黑 / 我也不蒙头睡 / 因为有了昨日的星辰和我做伴”。这首诗写出了“家”的意识,也体现了香港的味道。
通过以上简单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香港的创作人,有相当自觉的“在地关爱”意识,且形成了从生活出发,以香港的眼光审视香港事象与社会人生,以香港的话语说香港故事的书写特色,充分展示了香港文学的独特风貌,这种“在地抒情”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绵延不断的。这就是我对香港文学的一点认识和看法。
蔡益怀:香港作家联会副主席
(责任编辑:吴江涛)